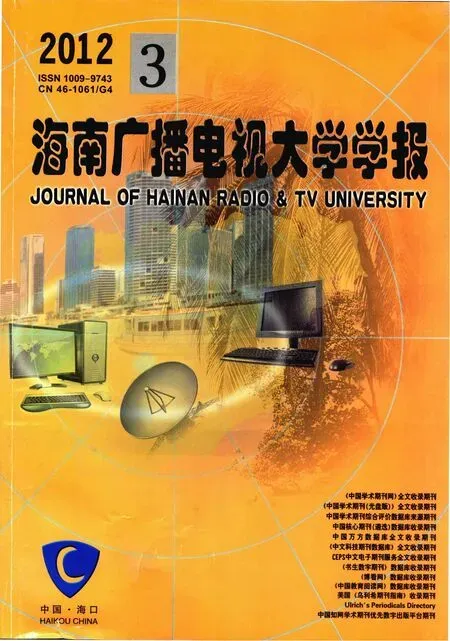回归童年——论汪曾祺新时期小说的独特视角
董友福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福建泉州362400)
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多是以儿童视角对故乡旧时生活的回忆。他力图通过人性善与美的抒写,使文学实现“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教化。他的回忆并不是往事简单的重现,而是在童心的照耀下,穿越时空,拾掇记忆中的点点滴滴,缀合出一首首温润人心的人性颂歌。本文将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磨难之后的情感特点及善且美的主题表达与其独特视角选择的内在联系展开探讨。
一 童年温情体验与审美取向的契合
童年作为生命的起点和人性的初展,往往定势地影响着一个人成长的轨迹。对于艺术家而言,童年的经验就是他艺术创作的生命宿因之一。艺术家们在创作中,会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吸纳童年所沉淀的生活底色,并嫁接现时体验,不断地生长变异出新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自小就受足了诗书教化和琴瑟熏陶。祖父汪嘉勋曾教他研读《论语》,学作八股文。对于心智早开的汪曾祺来说,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观念,自小就为汪曾祺的人格发育铺就一层温柔敦厚的底土。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在他的儿童生活阶段,父母的脾性,会极大地影响作家将来对生活的情感体验及审美取向。所以在作品之中,人们往往可以分析出作家投射其中的“母亲意象”或“父亲意象”。巴金曾深情地说:“我带着一颗纯白的心,走进这世界中来。这心是母亲给我的。她还给了我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
汪曾祺的母亲早逝,他生命中“母亲”的效应角色是由他温柔敦厚的父亲来扮演的。他的父亲汪菊生对子女很随和,从不声严厉色。汪曾祺在家里练唱戏,他父亲则在旁为自己的儿子拉胡琴伴奏,甚至欣喜地参加儿子在校的同乐会。汪菊生喝酒时,也会给儿子倒上一杯。抽烟时则是你我各一支,而为儿子先点上火。十七岁的汪曾祺陷入爱河,在家里写情书,他父亲不仅没有干预,反而成为他热心的谋士[1]。父子之间有着“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默契和温情。反观等级森严的现实中许多家庭,汪曾祺感叹道:“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令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1]汪曾祺的生活态度以及创作中审美意识都深受父亲影响:“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不仅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2]。对“父亲”意象的呼唤和礼赞,在汪曾祺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故里三陈·陈泥鳅》中水手陈泥鳅对邻家无钱看病小孩的救助,《七里茶坊》中市镇公厕掏粪工人对“我”的关照,都突显出“父亲”所具有的深爱。
汪曾祺的童年是欣悦的:在祖父药店里学搓蜜丸,在父亲的画室里胡乱涂鸦。高邮的渔舟和大淖的烟岚,小锡匠的锤声和戴车匠的车床,喧闹的市井街巷和静穆的的山林寺庙,炫目焰火和陈四的高跷,都曾在他的记忆里沉睡,并在他的小说中被唤醒。正是这样一种让同龄人难于企及而羡慕的少时生活,对他后来的人生体验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汪曾祺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3]。汪曾祺年少的生活经历,高邮的乡情民俗和地域文化,尤其是汪菊生对子女的宽容、关爱和人道情怀,早已融入他的血液,沉淀为作家的审美伦理。同为乡土文学,与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表达不同,汪曾祺的乡土小说是一首首浅淡平和的田园牧歌,对现实社会缺少批判性,而是以儿童的视角和表现方式,怀着朴素和欢愉的情绪,在追忆和想象中,表现人性的质朴和自然之美。他将生活中的美分解开来,着眼于人性美的理解和挖掘,同时也将人性的弱点在解析中淡化,对人性的弱点予以理解和同情。
二 浮躁情感规避与旧时回忆的契合
如果说汪曾祺的早期生活是幸福的,跨过充满欢愉的少时生活,横亘在他面前的却是粗野甚至狰狞的一面。十九岁的汪曾祺离开家乡,他经历了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次又一次的历史狂潮。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单位完成不了打右指标,安守本分的汪曾祺听从党支部书记的安排,为黑板报写一篇批评不正之风的短文,因此成了“莫名其妙”的右派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汪曾祺更是在劫难逃,游街、罚跪、挨斗、挨打、劳改,无一逃脱。“文革”后,又因参加样板戏创作而反复受审查近两年,写了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文革”十年的闭目塞听、夹尾巴做人,令他身心俱疲、饱经摧残。他无奈地说道:“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4]。所有的这些人生遭际,都不是那个当年生活在高邮温馨天国的小孩所能料想得到的,因此其言语之中流溢出对自我身世的悲悯和对“污浊而又混乱的时代”的愤慨。
饱经沧桑的汪曾祺,在他新时期的小说中,为什么没有伤痕文学的苦难诉说,反而为人们营造了一个人间难觅的桃源仙境呢?如果说这是作家的“童年情结”使然,那么除此之外,其中还有什么内在秘密呢?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的一段关于小说的“情感”处理的言说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的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3]。(本段引文,用楷体)
汪曾祺是透辟懂得文学本质的明白人,他特别注重小说创作的艺术情感,强调“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5],并把自己定位为“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这位情感生产者,注意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感情和小说的艺术感情是有区别的。还“相当浮躁”的情感是属于自然的感情,而进入小说中的情感则是艺术情感。只有在回忆中,将“热腾腾”的自然感情“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才能转化为小说中所需的艺术情感。
艺术情感来源于生活中的自然情感,但又不同于自然情感。美国著名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说:“一个专门创作悲剧的艺术家,他自已并不一定陷入绝望或激烈的骚动之中;事实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处于上述情绪状态之中,就不可能进行创作,只有当他的脑子冷静地思考着引起这样一些情感的原因时,才算是处于创作状态中”[6]。苏珊·朗格所说的“陷入绝望或激烈的骚动之中”就是指作家的自然感情。对此,鲁迅也有精辟见解:“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7]。
“文革”后的汪曾祺情感是浮躁的。从土地改革开始,汪曾祺经历了所有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整整十年的“文革”。面对这段纲纪紊乱、信仰崩溃的历史,一向善良斯文的汪曾祺甚至在义愤难抑时破口大骂道:“这他妈的‘文化大革命’!这叫什么事儿!”[8]他的《八月骄阳》是以老舍自杀为题材,揭示政治迫害的残酷无情。汪曾祺借助一个老艺人的嘴,发出这样的长叹:“我真不明白。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9]
没有一定的时间距离,浮躁的感情没能经过沉淀,内心的火气是难以“除净”的。自然情感难以抑制而任凭发泄的状态,对创作而言是头等的忌讳。汪曾祺对此有过深切体会。
他在“文革”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骑兵列传》,这是根据他1974年写剧本《草原烽火》时,在内蒙古采访几个老干部的经历而写成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属于汪曾祺自言的“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的说教小说。小说在选材和笔法上有浓重的伤痕文学色彩。文中对人性尊严受凌辱的愤怒流贯整篇小说。一向主张感情内化的汪曾祺,在文末禁不住跳出来说:“但愿以后永远不搞那样的运动了。但愿不再有那么多人的肋骨、踝骨被打断。”[10]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几乎没有影响,此后汪曾祺多次自选小说集时都没将其收入,对其不满意从中可见。
那么自然形态的情感要经过怎样的转换才能变成艺术情感呢?就是要经过回忆的沉淀,“把热腾腾的生活”中的火气除净。汪曾祺在此后的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等中就自觉避开浮躁感情,将视角转向遥远的“旧社会”。
三 美且善主题与童年视角的契合
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理念中,他是以“人性之美滋润人心”的美育追求,来支配其童年视角的实用理性。
童年在蜜罐里长的汪曾祺,在“污浊而混乱的时代”过后的沉静反思中,自觉而深刻地意识到,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而应该承担起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使命,“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11],用美与善弥合人们心灵的创伤,温润人们焦渴的心田,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有益于世道人心”[13]。他新时期的小说与“伤痕文学”不同,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控诉和对人性扭曲的暴露,而是超越控诉去抒写人性善与美。在文学的认识、教育及美感作用中,他强调教育作用中“善”的教化。他满怀忧患提醒人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总要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道德之柱,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无情,将是极其可怕的事。我们现在常说提高民族的素质,什么素质?应该是文化素质,心理素质,伦理道德素质。”[8]“善”的教化的实现不是说教式的,而是通过美化来传达的。在汪曾祺看来,小说是“善”与“美”的统一。“善”与“美”二者度的把握,是小说创作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难点,偏向其中的一端就会使小说陷入说教或者游戏。汪曾祺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结合点,那就是以童年为视角,对小说的人与事作童心的观照。他说:“性善的标准是保持孩子一样纯洁的心,保持对人、对物的同情,即‘童心’、‘赤子之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8]。
儿童之善与成人身上的善意是不同的,是未被成见所污染而不带世俗之态的善,是本真的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童心”。儿童由于身心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社会知识和经验甚少,他们不知虚假矫饰为何物,因此就以毫无顾忌的赤裸心灵去面对世界。当然,作家的童心虽然与儿童的本真之间,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儿童的天真童心是孩子自然天性的表现,这种“童心”会随着成长而逐渐消失。作家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在扮演了社会角色后仍能保持真诚的童心,则是经过世俗污染之后,向自然天性的回归。它是更高一层次的天真。这就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第二次天真”。作家的“第二次天真”是成熟的、老练的、深刻的,它是创作审美的自觉追求,是褪去自然天性的审美创造。
汪曾祺显然是一个葆有童心的作家,他称赞自己所推崇的文学前辈废名的文学成就时说:“他用儿童一样明亮而又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用儿童一样简单而准确的笔墨来记录。他的小说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3]他最杰出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便是以“天真”的孩子眼光来表达自己对人性的顿悟,小说所营造的是一片童趣盎然的天真世界。
《受戒》的故事背景是在一个寺院里,但与汪曾祺另一篇同为寺院背景的《复仇》完全不同,小说叙事采用的是儿童视角,表现出清纯儿童眼中的美。《受戒》没有那种宗教的神秘,而是处处洋溢着童趣的世俗生活。《受戒》中的寺庙生活没有神秘色彩,也不谈宗教信念,而是以少年明海和少年小英子特有的视角,虚构出温馨虚静而又童趣盎然的天真世界。和尚可以杀猪吃肉,甚至谈情说爱、打情骂俏。小说中的人物无需经过“苦行”的磨砺,明海不受清心禁欲和苦行修练的苛求。对于纯真少年的明子来说,受戒并不是痛苦之事,它只是领取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而已。明子在善因寺受戒后,小英子驾船去接他。小英子不让明海将来去当方丈,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要给他做老婆。明海应允后,两人就将小船划向那片芦苇荡,去享受为人所应有的幸福。在《受戒》的末尾,作者特意注明这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充满人性之美的梦中世界,正是一个历尽磨难老人的梦中之梦。面对冷硬的现实,此梦只能回到四十三年前的故里圆成。他情不自禁地将温馨梦乡涂画成和谐的仙境,使之与冷硬的生活形成鲜明的比照,借以实现“人心”的拯救。
汪曾祺新时期小说多是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他的回忆不是对往事简单的重放,而是在童心照耀下穿越时空,拾掇记忆中的片断,将其编织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人性颂歌。他的小说也正因为凝集着超越生活原态的善与美,才成就了他的《受戒》和他的文学。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转引于自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J].读书,1998(11).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苏珊·朗格[美].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7]鲁迅.鲁迅全集(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八)[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