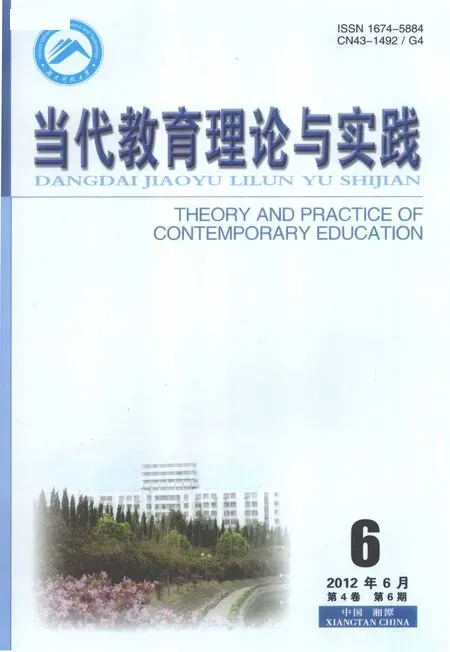解析《比利·巴思格特》中的父与子关系母题①
唐静静
(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六盘水553004)
解析《比利·巴思格特》中的父与子关系母题①
唐静静
(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六盘水553004)
父与子关系母题在多克托罗的小说中得到了十分集中和典型的体现。文章从比利本身的智力和气质以及他的家庭结构方面分析了比利寻找父亲的实质,指出比利在对父亲忠诚与奉献的同时,也对父亲存在着背叛与冲突。父与子关系在本小说中是对立存在的。
父与子关系;比利·巴思格特;忠诚;背叛
在家庭关系中,父与子关系往往表现为:儿子从父亲那里寻求庇护与帮助;另一方面,当父亲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并且极力维护自己权力之时,儿子却会打破牢笼,追求自由。因此,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既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又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父与子关系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中。但是在犹太文化中,它却有着特定的犹太文化底蕴。
一 历史的沉淀和《圣经》(旧约)中的父与子关系
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人性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反权威的标志之一。无论是弑父夺权的宙斯,还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父子冲突都是最突出的主题,为此弗洛伊德还演化出“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其内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犹太人的父与子的冲突关系最初体现在《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到了第六天,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他的妻子夏娃,让他们居住在伊甸园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同时也受到了上帝惩罚。“(上帝)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又对亚当说,你既要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违为你的缘故收诅咒,你必终生劳苦”(Genesis 5)。上帝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不允许他的子民有任何违抗的意念。他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始祖设定了生存方式,害怕他的儿女获得知识而学会反抗他的意志。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上帝又是一位具有权威的严父,不能允许儿女们的背叛。这样的对立一直在犹太人的历史发展中延续,不仅贯穿于整个《创世纪》的故事中,同时在希伯来这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流传。即使后来上帝与希伯来人立约,当他的“子民”稍微表现出对他不信任和不满,他就用“天父”的权利惩罚他们,同时降灾祸于他们,使他们倍受煎熬,过着痛苦的日子。
不仅在希伯来《圣经》中存在这样的父与子关系,在犹太人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关系也不断呈现。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这种典型的民族特性必然会使父与子关系这个模式延续至今。在不停的周而复始的流浪与迁徙中,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在不由自主的离开旧地,寻找他们的希望之乡,而且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必须对新的文化环境进行适应。所以犹太人永远要面临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文化难题:对传统的保留和延续;还是要改变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所谓的犹太文化特性。
二 父与子关系母题在美国犹太文学中的体现
在美国犹太文学中,父与子关系母题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懦弱无能的父亲,他常常屈服于自己霸道健谈的妻子脚下。杰克·波特诺在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的抱怨》中就是这样一个原型。这种类型的父亲有许多相同的属性:固执,顽强,勤劳以及对家庭的奉献。即使在缺乏教育以及反犹主义的障碍下,他们也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甚至取得成功。在这种类型的父子关系中,儿子显示了双重的动机:一方面,他怀念自己的父亲,并且记录家族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想通过自己的技能技巧战胜自己的父亲。菲利普·罗斯是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他的父亲不断的与反犹主义作斗争,并且通过辛勤劳作使自己的后代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融入美国社会。罗斯的成功产生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儿子的教育程度超越了父亲,对父亲的行为产生一种叛逆,在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又没有完全保留自己的犹太传统。第二种类型的父与子关系中父亲十分专断,蛮横地反对后代的一切自己不赞同的行为。亨利·罗斯的小说《睡眠》中的父亲阿尔伯特,索尔·贝娄的小说《只争朝夕》中的父亲阿德勒医生以及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纯真如金》中的父亲高尔德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一类型中,父亲往往表现为固执己见,盛气凌人,吹毛求疵并且控制欲极强。儿子的表现则是荒谬且懦弱无能的。父亲一方面承诺给儿子未来的生活,爱情以及幸福;另一方面,他又极力维护传统与标准,有时采用极端的措施,甚至杀害他的儿子。第三种类型的父与子关系则是父亲的缺失。如在亚伯拉罕·卡汉的小说《大卫·列文斯基的崛起》中,大卫的父亲去世了;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奥吉的父亲跑掉了。多克托罗的小说《比利·巴思格特》中的原始的父与子关系就属于这一种类型。比利的父亲因不堪生活的重压,抛弃了比利母子。成功的诱惑,社会和经济的力量使得比利不得不追求权力与金钱,最后选择了黑帮老大苏尔兹作为自己的精神父亲。
三 比利自身的才华与气质是其寻找精神父亲的基础
比利是多克托罗笔下寻找父亲的典型角色。比利的父亲遗弃家庭;母亲神志不清,贫困,几乎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和小比利。在这些有限的环境中,比利渴望美好的生活。父亲在比利的生活中是未知的量,并且父亲的缺失往往会在孩子的精神上产生裂口。于是,比利找了另外一个其影响力自己可以衡量的人物作为父亲。很明显,比利附属于一个和他自己父亲一样离家的人,但是这个人的离家似乎合情合理,能够让人理解;同时,这个人的经历和气质又和比利非常相似。事实上苏尔兹的父亲也抛家弃子,留下妻子来抚养和教育孩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苏尔兹六年级便辍学,但却因为其聪明才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追求上进,加上自己的商业触觉,在美国禁酒时期因为经营一间酒馆而暴富起来。在小说中,苏尔兹不断强化比利的身份,称他为成功的“杂耍者”,一个盖茨比式的人物,“基督,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赚来的,没人给我一点东西,我从乌有之乡来,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Billy 65)。当法律和竞争对手使他陷入绝境,苏尔兹不禁感叹自己的命运,并且夸张的质问别人怎么可以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他暗指的是巴思格特大街上美国梦的成果。在苏尔兹的黑帮职业生涯结束之时,比利仍然不断接近苏尔兹,似乎具有讽刺意味。但是,如果苏尔兹仍在其权利鼎盛时期,他从不用担心寻找继任者。当他感觉自己的力量正在消退,他需要一个后继者,正像老贝内特需要乔一样。
《比利·巴思格特》提供了对美国英雄系统运作令人信服的观点。苏尔兹的成功是基于一种原始的冲动和欲望,充满了血腥和复仇,一种深刻的诱人的权力,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自我肯定。苏尔兹是我们潜意识里的欲望,是人的阴暗面。实际上,他拥有无条件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无所谓好坏的。为什么比利要接近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人物呢?作为大萧条时期一个没有父亲的街头流浪儿,比利几乎无法引起苏尔兹的注意。比利解释道:“我的希望本质上并不比任何别人的希望特别。邻里之间,本就如此。这就是你住地的文化。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决不会比那更多,而经常的是比它更少…… 只要那是我们的,它是什么都没关系。因此,它满足了你爱名声的想法,那只要在世界上简单挂个号就行了,你就出名啦,或者你的追忆与大伟人或准伟人见过的一样。”
在多克托罗的笔下,比利是个特别的天才式人物——拥有杂耍的高超本领和敏捷的思维能力。他街道上的朋友用在赫斯特报纸上成名的一个喜剧演员给他命名,称其为曼德拉克魔术师。而比利认为,他们本该管他叫做“幽灵”的,以赫斯特另一个喜剧主人公来命名,该表演者头戴面具,是个孤独的演艺者,在生活的阴影处潜伏。当比利在表演“小行星”,杂耍“那两个球,那只脐橙,那个鸡蛋和石头”的时候,恶名昭彰的苏尔兹看见了他,并奖励他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比利认为这是“命运的巨变”。比利把苏尔兹称为“国王”,是“梦想中的伟大的匪徒”。通过追随苏尔兹“帝国的意图”以及他的信任,而不是他的智力和理性,比利巧妙地作为一个学徒融入到其黑帮中。比利回忆道:“在这个时候,我所做的一切都起作用,我不会出一点点错,这对我确实是神秘的。尽管我不知道在这世界上我的命运将会怎样,但我已经知道它将跟苏尔兹先生有关”。“一个能干的男孩,”比利进入了充满血腥与仇杀的黑帮世界。
四 对母亲的关怀与爱促使比利与苏尔兹建立父子关系
尽管比利的才华和气质可能引发他参与有组织的犯罪,他的家庭结构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细读小说,不难发现比利看似疯癫的母亲对他以及小说本身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母亲与后现代主义》中,特里·P·凯撒认为,在由当代男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中,母亲的形象一般表现为使人不安的,精神破裂的形象,因为在面对科技以及后现代的伪装理论时,她们本身的经历却是非常真实而又奇异的。凯撒认为,在父权社会中,母亲的职责主要是管理监督自己的儿子;而拥有一个违法的儿子则主要是在表面上承认与其儿子的关系。除了这种监督功能以外,母亲也是弥足珍贵的角色。在小说中,当苏尔兹和波·威恩伯格垂死之时都在呼唤自己的母亲。在苏尔兹死后,比利并没有立刻获得金钱,他也曾表达了自己让母亲失望的情绪。在与克里斯托弗·莫里斯的一次采访中,多克托罗指出,比利的母亲是苏尔兹的黑帮世界的对立体,而且“如果比利的母亲不是处于现在的情形,比利不可能成就任何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其母亲”。
尽管她似乎脱离外部环境,母亲对其儿子的行为却是敏感的,甚至弥补了比利从小缺失的父爱。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她几乎被遗忘的声音由于比利代替了苏尔兹的位置而重新获得。单亲母亲在低收入的家庭是随处可见的,父亲因家庭重担的压力而离家出走的情况比比皆是。在一个机灵敏捷智力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青少年往往比成年人拥有更多的权力,特别是对于比利母亲,她一直没有从其父亲的离去中恢复过来。表面上,比利确实从感情上和经济上支持了母亲。虽然很感激儿子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母亲的话也暗示了贫穷的父母怀疑自己的后代参与了犯罪活动,但因为他们确实需要钱,还是接受了这种犯罪带来的好处。
对于母亲的关怀与爱促使比利参与了非法行为,但是在小说中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方面,当比利盯梢托马斯·杜威的时候,母亲的棕色柳条婴儿车很好地伪装了比利,使他免于被发现。在小说的结尾,比利使用同样一个婴儿车来抚养自己的儿子。在苏尔兹被谋杀后,母亲的理智与情感也恢复过来。
在《比利·巴思格特》中,儿子对父亲忠诚与奉献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存在着背叛与欺骗。比利私底下想成为苏尔兹,占有他所拥有的一切。比利也明白如果苏尔兹知道他心底的秘密,他将难免一死。另一方面,比利与杜·普雷斯顿相互的性吸引也必须隐瞒苏尔兹。比利对于杜的性欲望显然是一个经典的俄狄浦斯情结。比利父亲多年以前就离家了,他需要引起苏尔兹的注意与尊敬,使其成为精神之父,而与杜的私情却使他们成了竞争对手。
在先后是波·威恩伯格和苏尔兹的情人之后,比利得到了金发美女杜·普雷斯顿。从一开始,杜的名字叫洛娜,她是波的女朋友;当他们到奥农多加旅馆替苏尔兹的逃税做准备的时候,杜成了比利的监护人;当他们一起去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时候,比利成了杜的护送者。杜首先嫁给了一个腐朽的继承了大笔财富的铁路继承人。她最终也和比利一样,因为黑帮的势力,恐怖谋杀活动以及他们禁戒的具体化而慢慢地成了黑帮头子的情人。杜认为如果任何时候她想退出,自己的美貌与财富可以使她免于受到伤害。对于这一点,比利相当清楚。并且,他答应了垂死的波·威恩伯格保护杜。在前往萨拉托加的路上,比利和杜到达一片绿色的无名地带,他们仿佛短暂地脱离了现实世界,“我们用这冰冷的泥巴互相涂抹,然后像孩子般并肩走进森林越来越黑的暗影里,手挽着手像童话中深深地陷入可怕的困境里的孩子”。在萨拉托加,杜显示了其高贵的上层阶级的气质,比利显然意识到了这种阶级差距。然而,比利不断地保护杜,防止她陷入苏尔兹黑帮团伙之中。
在小说中,杜作为母亲的形象并不明显。但是在教比利合理的穿着,合适的礼貌方面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比利获知苏尔兹无罪释放以后,他欣喜若狂,似乎证实了他对于苏尔兹的所有信念与投入都是值得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母亲拿出一张报纸上苏尔兹的照片,把它放在棕色柳条婴儿车里。之后,比利曾说:“我爱我妈妈,因为她对周围的谋杀是无罪的。”。比利认为,正是这种无罪使他坚定了自己追随苏尔兹的决心。在小说最后,苏尔兹死后的春天,一个“穿着淡灰色司机服装的男人”给比利留下一个草篮子,里面放着他跟杜生的孩子,母亲抱起婴儿,并放在棕色柳条婴儿车里。“在那时,我感到在公正的宇宙里受到小小的惩罚,我作为一个男孩的生活结束了”。俄狄浦斯情结至此结束。比利通过给其母亲自己的孩子,开始扮演父亲的角色。比利最后有了自己的孩子,虽然这个孩子是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结合的产物,并且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但是他却是“我一切记忆的源泉”。
五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对于金钱的追求,家庭的变故,以及通过犯罪进入上层社会的期望使得小说主人公比利最终加入了黑帮组织,并且成了拥有财富和权力的黑帮头子的继承人。从很多方面来说,小说《比利·巴思格特》讲叙的是有组织的商业犯罪团伙背后发生的血腥与仇杀故事,主人公比利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进入该犯罪集团,因为他只是像其他年轻的小伙子一样,被黑帮的暴力所吸引。相反,比利只是在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因为他有这种能力和智力。
[1]Baba,Minako.The Young Gangster as Mythic Hero in E.L.Doctorow’s Billy Bathgate[J].MELUS 18(summer 1993):33-46.
[2]Doctorow E L.Billy Bathgate[M].New York:Random House,1980.
[3]Henry,Matthew A.Problematized Narratives:History as Fiction in E.L.Doctorow’s Billy Bathgate[J].Critique 39(fall 1997):32-40.
[4]Levine,Paul.E.L.Doctorow[M].London:Methuen,1985.
[5]Morris,Christopher.Model of Representation:On the Fiction of E.L.Doctorow[M].Jackson:U of Mississippi P,1991.
[6]Caesar,Terry P.Motherhood and Postmodernism[M].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7(spring 1995):120-40.
[7]杨仁敬.关注历史和政治的美国后现代派作家E.L.多克托罗[J].外国文学,2001(5):3-7.
[8](美)E.L.多克托罗.比利·巴思格特[M].杨仁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责任编校 王小飞)
I106
A
1674-5884(2012)06-0165-03
2012-04-23
唐静静(1984-),女,湖南湘潭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