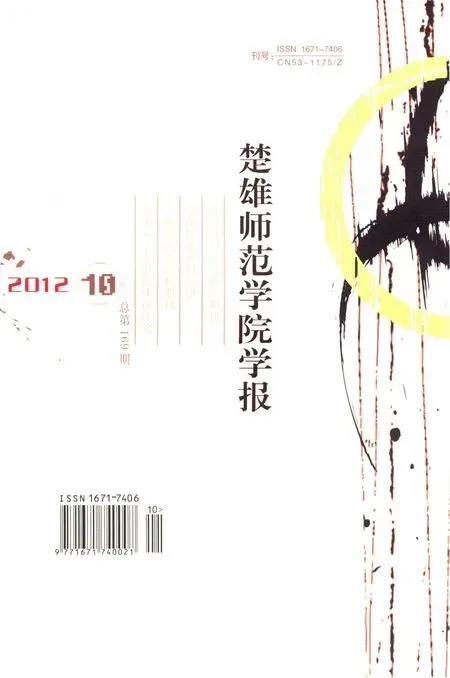浅析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的民族思想*
杨宝嘉 张 刚
(玉溪师范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自汉代开始,儒学就开始在云南传播,后经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努力学习,云南儒学不断取得进步。尤其明清时期,在云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大批足以与中原相媲美的儒学大家,他们不仅有鸿篇巨作传世,更有迥异中原儒学的独特思想,其中民族思想就是典型的代表。
一、“大一统”的国家认同意识
儒家“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一再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倾向。约产生于战国晚期的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大一统”思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P1)汉代儒学家大多继承了先秦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如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何休也说:“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2](P1)这种“大一统”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即要求维护中原君主的至上尊严,反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中原政权,最终实现“天子守在四夷”的政治目标。而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基本上都主张“大一统”思想。如李元阳在《云南通志》序言中说:“云南在汉,文献之所渐被,声教之所周流,其来久矣。”[3](P232)开宗明义地强调了云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明自从汉代在云南设立郡县以来,不仅政治上确立了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统治,而且中原文化已深入云南;不仅云南是汉王朝版图的一部分,而且汉代在云南“授经教学”,使云南的思想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原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云南与内地的密切关系他详加记述,认为“今之云南,即汉唐之云南也;云南之郡县,即天下之郡县。”[4](P657)对于南诏脱离唐朝建立独立政权的史事,他如实记载,但也指出“不观土壤分裂之乱,何以知大一统之治。”[4](P656)这充分说明李元阳始终坚定地从“大一统”角度来理解审视云南与中原的关系。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甚至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大一统”关系产生的原因。如《滇鉴》序言中,高奣映觉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说:“天下谓甲申之变极已,滇仅一区,远土也,亦咸相曰甲申之变极已。……今滇远于神都,而亦曰甲申之变,同是鼎烹而釜泣,一与天下分甘共苦者,夫恃远也,岂独能免也哉!”[5](P1)“甲申之变”指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统治中原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的事件。但就是这件发生在遥远北京的中原王朝兴衰更替的政治事件,却使远在西南边疆的云南各族人民痛心疾首,甚至有“鼎烹釜泣”的感觉,如高奣映的父亲就是因效忠明王朝而在明灭之际选择了出家归隐。究竟什么导致云南与中原之间“一与天下分甘苦”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高奣映撰写《滇鉴》最想要弄明白的问题,如他说:“由是以思前明一家之治乱,转而思滇之为滇,亦譬如一家之治乱。”[5](P1)最初是为了思考明王朝治乱成败的原因,最终却升华至对云南与中原“譬如一家”的共生共存命运的思考。首先,高奣映认为,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自孟津首会,筇筑塞通,内之外之,木之托始于勾芽,蛮弱必化为华蔚。”[5](P1)从武王伐纣始,云南与中原初步建立起联系,秦汉时期又开辟了交往通道,之后分裂、统一间歇有之,但从整体上看云南与中原的联系在逐步加深。其次,高奣映认为,这种紧密联系来自儒学在云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他说:“云南未服中国以前,为儌外西南夷地,其种类不一,……大抵各据一方,不相统辖。至汉武帝时,始通圣教,于是设郡县,隶职方。其时,张叔、盛览辈受经于司马长卿,归教乡里,即已习诗书,明礼义。虽自唐以后,叛服不常,蒙、段两姓窃据数百年,然亦知延师儒,兴文学。迄于有明,熏陶培养,风气日开,礼俗、人文无异于中州矣。”[5](P4)这段话被高奣映安置在《滇鉴》首页,其用意就是用来回答在《滇鉴》序言中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在其来看,云南这几千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成为可以与中原相媲美的礼仪之邦,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导致云南与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综合起来看,高奣映就是认为,云南各民族对儒学的认同程度直接决定了云南与中原之间的关系,云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就是儒学在云南传播认同的历史。如同李元阳、高奣映一样,清代云南白族大儒王崧始终强调云南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于古梁州为边裔,三代盛时,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固尝与朝会之数也。汉置益州,云南隶之。”[6](P199)这就把云南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推至三代时期,借此佐证云南从属于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因此,王崧特别反对中原王朝与云南割据势力之间的妥协行为,认为违背了最基本的君臣隶属关系。如在评价南诏与唐王朝关系时,他说:“南诏始受唐封,既而废,臣吐蕃,及韦皋镇蜀,复归于唐,其反复无常,视边将得失以为向背也。世隆僭称大号,唐无如之何,至以公主妻隆舜而讲舅甥之礼,何其悖哉!”[6](P179)由于在天宝之战中取得胜利,南诏脱离了唐王朝的统治,并僭越称王,欲以兄弟或舅甥关系来处理与唐王朝的政治关系;对此,王崧视之为悖乱礼法纲常的事情。
二、“无间华夷”的民族平等意识
身为少数民族,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都积极追求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关系,反对歧视误解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如李元阳说:“元儒李京景山传夷方风俗之陋,以今观之,绝不相类,乃知秉彝恒性,无间华夷。”[4](P642)元儒李京曾在自己撰写的《云南志略》一书中,专门介绍过当时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认为“其人生多犷悍,不闲礼教。”[7](P124)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李元阳却看到云南各民族“道不拾遗,外户不闭,归敬其夫,妻妾不相妒,尊其长上,虽暗室闻传必跪,织者下机,业者停手,盖有古封建之遗风焉。”[4](P590)根据云南各民族前后生活习俗的巨大变化,李元阳意识到不同民族在本性上是相同的,都具有仁义礼智信的禀赋,只要加强教化都可以成为谦谦君子。因此,他引《元御史郭松年记》中的话说:“教无类也,孰谓异俗之不可化哉!今夫云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风以资于闻见也,又非乡党师友之习也,一旦举中国之治以加之,皆反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见王者之德大以遐,夫子之道尊而明,而异俗之果不难治也,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辈出,彬彬乎齐鲁之风。”[4](P596)这是李元阳通过亲身经历验证了少数民族在德性、才性上无异于汉族的结论,体现出其民族平等的观念。清代回族儒学家马注则从各民族同根同源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他说:“阿丹首出之君,即《通鉴》所谓盘古。朱子云:‘天地开辟而盘古生焉,神于天,圣于地。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西洋又名亚党,即天下古今共祖。故曰‘人祖’。”[8](P104)“阿丹”是伊斯兰教认定的人类始祖,在马注看来,“阿丹”与汉族始祖“盘古”及西方人始祖“亚党”实乃同体异谓,因此世界各民族“实同一体”。[8](P111)更可贵的是,马注不仅强调“天地一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8](P226)的世界各民族的一体性,也看重不同民族的多元性,如他说:“盖天有时令,四时之变幻不同;国有俗,万国之语音不一。如欲强合为一,是春夏同于秋冬,蛮夷同于中夏,岂足以见造化之全能?”[8](P573)不同的民族特性如同天地四时的差异,是客观必然的,如果一味求同就如同把“春夏同于秋冬”,破坏了民族发展的生机性。这可以说是在更高层面对民族平等内涵提出了诉求,在民族平等理念的引导下,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坚定地宣扬“仁及夷狄”的大爱精神,要求中央朝廷给予云南各民族应有的尊重和关注。如李元阳从边疆少数民族思想家的角度,吸收儒家传统中重民爱民的思想。认为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功名、私利,“兴无名之师,杀无辜之民,费帑藏之金,破边氓之产……杀人盈野,草原为赤”[3](P357)的行为是绝对错误的。因此,他大声疾呼:“万里边氓亦国家之赤子,何忍急一己之功名,而视民曾草菅之不若耶?”[3](P357)为边疆的安宁、少数民族的生存权益发出热忱的呼唤。再次,他们坚定地主张“夷狄可化”的思想。由于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状态,云南各民族被中原汉族统治者经常藐称为“夷”或“狄”,由此动辄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施以武力,视征讨杀戮为当然,从而给云南各民族带来惨祸。而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大力宣传“夷狄可化”的思想,认为云南各民族尽管处于落后未开化的状态,但只要坚持教育就可以把云南变成和中原相媲美的礼仪之邦,所以不需要动辄施以武力。
三、“用夏变夷”的文化认同意识
“用夏变夷”一直是儒家族群思想的核心,是儒家企图通过文化征服周边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对儒家这样的思想观念,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不仅没有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大力排斥,反而给予了高度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如李元阳引《元御史郭松年记》中的话说:“惟夫子之道,与天地并,语小则无内,语大则无外,固不可以古今夷夏为限阂。”[4](P596)言下之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如同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所以无论夷夏都必须学习掌握。甚至把儒家“用夏变夷”主张视为神意的安排:“帝之昭灵于兹山,所以警群欺而化南服、变遐荒以匹中原,此理之所必有,不待卜而知其然矣。于惟重臣硕僚,会其时亦莫不怀临汝之惕而操用夏之权者。”[3](P101)万历三年 (公元1575年),云南马龙州中和山现祥瑞,李元阳则认为,这是上苍要求地方官员积极推行“用夏变夷”之道的征兆。[4](P522)更重要的是,他还把推行儒家文化当作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云南古荒服之地,自汉始通中国,然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惟纲常之道粲然明于世,而礼乐刑政所以管束人心,维持世道之具胥此焉。”[10](P15)换言之,只有努力推行儒家文化,最终达到云南与内地“车同轨,书同文”才能保证边疆稳定与巩固。清代回族儒学家马注不仅强烈认同儒家文化,而且认为儒学与伊斯兰教义本质上是相通的。他说:“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8](P61)从道的层面看,伊斯兰教与儒学根本没有差异,都敬畏天命、穷究天地生死之化,遵守人伦纲常。因此,彼此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偏执之见造成的:“东方有圣人焉,西方亦有圣人,东方治东,西方治西,执东方以论西方,则道不同。”[8](P299)由于伊斯兰教主要在西方传播,儒学则在东方传播,彼此一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了解,所以习惯性从东方人的生活习性去观察伊斯兰教或从西方人的生活习性去观察儒学,最终都不免是己而非人,从而把两者视为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清代白族儒学家王崧也说:“夫儒者诵法周、孔,其道本于尧、舜、文、武,薄海内外,罔不遵循。”[3](P299)因此,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都非常自觉的认同儒学,视之为立身处世乃至治国安邦的根本之道。
四、结束语
综合上述,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对儒家民族思想不仅仅是简单的接受,更是在结合云南民族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在某些方面矫正了儒家民族观的缺陷。
第一,从排外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走向文化包容。文化虽是儒家识别民族身份的根本标准,但在他们看来,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始终是天下最先进的文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则是野蛮未开化的,所以只允许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文化而反对华夏学习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儒家民族思想始终关切华夏文化延续与统一的问题,不容许任何外来文化威胁其正统地位,这直接导致儒家民族理论在文化层面的排他性。如在南朝刘宋时期,顾欢就曾著《夷夏论》以明佛教之与华夏的利害关系,认为佛教违背华夏礼俗,不适宜为华夏族所信仰,坚决要求“辟佛”乃至“灭佛”。这在民族文化方面明显具有妄自尊大、抵制文化交流的倾向。而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虽然都非常认同儒家文化,但不代表他们也坚持华夏文化中心论,如马注就始终强调文化多元性存在的必要性。在儒佛关系上,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基本都持儒佛兼容的观点,如李元阳说: “志于道者,不主儒、不主释,但主理。”[3](P204)又说:“良知与良能,日月悬中天。老释方外儒,孔孟区中禅。”反过来说,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身为少数民族却能够抛开传统习见,勇于接受儒家文化,这本身就体现出文化包容的精神。
第二,从民族立场的两重性走向坚定性。儒家民族理论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特征:一方面积极提倡“用夏变夷”,用仁爱之道去融合边疆少数民族,要求实现“华夷一体”;另一方面又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企图将华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隔离开来。这两种相反的思想倾向一直交替出现在儒家民族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当中原王朝实力强大时,儒家就强调夷夏之间的融合,反之就要求严“夷夏之防”。而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在民族思想立场上始终是坚定的,自始至终认为云南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他们分别从历史、地理、文化多个层面论证了云南与中原内在的紧密联系。
[1]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李元阳.李元阳集 (散文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4]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 (第六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5]高奣映.滇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6]王崧.道光云南志钞[Z].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
[7]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 (第三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8]马注.清真指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