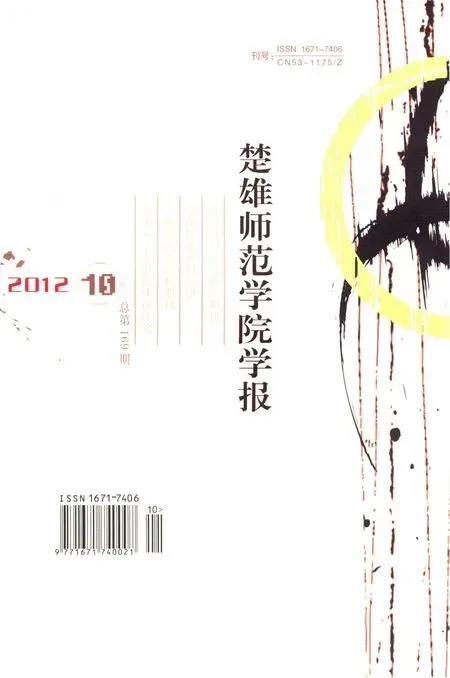以荣格的原型理论解读《陆犯焉识》*
汪倩秋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1756)
有“多产多奖”之称的旅美作家严歌苓近年来异常活跃,善于描写女性角色。在2011年的《陆犯焉识》中,她首次以男性为主角,用不卑不亢、自嘲和智慧的语调叙述了陆焉识从年少轻狂到锒铛入狱,出洋留学、流亡大后方、肉体出轨、重庆入狱,乃至从青海劳改营出逃……所有的变动都不影响它们最终汇集一处——几十年风雨沉浮的背后是爱情的隐忍、执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兴起落寞的历史。
严歌苓曾说:“我研究心理学,看弗洛伊德和荣格自述等心理学书”,“文学与心理学的交汇,给文学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遗留给文学一个大的空间”。[1]那么融入心理学解释是否可以更好地理解《陆犯焉识》呢?笔者就此以荣格的原型理论来对文本进行分析。首先简述相应的理论背景:卡尔·荣格 (Karl Jung 1875-1961)是神话原型批评的创始人,原型意象和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原型批评理论的核心内容。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 (archetype),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心理现象,甚至是生命本身的载体,[2](P39-52)反映了人类在以往历史进程中的集体经验、种族记忆。荣格曾说:“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3](P48)他认为对于人格 (personality)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型共有四种:人格面具 (the persona)、阿尼玛 (anima)和阿尼玛斯 (animus)、阴影(the shadow)以及自性 (the shelf)。其中,人格面具是人类必须在社会中扮演、呈现的那部分角色;阿尼玛斯是女性精神中的男性特征,阿尼玛是指男性精神中的女性特征;阴影由人类从集体意识中遗传而来,是精神中最黑暗、深入的部分,包括动物所有的本能,使人具有激情、攻击性甚至暴力倾向;自性调节精神的各部分,使得人格统一、平衡和稳定。[4](P140—149)
一、爱情的转向
严歌苓说:“只有执着的人,才会爱得笨。有这样的执着才能使人升入另一个境界,在那个境界里有她自己的一套苦乐观和荣辱观,世界在于她全是主观的,所以反而是一种幸福。”[5]正如小说里描写的:婉喻的手指,一张一合的嘴,走不稳路的解放脚,端庄达理的仪态,瘦成一条缝的背影,戴着蓑衣在雨里立成雕像的送行,把上海弄堂刷成粉色的换屋告示……想象不出哪一个女人可以还原婉喻天真思绪里的种种美好误解,以及纤细身躯里推土机似的力量。她一生不怒不怨的等待,终于将不爱等成了爱。
1.阴影的恣意行进
“自由”一词在书中反复出现,对陆焉识意义非凡。严歌苓说:“陆焉识一辈子的挣扎和渴望都是围绕自由的,他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被一个无形的枷锁套牢。后来他回忆起在青海时的流放生活,他一步步颠覆自己对自由概念的诠释,但是一辈子他都在渴望自由。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6]在作品中作者“永不停息地寻觅更好的象征”,[7](P91—93)“自由”即是焉识阴影的一种象征,我们可以根据概念将他的心理阴影分为两部分:一是艺术创造力,二是隐秘的欲望。
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型的少爷,又是智商超群且学识极高的留美博士。他是民国直到解放初期大多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的典范,西方的留学生活拓宽了他的意识和创造力。他精神活跃,会四国语言,能力超群。同时又潇洒倜傥,“生理上也更为机敏活跃,精力更为充沛”,[7](P80—84)很讨女人喜欢。在美国,他毫无愧意地做着花花公子,把激情、诗意、头晕目眩的拥抱和亲吻给了异邦女子望达。在重庆,他疯狂地拿艳丽、性感、厉害的韩念痕来实践自己在婚姻里对男女事物的觉悟。
陆焉识同时在矛盾着自由的暧昧意义。自由使他能自主地生活,然而也日渐“脱离外在权威而独立”,并感到“孤立”、“无足轻重与无权力”。[8](P1—10)为了挣脱约束,他远走美国,可“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渴望逃避自由。”[9](P1—3)在种族无意识和东方人典型的内倾型性格驱使下,他重蹈凌博士们的覆辙,返航回国,束缚上新的羁绊,成为不站在任何的阵营里、受尽推崇的大学教授,周身又充满了生命力。战争爆发,他随迁校只身来到重庆,逃离了两个女人的枷锁,从萍水相逢的韩念痕绵长的爱情里重获新生,而“新的自由带来了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8](P90—95)战事一过,他再次选择逃避自由,重回上海,再入枷锁。50年代,他内心阴影中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时时压倒意识的自我,“显得暂时疯狂失态”,[7](P80—84)并因此成为“反革命”,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更导致了他被多次加刑直至无期,送往西北大漠劳改。如此,他在枷锁和自由的门外反复进进出出。
2.阿尼玛的胜利
“男孩子与母亲在一起的种种生活经历决定着其阿尼玛的发展方式;而男孩子与父亲在一起的种种生活经历则决定着其阴影的发展方式。”[7](P88)焉识早年丧父,受其影响甚小,阴影得到了自由的发展。男人心中“明确的女性意象”,[7](P42)除了从遗传获得外,母亲的经验对他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生活在恩娘主导的母系家庭结构中,并将阿尼玛原型投射于恩娘,故一生不能摆脱她的吸引力,看尽了她的眼泪,所以见不得女人可怜。正如巴赫芬所说,母系结构“限制了他的个性及理性的发展”,[7](P89)阿尼玛原型倾轧他内心的阴影,使他“一错再错”。他想“女人都这么可怕”、“一刻不停地往你身上缠绕羁绊”,他在恩娘的软硬兼施下娶了排斥、厌恶的婉喻,开始了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然而,陆焉识内心的阿尼玛原型却在二次入狱后爆发。“当困境出现之时,无意识中与之相应的原型将如星座般地自然形成。这一原型因特定心理能量的聚集而吸引人们的意识,从而为人们的意识所感知。”[3](P273)为了迎合外界环境的期望,他带上虚伪的人格面具,时刻生活在不安中,自我身份感消失。他本能地渴求安全感,“力比多返回集体无意识去激活某些原型”,[10](P165—176)迫切地“想要不断地靠着得到别人的赞许”,“惟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期望,他就是可以确知他自己的身份。”[10](P30—45)反刍繁华半生的“盲写”,对话了他的意识和无意识,扩展了他的意识,阿尼玛原型突入到“起决定性作用的”[11](P88)意识中来,“造成人格的急剧转变”,[8](P113—120)在反复求索、回归后,他重新认识身边始终不离不弃的婉喻,并确认了对婉喻的深爱。
婉喻就是一个小恩娘,是焉识内心阿尼玛原型的投射,这也是让他“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或者强烈的厌恶感的主要原因之一。”[3](P198)婉喻身上有恩娘的忍耐、持家、勇敢、给予,是“旧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代表:美丽、知书达理。她隐忍,为了让焉识获得“幸福、发展和自由”,[12](P25—30)无畏母子博弈和丈夫背叛,满足繁琐生活和小恩小惠,被时间隐隐地抛弃。她奉献生命力,赋予焉识“次要的自我感”、[9](P95—97)使其体会爱情“给予”的本质。她为焉识买欧米茄、剥蟹肉、失去贞洁、跋涉送别……如执着埋伏于岁月中的欧米茄,分享了焉识的一生,使丧失自我的焉识自然地和过去取得了联系,获得了温暖,孤立了他人的不赞同,补足了自我意识和存在感。当浪子回头,焉识逃狱只为心中的婉喻,最终在窥见婉喻的安定后终结逃亡,毅然选择自首、离婚。
二、人性的苍凉
《陆犯焉识》将现实与回忆交错,婉喻只是写作焉识中的一个“对称体的存在”,爱情只是故事串起来的线,精彩的是线上的珍珠——“饥饿一场,遭罪一场,生死一场”的牢狱生活。
弗洛姆提出:“社会的禁忌是社会意识体系的主要成分。每一个社会,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联系的方式,通过感情和知觉的方式,发展了一个决定意识形式的体系或范畴。确切地说,这种体系的作用就像一个受社会制约的过滤器,它宣布某些思想和感觉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危险的。”[13](P132—150)由此推断社会成员一旦特异于所在的社会,便面临着被彻底排斥和放逐的危险。严歌苓对特定时期下特殊的群体着重笔墨,放大、激化阴影和人格面具的潜力和矛盾,深刻地拷问了苍凉的人性。
荣格认为:“人格最外层的人格面具掩盖了真我,使人格成为一种假象,按着别人的期望行事,故同他的真正人格并不一致。人可靠面具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一个人以什么形象在社会上露面。”[14](P122—130)牢狱初期,焉识被叫做 XX号,后因辩解自由,吃尽苦头,有了类似于无名氏的外号“老几”。他渐渐承认个人对于社会需求和言论的无力,从“外倾者”变成“内倾者”,不再用尽义务普及通俗哲理,开始乐于探索、分析内心世界,喜欢孤独离群,学会读人眼色,已习惯用肢体语言和“口吃”来掩饰自己。老几一直谨慎地做着孤傲的囚犯,却为了去咫尺天涯的场部礼堂看小女儿的科教片,放弃尊严、用尽伎俩,甚至豁出命,蜕变成一个狱油子。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使他戴上人格面具,“口吃”的面具为他赢得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需的时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
小杀人犯梁葫芦作为老几人格面具和阴影发展的参照而存在。阴影“受到压抑时,‘我们心灵中的野兽只会变得更加凶狠残暴。’”[7](P80—84)梁葫芦公开描述过杀人的震撼场景,将尸首上收获的土豆分予老几,让老几成为自我阴影的奴隶,啃吃尸首的豺狗。他未得过纯粹的好,内心懦弱、依人的阿尼玛让他在无意识中寻找温情,一厢情愿地靠近老几。他因给老几偷欧米茄而被人“加工”,获得了无知、热情的围观。酷刑之下,老几在阴影不由自主的力量面前束手就擒,认为梁葫芦的受罚理所应当,为了实现目的,他带上人格面具,没有说出个中缘由。“阴影是一道窄门,任何走下深井的人都逃不过那痛苦的挤压。”[15](P78—81)梁葫芦硬汉铮铮地没有招出欧米茄,内心的阴影却让他在临刑前,把死里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了揭发老几的假结巴上,而依旧难逃死刑。之后,老几成功地利用人格面具恰当地应对监视,再次获得了邓指的信任。
20几年的劳改生涯,老几亲历了人格面具和阴影角逐的双重生活。犯人们只有在阴影和人格面具融合一致时,才能免受看守的斥责和惩罚。当阴影冲破其压抑的屏障,犯人便以病态的方式表现自己。这种双重生活如肆虐的牙痛,侵蚀着整个荒漠,“各种分裂成了不仅是个人,而更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16](P230—242)冤死鬼徐大亨、高傲的犯人组长、使尽计谋的张狱友,“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贼王、猥琐卑劣的农村大队书记、“没长脑子”的伪连长,空想家知识青年小邢、吃人肉的张现行……犯人们在人格面具和阴影的双重生活下进退两难,既需要人格面具去保护真我,又需求阴影来释放内心。结果,他们一直生活在畸形的状态下,孤独且行为怪诞。
同时阴影也有积极的一面。邓指和有外遇的妻子平静地过完后半生,老几通过欧米茄构建了和邓指的感情,这也成为苍凉的人性荒漠中开出的绚丽之花。无论怎样,恩娘、焉识、婉喻一生都是幸福的,虽然坎坷,但他们毕竟走过,并曾经拥有。而荒漠上的其他人只能草草地划下寥寥的几笔,便悄然而逝。
三、“自性化”的回归
“文革”后,劳改特赦的焉识已是皱纹纵横,然而回到上海,他发现儿女们却在集体标准强制下,过着肤浅、无阴影的生活,自我片面地等同于过度膨胀的人格面具,都觉得为了父亲牺牲太多。婉喻却是等他等到失忆,而焉识无奈与冷静的苦楚更是沁人心脾。
儿子冯子烨终成俗庸小市民,沉迷于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惧怕一句“爸爸”可能造成的政治安全,一直担心父亲会惹祸,训斥和利用他……而焉识面对儿子的“恋爱悲剧”,以及在“文革”中受到的“过街老鼠”般批斗的苦楚满心自责。才貌俱佳的小女儿终成大龄剩女,在和漂亮、胸无大志的刘亮组成的家里完全是空架子,异化的人格因为爱的屈尊而丧失了尊严感。刘亮的孩子超年龄的畸形直觉,无顾忌地嫌弃、诋毁焉识为“老罪犯”;刘亮的穷凶极恶、无理力争,更让焉识愕然、心酸。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不到多少爱和恨”,[9](P66—70)只充斥着距离与冷漠。同自我离异的儿女让人格面具操控了人生,而这人格面具使“他人常常享有比他更大的份额”,[16](P147)所以,妄自尊大的夸张感使得儿女们希望父亲重塑自我角色,常常埋怨、推脱他,并见缝插针地抓他的差。
带上面具的焉识也是人格面具的受害者。从风度翩翩的陆教授变成孤独无助的老几,为了弥补无法达到的团体期待标准,他一直靠着符合他人的期望来得到一种安全感。然而,表象与本真虽然分裂,却没有“被融合”,他从未泯灭内心固执的阴影,更意识到自由的相对和辩证。他依旧容不得别人在文字里揉半点沙子,囹圄之夜反复地润色,古稀之年又放弃了编写词典的荣誉。然而在婉喻过世后,他发现这个社会已然不是他生活过的世界,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处,面对人格面具的围剿,孱弱的“自我”无法处理来自内心的繁杂信息,更找不到心理和现实的出路。荣格说:“正如自我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种经验那样,自性是我的自我的一种经验。”[14](P247)即一切都成为自觉意识后,“自性化”才可获得成功。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孤独的悲怆、存在的支离破碎完善了焉识对自我的了解,最终他在邓指儿子的启发下,“沉没进无意识里面”,[7](P72—75)一切成为自觉意识,明确了生活方向,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最后,他带着婉喻的骨灰盒回到西北大漠,通往了自我实现的道路。
在《陆犯焉识》中,很多细节和人物特征定型明显、顺理成章,破解了小说中人生的丰富性。作者冷酷的笔调中潜藏着文艺女性的天真,将小说写得饱满丰富、滴水不漏,更开辟出世外桃源——西北大漠,将“出走”——抛弃世人、离群索居作为自性的象征,用“类比的方式去解释某种存在的尝试”,[3](P265)以此来美化一切,正如大漠风沙中的最后一根绿草,更显凄凉。荣格认为“自性”只有拥有强大的“自我”,才能与之融合,实现自我价值。[14](P145)虽然与日俱增的个体化需要宣泄口,孱弱的“自我”的出走更像是一种逃避;然而哪有处处可逃避的出口,弗洛姆所深信的“自由而不孤独”、“不会充满怀疑”[8](P132)的积极自由,在面对现实社会、人生的阵痛,以及在《陆犯焉识》中都是无力的。因为无处可逃,焉识“被选择”了如道家“出世”的自我修行,“体验他自身的内心存在”,[3](P50)实现了可行性令人质疑的自性化的圆满。
《陆犯焉识》饱含着一种悲壮的美感,严歌苓在作品中极力地想突破自己,首次采用了男性主角,真实而动人地描写了西北大漠劳改营里的残酷生活状态。陆焉识所有的财富——自由、学识和爱一直被剥夺、虚误,他的命运已不再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事情,而是关乎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纯粹。从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弗洛姆对于社会、自由、爱的理论视角,我们进入到作品主人公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解析了小说中动人爱情的伟大缘由,洞悉了人性的摇摆与矛盾、复杂,探索了“自性化”回归的可行性。
[1]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3).
[2](瑞士)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瑞士)荣格.荣格全集[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英文版.
[4]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严歌苓:欲望不强是我活着的准则[EB/OL].http://eladies.sina.com.cn/qg/darenwuyangeling/
[6]齐书勤.严歌苓写祖父风流生活,遗憾父亲没看到自己转型[N].半岛晨报2011-12-29.
[7](美)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M].张月,郑州译.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8](美)埃利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9](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10]冯川.神话人格[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11](瑞士)荣格.荣格自传:回忆、梦、反思[M].刘国彬,杨德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12](美)埃利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3](美)埃利希·弗洛姆.人性·社会·拯救[M].黄颂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4](瑞士)弗尔达姆.荣格心理学导论[M].刘韵涵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5](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6](瑞士)Jung,Carl Gustav.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