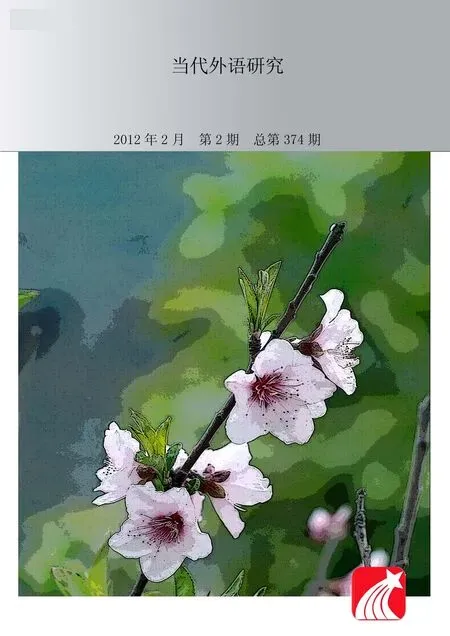论《黑王子》中的爱欲、认知和艺术
胡可清
(徐州师范大学,徐州,221116)
作为重要的道德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认为人们在认知他人的尝试过程中,应更深入地思考想象和内在道德的重要性。“默多克道德哲学的中心就是善的定义,以及如何用善的光芒来指导和提升生活”(Steiner 1997:2)。其道德观不仅强调行为与责任,而且关注人应如何使自己的内在自我更加完善,摒除个人主义,更加清楚地认知他人。这一观点影响了默多克一系列的著作——《善的主权》、《火与日》和《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以下简称《形而上学》)。默多克的哲学成就不仅表现在纯粹的哲学著作中,也体现在她的小说中,但她反复强调不应把她的小说看成是代表某种哲学理论著作,这样会令读者过度强调小说的抽象性,而回避其现实性,使小说成为遮蔽认知的空洞理论作品。
在《形而上学》中,默多克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提出小说本身也是一种道德伦理形式,目的在于揭示关于人生的真知灼见。因此默多克的小说可以被看成是对人类之爱与道德的沉思,“为了在道德上变得更好,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需一种艰辛的道德奋斗或者精神历程,打破个人沉醉其中的迷惑,把充满爱的关注目光投向身外广阔的世界,最终才有可能达到善的真实,爱欲是寻找善的动力源”(何伟文2009:41)。除了关注默多克小说中体现出的道德观(何伟文2009,2011)外,还有学者(安宁、袁广涛2011)探析了默多克的女性意识,而本文将通过分析《黑王子》的复杂结构,揭示默多克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爱欲与认知以及艺术与认知之间的关系。
《黑王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由小说主人公布莱德利讲述他的爱情经历和悲喜交织的结局,这在默多克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因为默多克很少对某个人物表现出如此的信任,通过单一视角呈现出如此复杂的小说世界。当然布莱德利讲述的故事可能与事实并不完全吻合,所以在他的讲述之后,有四个故事参与者(布莱德利的爱人朱利安·巴芬、朱利安的母亲拉歇尔·巴芬、布莱德利的前妻克里斯丁和克里斯丁的兄弟、心理学家马娄)进行评述。四个人都认为布莱德利不可信赖,他们将布莱德利的叙述贬抑为“幻想”或比“幻想”还糟糕的东西。朱利安甚至批评布莱德利的创作以自我为中心,全是虚情假意,因为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布莱德利只字未提。
故事伊始,布莱德利·皮尔森,五十八岁的失意作家和朱利安·巴芬,芳龄十九的学生,在伦敦邮政大楼顶层的餐馆用餐。多年之后回忆这个晚上,布莱德利写道,
在那一刻,我体验到了令人目盲的快乐,星星仿佛在我面前爆炸了,于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呼吸急促,从外部觉察不到的颤栗悄然地控制了我整个躯体,我的腿开始跳动,双膝无力,头晕目眩的感觉充满了全身,这些感觉迫切需要文字描绘。心灵的狂喜与肉体融合、分离、再融合,像狂野而优雅的舞蹈;如何用文字表达呢?宇宙中的每一条射线都证明了我正处在绝对恰当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情令智昏,在星星的爆炸中,眩目的景象吞没了现实存在的每一个细节。在茫茫众生之中,她宛若飘飘仙子,凝视着她仿佛探得天机,我快要晕厥过去了。(Murdoch 1975:238)
这段文字艺术地刻画了记忆中爱欲那令人头晕目眩的力量,其中布莱德利数次提到了柏拉图的《斐得罗篇》。在柏拉图那里,激情被描述为令人目盲的光亮和乍现的洞见,具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美,善在恋人眼中突然显现。上述引文中的描述和《斐得罗篇》中的爱欲体验相吻合,似乎表明,通过爱欲,人可以洞见以其他形式无法获得的真理。在整部小说中,布莱德利都在证明这一观点。与此同时,小说里也存在相反的观点,即布莱德利对爱的洞见实际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觉,他并不能认知自我之外的世界真相。即使《黑王子》中爱的体验和柏拉图描绘的一致,也不一定使读者确信能看清真正的巴芬及其美与善,因为恋爱中的人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将想象的幻觉投射到爱人身上。布莱德利最初感觉自己爱上的是拉歇尔,但随后表示疑惑,“这是爱情吗?或者什么也不是,只是上了年纪的很长时间没有爱情经历的清教徒昙花一现的尴尬事”(同上:142)。布莱德利的兴趣很快从母亲转移到女儿,读者可能嘲笑布莱德利的朝秦暮楚。但小说提供的事实是:布莱德利在拉歇尔面前尴尬到了性无能的程度,只有和朱利安在一起时才感到兴奋和激动。可是,在朱利安看来,尽管表面布莱德利很爱自己,但他并不渴望真正地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听起来在你心中除了你没有别人……看起来你并不了解我,你确定你爱的是我吗”(同上:264)?这些场景中描述的布莱德利专注于自己的心理状态,对朱利安的痛苦和经历漠不关心,“令人目盲的快乐”——他对爱情的评价也表明了这一点。
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爱究竟是借助其他方式无法窥见的善与恶的源泉,还是层层遮蔽下的自我中心感和欺骗的根源呢?
1. 爱的神性
苏格拉底认为现实生活缺乏真正的洞见,但充满着对另外一个世界中善的渴望,我们努力回到那个世界,回到善的感知。在回到善的努力中,美和身体对美的感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苏格拉底在《斐得罗篇》中指出,
视觉对我们而言是身体最敏锐的感官,但视觉看不到智慧。如果智慧进入我们的视野并提供一个明确的相似物,也能够引发强烈的爱欲,其它引起爱欲的物体也一样,但只有美拥有那样的命运,美是最普遍的,力度最强的(参见Plato 1901:103)。
道德感不强的人处理爱欲的方式非常愚蠢:以简单的性发泄为目的寻求肉体满足,放纵情欲。为身体外形所迷惑的欲望是肤浅的,因为没有尊重内在的神性美。对于离理想世界更近的人来说,爱欲有更深刻的基础——即灵魂美和外在美合二为一。
欲望是整个灵魂的大地震,颠覆了生活的习惯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向善的趋近。看到美丽的爱人产生敬畏的震颤,然后是神秘的出汗和灼热,美源源不断地流入眼睛,滋润着灵魂羽翼干枯的根部。灵魂羽翼的生长改变着灵魂的内在形式:灵魂的情感和灵魂的智性。灵魂沸腾着,搏动着,疯狂的感觉摧毁了睡眠,灵魂被快乐和痛苦劈成两半,当情人出现在面前时,爱的灵魂如同灌溉水渠一样将欲望之流导向对方,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欲望,在那一刻,爱的苦痛和折磨得到缓解,收获人生最甜蜜的快乐果实。(同上:89)
从柏拉图的这段话中可以总结出关于爱欲的四个论点:第一,爱欲是灵魂寻觅善的必要动力源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没有美所引发的灵魂震动,没有美的独特洞见,灵魂就不会寻找善,永远处在干涸枯萎的状态之中。第二,爱欲是洞见的重要来源,爱使人探索所爱之人的内在本质甚至内在的神性,如果没有灵魂的激烈反应,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爱和外在的善是密切相联的,情感和智性协调一致的性爱表征了善的存在。善激发的爱欲可以在想象中驰骋,在经验中却很难实现。但是我们需要身体对美的反应获得感悟,然后用感悟去寻找善。柏拉图承认盲目的性爱是常见的,然而迟钝的理性也是普遍的,如果没有爱欲的指引,理性永远是呆滞的。第三,爱欲不仅是灵魂寻找善的起点,而且终生伴随着对善的追求。最高境界中的爱人完全杜绝性行为。柏拉图认为身体极度的快乐会遮蔽灵魂的视野,爱人们仅用爱抚表达爱意。但是那些有性行为的情侣在来世也会得到上帝的奖赏,爱侣们被上帝福佑的一生都会彼此相伴,在光亮中游历,长出天使的翅膀。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剔除爱欲中的性成分,相爱的人凝视着对方,终生追求着善,爱欲是年青人精神成长中重要的因素。第四,最高境界的爱欲形式中存在两个方面的认知,彼此相爱的人都具有主体意识,都在朝着善而努力,尊重彼此的独立,尊重所爱的自由,培养自由独立的精神,这是慷慨的爱和占有的爱之间的主要区别,因此年轻人常被警告不要将爱变成占有和嫉妒。爱侣承认彼此的精神特质,爱是对神性的感知。
灌溉、沸腾、刺痛交织的丰富体验,用情人之美灌溉灵魂的无上快乐,柏拉图精彩描述了挑战世俗的爱欲萌动。当视觉捕捉到优美的形象时,对美的渴望神秘地激发灵魂中爱的洞见,“恋爱使人的精神之翼真正生长”(泰勒1996:348)。柏拉图关于爱欲的主要论点在默多克的哲学著作《火与日》中有集中体现,在《形而上学》中她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而在小说《黑王子》中,它们构成了故事情节和人物行动的基础。
2. 世界的迷雾
但丁穿越了惩戒好色者的火焰和贞洁天使净化灵魂的火焰,他高唱:“幸福啊!心灵纯净的人!”但丁去除了额头上罪恶的最后印记,立于天堂之上,天堂在举行盛典,预言者高唱《圣经》里的所罗门之歌:“从黎巴嫩和我同行,我的新娘。”歌唱富有激情,和但丁一样,激情中净化了欲望的成分。这时在花团锦簇的双轮战车中出现了一位女士,面纱是基督信仰的白色,披风是希望的绿色,长袍是基督之爱的红色,但丁和贝阿特丽不是第一次相遇。
“昔日相见,数载已逝/在她面前,我灵魂震颤、充满敬畏/她周身放射着力量/凡夫俗子感到永恒的爱”,但丁的灵魂像《斐得罗篇》里的情人一样被爱情震动。贝阿特丽长袍下的火焰象征净化肉体欲望的基督之爱,贝阿特丽深情地呼唤但丁,但丁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诗里,“但丁,不要哭泣,……看着我,我是贝阿特丽,这里所有的人都住在福址之中”(Dante 2004:30)。此时的但丁已经净化了灵魂的罪恶,古老的火焰消退了性的热度,当贝阿特丽含情脉脉地凝视但丁时,但丁的全部个性被她发现并赏识,在净化欲望之前,人看不到对方的个性,因此但丁对他的读者说,这个世界是盲视的,“兄弟啊,世界是盲目的,你的确是从那里来的”(但丁1961:154)。世界上林林总总的诱惑——名声、荣誉、金钱、情欲——为人的视觉制造迷雾,使其不能真实地观照他人,同样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在《炼狱》中被净化的罪恶是错误恋爱的不同形式,灵魂过度沉溺于自我,在主体和真正值得爱的人之间制造了障碍。在骄傲的情感中,人只看到自己的立场,这样就看不到所爱之人的需求;在嫉妒的情感中,人只看到别人的所有,同样忽视了他们是谁,他们需要什么;在愤怒之中,因为对别人充满憎恶,所以看不到别人的经历和需求;慵懒和贪食的人专注于自己的舒适和满足,对别人的需求不理不睬。同样,欲望被视为畸形的恋爱,纵欲的人只关注身体的快乐和兴奋,看不到爱人独特的天性,也不能回应爱人真正的需求。一个被视为快乐容器的人会遮蔽他人的本性。读过但丁作品的读者会忆起鲍罗和弗兰西斯卡的爱情,尽管二人永浴爱河,却看不到彼此的特性,他们都不把对方视为主体和中心。从但丁《神曲·炼狱篇》也可总结出四个论点,和《斐得罗篇》中的观点有矛盾之处:首先,对美的身体反应将头脑束缚于错误的恋爱对象,削弱了对善的追求。其次,欲望像其他罪孽一样,在爱人周围制造自我中心的迷雾,阻碍了对真实和善的认知。再者,即使性爱作为人生活的一个阶段不能避免,爱必须首先净化肉体的欲望,才能达到真实、达到善,然后抵达最高形式的爱和仁慈。最后,性爱不能尊重恋爱对象的主体性和特质,将其视为被动的享乐对象。
现实生活中的有些爱欲具有《斐得罗篇》的特征,另外一些具有《神曲》的特征。柏拉图指出某些爱欲的认知是肤浅的,不能够达到真和善。但丁明确地表明即使在人类最高形式的爱欲中,其中的性成分也是认知的障碍和谬见的根源。真正的认知在净化灵魂之火熊熊燃烧之后显现。如果人从开始就没有欲望,就会更出色地扮演观察者和爱人的角色。和当代许多伦理学家相比,默多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用温馨的迷雾包裹自己的方式,迷雾使人不能达到他人的真实。如果保罗·萨特认为他人是地狱,默多克的地狱则包裹在舒适温暖的自我之中,无法通达别人,也无法达到善,只有天堂般的真正的无私洞见,天堂的道德努力可以使我们挣脱自我,认知他人。无论在默多克的哲学作品中,还是在她的小说中,爱中的欲望都是但丁认为的罪过,是自我中心、自我欺骗和自我沉浸的根源,是横亘在我们和爱人之间的障碍。默多克接受柏拉图在《斐得罗篇》中讲述的人类重获翅膀的故事,赞同柏拉图赋予美的特殊角色,认为对美的身体反应在认知动力和洞察力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默多克不能接受的是承认性爱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作用。
3. 焦虑和疯狂
就布莱德利和朱丽安的爱情而言,《黑王子》里许多迹象似乎表明布莱德利是但丁式的罪人,他的爱是自我中心的雾障。尽管爱欲最初使他对周围的人充满关爱和慷慨,但慷慨施爱的快乐很快就被焦虑的痛苦,被嫉妒和占有所取代。特别是当两个人到达乡间别墅时,布莱德利感到无名的焦虑。他本来打算一个人度假。为了取悦朱利安,必须隐瞒妹妹普里斯西拉自杀的消息,还必须设法使自己从内疚感中解放出来。由于坠入爱河导致的疏忽,布莱德利对妹妹的死负有部分的责任。布莱德利没有认真地对待朱利安的感情。当她知道和一个刚收到妹妹死亡消息的人相爱时,会不会感到震惊和崩溃呢?爱欲的焦虑和虚荣使他看不到爱人真正的心理状态。布莱德利也没意识到在年龄上撒谎对朱利安的影响。当朱利安从父亲那儿知道布莱德利的真实年龄时,顿时爱意全消。小说结尾的四段叙述都在指责布莱德利自私自利的各种表现形式。对克里斯安而言,布莱德利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清教徒,对朱利安的迷恋难掩对自己的一片真情。对于心理学家马洛·弗兰西斯,布莱德利的故事印证了弗洛伊德理论。由于在童年时期对母亲产生的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对母亲热切的依恋,一方面因母亲不忠而感到憎恶,布莱德利因害怕女性而成为同性恋。当朱利安装扮成哈姆雷特时,布莱德利感到异常激动,这个细节似乎证明了布莱德利被童年妄念所控制。拉歇尔自认为布莱德利爱的是自己,他对朱利安的感情是典型的爱情梦幻。朱利安在和布莱德利交往前刚和十几岁的男友分手,在两段情感间游移不定。欲望能够揭示真理吗?爱和占有相关,是证明自我的手段,欲望遮蔽了真理,腐蚀了艺术,布莱德利的作品不能够真实地描述爱的真相。
默多克在《形而上学》中就真理和欲望的认知能力问题发表了这样的观点:“爱是精神的果实,精神的充盈满溢”(Murdoch 1992:23)。柏拉图的爱情观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启迪。坠入爱河对许多人来说是最强烈的体验,爱不仅能够产生宗教般的确定感,还能消解自私的心态,使人学会观察、珍视、尊重非我的存在。但另一方面爱也会产生焦虑,因为爱把思维中心从自己转移到他人。为了主宰他人,爱情关系能够产生极端的自私和以占有为目的的暴力行为。因此,默多克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教诲,如意识到什么时候该放弃,如何放弃,何时以分手的方式表达爱,慷慨大度地让爱人离开。默多克认识到爱欲既有产生暴力和极度自私心理的可能性,也能使人挣脱自我的桎梏,在爱人强大魅力的感召下,走向自我,趋向真实。无独有偶,在另一部作品《神圣的和亵渎的爱机器》中,作家直接用自己的声音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爱是一种光彩夺目的崇高价值,甚至享受这个字眼也是对爱的亵渎,它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东西,爱所到之处发出耀眼的光芒,使全世界黯然失色”(Murdoch 1984:35)。
在这里默多克把爱欲描绘成洞见和真相的源泉。布莱德利经历了爱的体验,也许并不是四个续篇中描述的自我欺骗的可怜虫。但丁式的罪人不是布莱德利,而是四个续篇的作者。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对世界的认知荒唐可笑。克里斯丁慷慨大方、精力充沛、令人敬佩,但本质上自负而且功利,完全缺乏生活的精神层面。也许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太长时间,对艺术价值的不解遮蔽了视线,可笑地认为布莱德利爱上的是她。弗兰西通过普遍理论的透镜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于简单化,不能够理解个体的复杂处境。拉切尔把整个生活的赌注压在一系列谎言之上,默多克作品中最接近罪恶的就是拉切尔这样的人物。在欺骗和自欺中,别人的现实处境对他们根本不存在。布莱德利说,“罪恶有时候不是斜着眼的有意识的卑劣阴谋,而是故意疏忽的产物”(Murdoch 1975:45)。在四个叙述人当中,朱利安是最不幸的。在母亲、父亲、情人的争战中筋疲力尽,远离人群,退缩到禁欲的艺术当中。反观布莱德利,他的爱情经历实际上印证了《斐得罗篇》中的爱情观。多年以来,世界的中心是他自己。但作为艺术家,他灵感枯竭,对成功的畅销书作家阿诺德·巴芬充满嫉妒。当朱利安走进他的生活时,激情打通了视野,通过艺术看到了真实。焦虑和嫉妒遮蔽了布莱德利的视野,爱情让他睁开眼睛,看清了小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个体的焦虑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焦虑是人类这种动物所特有的,它是一种贪婪,一种恐惧,一种嫉妒,一种憎恶,我喜欢隐居,当焦虑减弱时,才能够反思灵魂的自由和过去的束缚……但是这一丁点的黑暗不能看作缺陷,它用一种暴力将现在的时刻升华为心荡神弛,焦虑与爱是对手,爱情是战胜焦虑的强大力量”(Murdoch 1975:155)。布莱德利摆脱了自我中心的迷雾,爱情使他为了朱利安,隐瞒了她母亲谋杀她父亲的事实,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勇气承担了罪名,接受了判决和刑期,在狱中创作。爱使他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4. 爱欲和艺术
综上所述,《黑王子》中的爱欲图景更接近柏拉图。比柏拉图更深刻的是小说分析了摆脱个人中心主义的根源,爱欲使布莱德利突破了自我的桎梏,寻觅世界的善和真实,并创造出真正的艺术。“艺术来自于灵魂深处,那里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就没有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也没有人,因为没有爱欲,人只是一个幽灵”(Murdoch 1997:487)。《黑王子》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艺术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布莱德利起初是一个灵感枯竭的失败作家,爱欲打开了灵感之门,邮政塔楼一幕引发的是有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小说中有没有揭示朱利安的本真面目?是谁的洞见揭示了她的真相?是作为情人的布莱德利?还是作为艺术家的布莱德利?一个不会成为讴歌爱情的艺术家的情人能不能看清爱人的本真?赋予作品生命的洞见属于艺术家,不属于情人,或者属于在孤独的艺术生涯中保留爱之印痕的情人。朱利安这个现实中的女人在作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小说里有没有对一个女人真正的认知?或者现实不过是创作的原始素材而已?换一种说法,艺术家的洞见是对他人真正的爱,还是利用他人达到创作的目的?
小说给出的答案是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揭示了朱利安的真相,布莱德利讲述的故事是那样丰富、多样、深邃,和四个后记中的粗糙叙述形成鲜明对比。艺术家布莱德利使我们反复思考情人布莱德利的幻觉、焦虑和错误。爱欲让布莱德利睁开双眼,但爱情真正有价值的果实是我们面前的艺术品和艺术观念。“小说由于朱利安而存在,朱利安必须成为小说,这是朱利安的异化,但偶然间也成就了她的不朽,这是我给她的礼物和我最终对她的占有”(Murdoch 1975:256)。艺术作品或作为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能够认知他人的真相,这是默多克道德的本质。布莱德利直到身陷囹圄,与人类社会隔离。在孤独中创作自己的小说时才达到这一高度。爱的洞见在本质上既不稳定也不持久。只有通过艺术生活,我们才能成功地拥有我们爱过的一切,只有那时,我们的头脑才能以具体性和准确性拥抱过去的经历。普鲁斯特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嫉妒和焦虑我们永远无法达到艺术品对真实的洞见。
现实生活中的爱人在爱情激发的艺术品中处于什么地位呢?普鲁斯特认为“艺术品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经验之上,从几种不同的恋爱经验中,我们提炼出爱的一般形式”(Proust 1982:78)。作家为了获得本质和真实,为了获得普遍性,需要观看很多教堂才能描绘一个教堂。为了描述某一情感,需要在观察很多个体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对个体的背叛是创造性的前提。艺术家不是为了这种爱或那种爱感到愉悦。而是对具体经验中提炼的爱的普遍形式感到愉悦,艺术家被事物的本质所滋养,在本质中发现营养和愉悦。“在爱情的记忆中,艺术家只不过把爱人看作摆几个造型的模特罢了”(同上)。换言之,普鲁斯特的观点是艺术家从未充分地认知他人的具体特性或他人的主体性,具体性湮没在对爱的本质形式的探求中。普鲁斯特认为没有人看到具体性。艺术家热衷于一般形式,普通人蒙昧而愚钝,无一例外。和他人具体性或主体性的接触只发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艺术家在文本里成功地捕捉他或她的主体性。艺术的透镜是我们达到他人思维真实的唯一途径。默多克在很多方面比普鲁斯特更加肯定爱情。她没有建议艺术家忽略具体的爱人寻求一般形式。在《形而上学》中,默多克强调艺术能够揭示人类整体身份的真相,即一个真实生命的所有怪诞和偶然性。艺术视野被艺术的功利目的所局限,布莱德利最终在朱利安不可捉摸的真实面前妥协了,
我不希望最终在我幽独的幸福中,忘记了作品中人物的真实存在……朱利安,我爱的女孩,你永远逃离了我的怀抱。艺术不能将你同化,思想不能将你解读,我不了解你的生活……你笑,你哭,你读书,你做饭,你打哈欠,你躺在别人怀里,我不会否定这一切,在我卑微、艰难的生活现实中,我爱着你,爱情依然存在,朱利安,爱没有减弱,尽管爱变成了清晰忠实的记忆。回忆给我带来了些许痛苦,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当我想到你在什么地方生活着,我流泪了。(Murdoch 1975:167)
布莱德利在孤独的泪水中默默地怀念他的爱人。他爱的不是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充满喜怒哀乐的有血有肉的人,这表明了默多克对艺术家超越艺术功利、契达真爱境界的向往和希冀。
Alighieri, Dante. 1961.ThePugatorio[M]. New York: American Library.
Murdoch, Iris. 1975.TheBlackPrince[M]. London: Penguin.
Murdoch, Iris. 1984.TheSacredandProfaneLoveMachine[M]. New York: Penguin.
Murdoch, Iris. 1992.MetaphysicsasAGuidetoMorals[M]. New York: Penguin.
Murdoch, Iris. 1997.ArtandEros:ADialogueaboutArts[M]. Allen Lane: Penguin.
Plato. 1901.OperaVol. 2 (John Burnet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oust, Marcel. 1982.RemembranceofThingsPast[M]. New York: Vintage.
Steiner, George. 1997.ExistentialistsandMystic:WritingsonPhilosophyandLiterature[M]. Allen Lane: Penguin.
A.E.泰勒.1996.柏拉图:生平及著作(谢随知等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安宁、袁广涛.2011.超越性别?——以《黑王子》为例浅析艾丽丝·默多克的女性意识[J].当代外语研究(10):47-52.
但丁.2004.神曲·炼狱篇(田德望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何伟文.2009.善、爱欲和艺术——论默多克作品对“道德”主题的探讨[J].外国文学评论(3):41-54.
何伟文.2011.超越经验世界的艺术和道德深意——解读《沙堡》[J].当代外语研究(4):49-55.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