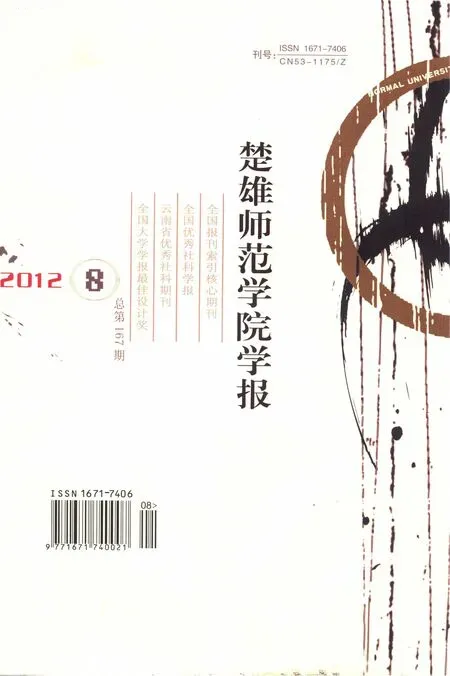当代文学史的“完成”与“未完成”*——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与问题
丁 宁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洪子诚先生的个人写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可说是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雏形。[1]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以下简称《概说》)以“小书”的外形将洪子诚厚重的文学史观[2]包含其中。《概说》体现了作者写作文学史的素朴精神。所谓素朴精神,是指洪先生在写作《概说》时采取的一种“小试牛刀”般的试探性文学史处理姿态,而非宏大的、“力透纸背”的、颠扑不破的文学史建构姿态。正如洪先生拟定的题名“概说”一样,它是一种有探讨空间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洪子诚有心作《概说》,而非史论,并不是非宏大叙事不取的“大腕儿风”,而是谦虚谨慎的“学者风”,看似无心,实则有心。作者在《自序》中谈到,成书过程是由作者在东京大学任教的讲稿整理而成。在任教期间,作者发现“他们中的有些人读过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但普遍对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学的面貌缺乏整体印象。”[3](P3)鉴于这种情况,作者“当时的设想,是对这些于这一领域知之不多的听者,简略而又较完整地介绍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文学状况。”这种动机相对而言是较为朴素单纯的。洪先生最初只是想帮助学生填补空缺,因为他发现“他们”缺乏整体印象,只是零散地知道一些作家作品的状况,于是便产生了写作系统性讲稿以帮助学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之脉络的想法。1997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由香港青文书屋首次印刷发行,讲稿变为书稿,而书稿则成为洪子诚治史方法、观念和智慧的结晶。《概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洪子诚在面对复杂浩瀚的史料时所采取的治史姿态和写史方法,透过《概说》并不庞大的外形,我们可以找到深藏其中的“洪子诚特色”的文学史意识和方法,[4]看到一种当代文学史的“完成”形态。
一、史的全貌:历史整体意识
洪子诚在书中体现了一种历史整体意识,这来源于他对中国20世纪文学而非仅仅是当代文学的整体状况的系统把握。对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有较为客观的了解,加上对史实材料的重视多于个人感慨的抒发,使得他能跳出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写史的藩篱,以对文学史的整体考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意识可通俗表述为:因为有这样的文学历史状况,所以有这样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在历史整体意识中把“史”还原为“史”。他在《前言:分期与方法》中说:“基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状况的这一理解,即对某种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的性质及其演变的把握,我把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称为‘当代文学’。”[5](P8)因为当代文学发展过程有这样的特点,于是他选择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分期方法。其实,这种分期在《概说》中只有区分一种文学规范即“工农兵文学”的地位演变的作用。在内部,他从对史实的处理方法上,反而实现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践行。可以分期的是时间,无法分期的是文学整体发展的理念;文学发展是有流脉的,不是空穴来风,这样的观念使得洪子诚处理文学史时有“瞻前顾后”的优点。他的考察不仅限于“点”,而是由点到面,由面到一个三维的历史空间。是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文学?洪子诚选择了后者。[2]他在处理某些文学思潮时,注意其产生的源流,产生时与当时环境的关系及产生后可能形成的流脉,他对80年代现实主义精神回归的叙述就是例证之一。这样,《概说》让读者看到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不仅告诉了读者当代文学长成什么样,还启示读者当代文学为什么长成这个样。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是洪子诚带给我们的欣喜。
二、史的真相:历史还原方法
《概说》还践行了一种历史还原的文学史写作方法。洪子诚能够“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让史家发生位移,“努力将问题‘放回’到 ‘历史情境’中去审察”,[6]“一方面,会更注意对某一作品,某一体裁、样式,某一概念的形态特征的描述,包括这些特征的演化的情形;另一方面,则会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并提供显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7]并以客观的眼光分析其成因。洪子诚在《前言:分期与方法》中说:“在上编,……主要是了解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在下编,主要是考察控制削弱之后,在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作家心理素质和文化性格的状态,以及这种性格、心理状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5](P9)这表明,他侧重从“文学——社会”的角度进行文学史处理,因此他非常重视材料的客观性呈现。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指出记忆的不可靠性:“记忆的可信度有多大?在以文字形式见诸记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人为的美化和丑化记忆的内容。合理的遗忘可能使历史的真相永远深埋于地下。”[8]所以,他注重对历史感的还原。他在《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对五六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学问题和艺术形态特征的谈论,由于多少失去‘历史记忆’而常常反应失措和缺乏深度。”[9]对历史记忆的还原,使得他的社会政治视角脱离了对主流政治话语的附庸而建立起来。他力求以客观中立、不动声色的姿态将历史的本来面貌摆在读者面前,而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由读者在了解历史实情后,自己去感受、去评说,历史真相[2]得到了保护。比如,在叙述“十七年”文学规范与控制的历史情境时,洪子诚并没有激昂地评判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而是客观地将社会现实用不带价值暗示的文字呈现给读者,让读者感受到真正的历史气氛,巧妙地把读者圈进了与作者一同反观历史的世界中。这种方法也为当代文学的价值评说留下了可供阐释的空间,面对那样的历史与那样的文学,不同的读者将会有不同的感受,可能会总结出不同的文学—社会关系。于是,《概说》成就了这样一种阅读体验:相同的是当时活生生发生的历史,不同的是人们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各种解读。
三、史的笔墨:零度写史笔法
《概说》以洪子诚冷静客观、不露声色、不明确褒贬的叙述方式和行文,突破了文学史写作的窠臼,它以一种“零度写史”的姿态为文学史写作吹来了清新之风,[10]使思辨、创新、严谨的治学作风得到发扬。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说:“我们知道,某些语言学家在某一对极关系的两项之间建立了一个第三项,即一中性项或零项。这样,在虚拟式和命令式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像是一种非语式形式的直陈式。比较来说,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又毫不介入,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11](P102)笔者借用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将它位移到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中,以形象描绘《概说》的文学史叙述风格。从以上罗兰·巴尔特的阐述中可以看到,零度的写作正是一种理性的写作,它“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又毫不介入”,这种写作和叙述看似没有作者,作者看似置身事外,就像《概说》,在它的字里行间似乎看不出作者的任何偏好和态度,作者像是一个局外人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从文字层面成功拆除了学者常说的当代史与当代史家的“共谋”关系,形成了静观的“史家笔墨”。韦恩·布斯曾提出“隐含作者”理论:“尽管作家努力做到诚实,他的不同作品会隐含着不同的化身,不同观念的理论组合。在一个人的私人信件中,因为与每个通信者的关系不同,每一封信的目的不同,就隐含着自己的不同化身,与此相同,因为每一部作品的需要不同,所以作家在每一部作品中的化身也不同。”[12](P78)如上所言,面对自己的写作,作者要真正地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毫无温度是难以做到的,其实,洪子诚对文学虔诚的关切之心掩藏在文字深处。相对于常规的文学史写作,《概说》的特点在于写作者更擅长巧妙地“移情”,他对文学史的理解之心其实真实地存在于零度叙述的背后。不做历史的看客,不做文学的“局外人”,使得《概说》在零度的背后有高度的温热在沸腾,而体现在外层,则是冷静的零度感。笔者认为,《概说》形成内热外冷的文学史风貌,正是因为洪子诚真正走进了文学史本身,他靠得太近了,太接近真实,反而显示出真实的冷峻。“这种分析是包含着批判性的价值评价的,但作者也只是‘点到为止’,并不作情感的渲染与尽兴发挥,有的读者或许会有不满足感,但我认为,这恰恰可以视之为‘史家笔法’。这同时也显示了一种叙述风格,我想把它概括为‘绵里藏针’。‘在委婉里见犀利,于稳健中显锋芒’。”[6]这是洪子诚治史的智慧,也是他在看遍了史家与历史的纠葛后,试图脱离这种纠葛的一种努力。
四、史的“未完成”:探讨空间的留存
《概说》浓缩了洪子诚的治史智慧,实现了多重维度上的当代文学史的“完成”,但《概说》在史的“完成”之外却依然回荡着史的“未完成”话外音,作为读者,也有没有实现的期待:[6]第一,虽然洪子诚能够在主流文学中挖掘出非主流文学的价值,提示我们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藏身之处”,但《概说》的社会历史意味依然较浓厚,[13]这主要是指,洪先生在处理和平衡文学史的社会历史意味和作家作品的审美意味的关系上,似乎还有“未完成”和有待探讨的空间。譬如说,《概说》的叙述始终以社会历史为着眼点,在“十七年”时期是政治环境,在新时期是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而对于作家作品体现的审美性的论述则稍显吝啬。尽管当代文学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得审美意识在一部分“主流”作品中不幸缺失,然而,在“百花时代”、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期以及新时期,始终有一批坚持文学审美价值的作者在进行着“地下的”、“朦胧的”创作。他们在当时汇入“非主流文学”,其审美价值是有待认定和阐述的。第二,对八十年代的评述似乎显得单薄了一些,对“十七年”时期外部条件的侧重又使得这种当代史内部分期有头重脚轻之感。在“十七年文学”中,把文学现象归纳为各大类别或许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如果没有这种归纳,反而不适应当时的文学环境。而在新时期的文学背景下,依然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为线索做类似的归纳,尽管有利于文学现象的整合,但却有模仿“十七年”之嫌。因为到了新时期的文学背景下,依然做类似的归纳而未能找到更新的串起文学事实的方法,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不论是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分期还是各个小阶段的内部分期,《概说》似乎都没有根据文学环境的变化进行处理方式的变换。作者如果能找到更鲜活的处理文学史的时间划分的方法,或许会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惊喜。第三,过于追求还原历史的纯正而忽视了文学史也可以在真相中有声有色,这或许是个问题。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就提出,我们对历史的叙述不能做到完全客观,我们在叙述历史之前,已经被抛入历史之中了,因而本质上没有真正客观的历史,重要的是我们让什么成为我们的历史。前文谈到,洪子诚将他对文学的关切之心、参与之心掩藏在零度叙述的背后,这成就了他的“史家笔墨”,然而,过于深刻的隐藏难免让读者有“不吐不快”的遗憾感。这种超理性的写作,期待的是同样超理性的读者,感性的读者总是难以找到洪子诚文字中的感性线索。尽管作者有心隐藏,期待有心的读者能发觉闪光的金子,但是如此高要求地预设“隐含读者”,便会酿出曲高和寡的遗憾。最后,《概说》中囊括的真正影响着当代人的作品是有所缺失的,这让我们对洪子诚先生选取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框架的标准和维度产生了好奇。当代史处理的似乎还是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14]是因为普通民众没有真正走进当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始终没能真正走进普通民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作者将重心放在了作品分析上,而在作家作品的选取上,读者熟知的如朦胧诗《一代人》、路遥的小说《人生》、汪曾祺的《受戒》、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以至于探索电影《黄土地》等,都没有缺席而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这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与《概说》在叙述文学史时选取的角度之各异。然而,读者总归不希望当代人读的当代作品在当代史中销声匿迹,因为作家作品是文学史的主角,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缺失是令人遗憾的。
综上所言,洪子诚以其“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文学史研究姿态,巧妙地处理中国当代文学史,使得《概说》呈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史写作风貌。面对宏大的中国当代史,洪子诚取零度写史、不动声色的态度;面对纷繁复杂、流派众多的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又取社会历史的维度,以历史整体意识和历史还原方法,将当代文学在历史中沉浮不定的真相尽量摆在读者面前;在卷帙浩繁的史料面前,洪子诚纵横捭阖,拓宽他写史的经度和纬度,当“入”时及时投入,当“出”时潇洒而出,投入处虔诚真挚,充满智慧,退出时冷静严峻,又心怀理解。洪子诚通过《概说》,使自己在当代文学史的天地中,赢下了属于《概说》的独特且不单薄的位置。它体积小,却清晰、明确地指明了文学史写作目前所能达到的位置和以后将要前进的方向。它立下了丰碑,也留下了期待;它有所“完成”,也有所“未完成”;它指示着新的开始,而不是最终的结束。这也正是文学史著作及文学史研究所具有的真正意义。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侯桂新.洪子诚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性 [J].南方文坛,2009,(4).
[3]洪子诚.自序 [A].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戴锦华.面对当代史——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J].当代作家评论,2000,(4).
[5]洪子诚.前言:分期与方法[A].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钱理群.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J].文学评论,2000,(1).
[7]转引自:王莹.建构当代文学学科的话语体系——论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及其超越之路 [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8]转引自:陈明华.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对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一种解读 [J].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9]洪子诚.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J].天津社会科学,1995,(2).
[10]谢玉珊.创新·严谨·朴实——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读后 [J].天中学刊.2002,(4).
[11](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 [C].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12]转引自:杨波.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思想浅析 [J].电影评介,2011,(9).
[13]姚晓雷.当代文学史写作探索刍议——由当前四部文学史著不同的写作模式谈起 [J].文学评论,2004,(2).
[14]曾令存.洪子诚与中国当代文学[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