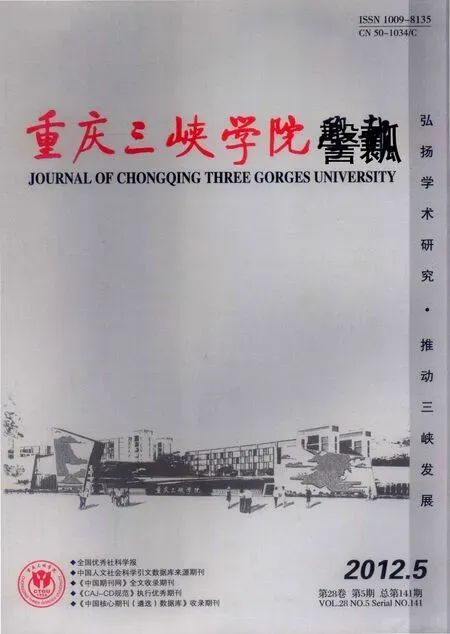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熊 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熊 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翻译诗歌;诗歌创作;语言观念
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人,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同时也致力于建构中国新诗格律理论,是中国新诗史上少有的将诗歌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的诗人。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早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他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何其芳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据已有的文献资料查证,他在该时期没有翻译任何诗歌作品,但这并不表明翻译诗歌对何其芳的创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何其芳正是在阅读了大量英文诗歌及其译本的基础上才在古典诗歌传统之外积淀起了丰富的新诗创作素养,有的诗篇带有明显的译诗影响痕迹。
何其芳认为在世界文化语境下翻译诗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人们为着文化交流或扩展文化视野的目的应大量阅读译诗。何其芳先生对翻译诗歌的认识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译诗不能带领我们驶入“外国的诗歌的海洋”,但另一方面却主张为了观赏“奇异的景物”而阅读译诗。何其芳先生对译诗的语言艺术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诗歌,这种高度精巧地由语言来构成它的美妙之处的艺术,我们怎么可以只从译文来欣赏它,来谈论它呢?我们又哪里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些既忠实地表达了原来的内容、又巧妙地保持了原来的语言之美形式之美的译文呢?”[1]110这等于说任何译诗与原诗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译诗难以再现原诗的风貌。何其芳先生从诗歌的文体特征出发所得出的以上结论自然有合理的地方,但以原诗为准绳去评判译诗难免会抹杀译诗的创造性,毕竟在中外翻译史上译文风格胜出原文的例证并不罕见,很多优秀的译作后来成了民族诗歌史上的经典作品,比如英国人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波斯古诗《鲁拜集》和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东方诗歌后结集的《神州集》等就是范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何其芳先生认为阅读外国诗歌是必需的,哪怕是从译文中读到原作的基本内容也能帮助我们拓展眼界:“仅仅为了阅读那些外国的杰出的诗歌,我们也是值得去学习外国语的,虽然通晓外国语的好处并不止于此。但产生过杰出的诗歌的外国语言是那样多,一个人怎么可能都学好呢?还是不得不读翻译的作品。理想的译文虽然很稀少,不能保持原来的语言之美形式之美也就难免要有损原来的内容,但从翻译仍然是可以读到它们的基本内容的,仍然是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的。”[1]110从以上引文的后半段可以看出,何其芳先生实际上仍然认为翻译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面对众多的民族语言和繁多的优秀作品时,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掌握每门外语并穷尽所有的外国文学作品,因此每个人为了积淀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开拓创作视野就会不可避免地阅读外国文学的翻译本。
在何其芳看来,诗人的创作受阅读译诗的影响是必然的。何其芳先生在谈写诗的经验时认为诗人必须要有“一般的文艺修养和诗的修养”,至于如何培养修养的问题,何先生觉得最根本的就是阅读前人的作品。“读前人的作品,如果不是有意地模仿,而是自然地接受一些影响,那不但是难免的,而且对于我们的生长和成熟是必要的,有益的。”[2]458在今天这样开放的语境下,阅读前人的作品自然包含着阅读外国诗歌的译本,因此某个诗人由于阅读了外国诗人的作品而很自然地受到了影响是不可回避的创作现象。何其芳认为外国诗歌的译本甚至是并不成功的译本也会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影响。在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60周年的文章中,何其芳曾这样说道:“通过并不怎样理想的翻译,而且有些还是重译或节译,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却早就对中国的年轻的革命诗歌发生了显著的影响。”[3]431何先生此种关于译诗的认识正好符合我们今天译介学的观点,传统的翻译研究“实质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研究”,译介学“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研究目的的不同:传统翻译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和指导翻译实践,而比较文学学者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它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他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4]11译介学和翻译学的根本区别也为我们研究翻译诗歌去除了很多争议和障碍,我们不必再去计较诸如“诗的可译与否”、“好诗的标准”以及“诗人译诗的利弊”等诸多问题,它把所有的翻译诗歌都视为一个既定的客观的文本,从这个客观的文本展开文化的影响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许多在原语国不著名的作品可能会在译入语国中引起轰动;同时,一部翻译作品质量的高低也不一定会成为它是否受到译入语国读者欢迎与否的标尺等诸多看起来扑朔迷离的问题。以外国的诗歌作品为参照进行新诗创作也是何其芳的新诗创作路线。比如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他曾写过一篇名为《毛泽东之歌》的回忆录,其中这样写道:“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在世的时候,我不曾写出一篇《毛泽东之歌》。我是多少年都在想着、构思着这个题目,而且梦想着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像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的诗呵!”虽然何其芳最终没有完成他构思多年的《毛泽东之歌》,但如若当年他要完成这部诗歌作品的话,必然会借鉴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经验,甚或以《列宁》为蓝本进行创作。
何其芳早期的诗歌创作曾受到他人译诗的影响。何其芳作为早期中国新诗史上追求唯美的现代派诗人,其诗歌创作风格除继承了古典诗歌传统外,在西潮涌动的语境中必然会接触到外国诗歌并受到外国诗歌创作技法的影响。卞之琳先生在谈何其芳诗歌创作受到的影响时十分肯定地说:“现在事实清楚,何其芳早期写诗,除继承中国古典诗的某些传统外,也受过西方诗影响,他首先(通过《新月》诗派)受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及其嫡系后继人的影响,然后才(通过《现代》诗风)受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法国象征派和后期象征派的影响。”[6]3作为熟识何其芳创作的老朋友,卞之琳的话当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在1920—1930年代通过胡适、郭沫若、傅东华、朱湘、徐志摩等人的翻译刊发在《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和《新月》等报刊上,而在1970年代之前几乎不接触外语的何其芳只能借助译诗去了解外国诗歌,他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其时就是翻译诗歌带来的影响。为了具体说明何其芳早期诗歌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我们不妨先看两首诗歌:
首先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她住在人迹罕至的乡间》(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顾子欣 译):
她住在人迹罕至的乡间,
就在那鸽溪旁边;
既无人为她唱赞美的歌,
也甚少受人爱怜。
她好比一朵空谷幽兰,
苔石斑驳半露半掩;
又好比一颗孤独的星,
在夜空中闪着光焰。
她生前默默无闻,也不知
她几时离开了人间;
呵!她如今已睡在墓中,
这对我是怎样的变迁!
接下来看何其芳早期最富盛名的《花环》:
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
无人记忆的朝霞最有光。
我说你是幸福的,小玲玲,
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
你梦过绿藤缘进你窗里,
金色的小花坠落到你发上。
你为檐雨说出的故事感动,
你爱寂寞,寂寞的星光。
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
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
你有美丽得使你忧伤的日子,
你有更美丽的夭亡。
如果不是刻意的模仿,这两首诗很难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很少有人注意的美丽少女、少女的夭亡、孤独与寂寞的心绪、幽静偏僻的意境、诗人内心的悲伤与叹惋等。据查证,华兹华斯的这首诗歌于1925年3月被翻译到中国,当时《学衡》杂志第39期开始增加了“译诗”栏目,发表了华兹华斯《露西》组诗中的第2首的8种译文,标题为《威至威斯佳人处偏地诗》,译者及各自翻译的诗名分别是贺麟的《佳人处偏地》、张荫麟的《彼姝宅幽僻》、陈铨的《佳人在空谷》、顾谦吉的《绝代有佳人 幽居在空谷》、杨葆昌的《女郎陋巷中》、杨昌龄的《兰生幽谷中》、张敷荣的《德佛江之源》和董承显的《美人居幽境》,译文都是采用五言体形式。“八首诗的作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国诗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华氏诗中那个幽凄而逝的露西进行了再创造,使她成为我们传统眼光所熟知所期待的这一个‘佳人’形象。”[7]在同一期刊物上刊出同一首诗的八种译文,这在中国翻译史上属于罕见的现象,加上译者又对之作了中国化“误读”,那华兹华斯的这首诗必然会引起文人学者的广泛关注,使之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何其芳的《花环》一诗创作于1932年9月19日,是在华氏的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一诗被翻译进中国7年半之后才创作出来的。如果没有现成的材料证明前者阅读了后者的作品之后才创作了自己的作品话,难道从两首诗的诸多相似之处中还不能寻找到答案吗?倘若何其芳真实的生活世界里没有“小玲玲”的话,那他如此凄美的诗情又该从何而来?因此,何其芳早期的诗歌创作肯定受到了其它人所译外诗的影响。
何其芳后来诗歌语言观念的形成也与他接触外国诗歌并阅读翻译文本有密切的关系。何其芳先生1951年在谈诗歌创作的形式问题时说:“运用欧化的句法过多,有些片段还写得有些松散,不精炼,都是缺点。但运用现代的口语来作新诗,语言还比较自然,这一点,恐怕还是应该肯定的。写得句子更中国化一些,更精炼一些,节奏更鲜明一些,更有规律一些,同时仍然保持口语的自然,我想这就是比较可以行得通的写法。”[8]35很显然,这一时期何其芳对于诗歌形式、句法和语言都有比较明确的理念,避免欧化和力争中国化是其核心内容,而要使诗歌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采用清新“现代的口语”。可以肯定的是,何其芳在中国新诗形式问题的探索中从来没有舍弃过对中国元素的找寻,在1950年代后期那场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中,他对于别人指责其新格律是剽窃“欧洲的十四行诗”或“英国的高蹈派诗歌”的“皮毛形式”感到十分可笑,因为他的形式主张实乃“采取的我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和“采取的我国民歌的格律的传统”,并“以我国现代口语的特点和五四以来多数新诗的收尾的句法为依据。”[9]14-15不管后来何其芳先生的诗歌形式主张是否在创作中得以很好地践行,但至少说明了他在诗歌形式问题上的民族化立场。在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民族化追求上,何其芳与英国浪漫派形成了默契,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当年创作《花环》时对华兹华斯作品的模仿。如果说鲁迅极力向国人推荐“摩罗”诗人是出于这些诗人的作品在内容上具有反叛和革命精神的话,那五四时期人们大力介绍彭斯、华兹华斯、惠特曼等诗人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在形式上具有反叛性和革命性。18世纪影响英国诗歌进程的是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人的一大共同特征就是对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的改造,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背叛了之前的新古典主义诗歌风格——严整的形式和韵律,在语言和韵式上向民谣靠近。彭斯(Robert Burns)是苏格兰农民,他的诗歌充满了“颠覆分子”的话语;布莱克(William Blake)本身是一个油画家,“他擅长用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形象的方式说最深刻的道理。简单得像童话,富于乐感如儿歌。”[10]222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许多诗作在文体上属于白体诗,不像蒲柏等新古典主义者的诗作那样有很浓的人工雕琢气味,显得比较自然,他认为“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在较轻松的作品中,诗人使用韵律的自如和得体本身被公认为是读者获得快感的一个主要源泉。”他们在语言和形式上的反叛精神导致一股纯朴、清新的诗风在英国诗坛上流行开来,英国诗歌也从此步入了巅峰期。这种具有语言反叛精神的诗人在中国受到了欢迎,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对中国新诗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徐志摩受到了华兹华斯的影响而创作的《东山小曲》便采用了其家乡“硖石镇”的土白方言。作为熟悉英国浪漫派诗风并受其影响的何其芳,即便其诗歌语言观念没有受之影响,也多少会从中得到启发。
总之,早期的何其芳虽然没有翻译外国诗歌,但他的诗歌创作理念和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译诗的影响,而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也与他阅读英国浪漫派诗歌及其译本存有关联。对于何其芳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和在译诗影响的基础上写作新诗的创作现象,应该成为何其芳研究的重要内容,理应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注 释:
①1961年,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一书中说:“我们的航行只能停止于此了。还有一个十分辽阔并且充满了奇异的景物的海洋,那就是外国的诗歌的海洋。我是曾经打算进入这个领域的。但我知难而退了。”(何其芳:《诗歌欣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0页。)
[1]何其芳.诗歌欣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M]//何其芳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何其芳.马雅可夫斯基和我们[M].何其芳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何其芳.毛泽东之歌[M].何其芳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代序)[M]//何其芳译诗稿.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7]葛桂录.华兹华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1900-1949)[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2).
[8]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重印题记[M].何其芳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M].何其芳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王佐良.英国诗史[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7.
[12][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前言[M]//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塞尔登,著.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郑宗荣)
Abstract:There is a vast literature on He Qifang’s poem composing and poem theorizing, but few works are about his remarks on poem trans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poem translation on his poem composing.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a discussion of his theorizing on poem translation, then how he was influenced in his poem composing and his view on poetic language. We hope this paper can disclose new angles of He Qifang Study.
Keywords:poem translation; poem composing; language view
On the Influence of Poem Translation on the Poem Composing of He Qifang
XIONG Hui
(China New Poem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
I206.7
A
1009-8135(2012)05-0084-04
2012-07-18
熊 辉(1976-),男,四川邻水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和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10FWW005)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