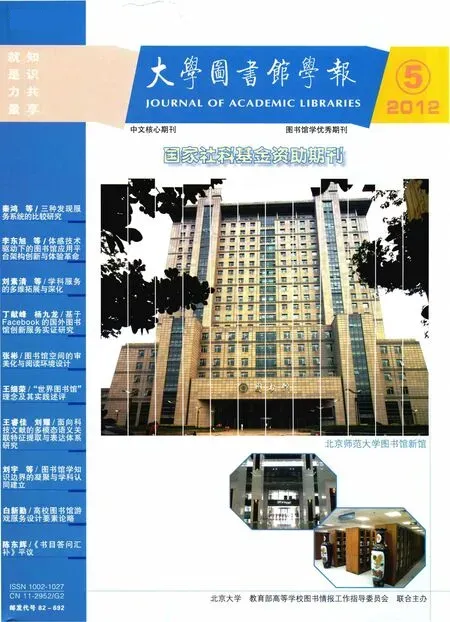《书目答问汇补》平议
□陈东辉
《书目答问》是一部带有导读性质的重要著作,曾经影响了几代学者。梁启超曾云:“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1]鲁迅在《读书杂谈》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2]胡适于1923年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将其修订精简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书目答问》位居该书目之首。余嘉锡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余氏1942年在辅仁大学开设“目录学”课程时,即以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和他自著的《目录学发微》作为课本。余氏谓:“书目诸无序释而能有益于学术者,自樵(引者按:指郑樵)之外,惟张之洞所作,庶几近之。”[3]又谓:“但欲求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亦惟《四库提要》及张氏之《答问》差足以当之。”[4]顾颉刚曰:“所见的书籍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到现在,虽已荒废了十余年,但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5]陈垣在少年时代,就熟读了《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黎锦熙当年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开设“要籍目录”课程时,将《书目答问》用作教材。后来成为一代藏书大家的周叔弢最初购书时即以《书目答问》作指导。
汪辟疆对《书目答问》评价甚高:“其书之善亦有十:一举要籍,二注板本,三别良楛,四著通行,五存次要,六示概略,七列众本,八审异同,九存未刊,十标足本。凡此皆极便于学人者也。自光绪元年刊布后,各省督学使者翻刻尤多,诸生赴试获隽者各赠一册,而坊间椠本、石印、铅印尤备。以故近六十年中,海内志学之士受此书之益者,几遍全国。殚见博闻之彦,复就本书或订补未备,或罗列众本,其后出之书并得详加著录。以余所见,则有桂林王鹏运、南昌熊罗宿之书,细行密字,几无隙地。今此本不知流落何许矣。若范希曾氏之补正,则挂漏尚多,未足与王、熊抗手也。”[6]
王重民曾经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专门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开设“《书目答问》课”[7]。同时,刘修业所撰的《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的“一九六五年”条下,有如下记载:“他与胡道静先生通信中,曾计划为张之洞《书目答问》作校注,现家中还藏有《书目答问》校注本原稿。”[8]此外,孟昭晋在2000年前后也曾经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开设过选修课“《书目答问》研究”。
张舜徽在《曾国藩张之洞学术思想之影响》一文中指出:“辨章学术,晓学者以从入之途,则张之洞所为《輶轩语》、《书目答问》影响最大。张氏为清季疆吏中最有学问之人,其识通博而不拘隘。《輶轩语》中《语学》一篇,持论正大,几乎条条可循。益之以《书目答问》,则按图索骥,求书自易矣。”[9]
《书目答问》之分类在大致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的基础上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将“丛书”列为与经、史、子、集相并列的一级类目,影响深远。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即略依《书目答问》而排架。叶德辉对《书目答问》之分类体系颇为赞赏,云其“虽仍四部之旧,与《四库》分类出入,多有异同。大致本之孙星衍《祠堂书目》,参以《隋志》、《崇文总目》,不倍于古,不戾于今,大体最为详慎”[10]。又云:《书目答问》“分类与《四库》不同,其分古子、古史两类尤为提纲絜要,截断众流。”[11]古籍数量众多,人的精力有限,许多古籍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精读甚至泛读,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很多古籍仅需了解其大体情况。虽然近现代曾先后推出了多种古籍导读著述,但就总体而言,至今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书目答问》之作。《书目答问》仍为此类读物之翘楚。笔者每年为浙江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课程时,均将《书目答问》列为首部向学生重点推荐的精读之书,避免学生在学习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生在初读之时,确实感到满纸书名、人名,颇为枯燥,但渐渐入门之后,感觉收获甚大。笔者将《书目答问补正》视为案头必备之书,收有该书的多种版本,当时感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刊布的方菲点校整理的《书目答问补正》颇具特色,因为它加入了部分重要图书在1949年以后的整理出版情况。关于《书目答问》的增补之作,数量不少,但分散各处,并且大多印数较少(有的还是稿本),流布欠广。当时曾想,如果有一部著作能把上述增补之作汇成一编,必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将使《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大为增强。中华书局于2011年4月推出的来新夏、韦力、李国庆共同完成的《书目答问汇补》(以下简称《汇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笔者见到此书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部120万字的著作通读一过,在受益匪浅的同时,深感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该书之特色至少有如下数端:
1 材料丰富,内容完备,堪称《书目答问》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汇集了江人度、叶德辉、伦明、孙人和、赵祖铭、范希曾、蒙文通、邵瑞彭、刘明阳、李笠、高熙曾、张振珮、吕思勉、韦力等清末至当代16位学者、藏书家的增补批校(含两位佚名氏批校本),其中大多乃首次公开刊布。如伦明批校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邵瑞彭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自书肆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刘明阳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自书肆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诚如该书“后记”所云,刘明阳批校本考订精审,见解独到,品评是非,冰释疑窦,实有点睛之效。如在该书第769页《笠泽丛书》一条下,刘氏批“陆本、顾本两本行格同,显明区别,只在卷末‘清朝’两字抬不抬”。高熙曾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韦力批校本乃稿本,今藏韦氏芷兰斋,此前从未公布。该书中有不少汇补者按语,对各家校语及贵阳底本略作说明,同时兼采其他学人的研究成果,以断是非。正文中为来先生所加,附录中为李先生所加。如第261页的按语指出,张锡瑜《史表功比说》一卷,范希曾误“表”为“记”。第277页的按语指出,孙联薇,范希曾误“薇”为“微”。第284页的按语指出,《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四川初刻本著者作倪璠,笺补本作倪粲,并误,应作倪燦。第325页的按语指出,《穆天子传郭璞注》七卷平津馆本刊于嘉庆丙寅(十一年),嘉庆无庚寅,叶氏题“庚寅”,佚名及伦氏并题“庚申”(嘉庆五年),亦皆误。第358页的按语指出,范希曾题“旷照阁”,当系“照旷阁”之误。第370页的按语指出,《武林旧事》十卷的知不足斋本刊于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叶氏所题“癸亥”当误。第393页的按语指出,《曾文正公奏议》三十二卷,《书目答问》初刻本作薛氏编,苏州刻本、贵阳本有增改。第458页的按语指出,宋刘邠撰《汉官仪》三卷,晁志作刘敞撰,非。有绍兴九年刻本,阮元有影宋钞本缮写本。第788页按语指出,刘氏误“嘉靖”为“万历”,“己巳”应作“乙巳”。关于宋苏过《斜川集》六卷《附录》上下二卷,该书第784页的按语指出,《宋史·苏过本传》,有集二十卷,久已散佚。乾隆时吴长元得旧钞残本,复从各书纂辑成帙。阮元从旧本重加缮录,釐定诗文六卷。除了上述正讹纠谬、补充材料、考辨原委之类的按语外,尚有一些按语乃言简意赅之点评。如第259页按语谓明凌稚隆刻本《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乃“精刊大本”。
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与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同为清代尔雅学最有影响之论著。关于郝、邵二书之高下,多数学者认为郝书胜于邵书,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梁启超就是典型的挺“郝”派[12]。《汇补》第154页《尔雅义疏》条下,张之洞曰:“郝胜于邵。”叶德辉斠补云:“按邵书胜郝,谓郝胜于邵,耳食之言也。”第154页《尔雅正义》条下,李笠批曰:“不及郝。郝取材极富,精读之,识字之道思过半矣。”《尔雅义疏》、《尔雅正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并且此类评价见仁见智,不易断定。在此我们无意评论郝、邵之高下,但《汇补》所收录的上述相关资料,对于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颇有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就总体而言,叶德辉的《书目答问斠补》质量是较高的。叶氏学识博洽,功底深厚,但笔者发现他在治学上有时也跟生活上一样“不拘小节”。叶德辉曾经指出,《书目答问》中“各书刊刻年月,时有传讹,卷数间多缺略。千虑一失,偶然有之。”[13]其实叶氏之《书目答问斠补》,在刊刻年月方面也有不少疏误之处。关于这一点,《汇补》已多次指出。如第264页按语指出,知不足斋本《补汉兵志》一卷,刊于乾隆己亥(四十四年),叶氏题“乙亥”,误。第370页按语指出,知不足斋本《武林旧事》十卷,刊于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叶氏所题“癸亥”当误。
2 附录完备,索引详细,在编纂体例方面颇具特色
《汇补》之附录包括“书目答问版本图释”、“书目答问刊印序跋”、“书目答问题识”和“书目答问通检表三种”,从而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其中“书目答问版本图释”详细著录了编者经眼的49种《书目答问》的书名、著者、出版者、行款以及收藏者。此外,编者还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较为重要的版本,配以清晰之书影,共计53幅,以达版本比勘之功效。《书目答问》问世之后,各家不断翻雕递印,由此产生了大量版本。各家翻刻时多有序跋述其刊刻原委。“书目答问刊印序跋”收录了8家11种序跋,包括潘霨的《书目答问序》、王秉恩的《书目答问跋》、李元度的《重刻輶轩语书目答问序》、舒龙甲的《书目答问笺补序》、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自序》、《上南皮张相国论目录学书》和《书目答问笺补凡例》、叶德辉的《书目答问斠补序》和《书目答问斠补后序》、柳诒徵的《书目答问补正序》、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跋》。这些序跋对于明了各家刊印《书目答问》之旨趣,以及该书之流布颇有助益。《书目答问》乃影响巨大之重要书籍,不少学者和藏书家常常把相关感想记在所得书上或所编书志中。“书目答问题识”收录了陈彰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叶德辉的《书目答问》题识十二则、秦更年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伦明的《书目答问》朱笔题识、孙人和的《书目答问》蓝笔题识二则、王伯祥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二则、袁行雲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二则、王秉恩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二则、潘景郑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罗惇的《书目答问笺补》墨笔题识、高熙曾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三则、来新夏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五则、刘明阳的《补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五则、邵瑞彭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这些题识虽然多为短札片语,但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刊有这些题识的《书目答问》大多珍藏在各大图书馆,故对于《书目答问》的研究当属不可多得之宝贵资料。“书目答问通检表三种”包括《书目答问所谓著述家之姓名、籍贯、学派、著述表》、《书目答问著录之书籍而作者未列著述家之书名表》、《书目答问未列著述家而著作著录于书目答问中之各家姓名、著述表》,系来先生1943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时,在其师余嘉锡的指点下,利用暑假编制而成,有点类似于课外作业,但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
《汇补》附录中有不少精到的考辨文字。如第1119页指出,清光绪二年四川初刻初印本《书目答问》四卷、清光绪二年四川修订重刻本《书目答问》四卷的行款字数相同,而其他版刻方面则完全不同,实为两个版本。二者相异之处如下:一、两个版本经部正文从第四行双行小字开始文字不同;二、两个版本的刊刻字体不同;三、两个版本的版框大小不同,初刻初印本大,修订重刻本小;四、卷端下书口所题刻工姓名不同,初刻初印本题“邹履和”,修订重刻本题“彭焕亭”。又如第1121页著录了清光绪四年吴县潘霨影刻本,认为此本与清光绪二年四川修订重刻本的行款字数、卷端下书口题“彭焕亭”刻工姓名,以及经部正文第四行双行小字始题“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均相同,当据以影刻。再如第1131页著录了民国十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增辑书目答问》四卷(题艺风老人辑),初学者仅看书名,容易产生此乃《书目答问》增补之作的误解。其实,此书行款字数及正文内容几与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相同,唯边栏不同。同时,附录还纠正了某些版本著录之讹,如该书第1120页著录了《书目答问》四卷有近年《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影印清光绪三年濠上书斋重刻本,指出:影印本卷首载《书目答问》提要云“此为光绪元年刻本”,当错。上述种种,显示出汇补者在版本目录学领域之深厚功底。
3 底本选择妥当
因当时条件所限,来先生之旧稿以民国二十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作为底本。清光绪五年王秉恩所刻的贵阳本(简称“贵阳本”),改正了光绪二年刻本多处误字而成较善之本,编者遂决定改用贵阳本作为《书目答问汇补》之底本。柴德赓曾经先后撰写了《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辅仁学志》第15卷第1-2合期,1947年12月;收入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和《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载《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收入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揭示了贵阳本的价值。柴氏曰:“《答问》由光绪五年王秉恩贵阳刻本,与原刻颇有异同,予尝校得二百八十余条,大率原刻本误而贵阳本是,范氏补正,殆未见此本。今观范氏所补正者,贵阳本每先有之,贵阳本所已正者,范氏或沿旧未改,则范书虽佳,贵阳本亦自有其价值。”[14]此外,吕幼樵在《〈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贵阳本的价值。但吕氏在文中得出的“王秉恩学术水平、目录学眼光,均超过范希曾”这一结论,尚可商榷。范氏未能见到贵阳本确实是一大遗憾,《书目答问补正》之所以出现多处沿袭旧本讹误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利用贵阳本。然而就总体而言,范氏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前人已多有指出,此不赘述。从《书目答问汇补》所收录的16位学者、藏书家的增补批校也可以看出来,范氏所补之内容最为丰富,除了订正原书之误外,既有大量增补,又有不少点评,应该说总体上最有价值。
该书之所以能成为精品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三位编者的精诚合作。来先生撰有《“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东方文化》2003年第6期;收入《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2006年)一文。从古至今,“文人相轻”固然十分普遍,但“文人相亲”亦代不乏人。该书可谓“文人相亲”之硕果,堪称典范。该书凝聚了来先生近七十年的心血。来先生学识博洽,德高望重,提携后进,自不待言。《书目答问》在来先生的学术道路上占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他曾满怀深情地说道:“四十多年读了一些书。如果有人问我何书最熟?答曰:《书目答问补正》;如果有人问我有何经验?答曰:《补正》当是治学起点。”[15]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来先生精通古典目录学,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中克服种种困难撰写了《古典目录学浅说》这一高质量的著作。此书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刊布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至今已重印多次,被全国多所大学选为教材或指导参考书,另外还被译为韩文出版[16]。笔者长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目录学”课程,即以此书作为教材。来先生在古典目录学领域的高深造诣以及对《书目答问》的烂熟于心,乃《汇补》取得成功之基础。另外,私藏古籍善本之富超过不少省级图书馆的韦力先生,很爽快地将自己“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纳入《书目答问汇补》,来先生颇为感动,喟然而叹曰:“韦力君,固今之刘杳也!”①刘杳(479-528),字士深,平原(今山东平原)人,撰有《古今四部书目》5卷,是一部传抄行世之稿本。当他获悉另一位学者阮孝绪(479-536)在编撰《七录》时,刘杳便将自己所搜集的资料全部赠给阮孝绪,从而助其编成中国古典目录学名著《七录》。韦氏之补内容较多,版本丰富,尤其是收录了不少和刻本。
从该书的“叙”和“后记”可以看出,李国庆先生对该书贡献颇大。当时来先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甚至以前自己在书上批注的那些墨笔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李先生利用整整五年的业余时间,通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将来先生“毛笔行楷,蝇头细字,上下勾画,左右移写,密布于字里行间与天头地脚处,几无隙地,形如乱麻,如入迷宫”之旧稿整理成符合出版要求之清稿,并增补了大量内容。来先生旧稿校文系录自叶德辉、刘明阳、高熙曾、李笠、吕思勉五家校本。李先生将校语逐条析出,打成文本,复置于《书目答问》原处。然后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八家校刊本,并将各家校语及按语依次置于《书目答问》相关条目之后。值得一提的是,李先生还从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了珍贵的《书目答问》之图录。再则,他还在《书目答问》原书卷末所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加了按语,其内容是在每位学者之下增补字号、籍贯、主要履历及著述等,使《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带有简明清代学术史之性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此外,李国庆还撰写了学术性很强的《书目答问汇补后记》,既显示出他在相关领域的深厚功底,又为该书锦上添花。
值得一提的是,李先生十分注重索引的编制。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他个人之作,还是主编之书,均附有实用性很强的高质量索引。该书也如此。他指导常虹、王永华二人编制了“综合索引”,可以迅速查检相关书名和人名,既方便了使用者,又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同时,从该书之“叙”还可以看出,天津图书馆常虹女士为该书作出了积极贡献。来先生在“叙”中感慨道:“数易其稿而常虹女士了无异言,汇补之成书,其功不可没。”笔者通过检索,发现常虹女士还专门撰写了《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答问〉版本叙录》(《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3期)一文,这样就为她的相关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②此外,南京图书馆藏有多种《书目答问》的不同版本。参见徐昕.南京图书馆藏《书目答问》版本述略.东南文化,2003(10):70-73。
当然,如果从求全责备的角度而言,笔者以为该书在某些方面尚有一些可以改进之处。首先,《书目答问》之初衷是针对初学者的,该书汇集了大量版本,如能在评语中对相关版本之优劣加以点评,应该对读者帮助更大①《汇补》第967页所收的范希曾对《书目答问·别录》之点评“此录所收书,今已不尽切用,买置当分别”,就对读者尤其是初学者颇有帮助。。此类评语可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该书第409页按语指出,清代汪中的《广陵通典》,《书目答问》初刻本作三十卷,贵阳本作十卷,江、范二本均作三十卷,《贩书偶记》作十卷。按语仅罗列各家著录,未加考辨。其实《广陵通典》乃未完稿,原来计划写三十卷,最终只完成了前面十卷,故并无三十卷本传世。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将清道光三年刻本《广陵通典》著录为三十卷(存十卷,卷一-十),也是不准确的。该书第675页的按语指出,《邹徵君遗书》八种中的“恒星图二幅”之书名应为“恒星图赤道南北二幅”。更确切的书名应当是“赤道南北恒星图二幅”,即《赤道南恒星图》和《赤道北恒星图》。
该书第620页按语指出,清代蒋光煦的《斠补隅录》十四种,江人度笺补本书名后题“二十四种”,《吴越春秋》题“十一叶”,《酉阳杂俎》题“十一叶”,均与底本不同。其实不仅是江人度笺补本,范氏补正本亦作二十四种。《斠补隅录》的版本源流并不复杂,最初无单行本,因收入蒋光煦所编的丛书《涉闻梓旧》而行世。《涉闻梓旧》有两个版本,其中清道光十七年海昌蒋氏别下斋刻咸丰元年海昌蒋氏宜年堂刻汇印本收书22种,不含《斠补隅录》;清道光咸丰间海昌蒋氏宜年堂刻咸丰六年重编本②另有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清海昌蒋氏刻本、民国初武林竹简斋影印清海昌蒋氏刻本,以及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据《涉闻梓旧》排印本(包括《后山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986年版《丛书集成新编》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收书25种(《斠补隅录》作1种计),《斠补隅录》包括14种书,其中的《后山集校》注曰嗣出,但最终未刊行,故《涉闻梓旧》本《斠补隅录》实际收书13种。《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未注明《后山集校》嗣出,不够准确。清光绪九年(1883)海宁蒋光煦别下斋单行本《斠补隅录》③另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别下斋刻本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影印别下斋刻本(收入《清人校勘史籍两种》)。,收书也是14种(包括《后山集校》)。因此笔者认为江人度笺补本书名后题“二十四种”,当为“十四种”之讹;《吴越春秋》题“十一叶”,《酉阳杂俎》题“十一叶”,当为“十二叶”之误。此外,《贩书偶记》作“《斠补隅录》十四卷”[17],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其中的宋徐天麟撰,清钱泰吉辑的《东汉会要》有四卷(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该书第697页的按语指出,严可均的《抱朴子内外篇校勘记》一卷、《佚文》一卷,范本作《抱朴子内篇校勘记》一卷、《佚文》一卷,《外篇校勘记》一卷、《佚文》一卷。据此则《校勘记》、《佚文》当是各二卷。笔者经过考证,觉得按语所云是正确的[18]。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之“抱朴子内外篇八卷”条下亦云:“严可均作校勘记二卷,内外篇各一卷。”[19]然而《书目答问》原文中所谓的此书有《四录堂类集》本则欠妥当。笔者认为,《四录堂类集》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指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三《答徐星伯同年书》(作于道光十四年腊月八日)所附的严氏撰、辑、校书目中的书,共计73种,1251卷,总称为《四录堂类集》。这些著述大多从未刊刻,仅有稿本,如笔者曾供职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原杭州大学图书馆)即藏有严氏所撰《说文注补抄》稿本。二是指清嘉庆道光间刻本《四录堂类集》五种,包括清嘉庆九年香山书院刻《唐石经校文》十卷、清嘉庆七年刻《说文声类》二卷④虽然《说文声类》卷首严可均“自序”撰写于嘉庆七年(1802)季夏,“后叙”作于是年九月,但《说文声类》的实际刊刻时间当为嘉庆九年(1802)四月。、清嘉庆二十三年孙氏冶城山馆刻《说文校议》十五卷(严可均、姚文田撰)、清嘉庆间刻本《铁桥诗悔》一卷、清道光十八年严氏四录堂刻《铁桥漫稿》十三卷。《四录堂类集》较为罕见,《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著录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20],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本被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5页)漏列《铁桥诗悔》。笔者发现,首都图书馆未收藏《铁桥诗悔》,有可能当时编纂时依据首都图书馆上报的卡片而漏列。同时,因《铁桥漫稿》系道光十八年所刊,故《中国丛书综录》将《四录堂类集》著录为“清嘉庆中刊本”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中国古籍总目》所著录的“清嘉庆道光间刻本”。再则,《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之“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第1010页)仅著录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有《四录堂类集》,漏列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之藏本。此外,既然首都图书馆藏本缺《铁桥诗悔》,《中国古籍总目》也应该注明⑤《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之“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以符号〇表示该馆藏本为全书,╳表示该馆藏本有残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著录[21]与《中国古籍总目》基本相同,只是《说文声类》著录为清嘉庆刻本。但《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将其分为两条著录:一、《四录堂类集》□种□□卷(清嘉庆九年自刻本),存三种十三卷,即《唐石经校文》十卷、《说文声类》二卷、《铁桥诗悔》一卷;二、《四录堂类集》□种□□卷,存三种三十八卷,即《唐石经校文》十卷(清嘉庆九年香山书院刻本)、《说文校议》十五卷(清嘉庆二十三年孙氏冶城山馆刻本)、《铁桥漫稿》十三卷(清道光十八年严氏四录堂刻本)[22]。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之著录与此相同。此外,杨明照所说的《抱朴子外篇校勘记》“严氏曾刻入《四录堂类集》”[23],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抱朴子内篇校勘记》和《抱朴子外篇校勘记》,附在清代继昌所刊的《抱朴子》书末;《抱朴子内篇佚文》和《抱朴子外篇佚文》,则被收入严可均所辑的《全晋文》卷一百十七而行世。
第630页秦瀛《小岘山人集》三十六卷条下,叶德辉批曰:“嘉庆二十三年世恩堂家刻本。”佚名氏批曰:“嘉庆二十年家刻本。”伦明批曰:“嘉庆二十四年世恩堂家刻本。”范希曾批曰:“《诗集》二十六卷,《文集》六卷,《续集》二卷。嘉庆二十二年家刻。”韦力批曰:“嘉庆五年刻本,嘉庆二十二年城西草堂刻道光补刻本,民国二十二年环溪草堂铅印本。”《汇补》之按语云:“各家著录刻年不一,孰是孰非,俟考。”《小岘山人集》的版本较为复杂,“孰是孰非”确实不易判断。笔者通过调查,认为范希曾和韦力所批符合实际。韦力批语中所提及的三个版本各不相同,嘉庆五年刻本仅有《诗集》和《文集》,尚无《续集》和《补遗》;嘉庆二十二年城西草堂刻道光补刻本为《小岘山人诗集》二十六卷、《文集》六卷、《文续集》二卷、《补遗》一卷;民国二十二年环溪草堂铅印本由秦瀛乡人侯学愈重加编次,将原有《文集》增加一卷,但不含《诗集》,即《小岘山人文集》七卷、《续集》二卷、《补遗》一卷。
第630页的按语指出,《折狱高抬贵手》又名《折狱龟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盖一书而异名者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法家类存目》著录。这条按语大体上依据《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的“是书《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盖一书而异名者也”[24]。其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折狱龟鉴》[25]。关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疏漏,余嘉锡已作了如下考辨:“《书录解题》卷七著录此书,实作《折狱龟鉴》。(《提要》亦因自《通考》转引,未检原书而误。)惟《郡斋读书志》卷八及《通考》卷二百三作《决狱龟鉴》耳。《玉海》卷六十七则二名并用,知实一书异名也。”[26]笔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之误是事实,但是否因转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而致误,则可商榷。《文献通考·经籍考》作《决狱龟鉴》二十卷,然后分别引晁志、陈录之文,其中引陈录之全文如下:“陈氏曰:克因和氏之书,分二十门推广之,凡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事,起郑子产迄本朝。”[27]从上述文字并不能断定《四库全书总目》系转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而致误。笔者认为有可能是《四库全书总目》成于众手,而撰写相关提要时又未复核原书等原因而造成的。再则,《四库全书总目》所谓的“是书《宋志》作二十卷”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艺文志》作“郑克《折狱龟鉴》三卷”,入史部刑法类[28]。百衲本《宋史》文字相同[29]。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曰:“《解题》(引者按:指《直斋书录解题》)同此。《读书后志》(引者按:指《郡斋读书志》)及《通考》(引者按:指《文献通考》)均作《决狱龟鉴》二十卷。《四库提要》云‘《宋志》作二十卷’,非。”[30]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具有崇高地位,使得“《宋志》作二十卷”以讹传讹,流布颇广。笔者注意到,刘俊文在《折狱龟鉴译注》之“前言”中有云:“《折狱龟鉴》的版本共有三个系统,一为宋原刊二十卷本,内分二十门,凡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事,见《宋史·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和《郡斋读书志》,今已失传。”[31]商丽杰的《〈折狱龟鉴〉初探》沿用其误[32]。到了《四库大辞典》,更进一步讹为“《汉志》作二十卷”[33]。此外,《折狱龟鉴》收入《四库全书》,并非入“存目”,估计是由于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第849页版框左侧的“法家类存目”(该页有5部书之提要,其中2部列入“存目”)几个字而致疏忽。
同时,该书作为一部集大成之作,如能将海内外关于《书目答问》的研究论著(含学位论文)目录作为附录之一,也很有价值。其次,上文已经指出,韦力的批校为该书增色不少,但笔者认为韦批中收录了一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复印本。这些复印本并无特殊意义,是否值得收录,尚可商榷。同时,韦力所补诸书版本,以得书先后为次,《汇补》仍其旧。这固然是一种处理方法,但韦力所补往往版本数量较多,大量不同时代的版本(含和刻本)混排在一起,有时也给读者带来不便。
另外,由于资料难以搜集以及一些校补之作篇幅过大等原因,一些颇有价值的校补之作该书未能收录,甚为遗憾!如王伯祥的《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刊行,而当时该书已出校样,再加上王补内容较多,故该书难以汇入。吕幼樵的《书目答问校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也因为篇幅较大而难以收入。余嘉锡先生的《书目答问》批校本则由于寻访未果而未收入。另外,台湾新兴书局1964年出版的《书目答问补正》,加入了该书局所影印之古籍,从而成为《书目答问补正》一种新的版本;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年影印了台静农过录(并略加补订)的柴德赓校贵阳本,即《校订书目答问补正》;乔衍琯的硕士学位论文为《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史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60年)①乔衍琯还撰有《书目答问概述》(载台湾《图书与图书馆》第2辑,1976年12月;收入乔衍琯《古籍整理自选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和《书目答问补正索引评介——兼论书目答问补正之续编》(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70年10月),颇有价值。。前两种乃半个世纪以前海峡彼岸之出版物,而最后一种则从未出版,即使在台湾也极难获取,该书未加收录,自在情理之中。再则,日本近现代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也对《书目答问》作过补正,可惜未留下原稿,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年)的《书目答问(史部)补正》乃根据其长子内藤乾吉所述而成文。笔者十余年前在日本任教时,曾认真拜读过,总体感觉还是很有价值的。还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刊行的《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中收有鲁毅点校整理的《书目答问》,脚注中有颇为详细的校勘记,总体质量较高。最后,该书在排版、校对方面亦偶有疏误之处。如第1133页的“孙仁和”应作“孙人和”,第1117页和第1219页的“袁行云”应作“袁行雲”,第1289页的“抱樸子”应作“抱朴子”,第1331页的“系”应作“係”。此外,第716-717页著录范氏补正中的“大兴刘廷献《广阳杂记》”之“刘廷献”(范氏补正原文如此)当为“刘献廷”。当然此乃求全责备,该书的总体校对质量是较高的,远胜于同年出版的另一部《书目答问》补订之作。
该书之性质有点类似于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和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不但嘉惠读者良多,而且必将大大推动《书目答问》的研究,堪称《书目答问》研究及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之著作。另外,我们欣喜地看到,徐扬杰的《书目答问补订》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5月刊布,几乎与《汇补》同时问世。孙文泱的《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也已于2011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似乎可以称为当代学术史上的“《书目答问》年”。《书目答问补订》以及上文提及的《书目答问校补》,重点在现当代版本之补,刚好与《汇补》互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德刚(1885-1962)从1926年开始对《书目答问》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中有不少疏漏之处,于是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博览群书数年,据《书目答问》所举要目逐步校对原本,进行订正补漏,名曰《书目答问订补》,1965年方始完稿,共计70余万字,引据版本不下万种。该遗稿已由刘氏后人初步整理完成,但因经费问题尚未出版。(参见刘采隼《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记〈书目答问〉其后的订补稿》,《图书馆》2004年第1期)同时,网上尚有署名毋苟先生笺疏的《书目答问笺疏》,共计20余万字。再则,张之洞的《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关系密切,司马朝军的《輶轩语详注》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刊行。当然,相对于《书目答问》的重要价值及其崇高学术地位而言,我们对于《书目答问》的关注和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以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而言,以《四库全书总目》为研究对象者比比皆是,考论《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书林清话》者亦有多篇,而笔者知晓的专论《书目答问》者仅有刘净净的《〈书目答问〉研究》(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因此《书目答问》的研究今后仍需加强,并且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19
2 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见: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0
3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成都:巴蜀书社,1991:11
4 同3:15
5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5
6 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见: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30
7 孟昭晋.王重民先生的《书目答问》课.图书情报工作,2000(2):90-93
8 王重民.冷庐文薮(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10
9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10 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87
11 同10:186
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317-318
13 同10
14 柴德赓.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见: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216
15 来新夏.我与《书目答问》.见: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1:5-6
16 来新夏.韩译《古典目录学浅说》序.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09(1):116-118
17 孙殿起.贩书偶记(附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76
18 徐德明.严可均著述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94-96
19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9:915
20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北京:中华书局,2009:1174
21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71
22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968
23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前言.见: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1:20
2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849
2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21
26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619
27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740
28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5144
29 脱脱.(百衲本)宋史.见:二十五史(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580
30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28
31 刘俊文.折狱龟鉴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
32 商丽杰.《折狱龟鉴》初探[硕士学位论文].湘潭:湘潭大学,2007:9
33 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