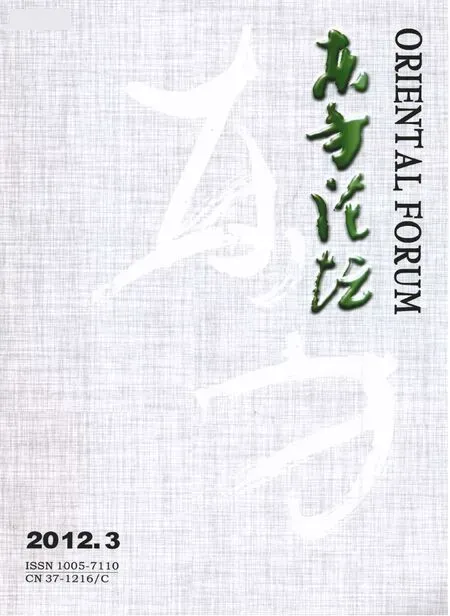卡夫卡《日记》及其“文学空间”
赵 山 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卡夫卡《日记》及其“文学空间”
赵 山 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卡夫卡的《日记》是进入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这与卡夫卡日记独特的综合形态密切相关。卡夫卡的日记具有“元日记”和“前日记”的特点,其“日记意识”与他的自我理解及对文学的理解不可分割。作为卡夫卡文学的“梯子”及“地面和墙壁”,日记与他的文学构成了不确定的二元关系。《日记》也可以看做一个“大而完整的故事”,在这一作品中卡夫卡对他的生活与文学的深层时空结构进行了揭示。
卡夫卡;《日记》;文学空间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莫里斯·布朗肖在其《文学空间》第三章第二节“卡夫卡与作品的要求”的第二段的开头写下“卡夫卡的情况令人困惑不解并且是复杂的”这句话之后,下了一个注:“下面章节中的引文几乎全部来自卡夫卡的《日记》全集……”这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的日记是进入“令人困惑不解并且是复杂”的卡夫卡及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在他看来,卡夫卡的日记“并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日记》,而是写作经历的活动本身——这是从卡夫卡赋予这个词的最贴近其起源和根本意义上讲的,《日记》应当从这个背景中去阅读和提问”。[1](P40)这话听起来像是卡夫卡在《日记》中说法的反响:“无论何时我对自己真正进行提问,总会得到某种回应,在我里面总会有某种东西燃烧起来……”[2](P12)《日记》既是卡夫卡向自己“提问”的记录,也是他“里面”的“某种东西”因被“提问”而燃烧起来成为“文学”的记录;也可以说,卡夫卡向自己提问的方式,按照卡夫卡赋予“提问”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卡夫卡后来在另一本“日记”即《八本八开笔记本》中写道:“我只是提问罢了。”[3](P90)),就是“写作”,并且首要地就是“日记写作”,卡夫卡的《日记》本身也因而成为一部特殊的卡夫卡式的“作品”。由这一作品可以牵出很多线头,对于理解他的作为“写作”之整体的“作品”的不同层面以及他的写作与作品的性质都是重要而有启发意义的。本文拟在考察卡夫卡日记形态的基础上,阐述卡夫卡的日记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背景中探讨进入卡夫卡《日记》的“文学空间”的路径。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及惯例,本文对卡夫卡日记文本的引述,仍依从布罗德的版本。
一、卡夫卡“日记”的形态
对卡夫卡赋予“日记”这个词的“最贴近其起源和根本意义”的理解,需要从卡夫卡日记的形态说起。据马克斯·布罗德在《卡夫卡日记·后记》(中文版全集日记卷未收入)以及理查德·格雷等人编辑的《卡夫卡百科全书》之“日记”词条可知:卡夫卡去世后,布罗德从卡夫卡死前留下的13本对开笔记本中选择了那些最像是日记的条目,编辑而成《卡夫卡日记》——只忽略了“由于其片段性特点而明显无意义的少量段落”和“太过隐私”及“卡夫卡必定不愿公开的对其他人的批评”的内容,[2](P489)先于1948和1949年分两卷出版英文译本(《卡夫卡日记:1910-1913》、《卡夫卡日记:1914-1923》),德文本稍晚,于1951年以《卡夫卡日记:1910-1923》为名出版。《百科全书》的编者认为,“布罗德的这个版本给人造成了卡夫卡确实写日记的印象,这只在部分意义上是对的”,因为“卡夫卡在自己的笔记写各种东西:速写或素描、书信的草稿、故事梗概等等,也在具体日期下写包含个人反思和一些我们会与‘日记’联系起来的东西”。[4](P264-265)后来也不断有人编辑不同形式的《卡夫卡日记》,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当然是1990年出版的由汉斯-戈尔德·科赫、米歇尔·穆勒与马尔科姆·帕斯雷等编辑、作为卡夫卡作品标准版组成部分的三卷本《卡夫卡日记》;据说,后者在权威性上已经取代马克斯·布罗德的版本。
围绕着卡夫卡日记版本展开的争论,其意义是让我们看到,在原初形态的卡夫卡的13本对开笔记本与后来经编辑而成各种版本的《卡夫卡日记》之间存在差异;但另一方面,过分地强调这一差异,其实也会掩盖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即卡夫卡是否“有意识地”或“知道”自己写的是“日记”?进而,我们应该按照卡夫卡理解“日记”的方式去解释他的日记还是应该按照对于“日记”的通常理解(即将“日记”看成有一系列成规所规定的“文类”)来解释他的日记?
翻开卡夫卡“日记”,可以发现大量对“日记”尤其是自己的“日记”的思考和评论。如:“一个不记日记的人,在日记面前会采取一种错误的态度”[2](P56);“写日记的人的一个优点在于:你对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的变易有着令你感到心安的清晰意识”[2](P145)。再比如:“我又读了旧日记”[2](P206);“从今天起抓住日记!定时地写!不放弃!即使不能得到精神与肉体上的拯救”[2](P180);“继续写日记变得十分必要了。我不稳定的脑袋,F.在办公室里精力的衰退,身体上的无能,这些都妨碍了写作,而内心却需要它”[2](P219);“稍稍浏览了这本日记,得到了一种如此生活结构的暗示”[2](P316)。可以看到,卡夫卡的“日记”具有“元日记”的特点,卡夫卡具有非常明确的“日记意识”,并且这一意识和他的“自我理解”(这一自我理解的动机构成了他写作包括文学在内的“作品”的基本动力)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基础上和更为基础性的层面上考察他的“日记”;也可以说,从他的日记出发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日记,比从一般意义上的日记出发考察他的日记更能深化我们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日记的理解。
就通常形态的日记和对日记的通常理解来说,鲁迅是个很好的例子。鲁迅写过日记体的小说《狂人日记》,也写日记,但他对日记形式的“文学”和作为一个文类的“日记”都颇不信任:“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意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他还说:“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的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5](P458)但并不存在“没有模样”的“真”,小说和日记都是在“做样子”,“模样不同”而已;不同的人其日记的“模样”不同——鲁迅认为自己的日记“写的都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因此就“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6](P179)但其实既在为自己“做样子”,也在为某种日记形式“做样子”。
从文学“模仿”的角度来说,“日记”之所以能够把模样“做”得比小说或其他文学样式“更真”,首先就在于日记所模仿的“模样”更“自然”,它所模仿的是日记作者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的“日子”。正如“一天”是人生的一个天然“单位”,一天的“日记”也是构成人生写作(life-writing)的一个天然“单位”。一方面,一天包括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一天的“日记”通常会包括一天的“活动”或“经历”以及对些活动和经历的“反思”;另一方面,写作日记这一“活动”常常会在晚上进行,在夜晚的写作活动中,日记作者会再度经历自我的“白天”和“黑夜”。看起来似乎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日记”对于一天的“回忆”对应着“人生”中构成一天的“黑夜”与“白天”——诞生在“黑夜”里的日记一方面以回忆的方式经历着或反思着自我的白天,另一方面在这种回忆和反思中也融合了在黑夜里浮现出来的更深层的那些经验。如果说,我们是在不断地“从经验中建构意义”,同时又不断地“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7](P293)那么,一篇日记就是这种双重运动的一个自然单位——以写日记这种“再度经历”的方式,日记作者在一个又一个的自然单位时间中整合起自我的“经历”和“反思”两个方面。粗略地说,这种“再度经历”的方式就是将白天的自我和黑夜的自我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也是自传作者为每一天的“自我”所做的“样子”。
从所有的写作都是在一个个“日子”中生产出来的这一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所有写作都是“日记”,而作为被他称之为“日记”的13本笔记及在此基础上由后人编辑整理的《日记》,则可以理解为对他这个人以及作为这个人的“文学性样子”的全部作品的一个“模型”。
二、日记:卡夫卡的“文学之梯”
就大多数写日记的作家而言,日记要么就是“文学”,要么与其“文学”有着一种内在的勾连,而卡夫卡的日记则综合了这两种情况,余华就说过:“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络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8](P96-97)①高玉教授很仔细地数过,《城堡》一共写了K在村庄一共“六天”时间的生活和经历。参高玉“论《城堡》时间的后现代性”,载《国外文学》2010年第1期,第84-90页。在1910年底的一则日记中卡夫卡写道:“我的内部液化(松动)了(目前还只是表面的),并将流溢(释放出)出存在于深层的东西。我内部的小小秩序开始形成,而我不也需要更多的东西了,因为对于天分不高的人来说,混乱就是最糟糕的事情。”[2](P33)此时的卡夫卡还没有创作出“像样的”文学,但这则颇有文学色彩的日记对于我们考察他后来写出文学的“样子”却很重要——他的文学就是“从内部”释放出来的“存在于深层的东西”,以及对于这种东西的“秩序化”。
卡夫卡日记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写作”。他的日记里每一页几乎都写下了关于写作的思考和写不出来他能够满意的东西的而产生的焦虑。日记里也有很多梦的记录,但即便在梦里,卡夫卡所梦到的大多也是写作;这显示出他的“日记”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1913年他梦到了一封重要的信,但看信的过程中他醒了,之后又“在清醒的意识里强制自己再入梦境,这种情况真的又展现出来了,我还很快地读了信上的两三行模糊不清的字,对于这些字我什么也没记住,同时在继续的梦境里也失去了这个梦”。[9](P272)
当然,日记就已经是写作,但他在日记里不断地谈到无法写作的焦虑,因此就显得日记写作还不是真正的写作;或许真正的写作就是他的“文学”或“小说”?但好像也不是。1917年,卡夫卡已经写出了《判决》、《变形记》、《在流刑营》、《乡村医生》等非常“像样的”作品,他日记中的看法则是:“我仍能从像《乡村医生》这类作品中感到稍纵即逝的满足,前提是我仍能写出此类作品(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但只有我能将世界提升到纯净、真实和永恒中我才会感到幸福。”[2](P386-387)可以认为,卡夫卡在写作中并没有得到这种意义上“幸福”,因此,以卡夫卡所设置的最高意义的写作标准,他所已经写出的东西实质上并没有差别;卡夫卡在“日记”与“写作”之间的区分只是“写作”内部的区分;二者的关系是内在的,理解了一个就能理解另一个,因此首要的是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1910年5月17日之前的一则日记里(在此日期之前,卡夫卡的《日记》没有日期,大约可称之为“日记之前的日记”或“前日记”),卡夫卡回忆了自己过去的一段生活:“在我五个月的生命里我没写任何东西”,他接着谈到“对自己说话”,但他又觉得总理解不了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我的状况并非不幸,也非幸福,不是冷漠,不是虚弱,不是疲惫,也不是其他的东西”。卡夫卡将这一状态与写作联系起来:“我对此的无知或许与我无能写作有关。尽管我不知道它的原因,我相信能理解后者。所有那些东西,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发生在我的思想里的东西,都不是从根基处、而是从半空中进入我的思想的。那么不妨让谁去试试抓住它们,让他去试着抓住、死死地抓住那刚开始从半空生长出来的那丛草。”[2](P12)
卡夫卡的写作所要抓住的就是这丛“从半空长出的草”(或许这就是他的“文学”的一个比喻性说法),为此他觉得必须学学那些日本杂技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攀爬,这梯子不是架在地上,而是支撑在一个半躺着的人高高抬起的脚掌上,这梯子不是靠在墙上,而只是悬升在半空。”[2](P12)他觉得只要自己每天能够用一个句子抓住一棵出现在半空中的“草”就够了:那个句子瞄准了它,就像“人们用望远镜瞄准彗星”;这个时候他就会感到登上了梯子的“最高一级”:
这架梯子是稳稳地立在地上的,依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子的地呀,什么样子的墙呀!不管怎么说,这架梯子却没有倒下,我的双脚就这样将它压在地面上,我的双脚就这样将它抵靠在墙上。
在这则日记中,卡夫卡使用了一系列比喻来解释自己的人生状态,但这些比喻构成了复杂的组合关系,仍需要进一步解释。要而言之,无法理解的人生状态需要用写作的无能来进行类比解释,但要进一步解释前者仍需要有能力写作;写作就相当于用句子瞄准出现在半空中的事物,这需要一架梯子……“写作”所用的梯子、梯子所立足的地面以及所依靠的墙已经就是一个文学比喻,这个文学比喻由于叠合了之前日本杂技艺人的表演的比喻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大体可以说:第一个比喻就是第二个比喻的“地面和墙壁”,第二个梯子建立在第一个梯子的基础上;进而,卡夫卡的“文学”是第二个梯子,而他的“日记”是第一个梯子,也是第二个梯子的“地面和墙壁”;“日记”既是卡夫卡的“文学之梯”,也是其“地面和墙壁”;他认为日记是他能抓住自己的“唯一地方”[2](P29),而小说则是“空中的表演”;但“什么样子的地面呀,什么样子的墙呀!”……说到底,日记也是空中表演。
粗略地看,卡夫卡的“日记”与“文学”构成了某种“不确定的二分组合”(indeterminate dyad),即“构成一对组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不能被简单地算作‘二’;相反,它们是整体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10](P3)卡夫卡的日记和文学都是其“写作”这一整体的部分。
要对卡夫卡的“日记”和“文学”进行区分,并不容易,但卡夫卡暗示甚至坚持这种区分,这倒是我们理解其“写作”和“人生”之间关系的一个线索。卡夫卡所写下的、在他看来尚不是“文学”的“日记”与他的“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大体就相当于“写作”与卡夫卡的“人生”之间的比例关系;卡夫卡要把“日记”与“文学”分离开来,就相当于他要把“文学性人生”(由他“写作”出来的“作品”为标志)从总体的“生活”中分离出来——他认为“文学”才是他真正的“生命”;与之相比,“生活”无关紧要: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命运很简单。我所具有的描绘自己内部那梦一般生活的天分将其他所有事情都推向了后台;我的生活可怕地缩小了,并且还将缩小下去。
卡夫卡对“日记”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复杂部分地源自他对“日记”可能对“文学”难以预计的影响的某种忧虑。1911年初的一则日记中,他写道:“这些天我没有写下多少关于我自己的东西,这部分地是因为懒惰(我白天睡得那么多那么沉,这期间我的身体重了很多),部分地也因为,我害怕暴露我的‘自我理解’。”[2](P35)他害怕在日记中暴露他的“自我理解”,这并不是说“自我理解”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恰恰相反,这种真正的自我理解需要在真正的“写作”即“文学”中被确定下来,这种写作必须包含“最大的完整性,所有的偶然后果以及全然的真实”。[2](P35)但这种任务“日记”难以完成。他担心,在日记中“写下来的东西”因为“有其自身的目的,也有已经被写下来的东西所具有的优先性”,因此就会取代那些“仍在被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如果这事发生的话,那真实的感觉就在其中消失了,此时再发现那些已经被写下东西的无意义,“就已经太晚了”[2](P35)。他1911年底的日记更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担忧”:
一个人在两个地洞前面等待着一种幻象的出现,它只可以从靠右的那个洞里出来。但这个洞正好是在一个模糊不清的盖子下面,而从左边的洞里一个幻象接着一个幻象升起,这些幻象企图把目光吸引到它们那里,最终毫不费力地用它们不断增长的身躯达到这个目的,这身躯最后甚至将真正的洞口遮盖住了,尽管人们十分想阻止这个行动。
这里的“两个地洞”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大致可以对应起他的“日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的是,随着卡夫卡文学天分的不断发展,他日记篇幅总体上却越来越短,这似乎也对应了他对“生活”的“不断缩小”的描述。从英译本来看,1910年的日记25页,1911年有124页,1912年55页,1913年36页,1914年74页,1915年31页,1916年18页,1917年17页,1918空缺,1919、1920年都只有1页,1921年6页,1922年25页,1923年不到半页。他对自己“日记”也大体经历了从依赖到“幻灭”,而经历这一过程的,还有他的“文学”……1923年六月,他留下的最后一则“日记”干脆对所有“写作”作出了“判决”:
我越写越感到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字词,都由幽灵之手扭结而成——手的这种扭结是其独特的姿态(模样),字词变成了变成了矛,反过来对准了写作者。……唯一的安慰或许是:不管你想还是不想,它都发生了。你所想的,没有帮助。比安慰更多的是:你也有武器。
也正是在这最后一则日记里,卡夫卡的“白天”与“黑夜”之间的结构塌陷成为一团混沌:“散步、黑夜、白天,无能为力,只有痛苦。”[2](P423)此时的卡夫卡或许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以“写下来的东西”(文学人生)来取代那些“仍在被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生活)的悲剧性,一年之后,他将因去世而不再有任何感觉;对于悲剧人物来说,“发现”总是“已经太晚”。
三、卡夫卡日记的“文学空间”
理解卡夫卡的《日记》,甚至比理解他的全部作品还要困难。用苏格拉底的一个比喻性说法,《日记》是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成的,[11](P51)这使其成为卡夫卡式“文学空间”的一个浓缩版;但对于读者,正如卡夫卡所言:“你也有武器”,这“武器”可能就存放在卡夫卡日记里面。在1911年的一则日记中他写道:“但愿我能够写大而完整的东西,它从开始到结束都被结构得很好,那么在结束时这个故事将不再从我这里离开,对我来说,平静地、睁大眼睛地、像一个健康故事的血亲听其被诵读就是可能的;但事实是:这个故事的每个小片段都像无家可归一样兜圈子,将我趋向与其相反的方向。——但是,要是这个解释正确的话,我仍能感到幸福。”[2](P105)也就是说,《日记》既象征着卡夫卡写出“大而完整的故事”的意愿,也是对他写作实际情形的展示和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正确的解释”;进而,无论《日记》是否一个“大而完整”的故事,使解释者感到幸福的“正确解释”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笔者将试着解读的努力局限于发现《日记》中的一些“大字”,这些字之所以显得大些,或因为重复的出现而显得对于这个“空间”有界定作用,或因为与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有密切联系而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的总体性质。
对于卡夫卡日记的“文学空间”的理解而言,观察者与这个空间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也令人困惑,“外”与“内”、“上”与“下”的空间-位置关系因观察的介入而得以成立,也因观察者的“观察冲动”而变得摇摆不定;正如“绝望总是超出自身”[2](P10),“观察”也总是被“观察冲动”所超出:“卡夫卡”总是被“走出卡夫卡的冲动”所超出,此类叙述在《日记》中比比皆是。仅以《日记》开篇为例。《日记》的第一个词就是“旁观者”——“Die Zuschauer/The onlookers”,完整的句子是:旁观者惊呆了,当火车快速开过。[2](P9);但“观察”总会“观察”到遗漏了某些东西——《日记》的第二个句子就是:“要是他永远地向我提问(frägt)。”这个“ä”从句子中滚出来,像一个球在草地上滚动。[2](P9)此时我们就会进入“在上面”的卡夫卡对于“在下面”的卡夫卡的“俯视”视角:“现在我淡漠地从上面看着他,就像看一场小小的游戏,关于这样的游戏一个人总是对自己说:即便我不能把球弄进洞里又有什么要紧呢,毕竟,这都是我的,这些玻璃杯,这些盒子,这些小球,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我能把它们统统收到我的口袋。”[2](P31-32)
如前所述,从“内部”解放出自己是卡夫卡写作的基本动力。这里的“空间”意义上的“内部”在“自然时间”的层面上所对应的就是“黑夜”,其灵魂状态的对应物就是“梦和睡眠”,也就是存在于卡夫卡“内部的巨大的不安”。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写作,卡夫卡想睡又不想睡:
我告诉自己,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安慰,我确实不止一次地压制过那存在于我内部的巨大的不安,但也不希望消灭它,我以前在此类情况下也经常这样做;相反,我希望在这种巨大不安最后的一次震撼中保持全然的清醒状态,这我还从未做过。或许以这种方式我才能发现隐藏在我内部的那种坚不可摧的东西。[2](P63)
卡夫卡要将自我的内部解放出来,为此不惜将自己的睡眠减少到极限,甚至进入一种“清醒地做梦”的状态。1911年的日记中写道:“无眠之夜。连续第三天了。我睡得很香,但一个小时后就醒来了,就好像我曾把脑袋放到了一个错误的洞穴中……我的确睡着了,与此同时生动的梦境使我保持清醒。可以说,我睡在我的旁边……”[2](P60)
卡夫卡睡在自己的旁边,这意象可以说是理解《乡村医生》的病人与医生关系的模型。以这样的方式,卡夫卡将自己的时间撕成最小的碎片,以便能够站在每一个碎片的外面“拯救/解放”自我的每一个碎片;但这只是意味着,为了将内部解放出来,他必须先占据一个外部的位置——内部里那些影像他能够模糊地感觉到,但还必须经过制作(做样子)才能看清楚。但或许他也搞不清楚的是,他所描绘的那些影像来自于哪里……卡夫卡的问题或许是:柏拉图洞穴中的影像所模仿的真正原型是来自洞穴外部还是隐藏更深的另一个洞穴?无论如何,可能的倒是,卡夫卡为了走出现实世界这个“洞穴”,就在这个洞穴下面另建了一个洞穴,按照他的说法是“我们在挖巴贝尔的竖井”[12](P237)。文学的制作没法改变灵魂的结构,灵魂的结构就是洞穴的结构,洞穴的结构也是身体的结构,理解洞穴,就是理解灵魂与身体的这种不确定的二元组合。卡夫卡要撕碎自己解放内部,无异于要摧毁洞穴的结构、分离身体与灵魂。
但分离身体与灵魂只有在“哈德斯”(Hades)这个洞穴里才能做到。卡夫卡制作“哈德斯”的方法就是对自己的灵魂实行“活体解剖”。1911年的一则日记里,卡夫卡谈到自己大脑经常的紧张:“它就像一种内部的腐败,这种腐败如果我只想观察而无视其令人不快的一面的话,其给我的印象就像是教科书上的大脑横切面,或者就像对活体进行的几乎无痛的解剖,手术刀——有点冷漠地、小心翼翼地停下又回来,有时静静地不动——剥开了那层比薄纸还要薄的、紧靠着还在工作着的那部分大脑的覆盖膜。”[2](P71)
从这里我们可以进入卡夫卡文学时间的“空间结构”。与身体化的灵魂之“活体解剖”相联系,卡夫卡写作的“恩典时刻”就是制作“文学空间”的时刻,这种时刻由一架“时间机器”或“时钟”所表征。1911年日记里,卡夫卡感受到了对某种时刻的渴望,预感到“那种正在迫近的某种伟大时刻就要来临的可能性”,“这一时刻能将我打开,能使我能做成任何事”,他进而想到法国大革命,想到一架“时间机器”——“我常常由此联想起巴黎,在被包围及其后的时代、直到巴黎公社时代的巴黎,在那些时候,对巴黎人来说还是异乡人的北方和东方郊区的人群在几个月长的时间里通过互相链接在一起的街道进入巴黎市中心,就像慢慢移动的钟表的指针。”[2](P61)1913年7月,已经写出了《失踪者》、《判决》、《变形记》等作品的卡夫卡在日记中描述了一架已经成型的“时间机器”:“内部存在的一组滑轮。某处一个小小杠杆秘密启动,起初几乎不能觉察,而后整个机器就运动起来。它屈从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像手表屈从于时间,它这里响一下,那里响一下,于是所有的链条都按照预先规定好的路径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叮当声。”[2](P225)但联系卡夫卡写作的实际情形,这一能够制造“恩典时刻”的“时间机器”的运行状况并非总是良好。1917年的日记中他表达了他能从作品中感到的“满足”,[2](P387)而这一时期所写的《乡村医生》描述的更像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机器”所报出的一次虚假的“恩典时刻”:“受骗了!受骗了!一旦听从了夜铃的一次虚假召唤——事情就永远没法弄好。”[13](P225)1922年卡夫卡写作了其重要作品《城堡》和《一条狗的探索》,但在这一年,他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精神崩溃,“时间机器”的状况令人堪忧。在日记中他详细记录了其内部进程的“疯狂节奏”:“钟表们并不能保持和谐;内部的那个以魔鬼般的疯狂速度运转,或者说这种速度是非人类所具有的,外部的那个以惯常的速度蹒跚而行。除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分裂之外还能够发生什么呢?它们确实分裂了,或至少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撞击在一起。”[2](P398)
和生活中的卡夫卡一样,日记中的卡夫卡拒绝自然的时间结构(日与夜),并且这种拒绝更为激进和彻底(在生活中他至少还有工作时间的自然节奏),他要根据自己的灵魂秩序重建“时间”。在对自然时间的无限分割过程中产生了对他的写作来说至关重要的“幻象”,但这种幻象仍无法逃避自然时间的“白天”(外)与“黑夜”(内)的结构——不知这是否就是他所说的那种“坚不可摧的东西”?
[1]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M].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Franz Kafka. Diaries[M]. Max Brod 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3] Franz Kafka, The Blue Octavo Notebooks[M]. Cambridge: Exact Change, 1991.
[4] Richard T. Gray, Ruth V. Gross, Rolf J. Goebel and Clayton Koelb. A Franz Kafka Encyclopedia[M], Greenwood Press, 2005.
[5]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A].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八)[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鲁迅.马上日记.豫序[A].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七)[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杨慧林.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建构”[A].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6辑[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8] 余华.卡夫卡和K[A].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9]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6)[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 萝娜·伯格编.走向古典诗学之路 [M].肖涧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1] 柏拉图.理想国[M].张竹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2]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5)[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3] Franz Kafka. The Complete Stories[M].Nahum N. Glatzer ed. Schocken Books, 1971.
责任编辑:冯济平
Franz Kafka’s Diaries and Its “Literary Space”
ZHAO Shan-k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Kafka’s Diaries is an important guide to his literary spac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diaries’ particularly comprehensive form. Kafka’s Diari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ta-diary” and “pre-diary”, and Kafka’s understanding of his diarie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self-consciousness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his literature. As the “ladder”, “ground and wall” of his literature, Kafka’s Diaries and literary works constitute an “indeterminate dyad”. The Diaries can also be read as a “large and whole story”, in which the deep space-time-structure of both Kafka’s life and his literature is revealed.
Franz Kafka; Diaries; literary space
I106
A
1005-7110(2012)03-0075-06
2012-01-06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卡夫卡的自传写作(日记与书信)研究”(编号:2011N160)阶段性成果。
赵山奎(1976-),男,山东莘县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