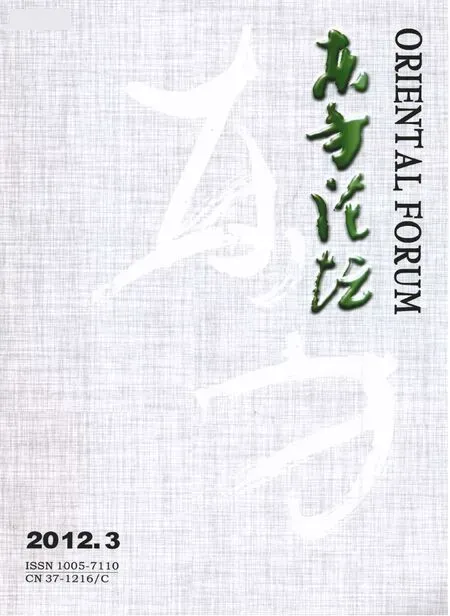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吴 忠 良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吴 忠 良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价值。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
傅斯年;东北史纲;李顿调查团;缪凤林;郑鹤声
关于傅斯年的治学风格,钱穆曾如是评价:“彼似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1](P168)对史家撰通史如是反感的傅斯年缘何会一反自己固有之主张去撰写通史性质的《东北史纲》?《东北史纲》的时代价值与学术价值如何?无疑很值得我们探讨。
一、背景
傅斯年在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函中言及:“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2](P103)其中所谓的“辽事”即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傅斯年称之为“沈阳之变”;关于东北史事的小册子即为《东北史纲》。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引语中阐述了写作动机:“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欲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3](P374)可见,日寇的入侵、国人“酣梦如故”是傅斯年邀集徐中舒、蒋廷黻等人编纂《东北史纲》的第一动机,即让国人从“酣梦”中醒来。
傅斯年编纂《东北史纲》的第二动机,是为了驳斥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说。其文中并未言及是日本哪位学者,据包瀚生、王汎森、李明诸位先生研究成果,傅斯年反驳的对象当为矢野仁一。矢野仁一(1872-1970),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曾任晚清学部进士馆教习,“中国非国论”的倡导者。1921年至1922年,矢野仁一连续发表《支那无国境论》、《西藏、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中国非国论》等文,后与另外一些文章结集为《近代支那论》,明确提出“中国不仅是没有国境,因没有国境的结果,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国家”,“云水缥缈地带的边疆的满洲·蒙古·西藏是假的国境,不是真的国境,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中国非放弃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域,则不能达成为国民国家和民族革命。”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对日本侵华分子发动战争具有很大影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大加赞扬,称“这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的立论,无可反论者也。”[4](P168)在此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构建了“满鲜学”或“满蒙学”,“可怜我国没有一个学者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5]。
正是在军事与学术双重侵略的情况下,在“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情怀感召下,傅斯年以急就章的形式,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东北史领域撰写了《东北史纲》卷首,其爱国之情不言而喻。
二、价值
因为傅斯年之作因时事而起,所以《东北史纲》不仅具有学术上之价值,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也恰是傅斯年所期望的。
面对日寇的入侵,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希望“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即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并电令出席国联理事会的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情况,请求主持公道。为了平息民众的抗日呼声,民国政府还特意发布了《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坦言:“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6](P373、375)国联最终决定派遣英国李顿爵士率调查团来华,以期能促进中日两国政府合力解决各项争议问题。1932年2月,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启程,2月29日到达日本东京,3月14日到上海,4月9日到北京,4月19日离开北京赴东北,6月5日回到北京。在李顿调查团在华进行调查活动期间,中国各界爱国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向调查团寄送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材料,其中就包括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对此,王汎森先生说:“《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心焦如焚下赶出来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说服国联李顿调查团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故出版不久随即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小册子送交调查团。”[7](P325)此说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是否是为了说服李顿调查团?显然不是。因为在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信中,傅斯年已经说了史语所同仁有撰写关于东北史事小册子的计划,而此时李顿调查团尚未成立,国联决议派出调查团是1931年12月10日之事;二为李济节译的《东北史纲》小册子是在《东北史纲》出版后不久吗?也不是。《东北史纲》出版于1932年10月,若李济此时节译肯定无助于李顿调查团采信中方证据了,因为1932年10月2日,国联在日内瓦、东京和南京三地同时公布了《李顿报告书》,所以,李济节译的只能是傅斯年已经完成了的《东北史纲》卷首,按照马亮宽先生的推测,《东北史纲》很可能于1932年1月完稿①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李顿的调查报告除绪言和附录外,共分十章。第一章:中国近年发展之述要;第二章:满洲之状况及其与中国其他部分及俄国之关系;第三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前中日关于满洲之争执;第四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满洲事变之叙述;第五章:上海;第六章:“满洲国”;第七章:日人之经济利益与华人之经济绝交;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第九章:解决之原则及条件;第十章:审查意见及对于行政院之意见。对此报告书,参与调查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报告书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日本一贯的扩张政策,以及为执行这种政策而长期准备的满洲军事行动计划。但是,总的看来,报告书受到中国报刊的欢迎。”[8](P58)换言之,李顿的调查报告在东北史事上的叙述看来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傅斯年对此也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其“叙说事实,如论‘九一八’之责任及满洲国之两事,与我们所见并无不同”[9](P39)。这其中傅斯年的《东北史纲》起了多大作用,很难评价,但影响了李顿调查团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作为傅斯年《东北史纲》的批驳对象矢野仁一在看到李顿的调查报告后,曾撰文《满洲为中国领土说之批判》、《满洲国之建国》加以反驳,其中就提及:“李顿爵士一行原未及见此以汉文著成之《东北史纲》,至未出版的第二卷以下四卷,亦未阅过,固无待论。然幸有李济君英文著成之《历史上之满洲》在,且此书可目为李顿爵士一行之见解之基础。”[10]就此点来说,《东北史纲》达到了傅斯年的预期目标,狠狠地反击了日人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论”。
《东北史纲》除了现实意义外,在学术上的价值也不容忽视。傅斯年预期中的《东北史纲》共分5卷,第一卷《古代之东北》 (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 (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 (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 (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执笔者皆一时之选。在《东北史纲·告白》中,曾提及“本书文稿及图稿皆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遗憾的是,最终出版的只有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从“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第二章为《燕秦汉与东北》、第三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第四章为《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第五章为《汉晋间东北之大事》,从神话、民族和考古发现等入手,证明古代东北居民与华北居民属于同一民族,且与中央政府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3](P375)。
此外,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引语”和“第一卷”中间插入了一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而非将之纳入“引语”或正文中来论述。傅斯年此种处理方式,可能大有深意。笔者揣测,傅斯年此意很可能是为了形成“东北史”的概念,与日本学者的“满蒙学”区别开来,并有与之相抗衡之意。其开首即言:“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明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3](P376)既然“满蒙学”中之“满洲”、“南满”等词毫无根据可言,“满蒙学”成为“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更甚之,“满蒙学”难以成其为“学”了。
事实上,傅斯年此书的完成,确实开辟了中国东北区域史研究之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学者对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视。因为“我国的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回顾我国,九一八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以后,则为了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做起文章来。”[5]此后对边疆史地研究重视的一个典型就是禹贡学会的创办,“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11]1936年4月起,禹贡学会还编辑出版了“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河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等具体的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禹贡学会的活动“在促成和发展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了突出的作用……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2]
再如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其编撰《东北通史》时,在“引言”部分回顾东北史研究时,特意提及:“近岁关于东北史之作,虽有多种,然能全部包举,为有系统之研究者,仅有东北史纲一书。惟是书于第一卷发行之后,迄未续出,无可依据。兹所述者,意在整理史料,藉以就正当世,姑以通史名之。终以率尔操觚,章创成编,亦可名为史稿,以为异日改修之地。沿用史纲之名,则未敢也。”[13](P3)金毓黻出版的《东北通史》上编6卷论述上古至元末的东北史事,与《东北史纲》原设计的一二卷范围一致,该书的立场亦与傅斯年相同,坚持东北之称,认为满洲一词非中国固有,称东北为满洲“为极无意义、极无根据者”[13](P13)。
关于傅斯年《东北史纲》的学术价值,其弟子陈槃认为:“这部书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以后,颇受人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办。批评的人从细微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人的,却不一定就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画出这样的轮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来做补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14]陈槃对《东北史纲》学术价值的评价大体允当,只是关于时人批评的申辩似有为其老师傅斯年鸣冤之意。那么,当时哪些人对《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是否中肯呢?
三、疏漏
当时对《东北史纲》提出批评的主要是郑鹤声和缪凤林,邵循正虽有批评,但主要是从正面立论,认为该书“重要结论颇多,有甚精审者,有材料未充者,间亦有可商者”,对傅著评价颇高[15]。
缪凤林在《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一文中,开首就对傅斯年所撰文章做了严厉批评,认为:“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也”,并从十个方面加以批评。
1、傅著对于中国内部移出东北之记载,但引箕子王朝鲜故事,“而于《吕氏春秋》、《史记》所载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由东北至中国及小司马索隐所引旧传殷汤封孤竹君事,绝口不道”。难道“由史公观之,箕子之往朝鲜,或尚不及夷,齐由孤竹东来之确实乎”?
2、箕子为《易传》中人物。然汉代新定郡县名,未闻取义《易传》者,则含资等郡县,或为箕氏朝鲜时所本有。先秦时代中国文化在朝鲜的影响,由此可知。“非若箕子封朝鲜之仅为汉人传说也,然傅君概未论列焉。”
3、傅斯年说“中国对四裔部落每多贱词,独于东夷称之曰仁”,于“仁”字字义之解释,不引证《说文》段玉裁注释,而仅据俗本所引毫不相干之“儿”字,以“儿”为“夷”之奇字。“今即谓俗本可从,然儿字与夷字何关。傅君凭空谓儿为夷之奇字,真令人有仰天而谈之感。”
4、傅著于第二章论《燕秦汉与东北关系》,不引《史记匈奴传》秦开破胡事,而反详释于第四章论东北部落种族时。不知“秦开之破东胡,则为燕国扩张疆域至东北朝鲜之关键”。“故谓东胡东迁夫余,句骊云云,不特史无佐证,且绝无踪迹可寻,要皆无征不信之谈。”
5、汉代于朝鲜文化,颇有发展,自日本灭朝鲜,八道古迹肆志搜访,汉世遗物,时有发见。如大同江南平壤府西南土城出土的“乐浪太守章”、“朝鲜右尉”等封泥和“乐浪礼官”瓦当等。其与历史最有关系者,一为汉孝文庙铜钟,一为秥蝉县神祠碑。“傅君仅知有十八年出版之貔子窝,稍前数年之出版品,了无所知。”
6、傅斯年认为,自汉武后数百年,东北太平无事,故史书不纪辽事;而临屯,真蕃及其他属县之罢废,为经济的政策,非昭帝以来疆土有所失。然稽之史策,则东北自汉武至桓灵间有三期祸乱,“昭帝时为第一期,王莽末光武初期为第二期,东汉中叶后为第三期。而二三期较第一期为尤烈”。盖“傅君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而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
7、东汉中叶后东北之边患,鲜卑犹愈于乌桓。傅斯年于乌桓犹别立一节,直录史文至千余言;于汉时鲜卑,则仅于论《慕容廆创业辽西》节中,略述三行,而于檀石槐之统治辽东二十余邑及国渊、管宁、邴原、王烈等为言东北史者所宜大书特书者,“则虽一字亦不著录焉”。
8、汉隋间东北与日本之关系,详见《南史》、《北史》中的《东夷传》等书,日本史书于此记述犹详。傅斯年则谓“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于正史记载史事,不见只字。
9、以东北包括辽吉黑三省之区域,而不论《晋书东夷传》之稗离等十国,录《北史》之《百济传》 《新罗传》而独遗其最重要之《高丽传》等。
10、傅著“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文义不明,句读不通,便肆解释,下断语,其欲免于纰缪缺漏,难矣。”
在批评之余,缪凤林也认识到傅斯年此文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为了驳斥日人“满蒙非中国领土”之妄说,所以他表示无限之同情和支持。但日本之研究东北史,远在二十年之前,当日俄战役结束,白鸟库吉氏已提倡对于东北朝鲜作学术上根本的研究,以为侵略东北及统治朝鲜之助。嗣后有白鸟等《满洲历史地理》,津田《朝鲜历史地理》,及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白鸟等之书,出版在二十年之前,虽亦间有缺误,而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实远不如《东北史纲》之多,此则吾人所认为史学界之不幸者也。吾民族今已与日人立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斗争之成功,必求全民族活动之任何方面皆能与日人之相当方面相抗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窃愿后之治东北史者,慎重立言。民族前途,学术荣誉,两利赖之。”[16]可见,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缪凤林希望处于抗战漩涡之中的中国学人,能够在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上压倒日本学人,以尽书生报国之职责。
郑鹤声撰写评论文章时正任职于国立编译馆,面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蒙非中国领土”妄说的盛传,“当即搜罗东北史料,从事编纂,藉以驳斥妄说,正其观听。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有编辑《东北史纲》之举,事属一体,因以作罢。”傅斯年编撰完成《东北史纲》第一卷初稿后,将之寄给郑鹤声,郑鹤声“拜读之余,良足欣慰”,因而撰《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一文。
与缪凤林开首即进行严厉批评不同,郑鹤声则给予傅著以较高评价,认为,“兹就傅君编著之第一卷论之,觉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求之于吾国学者著述之东北史书中,尚属少见,洵足以破日人之妄说,而感世人之兴会”。学术批评文章贵在批评,所以“优长之处,无俟赘说;关于疏漏舛误之处,则不可不加申述”。
郑鹤声从正名、补遗、纠误三方面对傅著加以评论。正名部分认为傅著各章,“名实颇有乖异,或内容不甚丰富”,有五大可议处:
1、第一章定名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然既叙殷末箕子之王朝鲜,而遗漏殷初孤竹国之封辽西,及伯夷叔齐之见西伯,则知有往而不知有来。
2、第二章专述燕王,秦将,卫满,汉武经营辽东故事,而名曰:“燕秦汉与东北”。 至于汉代,则仅举武帝平朝鲜一事,其他如王莽,光武,及安灵两帝时代经营辽东之事迹,则一概不书,似属遗漏。若重汉初事迹,则当名为“燕秦汉初与东北”,方副其实,否则本章即当包括叙述至汉末为止。
3、第三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第四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属部”,遽视之,仅以两汉魏晋为范围,而细按之,则并括南北朝事迹,则宜于两汉魏晋下加南北朝三字,方为符合,至其郡县虽兼包南北朝,属部则大抵至魏晋为止,则又为一缺点。
4、第五章专述曹操之征乌桓,公孙氏之据辽东等四事,则但名之曰“魏晋间东北之大事”可矣,而标名为“汉晋间东北之大事”。不知两汉对于东北之大事,果何在乎?其实,第二章既未暇述王莽,光武,安,灵间对于东北诸大事,移之此章,则不但无遗缺,且亦名实相符矣。
5、乌桓地当今热河一带,不属东北范围。本书于第四章叙述东北属部时既未提及《乌桓传》;而第五章忽叙曹操征乌桓一事,且别立一节,前后不相应,范围无所属。揆之情理,宜删去。
补遗部分认为傅著取材,以正史为骨干,其余则略供参考,其谨严之态度,未可厚非也。但因事起仓促,宜补充部分有七处:
1、第一章第四节“论殷商与东北”,除举玄鸟故事及亳之地望为证外,更及箕子王朝鲜故事,以为殷人东去之证。其实箕子之前尚有孤竹君。箕子与孤竹君东去,伯夷与叔齐西来,其间往来,交通甚密。加入孤竹君之事,是则殷与东北交通之殷繁可知。
2、辽东之开发,自殷以来,经若干先烈之努力,而后始渐臻文明之域,除箕子,孤竹君等外,其余诸先烈对于辽东疆域之展拓,政教之设施,稽之于史,亦班班可考。
3、东北属部自秦汉以后,与中国交通频繁,遣使朝贺诣阙献贡者,累朝不绝。谨恭之状,无改旧观。于此足见诸属部对于中国往还之频仍,关系之密切,理应钩稽《史记》《汉书》以下各史本纪列传及《东夷传》内关于朝贡事迹,列为大事表,以示属部之向化。
4、东北属部与中国交通既繁,耳濡目染,渐成华风,自政教文字,以及习俗所传,往往受我影响,亦足见我国声教之所暨。而傅著于各属部文化,虽亦略有论列,然仅叙述关于生活状态及习俗二项,至于政教文字,及中国文化传播之史迹,则略不道及。而其所据材料,又不出《后汉书》《魏志》所载,殊为缺憾。
5、傅著不但不能尽量应用各史本纪及列传中所载关于东北郡县属部之材料,即各史东夷传中关于东北属部之材料,亦多付阙如。东北属部及史料之被遗弃者,不知凡几。
6、就属部问题论之,傅著所谓东北,自括东三省全部,凡此三省内之各部,其已经与中国发生交通关系者,皆当归纳之。
7、傅著未能应用当地省县志,亦一憾事!而最近出土古器,可为史迹参证者,亦宜搜集。其余最近出土之燕明刀、汉孝文庙铜钟,秦戈等,对于燕、秦,汉初在辽东之史迹,皆足以资印证。
纠误部分主要是因为傅著各章“因排印校对不精,讹误之处,往往有之”而作。主要有纪年错误、引文脱漏和“将《汉书》正文,误以为《史记》正文等。
综观郑鹤声和缪凤林二人对傅著的批评,缪凤林所列的1、5、6、7、9、10诸点与郑鹤声相同。缪凤林在行文之际,对傅斯年之批评甚为激烈,几乎无一赞同之处①缪凤林的尖锐批评无疑刺痛了向以重史料、重考古文物著称的傅斯年。在傅斯年1933年自拟的著述计划表中,第四项即为“答缪凤林等评《东北史纲》”,可见,傅斯年对于缪凤林等人的批评甚为在意,可惜的是傅斯年并未成文。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缪凤林也曾写信给陈垣,说及傅斯年对于此事的反应。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8页。;而郑鹤声则认可其价值,并道出了他和缪凤林撰文批评的动机,谓“傅君等人之著《东北史纲》,实所以应付东北事变,不免有临渴掘井之嫌。然临渴掘井,犹胜于缘木求鱼,对于东北史实之研究,吾人自然当竭力赞扬介绍,即余撰评之原意也。然又不能不严加指摘,以期完善,此则赞虞之原意也。然平心而论,傅君之为此,虽属粗率,亦多可取之处。且以新法作东北史,此为第一部,自有其相当之贡献。惟傅君为吾国学术界上有地位之人物,而本书又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苟有纰缪,遗笑中外,总以力求美备为是”[17]
结语
日本学者对我国东北史的研究很早,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多为本国的侵略所服务。在矢野仁一的研究成果为日本军队侵略制造理论基础和九一八事变的双重冲击下,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并邀集同志拟完成全五卷的《东北史纲》,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从后面李顿调查报告的内容来看,傅斯年的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书生报国的理想也得到了实现。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关于东北史研究的现状,以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身上那浓浓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南北学派意气之争来评论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批评是不妥的①对缪凤林和郑鹤声的评论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文章有王汎森教授的《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和欧阳哲生教授《傅斯年全集·序言》二文中的相关论述,详见拙文《民国史学中的“南”“北”之争》,《聊城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因为这已经将双方的学术争论预设到了学衡派和北大新文化派以往的历史语境中去。此外,以民族主义的大帽来批评缪凤林也是不妥的,因为缪氏本人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依笔者之见,缪凤林和郑鹤声的评论文章主要应视为学术论争,而不应过度地从派别间争意气去理解。
[1]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7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4] 李明.日本知识人“中国论”的检证[A].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所.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冯家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J].禹贡半月刊,1934,(第1卷第10期).
[6] 赵朗.“九一八”全史[M]第五卷“资料编”上.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7]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4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0] 王仲廉.傅斯年等著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反响[J].图书评论,1934,(第2卷第8期).
[11] 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J].禹贡半月刊,1937,(第7卷第1、2、3合期).
[12] 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第1期).
[13] 金毓黻.东北通史[M].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
[14] 陈槃.怀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J].台湾:新时代,1963,(第3卷第3期).
[15] 邵循正.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N].大公报·文学副刊, 1933年5月1日,(第278期).
[16] 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J].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4,(第1卷第2期).
[17] 郑鹤声 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J].图书评论,1933,(第1卷第11期).
责任编辑:侯德彤
Fu Sinian and His Manchuria in History
WU Zho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Fu Sinian finished Volume One of Manchuria in History with his great love for our country, by saying, “What should I do in return for what I’ve got from my country?” This book fought back with historical facts against the Japanese statement that the two peoples Man and Meng did not belong to China and offered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by Li Dun’s investigating mission, having dual value in both politics and academics. However, written in a hurry, many parts of this book were criticized. For the sake of surpassing the Japanese academics, Zheng Hesheng and Miao Fenglin put forward some critical opinions.
Fu Sinian; Manchuria in History; Li Dun’s investigating mission; Zheng Hesheng; Miao Fenglin
K061
A
1005-7110-(2012)03-0007-06
2012-03-26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高学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2CZS001。
吴忠良(1977-),男,浙江富阳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