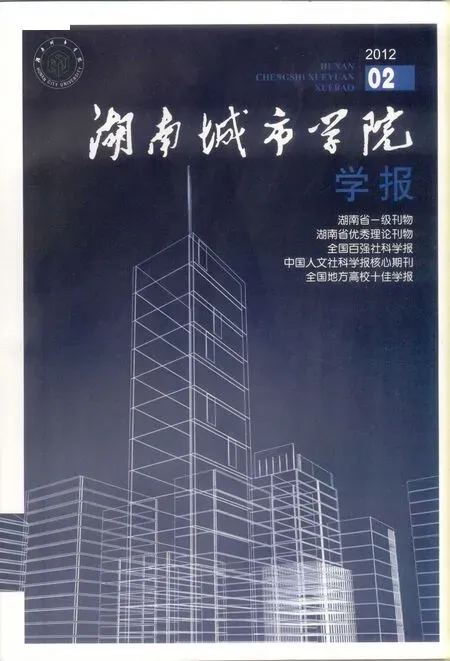城市扩张中的暴力拆迁之伦理思考
陈长里,鲍 莎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相伴而来的麻烦和问题也不少。由城市拆迁引发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重大恶性案件频繁发生。2003年,残疾居民翁彪因暴力拆迁而自焚,被称为抗暴力拆迁第一人;紧接着,2009年底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2010年9月江西省宜黄县钟如奎家3人自焚重伤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另据报道,“国家信访办 2003~2006 年的统计发现,在接待的上访者中,近40%的人涉及拆迁”等等。这些无疑刺痛了社会的神经,引起社会舆论的集体声讨。这些现象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权益,而且扭曲了政府的形象,制造着社会不稳定因素。
至于何谓暴力拆迁,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可以说它是强制拆迁的一种恶性升级。一般来说,暴力拆迁是指拆迁方通过种种暴力手段,例如断电、断水、恐吓、打人等来恐吓、威胁被拆迁人,逼其就范,甚至不惜与被拆迁方发生肢体冲突。为什么暴力拆迁这种恶习在当今文明社会屡禁不止?有人说是利益驱使,土地财政作怪;有人说是一场不均衡的“蚁象博弈”的必然。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更主要的、更内在的是拆迁双方的价值意识形态的冲突——价值与事实冲突。
一、事实与价值的分离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需依靠人去完成,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的价值理念、人对待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等。正如诺贝尔获奖者西蒙所讲:“每一项决策都包含着两种要素,分别成为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对管理来说,这些要素的区分具有根本意义。”[1]拆迁属于公共政策一种,也就必然涉及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事实属于客观实在,但并不是所有客观实在的都是事实。事实只有在被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掌握时它才成为事实,否则便不能成为事实。“事实并不是指未被认识的‘客观实在’的事实,而是被主体感觉到的经验事实。”[2]所谓价值,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大体可理解为是人类的各种所期望或者是满足需求的事物。价值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价值是以人为中心的,其存在是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反应了通过社会实践以人的视角所描述出来的世界,其相对于事实呈虚化状态。在某种程度讲,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是世界与人的关系,是世界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以及人自身超越。休谟率先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根据休谟的理论,事实表现为“实然”,价值表现为“应然”,两者之间处于不同领域,两者之间是相分离的,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事实不能推导出价值,不能从表述事实的语句推出表述价值的语句,即从“是”推导不出“应该”。1887年,威尔逊于《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行政主要关注的是事实,与价值无关,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是效率,主张通过发展和完善行政科学的方法来提高政府行为的效率。同时,威尔逊还认为,道德教育是培育个体道德行为的方式,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中的道德行为。在他眼中,作为科学的行政管理与作为价值的行政伦理是不可沟通的,公共行政人员的私德与公德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前,有些政府人员把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观念应用到在拆迁中,认为只要他们按照事实拆迁,就无可非议,根本不要考虑价值。在他们眼里,事实往往是指政府制定的关于拆迁的政策、规章制度、各种会议程序、手续以及行政效率等。城市拆迁“经济增长模式”成了他们首选价值判断,忽略了甚至抛弃城市拆迁应该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忽略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忽视了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等现代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1)拆迁政策理想与具体措施的冲突。我国现行制定拆迁政策的出发点是在宏观上确保社会发展、城市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体现公共利益取向,确保社会、城市的发展沿着科学有序、协调有效、持续快速的轨道前进,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体现。但往往因强调量化、追求效率而导致拆迁采取不当执行措施,如简单粗暴,武断专行;无视差异,千篇一律;政策宣传有失妥当;(2)拆迁者应有信念与实际利益冲突。从价值理性角度来讲,拆迁政策执行应以维护与实现最广大的公共利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它的根本宗旨和基本理念,这也是作为拆迁政策执行者的具体执行机构与执行人应有的信念。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拆迁政策执行者又有追求自身利益的一方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常附加一些对个人利益有利但原政策实际没有的内容,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实际的旗号,自立一套,自行其是,牟取私利,“搞土政策”,即政策执行扩大化。
对被拆迁方而言,价值主要是房屋对满足居民的客观需要和居民对原有房屋建筑的情感、原生活方式的眷恋以及公共利益的内在价值。多年来,居民对房屋产生了浓厚情感、对原生活方式的眷恋以及房屋的市场价值等都是他们的价值追求所在。因为房屋对于人们来说,不仅仅是生活居住的场所,更蕴含了丰富的生活情感,是人类灵魂的避风港湾。在我国乡村,人们对于房屋所寄予的情感尤为丰富,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深厚的乡村家园文化,村落共同体代表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同时也孕育了乡村伦理,塑造了乡村社会的人文价值。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被划入了城市化发展的范围,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舍和村落被拆迁,农民不得不离开自己有着丰富情感的老家而被动的过着城市化的生活,这也就是北京大学沈岿教授所提出的“家庭宅院模式”的城市化发展。所谓家庭宅院模式,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政府类似于家庭中的“家长”,拥有最终的决策与选择权利。这个模式所隐含的弊端,是容易造成家庭成员们的生活方式被单一地推进过去。也就是说,城市生活方式是人们被动的决定,比如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拥有纯天然的自然风景和清新美好的居住环境,相比城市的繁华,当地人们更愿意选择纯净的田园生活,完全不需要选择城市化的发展。而政府则通过各种宣传夸大城市化的好处并使用权力强行介入农民的生活,局面一旦失控便容易演变成暴力拆迁。这种权力滥用与强加的方式,如同一道枷锁戴在了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上,形成了一股城市化生活的“帝国主义”之风。
在拆迁中,政府、拆迁方往往过分强调事实,为了达到拆迁目的——效率和效益,采取一些极端手段也是在所难免的,从而忽视了拆迁根本目的——为了更多人生活更美好;而被拆迁方则偏执价值,把价值尺度当作超越历史、脱离现实的抽象目标,沉浸在以往生活情怀之中难以走出来,难以从城市建设大局出发,拒绝对城市发展实际进程和客观条件进行考察研究,结果导致双方矛盾加剧,进而演化为强制拆迁、暴力拆迁。
二、价值与事实共生——破解暴力拆迁的伦理展望
在古代与中世纪,价值与事实、发展真理论与发展价值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处于一种朴素自然的完整状态。近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发生断裂,现在愈演愈烈。尤其步入21世纪,这种僵硬的、分裂的思维方式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点,它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而且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对立,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暗示着另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诞生,于是共生理念应运而生。这种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城市建设房屋拆迁也不例外。为了保障拆迁工作正常顺利进行,应破除主客二分思维,坚持价值与事实、发展真理论与发展价值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生。
从词源上看,共生来源于希腊语symbiosis,Symbiosis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共栖”,尤其是指配偶双方共同生活一起,根据分工不同,完成各自任务,同时考虑到利害关联等原因,又必需加强协作。另一个是拉丁语 conviviality,Conviviality指虽然人们因价值目标、理想追求、文化背景、家庭出生等方面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双方各有利弊,能够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俗话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873年,德国真菌学家安东最早提出“共生”这个概念,原意是指不相同的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现象。接着,德巴里认为,“共生是不同名的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3]随着科学发展,科学家们发现,“共生”是大千世界普遍存在一种生物现象,它不仅广泛存在于植物之间,而且存在于动物之间,还存在于动物与植物之间。随后,人们进一步得出,这种“共生”行为还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把“共生”思想广泛应用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科学领域。
首先,拆迁中的事实与价值共生。在拆迁中,人们必需把握拆迁活动的两个尺度:对象的尺度与主体的尺度。拆迁的现实可选择性,主要不在于拆迁本身的技术可行性,技术的可行性只是提供一种客观前提与基础,关键在于其价值的合理性,它应当是真与善的统一。也就是说,既必需遵循拆迁政策、制度、程序等事实要素,同时又要考虑被拆迁人情感等,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活动,它无意识地适用于自然的状态:而人的活动则具有两个尺度,一个是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另一个是人自身的主体尺度。人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便使事实与价值得到了沟通。”[4]
其次,拆迁的发展真理论与发展价值论共生。发展真理论与古代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历史观不同,它反对以神或超越物来解释社会历史,而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以自然主义视角来考量社会历史,得出类似自然科学的结论和规律。19世纪以来,发展真理论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也就是说,在美丽的发展真理论的光环下,有其阴暗、龌龊的不足。受发展真理论影响,人类实践明显出现悖论: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等,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忽略人的精神层面发展,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迷失、精神失落,尤其是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危机。为此,上世纪6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等人对片面的发展真理观展开批判和反思,提出发展目的和出发点是人类自身,主张从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层次研究”,探讨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这种新发展观强调人的作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无疑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是它过于追求发展的功利性,过分挖掘人的自利性,导致人的欲望恶性膨胀,缺乏对自我价值审视与定位,造就了无数个“单面人”,加剧社会道德价值滑坡,出现没有礼义廉耻、颠倒是非的奇怪现象。对这种现象,不少西方学者展开研究,马克思对此更是深痛恶觉,加以深入调查、全面批判,并提出了新发展观,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关注人文情怀,主张将事实分析与价值评判在社会实践中统一起来,实施发展真理论与发展价值论的共生。因此,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之一——拆迁,也应以马克思的发展真理论与发展价值论的共生作为指导思想。拆迁是政府一项关系民生、社会发展的重要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重要发展活动,应坚持发展真理论与发展价值论的统一,不仅仅要提高经济效率,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更要把维护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拆迁评估内容上,要有长远的目标和战略的眼光,这要求不仅包含GDP,而且要有绿色GDP与人文GDP;在评估意识上,要有可持续发展思路,重视政绩成本、政绩道德,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次,拆迁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生。旧房改造,城市拆迁是党和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的利国利民的大事,是人的一种自主性的活动,一种自觉、自由的活动。也就是说,拆迁工作必需以理性作为指导思想,而人类理性又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个共同体。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保驾护航,提供方向指导,看护着人类的“心灵之命”;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坚实基础,不断满足和提升着人类的“肉身之爱”。没有价值理性作指导,工具理性会迷失方向,没有工具理性的现实支撑,价值理性就会成为雾中之花、水中之月,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紧密合作,才可能造就丰富多彩大千世界和人类栖身之地的精神花园。因此,在制定或实施拆迁政策时,必需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加以考量,使它们成为拆迁的指导原则。换句话来说,拆迁活动既是人的主体价值和创造性精神的活动,又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实践活动。
我们坚信,通过理性沟通和对话的方式,能够达到价值与事实、发展真理论与发展价值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内在地化解拆迁双方矛盾和分歧,预防、杜绝暴力拆迁事件。虽然似乎希望渺茫,但毕竟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人类社会恒久的法则。更何况,“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理性的吊诡”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现象,经过反复实践后,人类必然会选择事实与价值共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真理论与价值论共融的发展道路。
[1] [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杨砾, 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44.
[2] 王敏远.公法:第四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74.
[3] 林恩·马古利斯.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M].易凡, 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11.
[4] 李其瑞.法学研究与方法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