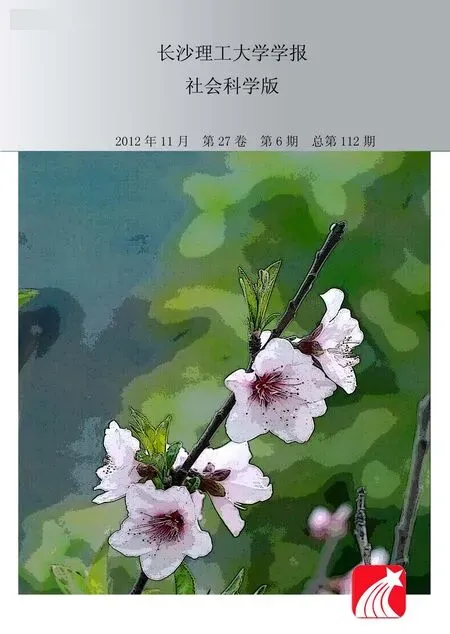论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
戴素芳,张家海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内在依据”。[1](P24)作为主体的人其本质在于将迎向自身的事物(包括自己)对象化,相对于外物,主体始终要求主动的地位,而不是被动地受制。这种主动性乃是主体内在的本质属性,主动意味着有目的的行为,被动则会摧毁目的。对主体来说将被动转变为主动的需要是不灭的,主动是本质的,被动是从属的。主体由其欲望所推动,对主体而言,若说主动是快乐的源泉,那么被动就是痛苦的根源。然而单单听命于欲望并不能体现主体的主动性,也许恰恰会陷入被动的处境。主客是互存的,我们的活动也时刻处于主动与被动之间,因此快乐与痛苦也总伴随着我们。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必须把伴随着活动的快乐与痛苦看作是品质的表征”,[2](P39)而“德性是与快乐和痛苦相关的、产生最好活动的品质”。[2](P40)所谓品质,亚氏说“我指的是我们同这些感情的好的或坏的关系”,[2](P44)或说“基于品质,我们才对这些情感处于一种好的或坏的关系”。[3](P254)不论是感情还是情感,亚氏所指的都是伴随着快乐与痛苦的各种情绪或心理状态。据此我们可以将德性规定为:德性是我们或好或坏地处理我们自身与我们的情感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品质。亚氏说“德性的目的是高尚”,[3](P267)所谓处理得好就是要遵循高尚的目的行事,反之,出于卑贱的目的行事就是处理得坏。我们的情感由心灵、肉体和外物三者的交互作用所产生。所以有的情感是积极的,带来主动的心理倾向;有的情感是消极的,导致被动的心理倾向。我们应当希求并培养善于变被动为主动的心灵,这样才符合我们的本性。而有利于我们存续的情感,是在冷静地处理欲望与外物对我们的影响中形成的。我们应该考察我们的情感以及导致情感的原因,而不是盲目地听命于我们的情感。这种考察的意向——也即将自己的情感视为认识和变革的对象的能力——正是主动性的直接表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品质的好坏取决于主动性(主体性)是否得到好的、恰当的发挥。据上,我们将从主体和情感的角度出发对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勇敢予以探讨。
一、勇敢的性质
我们的心灵善于将一切迎向我的事物对象化,当事物成为了我们的对象(不管是被给予的,还是主动选择的),我们便会在其发展中对其进行考察,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状况的把握,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的心理状态。比如在令人恐惧的危境中,勇敢的人会在沉着中尽快地进入对对象进行把握和分析的状态从而设法克服恐惧和危险;而怯懦的人则会惊慌失措,并没有意识将迎来的事物对象化,甚至会恐惧地失去对事物进行考察和预期的能力;鲁莽的人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计后果地向危险冲去。
勇敢与怯懦和鲁莽密切相关,亚氏也正是从三者的联系入手对勇敢展开论述的,总的来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主要给勇敢作了三种规定。首先从情感的角度出发,他说:“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2](P77)恐惧和信心是指人们在危境中的情感。所谓恐惧,他说“人们有时把恐惧规定为对可怕事物的预感”,[2](P77)而他实际要说的是,恐惧是对可怕事物的可怕体会,这种循环式的规定是不恰当的。从主体性出发,我们认为恐惧乃是主体面临外物时,受外物的影响(这往往出于自我对外物的无知)导致自我主动意识(对象意识)的突然丧失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强烈的恐惧会导致整个生理机能和精神的无力。关于信心,亚氏说:“一个对事物抱有希望的人自然就有信心。”[2](P81)希望在根本上是和主体性相一致的,某种意义上说,希望是对未来自我的内在肯定。所以我们认为信心乃是主体对其主动性和目的能够得以发挥和实现的心理上的肯定,怀有信心的人对自我和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抱有坚定的期望。
亚氏说“在信心上过度的人是鲁莽的”[2](P81),“在恐惧上过度的人是怯懦的”,[2](P81)“怯懦的人同时也在信心上不及”。[2](P81)据此,亚氏的论说从恐惧和信心转到怯懦和鲁莽,从情感的角度转到德性的角度,于是我们得到勇敢的第二个规定:勇敢是怯懦和鲁莽的中道。亚氏并没有直接这么说,然而这正是他所要表明的。怯懦的人承受着过多的没必要的恐惧,这往往出于他对事情的危险(困难、复杂)程度的过高估计,以及对自己能力的过低估计;鲁莽的人无视危险而盲目自信,这是一种缺乏自我省察或缺乏对事物加以考察的精神而导致的盲目行事的心理。在危境中,怯懦的人受恐惧情绪的宰制,于是其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主动性受到压制,从而向危险低头;鲁莽的人则受信心的盲目激励,于是其主体地位得以加强,主动性受到鼓舞,以致不计后果地向危险冲去。需要指出的是,亚氏是在危险情境的前提下对勇敢展开论述的,因此信心的过度才是鲁莽,而不是自大或者狂妄。另外这个危险必须是与行为者的某种目的相关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危险。从主体性出发也能得出亚氏所说的,与鲁莽相比,怯懦与勇敢更加相反的结论。[2](P54)纵然是盲目自信,鲁莽者也同勇者一样发挥了主动性,只是一个发挥的坏,一个发挥的好罢了,而怯懦者则完全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与勇敢更为相对的是怯懦,而不是鲁莽,怯懦的人也更加遭人谴责。虽说怯懦是勇敢的不及,但鲁莽并非勇敢的过度。“鲁莽与勇敢的程度无关,而与勇敢是否含有智慧有关:鲁莽是不智之勇……是得不偿失的勇敢”。[4](P548)
怯懦的人和鲁莽的人都受不经考察的情感的宰制,致使主体性都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怯懦的人由于恐惧而逃避一切危险,鲁莽的人则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硬碰,勇敢的人则扬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亚氏说:“勇敢的人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得住所该经受的,也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2](P80)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视为他对勇敢的第三个规定。这是一个从目的论出发的循环规定,所谓“该承受的”、“该怕的事物”的“该”,即指目的性或应然性;所谓“出于适当的原因”即是出于高尚的目的;该接受的、该怕的事物也是由高尚的目的所规定的,正如亚氏所说:“在实践中,目的就是始点”;[2](P212)这里,适当的方式即是出于高尚目的的无畏,适当的时间即在高尚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危境中。然而勇者也应当有所畏惧,这种畏惧并不是外因所导致的惧怕,而是出于内因的主动的选择,按亚氏的观点,勇者的畏惧是出于逻各斯的对高贵的希求,它有时表现为一种尊重和服从。比如,对法律所禁止的事情的“畏惧”。因此,怯懦是畏惧,但畏惧并不一定是怯懦;同样,勇敢是无畏,但无畏不一定是勇敢,鲁莽的人就表现得无畏。[2](P78)另外,勇敢与否也不在于承受危险的程度大小而在于承受危险的方式是否符合高尚的目的。[2](P80)
我们看到,在亚氏对勇敢的三个规定中都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与适度相对的过度与不及显然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追求适度。亚氏说:“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中,这种适度是由逻各斯规定的,就是像一个明智的人会做的那样地确定的。”[2](P47-48)这个“适度”源于情感与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2](P47)而把握它则要靠逻各斯。亚氏又认为逻各斯和明智只与手段,而不与目的相关,选择也是针对手段而不是针对目的的,[2](P66)因此适度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恰当的方式而存在的。然而亚氏说:“德性是一种适度,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2](P47)那么这个“德性”若从适度来说就只能从手段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然而这恰恰有悖于亚氏的主要意思。他说“明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着我们的活动,德性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明智则使我们采取实现那个目的正确的手段”,[2](P187)“道德德性是明智的起点,明智则使得道德德性正确”[2](P308);又说“德性的目的是高尚……设计高尚的目的完全是德性的任务”。[3](P267)如此看来,德性关乎目的,所谓“正确”即是高尚;明智关乎手段,“正确”即在于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可以说亚氏所言的德性指向主观目的,指向善,它是对应然的把握;明智指向客观事物,指向真,它是对必然的认识。适度通过明智来把握,这没有问题,然而事先若不出于高尚的目的,这适度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勇敢的人自然就有高尚的目的,然而对怯懦或鲁莽的人来说,又如何获得或树立高尚的目的呢?获得坚定而高尚的目的是怯懦和鲁莽走向勇敢的首要条件,没有好的目的,明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亚氏一再说逻各斯和明智只与手段相关,然而在确定善的根据时,亚里士多德最终引入了真的尺度,[2](P71)而“真”正是靠着逻各斯来把握的。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那么真既然给我们指明了善,也就为我们指出了目的。所以在亚氏那里逻各斯并不是完全不参与目的的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亚氏那里,必然与应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关于目的如何形成和获得并不是我们的主题,在这里我们也不追问怯懦的人和鲁莽的人如何获得高尚的目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这种追求高尚目的的意识是判断一个人品质优劣的关键,这也是亚氏所强调的。他说:“选择显然与德性有最紧密的关系,并且比行为更能判断一个人的品质。”[2](P64-65)也即是说,选择比行为本身更能表明一个人的德性优劣,这就说明,这个选择不是在手段的意义上,而是在目的的意义上作为德性的表征的。亚氏在《优台谟伦理学》中说:“从一个人的选择中,我们就能判断其性质,当然是从他的行为所为了的目的中,而不是他的行为本身中。”显然选择由目的所规定,它是目的的直接表达,因此目的先于选择,也先于适度。当然亚氏并不是说出于好的目的的一切行为都能得到辩护,从勇敢这一德性来说,他要告诉我们:唯有以强烈而高尚的目的意识为前提,选择和适度才能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逻各斯才能得到好的发挥。
我们所要指出的是,选择出于目的,而目的也即主体对应然性的直接诉求,同时又是主体力量得以发挥和实现的起点,主体力量的发挥和实现是目的的完成,也是人的自由之表现。勇者在任何危险的处境中都会捍卫主体这一最根本的特性。强烈的主体意识是勇敢的真正来源,勇者不必有主体性的概念,真正的勇者受着崇高感的激励,而崇高感本身就是主体要求自我确证的心理体验。这种要求也可能不是自觉的,而勇者顽强、无畏的生命力正是它最直接、最真实的体现,一切危险和恐惧在勇者面前都成了被超越的对象。在危险中,勇者以他的崇高、无畏和智慧捍卫和彰显了我们作为自觉的目的性存在和作为自由的应然性存在之地位,这就是勇敢最根本的性质。对目的性、应然性的维护,即是对人格自觉、自由的维护,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也正在于此。
二、五种“勇敢”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完勇敢的性质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第八章对其他五种勇敢做了详细的探讨,在亚氏看来这五种勇敢都不是真正的勇敢,对它们做一些分析是有益的。
首先是公民的勇敢,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他律的勇敢。这种勇敢出于羞耻心、荣誉和恐惧,因此亚氏说它最像是真的勇敢。[2](P82)他指出,不勇敢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勇敢则会赢得荣誉和奖赏,而之所以恐惧是怕招来法律的惩罚。亚氏认为出于羞耻心和荣誉感的勇敢要比出于免于惩罚的勇敢高一等,因为后者“想躲避的不是耻辱而是痛苦”。[2](P83)他并没有对出于羞耻心和荣誉感的勇敢加以比较,也许亚氏更推崇出于羞耻心的勇敢,因为羞耻心容易使做出勇敢行为的外因转化为内因,而对荣誉和奖赏的欲求,以及对惩罚的逃避则更多是出于外因。
其次是出于经验的勇敢。亚里士多德以职业士兵为例,说明他们因为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战场上表现得善于识别伪诈,作战沉着、攻防有素,因而被称为勇敢。其实这种勇敢是一种沉稳老练的处事态度,虽然它不是真正的勇敢,但老练的人因丰富的经验而得到智慧的积累,智慧则给他们带来信心,由于丰富的经验和信心,那么他们成功的几率就会增大,而每次成功都会增添信心,这就有助于塑造坚强自信的性格,因而经验丰富的人就容易变成真正勇敢的人。但对职业士兵来说,他们不是为了荣誉,更不是为了高尚而参战,他们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金钱利益,因而丰富的经验只是他们牟利的筹码,他们的目的决定了他们不会像公民士兵一样为荣誉而战。
第三是出于怒气的勇敢。亚氏说:“勇敢的人都具有一种怒气。怒气首先就是冲向危险的热情。”[2](P84-85)怒气一般都是由外界激发的,一个人被无端招惹时,或者受到不公的待遇时就会发怒。适当的怒气应当出于公正的报复心理,单纯听命于怒气的唆使,无异于被激怒的野兽。恰当的怒气有利于培养勇敢的心灵,怯懦的人往往不会或不敢在适当的情况下发怒,只会将怒气憋在心里;勇敢的人在适当的情况下发怒;鲁莽的人受到任何在他看来不公的待遇都容易动怒。
第四种勇敢是一种乐观。亚氏所谓的乐观源于有利的外因,有利的外因一旦消失,乐观就可能转变成悲观,甚至是恐惧。在亚氏那里出于对危境的理性把握和预期而表现的乐观和勇敢也得不到推崇,他说:“面对突发的危险表现出无畏和不受纷扰似乎比在所预见的危险面前的此种表现更勇敢,……面对已预见到的危险而如此表现,可以是出于推断和逻各斯的,而面对突发的危险如此表现则必定是出于品质的。”[2](P86)照这种说法,极而言之就只有天生的勇敢才算是勇敢了。而乐观正是出于对事物发展的美好预期,也可能是出于对外界和自我的充分接受而带来的心灵的宁静。若不是完全出于合理的对事情发展的逻辑的推断,乐观就类似于侥幸心理,只是乐观的人比侥幸的人更坚定,特别是在危境中。乐观可以是一种处世态度,而说勇敢类似于乐观或悲观是一种处世态度就有些不妥。另外明知道事情的结果是不好的,而仍然保持一种冷静与镇定,则是乐天、达观,相对于绝望的心理,这乃是乐观的升华。
最后是出于无知而敢于行为的表现被误认为是勇敢。无知对人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影响,若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无知,那么这种无知就总是危险的,我们越是因为无知而敢于行动,就越可能陷入消极的困境。正如亚氏所举的例子,由于阿尔戈斯人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斯巴达人,当他们向斯巴达人冲去就无异于送死,因为斯巴达人是最善战的。[2](P86)
三、勇敢、快乐和痛苦
亚氏说“对快乐与痛苦运用的好就使一个人成为好人,运用的不好就使一个人成为坏人”,[2](P41)又说“德性在情感中,情感在痛苦和快乐中”。[3](P315)德性反映了我们处理情感的能力,同样也反映了我们处理快乐与痛苦的能力。快乐与痛苦是天然的奖赏与惩罚,不能感受快乐与痛苦显然是灾难性的,离开了它们我们将无法存活。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快乐与痛苦给我们指明了目的,它们参与了目的的形成。亚氏说:“我们或多或少都以快乐和痛苦为衡量我们行为的标准,……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感到快乐和痛苦对行为至关重要。”[2](P41)由于勇敢与危险密切相关,那么相对于信心和快乐,与勇敢这一系列德性(勇敢、怯懦和鲁莽)关系更为密切的就是恐惧与痛苦。亚氏指出:“对懦夫而言,把不惊恐的认作了惊恐,把轻微的认作了猛烈的;而对于莽汉,情形刚好相反,把惊恐的认作安全,把猛烈的当作轻微。勇者的认识最符合实际。”[3](P390)不管危险是突发的,还是可预见的,勇敢的人都试图以恰当的方式去面对,对勇者来说,镇定和坚忍取代了恐惧和痛苦。亚氏说:“仅当一个人快乐地,至少是没有痛苦地面对可怕的事物,他才是勇敢的,相反,如果他这样做带着痛苦,他就是怯懦的。”[2](P39)并不是说勇敢的人感受不到痛苦,他是置痛苦于不顾,心甘情愿地接受危险的挑战。而怯懦的人往往会逃避一切危险,甚至是束手待毙,即使是他可以战胜的危险,他也深感恐惧。怯懦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作出较低的估计,或者事先就预感到失败。由于挫败感总是先于行动,怯懦的人就过多地承担了没有必要的痛苦,甚至会因此陷于自感无能的痛苦之中。
怯懦压抑着欲望,怯懦的人承受着恐惧之痛,同时也承受着怯懦本身带来的痛苦。怯懦的人性格敏感,一般不会无知到不知道自己的怯懦;而鲁莽的人则性格粗犷,其感受力也较为粗糙。所以在事先,鲁莽的人对痛苦和快乐的体会显得迟钝,他更多的是受盲目的激情,而不是苦乐的驱使。在事后,鲁莽的人若遭到了挫败,或者在认识到真正的危险后在半路中选择了逃避,那么他体会到的痛苦就是无能和耻辱,因为无能是莽夫所不能容忍的,别人的耻笑更是奇耻大辱;若他战胜了危险,那么他体会到的快乐就是得意,而这会助长他的鲁莽。在某种意义上,怯懦的人在事先就做了痛苦的奴隶,若他一旦战胜了危险,他体会到的快乐就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鲁莽的人往往是欲做危险的主人而不得,甚或相反;勇敢的人则始终是危险的主人,亦是快乐和痛苦的主人。
勇者抵抗危险的能力会随着每次的胜利而不断增强,他的主体地位也会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张;而怯懦的人会随着他每次的退却而逐渐削弱,这样他的主体性就被限制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危险中,勇敢的人看到的是希望,是事实向好的一面发展的可能,相反怯懦的人看到的是绝望和无力,对他来说,对痛苦的逃避就是对希望的放弃。亚氏说:“人最强烈的本能就是躲避痛苦和追求快乐。”[2](P237)躲避痛苦本身是积极性的表现,但若以不当的方式躲避,那么我们就会承受双重的痛苦。怯懦的人正是这样,他总是用消极的方式面对痛苦,用无用的痛苦来应对痛苦。若怯懦的人自知其怯懦而不能改变,那么痛苦就会时刻伴随他,他就会形成懦弱的性格,如此以来他的痛苦就不是出于外因,而是出于内因,而“痛苦遏制和毁灭一个人的本性”,[2](P93)因此怯懦最坏的倾向无异于自我毁灭,正如亚氏所印证的“卑贱者一旦被劳苦压跨,就爱恋死亡”。[3](P390)
勇敢也带来“毁灭”,但这是不朽的、再生的毁灭,也即是人最可贵的牺牲精神。勇敢的人是最善于发挥主动性的人,因此勇敢也最有利于我们的本性的发展。勇者出于高尚的目的去回应危险和痛苦的考验,他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快乐,而战胜危险和痛苦乃是主体力量的确证,是对自我的肯定,因此是快乐的,毋宁说是最根本的快乐。正如亚氏所说“快乐产生于我们对自己力量的运用”,[2](P219)人在勇敢的行为中体认到自己的力量,主体性便在主体力量的运用中得到确证。勇者在任何时候都彰显着人的主体性,在死亡面前也不例外。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死亡,而勇者则会以死赴义来捍卫主体人格的不朽。勇者也不会白死,他会激励后来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因此亚氏说勇者“在德性上最完善,他所得到的幸福也欲充足,死带给他的痛苦也愈大。因为,他的生命最值得过”。[2](P87)将高贵的生命献给高尚的目的,这就是亚氏所认为的勇者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身处战乱征伐频繁的尚武时代,他所论述和推崇的也主要是战场上的勇敢,然而勇敢本身并不以勇者的身份和处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现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我们正慢慢远离民族间盲目树敌的时代。我们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直接的、有目的的暴力,而是客观存在着的诸如贫穷、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等问题,后者正是滋生暴力的土壤。因而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仍然是我们的无知、贪婪和不宽容。所以,勇敢这一德性不应该表现在杀戮与战争中,我们也不期望如此,它应该表现在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中,以及对人类福祉的开拓中。勇敢是主体力量的彰显,它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必要德性,也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成为开拓人类文明的先锋。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不畏艰险为真理和自由而战的勇者铸就了人类的脊梁。
[参考文献]
[1]肖雪慧,韩东屏.主体的沉沦与觉醒——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思[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对《物理学》8.6(259b1- 20)的一种解读
——“自由落体”教学中的物理学史辨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一课的教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