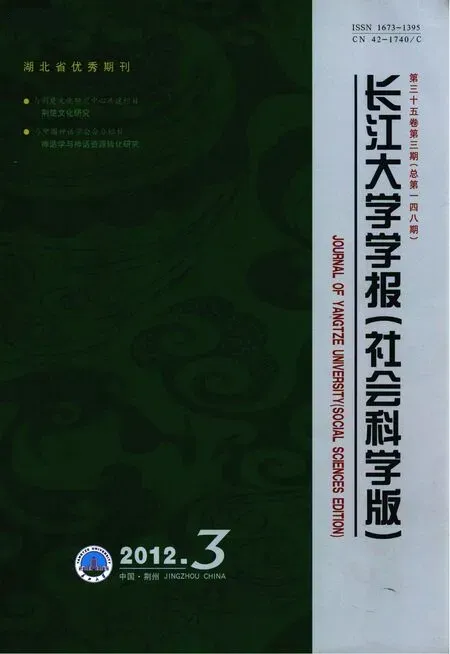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伦理
金 虹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伦理
金 虹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文学团体。他们在工业革命后自然生态危机刚刚显露之际,就在诗歌中热情讴歌大自然的诗意之美,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表现出对人类处境及命运的理性思考,以及超越时代发展的远见。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生态伦理;生态整体意识
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理性在人类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科学与技术的日益结合,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将科技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看成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对待自然的态度日益狂妄傲慢。英国工业革命因过度开采所导致的能源危机,因任意排放污水、废气而导致的水体和大气污染,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机器大生产使得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导致人性扭曲、道德滑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目睹工业革命和科技理性的汹涌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逐渐沦丧,以及文明本身所激发的社会矛盾,因而必须要为人类生存寻找新的价值基础。
一、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
作为浪漫主义诗学的领军人物,华兹华斯可以视为欧美最杰出的生态作家之一。他笔下的自然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自然,而是上帝与自然的同化,被赋予了神性的光晕,“推动着一切思维的主体和思维的对象,在天地万物间运转”[1](P316)。尽管基督教的上帝被启蒙运动的理性所摧毁,华兹华斯却在自然中重新发现了上帝的存在,他体现在自然万物当中,赋予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以神性的光辉,因而无论人或自然,都互相联系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华兹华斯强调对大自然保有敬畏之心,崇尚大自然与人心灵的交融,从自然万物中感悟人生真谛,以透视生活的本质。他认为,在人性受到工业文明的挤压而变得扭曲的当下社会,大自然和田园生活却提供了伸展人类天性的广阔空间。英国著名生态批评学家约翰逊·贝特指出:华兹华斯诗歌里对自然神圣性的尊重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生态伦理。[2]
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然是神性和人性的自然,同时也兼具理性,从他的诗歌中不难看出诗人对生态系统的重视和从生态系统利益来评价事物的标准。在诗人眼中,只有保持了平衡的生态系统才是健康的生态系统。他在《劝戒》、《鹿跳泉》等诗歌中警告后人肆意改造自然所带来的可怕灾难,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华兹华斯绝不单纯是歌咏自然景物的世俗文人,他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对自然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严肃的理性思考。
二、科勒律治的生态伦理寓言
作为最具有哲学深度的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相信万物一体,和谐共存:人作为生命个体在本质上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在生命的运动中实现着个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一样,都认为自然是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体,与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与华兹华斯歌咏自然的表达方式不同,柯勒律治则是通过把人置于自然的对立面来体现“罪”与“罚”的伦理警示。他的长诗《古舟子吟》讲述了一位水手在一次航海途中射杀了一只信天翁从而招致天罚的故事。在目睹同船的水手们相继死去,经历了无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之后,老水手才明白人类与自然万物皆为上帝造物,应该相互依存的道理。诗人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通过描述一种超自然的神力,使读者经历了从整一到分离,再回归到整一的思维旅程。这实际上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态寓言:信天翁体现着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原始理念,而老水手的行为侵害了生命共同体中其他生物平等的生存权利,将人与自然无情对立,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启蒙运动以来,工业化和科技的进步,普遍压抑了情感与信仰,把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人与自然发生了二元分离,人不仅与自然日渐疏远,而且以人类为中心,对大自然肆意掠夺与破坏。柯勒律治通过《古舟子吟》咏叹了一曲自然伦理的悲剧,用生态预警的方式警告人类:任意掠夺自然最终会使人类被孤立,以至走向灭亡。
三、雪莱、济慈的自由观念与生命意识
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自然是融合了诗人的内心情感,人景相融、物我一体的自然。雪莱将对社会的批判和理想的追求融合于对变幻莫测的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实现了物我相融的和谐境界。在《致云雀》一诗中,诗人把云雀比作尘世的讥嘲者,吟唱出充满真诚与欢欣的曲调,蔑视一切尘世的污浊与浮华的腔调。《西风颂》中的西风更是自由与力量的象征,倾注着诗人的一腔热情与对自由理想的执著追求,实现了诗人内心与外在景物的浑然一体。综观雪莱的诗作,无论是《致云雀》、《西风颂》等自然诗,还是《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反抗暴政的政治诗,都离不开自然的主体形象与争取自由、追求理想的思想根基。通过二者的结合,雪莱的诗歌彰显了诗人伟大的生态伦理思想:只有向一切不公正的事物挑战,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类本真的生存状态,以及和谐光明的人类未来生活图景。
济慈拥有异常敏锐的感官和超强的艺术天赋。在他的笔下,自然万物都绽放着绚烂的生命之花,即使再弱小的生物也能演奏出动人的生命乐章。无论是烈日下欢唱的蝈蝈,冬夜里高歌的蟋蟀,还是花丛中嗡嗡的蜜蜂,树荫间歌唱的夜莺,都共同造就了大自然的生机勃勃。诗人从这些弱小生命中领悟到生命的伟大与强悍。在这样的生命力面前,现实中的一切痛苦和折磨都能烟消云散,一切虚伪和迷信都显得粗俗可鄙。在《夜莺颂》一诗中,诗人从夜莺的歌唱中感受到极度的愉悦,忘却了病痛与烦恼,连死亡在这一刻都成了“无上的幸福”。这是因为,听到夜莺这样美妙的歌,感觉到人与这样一个生物伙伴之间的有机联系,生与死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死亡便是彻底地融入自然,便是获得永生。济慈诗中这种对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以及超越人类自身的生命意识,与多年后史怀泽所提出的“敬畏生命”伦理不谋而合:人类的同情如果包含了一切生命,那就具有了真正的深度和广度,具有了“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3](P23)。
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产生了全球变暖、大气污染、土壤沙化、物种灭绝等严重的生态后果。这告诫人类,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必将毁掉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最终将人类推向孤立的绝境。澳大利亚著名生态学家希德提出:物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环境并非我们之外的景物,一旦我们污染毒化了空气、水源和土壤,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毒害我们自己”[4](P45)。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人性的危机,是自我中心主义和短视的工具理性思想支配人类行为所造成的危机。而浪漫主义诗人则告诉我们,大自然是具有神性和灵性的存在,只有重拾一颗敬畏自然的虔诚之心,时刻保有对自然的生态责任意识,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能重新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然并不曾提出过生态伦理的系统思想,但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与对自然与人关系的理解显示出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其作品当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1]屠岸.英国历代诗歌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Jonathan Bate.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
[3](德)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I561
A
1673-1395(2012)03-0023-02
2012-02-2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优秀青年教师项目(CUGQNW0918)
金虹(1982-),女,湖北枣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