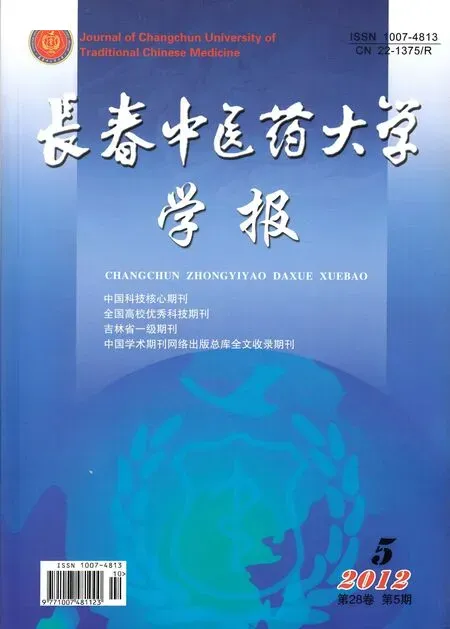《医医病书》用药论管窥
丁 勇
(淮阴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淮阴 223300)
吴鞠通,江苏淮阴人,名瑭,字佩珩,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医学家、临床家,著有医著《温病条辨》《吴鞠通医案》和《医医病书》。《温病条辨》以理论指导实践,《吴鞠通医案》以实践论证理论,《医医病书》述其未完,是吴鞠通完成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的一部力作,书成于1831年。全书记72论(篇),内容可归类为医德医术、杂病辨治、方药之道3个方面。其中涉及方药之道28篇,单及用药之论21篇,兹就吴氏论用药之道分5个方面略呈管见。
1 倡导用药用量中病之的
医术神奇,精于方药,方以药成[1],药物是治病的主宰,治病效与不效,与用药关系至密。吴氏临床对此十分重视,就用药分量而言,提出“用药分量,有宜多者,少则不效”“药有宜少用者,万不可多用”。用药分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疗效,用药分量不足或药量太过都不能达到理想的疗效,药量太小,杯水车薪,不能补偏救弊,何病可治?药量太大,药毒伤人,反致弊端,甚至伤人致命。
用药量的大小,一是视病情而定,大担重任,小生奇效。比如暑温、痹证、痰饮病证脉洪的患者,皆因肺胃热盛,石膏用量宜大,吴氏提及用此药,有1剂数两,有1剂量达斤,不效不罢。也有用石膏的量至数斤、数10斤……之多;有的病症则相反,如寒燥证用蟾酥量宜小,瘀血证用皂矾只能在几微之间,而每皆效佳。疾病的病程中,药量大小应中病之的。吴氏认为“病轻药重为不中,病重药轻亦为不中;病浅药深为不中,病深药浅亦为不中”。翻开吴氏之书,吴氏用甘草者,重则剂达6两,少则4分,15倍之差,周旋于临床,屡起沉疴,用药用量之精,乃临床家楷模。二是视体质而定,如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吴氏主张在小儿用药方面,贵在轻灵,这种思想渗透于他的各个作品之中,如他在《温病条辨》中提及“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症,则莫知其乡。”就是说小儿用药宜清轻灵动,中病即效,过则有伤正之虑。[2]
2 强调药必对证不容偏执
吴氏十分强调作为一个医生临床首要之事是“识证真,对病确,一击而罢”。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是辨证准确,后言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辨证是论治的前提,论治的要义在于药必对证。吴氏指出:“天下无不偏之药,亦无不偏之病”。凡药物多有寒、热、温、凉之不同的药性,寒凉之药多能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温热之药多能温里散寒,助阳通络,这是药物能治病的基础。健康状态是阴平阳秘,疾病状态源于阴阳失衡。阴阳偏盛则“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阴阳偏衰则“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医生以药治病,便是以药物之偏矫正病证之偏,逆其疾病现象而治,即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虚以补,治实以泻,以调整人体内部机能的偏胜偏衰,使之恢复阴阳的平衡而病愈。
吴氏分析药证不能对应的根源:一是医患中都时有“论药不论病”的错误观点,导致诊治疾病时“不论病之是非,而议药之可否”。二是医生对所用之药存有个人好恶,导致有是病不用是药,无是病,反用是药。难免出现治寒以寒,治热以热,助纣为虐、谷食变成毒药的后果。吴氏引用医家喻嘉言的话说:临床上当“先议病,后议药。”他又引用医家徐大椿的话告诫说:用药如用兵,“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作为医生必须懂得用药之道,万不能凭个人好恶来选择药物,有是病,虽险绝之药也敢用,如巴豆、甘遂、三棱等。无是病,虽平淡之品亦不能妄加,如人参、黄芪、山药等。吴氏用药之道,思维独具,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当认真效法。
3 反对恣用苦寒防生弊端
中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合称“四气五味”。中医依中药性味之偏来纠正疾病之偏,达阴阳平衡而治愈疾病,每位药都因气味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苦寒药即味苦性寒之药,味苦之药能泄、能燥、能降;性寒之药能清热、泻火、解毒,这是药物的正作用,但药物也有它的毒副作用,如性味苦寒的药物,苦能生燥,寒能伤阳,用之不当则生弊端。吴氏在《医医病书》中论及苦寒共4篇,他竭力反对恣用苦寒。
苦寒之味,用之不当,不但会影响邪正盛衰,且能变生它端,伤及正气。吴氏作为温病大家,熟知苦寒药的偏性和毒副作用,“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眼科疾病恣用苦寒之药,苦能化燥,燥邪伤眼,则眼疾会因燥而愈赤愈痛,导致损目;外科疾病阳热实证多,但若恣用苦寒,苦寒败胃,伤及胃阳,胃阳伤则不思纳谷,后天无化源,或伤及正气,正不敌邪则外科病症也难愈。如外科疾病中的痈疽,痈者,壅也,是气血被邪毒壅滞而发生的化脓性疾病;疽者,阻也,是气血被毒邪阻滞而发于皮肉筋骨的疾病[3]。痈疽的成因为“营卫不和,气血不得周流无间”而成。气为阳,血为阴,腑为阳,脏为阴。若一见痈疽,即以热毒而论,滥用大剂量寒凉药物,伤及阳气,会使阳气损伤,气血凝滞而毒聚不散,往往导致病深一层,还会导致毒气内传,毒侵入脏,最终甚至能危及生命。
对于苦寒药物的应用,吴氏绝非偏执一端,他说:“盖苦寒在湿热门中用处最多,欲其化燥也。风火门中用之甚少,要以甘寒用当权,断不可令苦寒当权,而使之化燥也”。温热病其特征是发热,热为阳邪,易化燥伤阴是其共性,过用苦寒之药,特别是清热燥湿之芩连类,则更易化燥伤阴,于病不利。而甘能补脾,脾旺则能布其津液,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所以风火门中要重视用甘寒,而不可以苦寒当权。这也体现了吴氏治温病注重阴精的学术思想,指出了苦寒药物用于中下焦湿热证更为妥当。对于火热上炎之咽喉疼痛等证,治疗用药应选用甘寒之味清热生津,不宜苦寒,这一见解值得临证用苦寒药时研究和借鉴。
4 述天道喻药道择药治病
吴氏认为“四时五行六气”乃天地运行之气,蕴含丰富的自然变化之理,只有四时五行六气之全,才能生长化收藏而养育万物,中药来源于自然产物,故药道也应符合自然之道,亦即天道。所以药用之道不仅可以从临床经验中总结提炼,还可以从自然之道中参悟。
在收汗法论中,吴氏论述秋小麦的功效好于浮小麦。自汗不止之证,在当时医生几乎都用浮小麦去治疗,但是汗为心液,吴氏主张“心虚自汗,用秋小麦”为好。因秋小麦能备四时之气,种于秋天成熟于夏天,走心经而能养心,其种于秋天,初生的皮纯得秋金收敛之气,可以收敛止汗,而浮小麦是自身生时得气不足或生虫有病所致,所以,吴氏认为浮小麦自身已经不足怎能为人治病,秋小麦治汗之功理应优于浮小麦。
中药赤芍和白芍原本不分,统称“芍药”,《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至梁武帝时期陶弘景始分。《本草纲目》指出“白补而收,赤散而泻。”[4]在白芍论中,吴氏指出白芍不应为“酸寒之品”。关于其性味,《本经》谓其“味苦,平。”《别录》谓其“酸,平,微寒。”元、明以后的医家自此沿用白芍为酸寒之品。对此吴氏意见相左,他认为白芍入口咀嚼无酸味,其生长期历经子、丑、寅、卯、辰、巳6个阳月(指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性味不可能为酸寒。故吴氏反对朱丹溪产后不可用白芍的观点,对此非仅吴氏反对,众多医家亦持异议,如《本草正义》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丹溪谓产后不可用芍药,以其酸寒伐生发之气故也。颐谓产后二字,所该者广博而无涯唉,芍药酸寒,虚寒者固不可用,然尚有小建中汤之成例在,若是实热当下,硝、黄、芩、连且皆不避,又安有独禁芍药一味”?
在产后恣用归芎论中,吴氏提出香砂能养胎元。“香附一节一膜,深藏根底;缩砂蜜一房一膜,深藏叶底。二者均有胎胞深藏之象,故能保胎也。”保胎需藏,香附、砂仁的天然结构有深藏之象,有利于保胎。吴氏的这一阐述也属于在自然中比类取象,见解独特,皆为吴氏参悟自然之道所得,今述兹以作参考,是对是错,当在实践中评判。
5 论脏腑体用言药之通守
《素问·五脏别论》指出,藏和泻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存在着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5]五脏所贮藏的精微物质是供给全身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果五脏不能化生贮藏输布精气,那么六腑就得不到营养物质的滋养而失去传导水谷排泄糟粕的机能;反之,如果六腑不能排泄糟粕,那么浊者不降,清者不升,精微物质也无法产生,五脏就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因此,吴氏指出五脏六腑体用不同,因此各有补法,补脏之体用守法,五脏的功能藏而不泻,以藏为用,补腑之体用泻药,六腑的功能泻而不藏,以通为用,故补腑之体用通法。药之通守即药的通药守药,一字之差,“天”“地”之别,吴氏将通药守药进行了大致分类:“凡补五脏之体者皆守药,补六腑之体者皆通药”。五脏主守类地气,六腑、经络、九窍等主通类天气,故补五脏之体者皆守药,因脏者,藏也,守而不走;补六腑之体者皆通药,因腑者,府也,走而不守故也,此之理也。
吴氏提示通药守药的划分是相对的。以四君子汤之组方为例:白术、炙甘草为脾经守药,人参、茯苓为胃中通药。4药中甘草纯甘,为守中之守药;白术兼苦能渗湿,是守中之通药;人参苦少甘多,为通中之守药;茯苓淡渗而能达下,是通中之通药。由此可见,通药中有守药,守药中有通药。
吴氏指出通药守药的使用是有原则的,也是有变化的。通常补五脏用守药,补六腑、经络筋经和九窍用通药,补肌肉则有守药也有通药。通药守药的配伍也是灵活的,辨证施药,因需而异。如:四君子汤的参、术、苓、草4味药,通守各有专长、各有特点,可分可合,变化多端。吴氏“用通,则去术、草;用守,则去参、苓。用通中通,则单用茯苓;用守中守,则单用甘草;兼用通守者,则兼用之。”“天人相应”,而地小天大,故临床治病通补之法用时为多,守补之法用时为少。所论非常贴近临床,不失为临床家之举,值得进一步探讨。
[1]严冰.吴鞠通医书合编[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643.
[2]李源,郭亦男.吴鞠通《温病条辨》对中医儿科的贡献[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4(2):126-127.
[3]吴爱萍.赤、白芍来源及其临床应用[J].陕西中医,2009,30(7):858.
[4]王玉芳.浅析《素问·五脏别论》脏腑藏泻理论[J].江苏中医药,2010,42(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