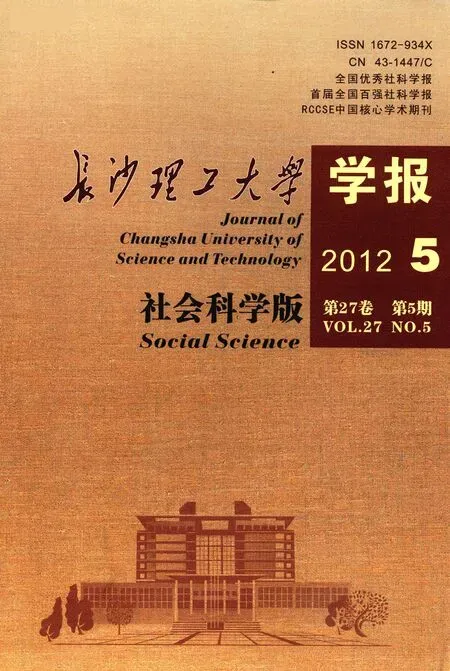略论唐兴玲其人其诗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略论唐兴玲其人其诗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诗人唐兴玲英年早逝,是湖南诗坛的重大损失。她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女诗人,对诗歌怀着真诚的热爱,既潜心写作,也热心组织和参加诗歌活动。在她的创作中,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是最能代表她创作特色的一部分。在她后期的爱情诗中,似乎游移着某种孤寂的情绪,然而也更见内在的热度,诗人的视野扩展到她的自我形象之外,对人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她的创作在湖南诗人中,可以说代表一个高度,在当代女性诗人中,她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
唐兴玲;湖南诗人;爱情诗;美学特色
现在想来,我和诗人唐兴玲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她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大都定格在“潇湘诗会”这样的大型诗人聚会场合,我们也在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主办的几次诗歌艺术节上见过面,偶尔也在博客里相互留言。有一年临近元旦的时候,收到她从广州寄来的一张新年贺卡,竟觉得有点意外,卡片上寥寥数语,都是诗一样的文字,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我想,这是兴玲身上温婉的一面。在大家的印象里,她有一种男人的豪气,似乎不拘小节,做事利索大方,豪不拖泥带水,即使喝酒,也有不让须眉的气概。她的诗歌里也有一种迥异于一般女性诗人的大气,几乎见不到那种自恋式的浅斟低吟,女性的温婉总是与一种内在的扩张性的诗性力量结合为一体,这使她的诗往往显示出一种阔大的境界。这可能是来自性格里的因素,也是与生俱来的禀赋,是诗神的赐予与垂爱。一个诗人的创作打上性格的某些印记,这大概是创作的一种常态,不足为奇,倒是那些毫无性格,只有所谓风格的创作显得非常可疑。这可能是我的偏见,不过也可以说是一种直觉和经验。我总觉得,如果在一个诗人的创作中看不到一点他的本来面目和个人的经历,那他的创作很难说是可爱的,也很难让读者产生亲近感。我很不喜欢那种其人猥琐而在诗中故作豪放的诗人,一些诗人见面之下,发现与其创作中的自我形象判若两人,我总有某种恶心的感觉。还是古人说得好:“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1]那种不见真性情的写作自然谈不上真面目,不仅与写作者自己隔着一层,在读者那里,更是显得面目可憎,恐怕这也是读者离开诗歌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在唐兴玲的创作中,来自她性格里的因素恰恰是她风格中的可爱之处,或者说,她的创作既是有性格的,也是有风格的,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诗与人两不相隔。确实,兴玲活着的时候,她小心地呵护每一首诗,像呵护自己的内心,活得真实而自然,因此,她的生命虽然短暂,却长留在一首诗的怀念中。对一个诗人来说,这何尝不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唐兴玲是几次“潇湘诗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都在会场上忙碌着,只能匆匆聊上几句,不便耽误她过多的时间。只有一次例外,我老早到达集合乘车的地方,没想到她已等在那里。那次的诗会没有像往常一样安排在省图书馆,而是安排在长沙市郊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为方便各地的诗人前往参加诗会,由兴玲组织大家乘车。记得是在正午的湘江边,太阳汹涌而泼辣,晒得城市里一片亮晃晃的空旷,万物的阴影无处藏形。我正在左右张望,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叫:“投文,来得早啊,第一个到!”我扭头一看,正是兴玲,原来她坐在河边一个遮阳的地方,在那里向我招手呢。我说:“不是你第一个到吗?在这样的大热天等我们。”她的衣着还是那样质朴,看得出没有刻意打扮,与那种习惯涂着大花脸的年轻女性相比,她的气质是恰到好处的自然,毫不做作,完全没有那种伪饰性的骄傲,显得亲切随和。她大概属于那种几乎从不涂脂抹粉的女性,素面朝天,这在特立独行的女诗人中也极为少见。也就是这次见面,我和她有一次比较深入的交谈,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一幅远方的风景画挂在墙上,画中的那个女诗人已经不知去向。在那次的交谈中,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健谈的人,对写作有自己的想法,在谈到她的一些写作设想和追求时,她显得坚定而自信。看得出,她是一个并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人,在写作上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走,对那种随风转的写作怀着自觉的警惕。从总体上看,唐兴玲的创作没有那种出人意外的突转性变化,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创作追求,这是并不容易做到的。我想,对她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来说,不为炫目的诗坛风尚所迷惑,是需要有内心的定力的。
说起来,我最早读到兴玲的诗,还是在二十来年前吧,那是一个文学尚未完全退烧的年代,文学青年还可以正儿八经地讨论文学,甚至还可以把文学标榜为一种充满诗性的生存方式,物质主义的鬼魅还没有被人们奉为心中的神灵。那时,我大概也属于文学青年中的狂热分子,整天在纸上涂鸦,偶尔有几行变成铅字,那份喜悦的心情是现在的大学中文系学生恐怕难以理解的。有一次,我的一组诗和兴玲的诗发表在同一期《湖南文学》上,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她的诗,因此印象很深。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她当时诗歌的那种近乎唯美的情调,在纯净中透露出淡淡的迷茫和愁绪,有一种浪漫主义式的青春基调。也许,我的记忆并不准确,手头又无法找到那期刊物。那时零星地读过她的一些作品,大体上说,觉得她对语言的美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和痴迷。和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一样,我们的写作也许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文学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文学的美虽然无法承受生存的重压和世俗的腐蚀性改造,我们仍然在内心中坚守文学之美的纯粹性。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语境下,我觉得唐兴玲的创作似乎具有某种标本性意义,她的诗歌有一种一如既往的连续性,没有跟随时代的风潮大起大落,没有像有些诗人那样耍戏法似地变换面孔。这二十多年来,不断有诗人失踪,杳无去向,她却一直坚持着在写,中间没有停顿和犹豫,但她的写作姿态却是边缘性的,可以说,兴玲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独立诗人,一直游离于主流诗歌圈外,属于有实力有才华却长期被诗坛忽视的那类诗人。我想,这并不是兴玲个人的悲剧,而是涉及到当前诗歌生态的整体性问题,不过,兴玲创作的意义大概也在这里显示出来,她的诗歌具有沉默而充实的艺术品质,内蕴着一种对世俗性力量沉默而坚韧的抗拒,可以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唐兴玲是一位有充分准备的诗人,只要一读她的诗歌,就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一个诗人的创作准备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才情可能最为重要,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才情当然包含着天赋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后天修炼的结果,一个诗人需要通过长期的磨砺,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才情。兴玲无疑是一位有才情的女诗人,即使是她的早期诗歌,现在读来也仍然鲜活如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爱人,请在我的爱情里出类拔萃》是兴玲早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时她才二十岁出头,是生命的黄金时节。这首诗写得华美而富有生气,与现在充斥各种报刊版面的所谓爱情诗立见高下之别。那类流行的爱情诗往往缠绕太多的伪饰性,爱情在诗中似乎是作为一种消费品或化妆品出现,也可能写得有那么一点缠绵的情调,但大都流于肤浅的低吟,缺乏骨子里为爱付出的勇气和真诚。兴玲的这首诗也是爱的歌吟,却完全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情出之以真,爱出之以贞,有一种火焰化为灰烬后那种飘浮却饱含余热的生命激情,这是一种内在的爱的激情。诗人倾心于一个梦幻般的情境,在诗中用心营造一种童话般的氛围,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纯情少女,她反复地呼唤“流浪的爱人”、“骄傲的爱人”、“危险的爱人”、“脆弱的爱人”、“坚韧的爱人”、“闪闪发光的爱人”,情不自禁地为爱人“挥洒一生的清辉”,呼唤爱人“在我的爱情里出类拔萃”,其中包含着爱的许诺和盟誓,包含着爱的忠诚和坦荡,让人在感动中体味到更深层的内涵。这首诗中对爱的歌吟可以说代表兴玲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她后来的创作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爱与美的结合,爱与善的交融是诗人唐兴玲创作的基本主题指向,这使她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清澈与明朗,有一种清新与优雅的大气感,诗人并没有把自己关闭在一个狭小的个人天地里,而是从爱情出发寻找人生的根本意义,赋予爱情以一种更宽广的人生意义,也有由爱的歌吟生发出来的更深一层的人生感叹。《哦,天使》是兴玲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一部诗集,这是她写给三岁儿子的一部母爱之书,实际上是一部由三十九首诗构成的大型组诗。兴玲患有生天性心脏病,自小饱受这一疾病折磨,直到三十八岁时才冒险生育,因此,对她来说,成为一个母亲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儿子是她心中的天使,是爱神的赐予,也是爱的化身。《哦,天使》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文本,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文本,爱的主题在诗中是贯穿性的,诗人在抒写人间至爱的时候,没有只简单地停留于血缘性的亲子之爱,她的心也在远处停留,把亲子之爱升华到更为博大的爱的境界,这使诗中呈现出一种辐射性的情感张力。诗中有大量的叙述性因素,叙写儿子的日常生活情境,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的幼儿形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这是诗人的情感寄托,其实也代表诗人对爱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笔下流溢着爱的温暖与柔情,但诗中似乎也压抑着一种疼痛的东西,有的诗中有一种很深切的内在的悲郁感。兴玲写这部大型组诗时,可能已有某种预感,生命的紧迫感似乎将要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因此,诗中流露出一种隐隐的焦虑,诗人在《哦,天使》的第三十首中写道:“对人世的眷恋和感激/让我找到我的灵魂,并且强大/足以让我面对死亡也有深度安宁。”然而,诗人对安宁的祈求在诗中还是透露出她内心的伤感和轻微的挣扎。在某种程度上,《哦,天使》是一部留给儿子的书,也是一部具有精神自传性的作品,诗人的自我形象构成天使的另一个侧面,或者说,在诗中还有一个隐秘的天使,作为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出现,这使诗中的天使形象显示出某种异常复杂的意蕴。在我看来,这正是《哦,天使》最为成功的地方,也是这一部大型组诗的艺术魅力所在。
在兴玲的创作中,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大概也是最能代表她创作特色的一部分。读她的诗歌,我的头脑里老是浮出一个问题:她为什么始终没有放弃爱情诗的写作?我之所以为这样一个问题困扰,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似乎处于一种总体性的荒凉背景下,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爱情似乎不再是人性美好的确证,对爱情的忠诚不再是人生信仰的一部分,而在很多的情形下,爱情恰恰是一种借口,成为对人性本身的戕害。这种悲观的心态不仅弥漫在现实中,也弥漫在文学作品中,对爱情的普遍怀疑大概是这个时代最令人痛心的精神悲剧之一。唐兴玲创作的价值也正在这里表现出来,她的爱情诗显示出一种非常难得的高远的视野,远远高出那些始终围着爱情打圈却始终不明白爱情到底为何物的“小女人”写作,她诗中的爱情既包含“人世的甜”,①更是一种理想形态的爱情,是一种符合人性本真的爱情,是现实中的爱情的超越形态。显然,这里面包含着兴玲对爱情本质的理解。她的爱情诗写得真诚而内敛,几乎完全没有当前那种流行文艺中虚浮而放浪的气息,而是在爱的歌吟中展开一片美的人生风景,但又不是那种单纯的青春型的歌吟,而是怀着人生中隐秘的疼痛和渴求。因此,在她的爱情诗中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复杂的人生体验,它是清澈的,却又包含着某种含混,它有一种超出一般女性诗人的大气,却又显得细腻入微。这可以说是兴玲爱情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兴玲在《偶遇》一诗中写道,“只有咳嗽、贫穷和爱情/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爱情诗正是至情至性的流露,显得真诚坦荡,毫无矫饰之气,这是兴玲的爱情诗深深打动读者的地方。
在兴玲的爱情诗中,组诗《聆听箫声的女子》是早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语言凝练优雅,境界婉转清幽,具有古典的韵味。诗中的意象似乎都是用清水洗过的,显得一尘不染;诗中的爱人是一个翩翩少年,显得超尘脱俗;诗中的女子生长在自然山水之中,是繁花丛中最素洁的一枝。我想,早年的兴玲沉溺在这种爱的幻境中,以一颗敏感的心去窥察爱的秘密,诗中似乎有一个放大的自我的形象。自然,在一个诗人的创作中,有这样一个放大的自我的形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甚至是诗人的癖好,是诗人创作个性的一个标记。不过,这在兴玲的创作中,这样一个放大的自我的形象是经过用心处理的,似乎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我想,这大概是一个诗人的秘密。可能因为兴玲自小饱受疾病的折磨,爱情对她来说相当于一场火中的梦幻,不真实却强烈地渴求着,这也许是她进行写作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在她后期的爱情诗中,似乎游移着某种孤寂的情绪,然而也更见内在的热度,诗人的视野扩展到她的自我形象之外,对人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爱情的梦幻色彩在她的笔下悄悄转化为某种晦暗的状态,其中有着深沉的人生感叹,这似乎表明诗人的心境在变化,也似乎表明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中诗人对爱情的困惑和困惑中的坚守。比如这首精短的《暗状态》:
熄掉晚灯,
所有的孤独患者
感到安全。
我的心脏有个洞。
我的爱情有个缺。
我的被子底下,
有一颗蚕豆。
这首诗近乎孤独的自语,是一种混沌莫名的自语。在诗人的这种自语中,实际上有一个由明转暗的过程,对此,“暗状态”真是一种极好的概括。那么,“暗”在何处?我想,不外乎人性之暗、孤独之暗和爱情之暗。这里面恐怕也有诗人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当然,这也代表一个普遍的心结,这就是人人都能体会到的生命的残缺,包括身体的残缺、精神的残缺、爱情的残缺、物质的残缺,等等。这种缺失性体验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会陷入的“暗状态”。这种“暗状态”在诗中表现为多种形式:对孤独的承受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残缺,所有的孤独患者只有熄灯之后才能感到安全,这是一种精神残缺的“暗状态”;“我的心脏有个洞”,这是一种身体残缺的“暗状态”;“我的爱情有个缺”,这也是一种爱情残缺的“暗状态”。唯一能得到安慰的,是“我的被子底下,/有一颗蚕豆”,然而,这是一种戏谑。在精神、身体和爱情的残缺面前,一颗蚕豆何足道哉?不过,在我看来,人生最致命的残缺大概还是爱情的残缺,精神、身体和物质等方面的残缺,都可以通过爱情来弥补,而爱情的残缺却永无弥补,是一种永久的残缺。这大概就是爱情在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我想,在兴玲的这首诗中,她的着眼点也还是爱情,她不是要为爱情寻找一个位置,而是在一种对照性的精神视野中呈现出爱情本身的位置。当然,爱情的位置因人而异,但在兴玲的诗中,爱情确实是处于至上的位置。这可以说是唐兴玲诗歌创作中的整体性取向,也代表她对爱情的基本理解。
读兴玲的诗歌,我有时感到很奇怪,她的诗歌常常把爱情与死亡连结在一起,似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隐秘的联系。沈从文曾经感叹:“爱与死为邻。”[2]他笔下的爱情故事常常以死亡或出走为结局,大概就是这句话的印证。尼采也说过,爱与死,永恒一致。求爱的意志,也就是甘愿去死。[3]爱与死的纠结确实是艺术处理的一个难题,也是诗歌需要处理的难题。在兴玲的后期诗歌中,死亡的魅影和与死亡相关的意象都频频出现,像墓园、陵墓、墓地、墓碑、墓园、古墓、坟墓、骷髅、死者、死神等晦暗的意象一再出现,有的死亡意象与爱情缠绕为一体,显示出一种别样的人生况味,具有某种沧桑感和苦难感。爱情与死亡在诗歌中往往有特殊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取得特别的表达效果。兴玲有一首《诗人之死》,诗中有某种自传性的因素:“这一瞬间,心脏上的许多洞,被修复一新”,还是“心脏上的洞”这一隐喻,从中可以发现诗人的内心压抑。这似乎是一种对自我的挽留,实际上是借诗人之死挽留人间的爱慕和“人世的甜”。兴玲还有一首《墓园》,第一句就是“我对墓园情有独钟”,诗人缘何对墓园情有独钟?因为墓园“牵扯生死的美”,与人间的爱恨情仇息息相关。因此,以死亡的方式看待爱情,这也许是一种最炽烈的情感,而当爱情以死亡的方式出现,这当然是一种悲剧,却也符合爱是牺牲的信念。应该说,在兴玲的后期诗歌中,爱情与死亡的缠绕显示出悲剧性的意味。与早期诗歌那种近乎清水无尘的柔美与深情相比,兴玲的后期创作显示出某种晦暗的复杂性,里面似乎有一种峻急的调子,但在倾诉中又时而变得犹豫和压抑。应该说,这是兴玲后期创作取得的深化和进展,这也是她的后期创作更有个性色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兴玲活着的时候,总是以她的热心和赤诚感动身边的人,在湖南的诗人中,她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大家和她相处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一种透明的快乐和由会心的交流所带来的诗的愉悦。诗人多有才高气傲的小毛病,这在兴玲的身上却没有,她是一个有极高才华的女诗人,但她的谦逊在诗人中有口皆碑,这是大家都乐于接近她的原因。也许走在人群中,她也是一个显得非常普通的人,和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作为一个诗人,她的创作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在湖南诗人中,可以说代表一个高度,在当代女性诗人中,她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她的诗写得很美,有女性特有的情怀,也有属于她自己的特别的创作视野。她和一般女诗人的区别,既是风格形态上的,也是个性气质上的,也有创作视野所带来的的差异。诗人韦白认为,在唐兴玲诗歌的柔美中透露出一股蛮悍的强力,“这种强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从她的血液里流露出来的激情。这也是她得以在柔美、纯情的写作中突然突围出来,走向越来越成熟的写作的关键原因”。[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兴玲诗歌中“蛮悍的强力”也是由特别的创作视野所形成的一种美学特色。由于诗人的英年早逝,她的创作追求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她一生不懈地追求美与爱,在读者和朋友的心中,她本身就是一首充满美与爱的诗。
[注释]
① 引自唐兴玲的绝笔之作《我如此贪恋人世的甜》,网络大量转载。
[1]叶燮,沈德潜.原诗·说诗晬语[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50.
[2]沈从文.生命[A].沈从文全集(第12卷)[D].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3.
[3]张文初.死亡·悲剧与审美[M].长沙:岳麓书社,1996.101.
[4]韦白.柔美与激情的混合物及其变奏——兴玲诗歌印象[M].未刊稿.
[责任编辑 刘范弟]
Brief Account of Tang Xingling and her Poetry
WUTou-wen
(SchoolofHumanities,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gtan,Hunan411201,China)
The poet Tang Xingling died at an early age which is a great loss to Hunan Poetic Circles.As a high-talented poetess with deep love for poetry,Tang Xingling not only devoted herself to writing,but also organized and joined poetry activities enthusiastically.Among her works,love poetry has a large proportion,best representing her writing style.In her late love poems,the poet is in a lonely mood but more internal heat appears.The poet's vision extended her self-image,which showed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life.Her works represent a high level among Hunan poets.Meanwhile,among contemporary poetesses,she is also one of those worthy of attention.
Tang Xingling;Hunan poet;love poetry;aesthetic features
I207
A
1672-934X(2012)05-0036-05
2012-09-03
吴投文(1968-),男,汉族,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