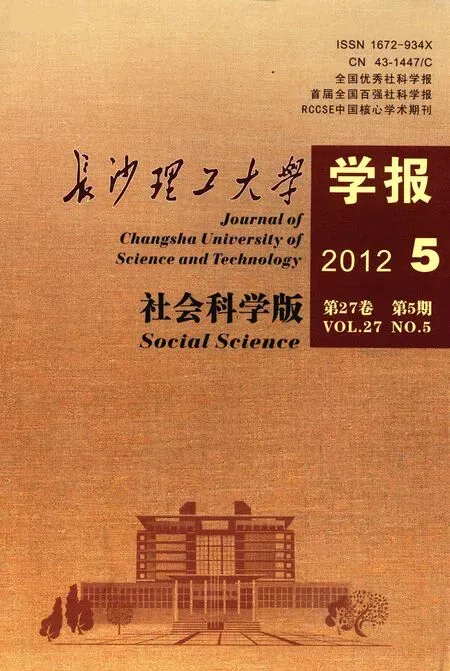“李约瑟问题”的部分消解
王以梁,张 宇
(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 110819;2.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2)
“李约瑟问题”的部分消解
王以梁1,张 宇2
(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 110819;2.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2)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以“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的方式,消解了李约瑟有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疑问。然而对于“李约瑟问题”的另一组成部分,即“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而后来却不是这样)”,却并未因此而一同消解。这一部分的疑问更多地涉及数理科学之外的技术,并且是一个能够证伪的真问题。
李约瑟问题;科学;技术;消解
但凡由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李约瑟问题”似乎总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即便如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先生撰写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以下简称“《继承与叛逆》”),像这样名副其实的专为解答“现代科学为何(且如何)出现于西方”的著作,它的宏篇布局也仍然是以“李约瑟问题”始,以“李约瑟问题”终,所不同者只在于该书决不热衷于宣扬中国古代的长期领先,却要用一部通史说明西方科学之自来有序,这大概也可算作一种研究中的“继承与叛逆”吧。
一、书中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看法
在该书作者看来,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其人不仅提出了那一著名的疑问,并且已经自己给出了明确的解答。这个在《继承与叛逆》当中被称作“李约瑟论题”(Needham Thesis)的答案,简言之就是中国历史上高度理性化的“官僚封建体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出现,而这两者却都能够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顺利发展。[1](P16)鉴于李约瑟始终坚信现代科学是由传统世界所有的民族造成,而又着力主张“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2]那么大约只有求助于一些社会经济制度的外部因素,方可圆满地解决中国“遥遥领先”与西方“后来居上”之间的矛盾。上述疑问(更确切地说应当属于引导性的“设问”或“诘问”)与归因于是构成了李约瑟的思想体系,更代表了一种在文化传统和科学家之外寻找科学发展动因的思想方法。
事实上,很多李约瑟之后的研究者正是循着注重“外史”,亦即以社会经济制度作为科学发展决定性因素的思路构建起各自的理论。例如,林毅夫以为“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3]席泽宗亦提出“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也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不必一直追着孔子、孟子”。[4]其它如文贯中主张地理禀赋是导致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最主要原因,[5]皮建才更将其视作一个制度交易层面的“投资阻塞问题”。[6]见解虽然各异,但他们——同样包括一批从思维方式角度来探讨的学者——都确信无疑地接受了中国古代获取及应用自然知识的效率、乃至就是科学均长期优胜这一来自李约瑟的基本前提。相比之下,像十年前江晓原那样直接将“李约瑟问题”斥为“伪问题”,并断言中国科学“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7]的论点,或许在国内总是比较少见的。
然而在国外,情况又迥乎不同。《继承与叛逆》的“导论”部分以相当的篇幅说明李约瑟的思想体系“对于西方科学史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也引起了态度相当一致的反应,即尊重、肯定其具体实证研究,但严厉批判其推论之空疏与有欠严谨”。[1](P26)这种不严谨,首先表现在他似乎从未把什么叫“科学”加以定义,如是则材料的取舍必将缺乏客观标准,出版工程也必定越做越多,以至非用“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①之名不能概括。读者从这一卷帙浩繁的巨著当中固然可以看到无数伟大的成就、天才的发明,不过这些内容究竟能有多少归入“科学”范畴,进而支撑起上述“长期优胜”的结论却颇能引发争议。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李约瑟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他往往忽略理论的演进,而对一些孤立的发现和创造过度拔高——本书对此虽无直接的评价,但通过其后的一段论说,作者显然已为自己心目中的“科学”划定了一个绝不似于李约瑟那般宽广的领域:“科学并非许多不相干的事实、观念、知识的集合,而是一个具有逻辑结构的系统,在其中基本观念、原理、推论、观测结果各有固定位置,并且是通过逻辑与数学严格地联系起来的……”。[1](P191)
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再去挖掘相应的文化遗产,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继承与叛逆》一书即可看作这方面的一项尝试,同时它又是对于李约瑟曾经的合作者、亦其论题重要的批评者席文(Nathan Sivin)所言,“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1](PIX),做出的回应。
二、书中的理论建构及其时代意义
作者坦言,《继承与叛逆》“全书布局、结构、论述方式几经改易,但有一点始终不变,即它以‘科学’为主题,为探究核心”。[8]科学的“内史”,也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与他们的思想、发现构成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在作者眼中,“外史”所侧重的社会经济等因素“对科学虽然可能有影响,但却是间接、不确定与辅助性的”,因此绝不可能取代“内史”。而鉴于历史基本上是连续的,“即使在急速变化过程中,‘传统’力量仍然有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科学发展的探讨需要顾及长期历史背景,而不能够局限于特定时期。这也就是说,科学前进的动力必须求之于‘革命’与‘传统’②两者之间的张力与交互作用”。[1](P27)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科学既包括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也包括以经验和实用为主的其它科学,但本书所致力的,只是有关西方数理科学整体发展的具体论述。如此选材的原因,在于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以来的科学革命终究是通过数理科学的突破实现的——这一点实际也为李约瑟所认同③——而据书中所见,他们这些科学家的成就无疑受到复兴了的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触发。若是继续追根溯源,则“西方科学史最瞩目、最令人感到震惊的,就是它的数学传统之悠久”,[1](P630)从远古时代的埃及和巴比伦(按书中的算法,这一起点较之中国《九章算术》成书的年代要早1500年),传承到古希腊,西方“发展出以探索宇宙奥秘为目标,以追求严格证明的数学为基础的大传统”,而“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而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也并非没有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究,而是没有将数学与这种探究结合起来”,[1](P628)……两者终于渐行渐远,乃至不可比较。
余英时在为本书写作的序言中用了一个关于“围棋与象棋”的通俗比喻④来说明东西方探究自然方式的“不可比较”。人们当然不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1]因为不同的游戏之间根本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同样地,既然古代中国与西方既无一致的数理科学传统,走过的路径又是南辕北辙,那种曾令国人引以为傲的“科学长期优胜”的说法就必须放弃了,而这在作者看来便意味着“李约瑟问题”的消解。
我们且将这一“李约瑟问题”的消解论放到以下部分来分析。此刻,至少读罢全篇,了解到西方科学系由“一个传统”经历“两次革命”(古希腊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和近代的“牛顿革命”)嬗变而来的基本历程,那种仅从近代寻找舶来的“赛先生”,而一谈到中国古代便要动辄领先欧洲多少年的思维定势⑤想必是得反思一下了——毕竟,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在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绩已经殊堪惊叹。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有言曰“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针对历史的研究、提给历史的问题莫不有其当代意义。如果说,当年的李约瑟及其合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告诉国人不必妄自菲薄,又通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诘问”,提醒人们对于本民族走向落后的教训必须反省;那么在今天,《继承与叛逆》的作者陈方正先生着力勾勒出独特的“西方科学大传统”,其现实意义或许是要告诉国人不可盲目自大,必须努力学习、而首先是能够认识到其他民族的长处。
三、数理之外的技术:书中尚未消解的疑问
假如李约瑟与陈方正两位先生议论“科学”的语境相符,那么本书的破解工作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再或者“科学”假如只是当下社会意识中的一个普通名词,不会立即使人联想到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崛起,那么我们也不妨以一种看待“棋艺”的态度坦然视之。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之前业已提及,李约瑟所讲的“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明显包含了更多技术的成分,就像他曾列举的领先西方的种种实用发明——从磨车到水排、从提花机到船尾舵……在接触这些古代技术的过程中,李约瑟自己也在不停地发问,为什么“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为什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能够“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10](P1-2)这些出自他笔下的、明确谈及技术而非数理科学的词句,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同样属于李约瑟想要讨论的问题的一部分,⑥甚至还应该进一步追寻,“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11]
上面有关技术的提问前后贯连起来,恰好可以构成一个真的问题(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李约瑟过度“挖掘”了中国古籍中的技术成果,或者是对西方的传统技艺过分贬低)。因为技术当然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区分,而中国古代如此之多的技术西传,[10](P253)与清朝末年火柴、铁钉亦以“洋”字命名的衰颓境况,确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的民族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实际上,李约瑟的研究之所以会产生巨大且持久的吸引力,之所以会有众多的学者愿意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参与其中,归根结底还要问出一个何以“技(术)不如人”、而不单是“(科)学不如人”、“理论不如人”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会苛求《继承与叛逆》的作者再去设置一条叙述西方技术发展的主线,毕竟书中在主要方向上做出的抉择已经注定了其内容将是“有科无技”的,其立论举证也绝非要同一切与李约瑟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例如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的、关于明清以后中国技术停滞不前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假说直接交锋。真正耐人寻味的,反倒是站在李约瑟的角度,他似乎更应当集中精力在掌握实证材料的范围内探究各类技术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进程,然后与同时期的欧洲进行整体与平衡的比较,看看这中间究竟有多大比例是中国超越了西方,往后的变化趋势又是如何?这总比承认“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还要再问中国何以未能抢先发生(类似牛顿经典力学体系那样的)科学革命更有把握吧?可是在李约瑟的思想体系中,却分明存在着一种近乎“悖论”的情形:即一方面,他是那样地看重应用技术,以至于谈论工艺或工程的卷目占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他最初发生乃至后来始终抱定的疑问⑦竟也是“有科无技”,单单落脚到“为什么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聚焦到“中西科学相对水平的大逆转”。那我们也不得不要问一下了:何以李约瑟具有如此浓重的“科学情结”,难道不是缘于那种认为技术必定是科学的应用、而科学本身象征着进步的信仰么?
四、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之后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技术是应用科学”之类的论断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培根(Francis Bacon),而就在李约瑟着手搜集中国科技资料的年代,美国学者布什(Vannevar Bush)已经借助向该国政府提交的、名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年)的报告,表达了当时人们看待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主导范式。在这其中,科学被视作技术进步的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动力,技术活动则相对地显得无足轻重,只被当作特定门类科学内容的体现和延伸。倘若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即不难理解,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实正希望通过大量的技术成就谈论背后可能的科学知识(例如通过磁针指南反映“超距离作用”,看到“宥坐之器”想起流体静力学),或者说,要是不将自己的论域引申到科学、“牵扯”进科学,那些技术发明便难以获得充分的合理性。
《继承与叛逆》对此又是怎样看法呢?在书中,至少那种从技术之“物”反观科学之“理”的思路是不能成立的,即如作者所言,技术“虽然也往往牵涉某些抽象观念或者宗教、哲学传统,但这和科学亦即自然现象背后规律之系统与深入探究,仍然有基本分别”。[1](P626)另从一些相对晚近的研究可知,这里的“基本分别”尽管并不妨碍理论与实践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应用技术都是由那些不懂科学又不会受惠于科学的人(即所谓“技术促进者”)来完善的,甚至“直到19世纪后期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止,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联系一直都是很薄弱的和或然性的”。[12]自此以后,一些重要的技术进步方才明显地依靠化学、物理学或者生物科学,而这已是现代科学形成之后很久的事了。
一旦了解到这一点,当读者在《继承与叛逆》中看到“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1](P628)的结论之时,想必在情感上更能释怀些吧!因为这丝毫不意味着早于2000年前中国在技术、以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注定落后。更进一步地说,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今天人们无比景仰的科学,特别是那种追求精确的数学化表达的数理科学其实只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在同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有效结合之前,亚历山大时代已经发展的圆锥曲线,还有关于地球周长的测量,都更像是一种局限在学宫中的“棋艺”,其最基本的发展动力只是“对于理论知识的热爱和追求”,[1](P201)而真正同社会需要紧密相联并且能够标识社会发展水平的,确实就是李约瑟热衷于探讨、且更适合着眼于“外史”来探讨的技术。
至此,我们大体可以对《继承与叛逆》一书提出的“李约瑟问题”的消解论做番评析了:李约瑟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便是在中国上千年的辉煌过去与20世纪中叶衰败现实的反差中展开,它也必然地被置于整个社会先进与落后的宏大命题之下。《中国科学技术史》体现的宽广视域因此不难理解,尽可能全面并深入地谈及技术成果更属必需,只是处处“牵扯”科学,还要问及科学革命何以不能发生,未免显得过于突兀而又文不对题。《继承与叛逆》正是抓住了这种从技术到科学的“跳跃性”的思维冒进,仅从西方数理科学自身的逻辑演进出发,便将李约瑟积累的绝大部分论据消于无形,从而达到了“釜底抽薪”的论证效果。可是,李约瑟的著作所引发的、长久拨动国人心弦的“从先进到落后”的思考绝非只在于科学(尽管他本人似乎倾向于把很多新事物皆归于此),纯粹的科学亦非社会进步的唯一要素,甚至直到近代早期都还不是关键性的。⑧这便使得人们在读过《继承与叛逆》之后,还是不禁会想起诸如“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以及中国在其古代后期,为什么没能自发地进行一场工业(或机械)革命[13],等等李约瑟及其相关研究者曾经指出的现象与问题,这些疑问是无法轻易消解的。面对着李约瑟的庞大工程,仍然是有人可以批判它,而无人可以忽视它。
[注释]
①这是李约瑟主持编写的煌煌巨著的英文原名,可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但在国内通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名。
②“传统”与“革命”即分别对应书名当中的“继承”与“叛逆”。
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科学出版社,1978年)的正文首页即强调“数学和各种科学假说的数学化已经成为近代科学的脊梁骨”,该书343页又曾谈到,“数学与科学的富有成果的结合的问题,只不过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发展起来这整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而已”。
④这一比喻远比席文提出的“‘李约瑟问题’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出现”那样近乎调侃的说法更为恰当且深刻。
⑤例如,以卢嘉锡为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2003年)在谈到古代世界的科技成就时,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其后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这种领先的势头”(《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第932页)。
⑥根据刘钝、王扬宗所辑《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书中所示,“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之谜”的说法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于1976年提出的。此后许多有关专家,包括《继承与叛逆》的作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阐述这一问题,有些仍是引用李约瑟的原话,有些则做了适度的引申——或许正是李约瑟的不严谨留下了相当大的伸缩空间。
⑦据李约瑟本人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64年)一文中透露,早在1938年他的研究工作开始酝酿时,注意到的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⑧我们可以引用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1987年)中谈及近代西方崛起时的论述,他说,“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使欧洲在商业上和军事上一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社会存在着一种动力,它主要受经济和技术进步驱使,虽然也总是同社会结构、地理以及偶然事件等其它变化相互影响”(见该书中译本第19页),这里明确提到了经济与技术,而对科学只字未提。
[1]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英)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徐汝庄译)[A].刘钝,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3.
[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71-272.
[4]科中国.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多关系——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J].今日中国论坛,2005,(1):90.
[5]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J].经济学,2005(4):523-538.
[6]皮建才.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我们到底站在哪里?——与文贯中、张宇燕、艾德荣等商榷[J].经济学,2006(1):318-321.
[7]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1):63.
[8]陈方正.对金观涛就《继承与叛逆》所作评论的回应[J].科学文化评论,2009(4):117.
[10](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袁翰青,王冰,于佳译)[M].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
[12](美)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周春彦,谷春立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27.
[13]Mark Elvin.The patterns of Chinese pas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317.
[责任编辑 刘范弟]
The Needham Question Being Partly Solved
WANGYi-liang1,ZHANGYu2
(1.SchoolofHumanitiesandLaw,Liaoning110819,China;2.SchoolofMarxism,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072,China)
The question"why Chinese failed to develop modern science",which was asked by Joseph Needham has been solved by Chen Fang-zheng,the author of the book"HeritageandBetrayal:ATreatiseontheEmergenceofModernScienceinWestern Civilization",through researching another question"why modern science emerged in western civilization".But,as to the other part of the Needham Question,"why natural knowledge had been found and adopted more efficientl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100BC to 1500AD(while after that it is no longer the case)"has not been solved at the same time.That part of the question especially relates to the technology outside mathematical science,and could be a real question.
the Needham Question;science;technology;solution
N09
A
1672-934X(2012)05-0019-05
2012-05-27
王以梁(1978-),男,天津人,东北大学科技哲学博士生;张宇(1978-),男,天津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出站,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