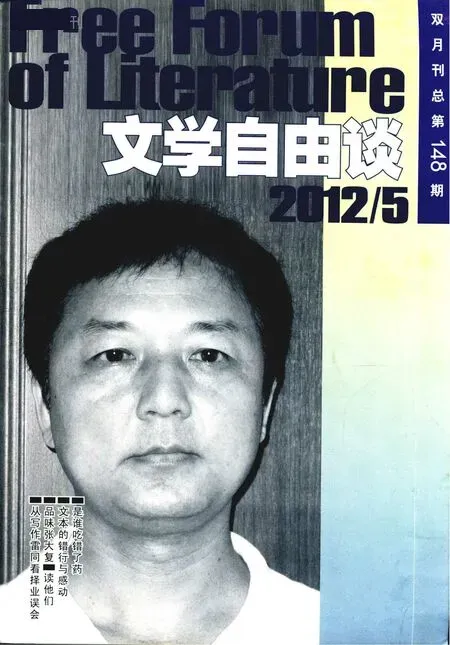读他们
●文/严英秀
格绒追美:《隐蔽的脸》
“看着从庞措神山上飞下来的雄鹰在头顶盘旋时,我多么想把内心的感受写下来啊,可是,我们掌握的汉字远不足以表现内心模糊的冲动。”
这是一个叫夏超晋美的藏族小孩发出的感慨。在庞大的汉语面前,他是那么的力不从心,但当时的他并不懂得这样的无奈却蕴示了一种极美好的可能:面对神奇博大的自然,面对生命中不可复制的感动,这个孩子在用心呼喊,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我想用手中的笔把你定格下来——这样的渴望,因这样的渴望而产生的无力感,都是诗人才具有的禀赋。
事实正是这样,多年之后,“夏超晋美”成长为一个叫格绒追美的作家,如今,他所掌握的汉字,不但可以惟妙惟肖地还原童年时那种无可名状的忧伤和冲动,而且如诗如画地抒写了一个雪域村庄神秘的前世和今生,他的笔直朝着个体、家族、民族的幽深、魔幻、动荡、恒定的心灵史去了。他已挺进到了藏族文化的深处。
是的,读完《隐蔽的脸——藏地神子迷踪》这部长篇,我欣慰地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藏人写藏人。它当然也是有缺陷的,譬如小说故事的停跳,事件的碎片式,譬如人物形象的稍嫌平面等等,它甚至不是自足的,存在着文本内在的矛盾和困惑。但它是鲜活的,真切的,深远的,诚实的,它是我所读到的反映藏地生活和涉藏题材的作品中,最让人感到亲切的一部。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深植在我们的血液中,这使我在读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时拥有了穿透汉语文本直视母族历史的第三只眼,一只隐蔽的眼。
作为一个具备完全的民族文化自觉和对故土家园有深厚情感的藏族作家,格绒追美在二十五万言的《隐蔽的脸》中表现出了他的文学“野心”,他要以这部小说为起点写出他的家乡康巴大地的神韵,对康藏近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做出史诗般的展示,进而对整个藏区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和生长,过往和现状给予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其实,这样的努力,有许多人已经做过,许多人已经做坏。有关青藏,有关康巴,可见的多是些被外界的期待视野所规训了的书写,藏区在这样的文字中看似瑰丽多姿,风情摇曳,实则浅尝辄止,面目全非,还有那些大量的所谓地域、民族文化的浮光掠影的展示……格绒追美不是这样,他做到了以文学的能指之笔抵达雪域高原的历史所指,所以,甚至可以说,我们可以拿《隐蔽的脸》当一本历史书看。
这样的深厚和沉潜,首先建立在作者对家乡水乳交融的情感基础上,可以说,格绒追美的文学世界离不开广袤而神奇的康巴大地。西藏作家次仁罗布曾认真地对我说,你要评论格绒追美的小说,你必须先去游历他的家乡。我深以为是,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完成完整的康藏之行。但我从格绒追美的笔下清晰可辨地看到了他的家乡,看到了他身后的山,看到了他脚下的根——他的创作和生命深植的根。格绒追美出生在四川甘孜的牧民之家,小说中的那些河谷村庄曾经是他长大成人的真实居所,而之后的求学求职,他虽走进了城市,但这只使他具备了在一定的距离外审视故土的眼界和立场,而并未削减他对过往的人和事的热情和眷恋,他的情感视野从未离开过生养他的康巴山水,他创作的起步,就是从歌咏家乡开始。多年来,他以一颗敏感多思的真诚之心,游走在故园和城市之间,在乡野村史和浮华现实之间的缝隙中,思考着“父亲”“母亲”们的故事,找寻着一条通往前生往世的村庄之路。他的执着坚持、厚积薄发使藏民族幽深玄奥的历史之门徐徐打开,露出了被时间之尘遮蔽已久的脸,真实的脸。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惟一的正解。所有的历史,都是在真相和幻影之间,在既定和生成之间摇摆不定的。面对一张“隐蔽的脸”,述说其实是无力的,怎样深入的表达,勾勒的也只能是半张脸,甚或连这半张脸也是模糊不清的。我相信格绒追美对此有着极为自觉的警醒,他是机敏的,他巧妙地采用双线结构交叉叙述的方式,一条线索是现实时空中定姆河谷村落中一个家族的兴盛衰亡,各色人等的生死爱欲,而另一条线索是藏地神子“我”对整个定姆河谷、定曲河岸的俯瞰,对所有故事的统观,是自由的精灵之身对雪域高原的人和事、大地和天空、云彩和雨露的穿越,是对所有的现实和飘渺、幻想和真实、历史和虚妄的疑惑、质询。因为有了这一条线索,有了如此匠心独具的关于“我”的人物设计,贯穿始末的象征、隐喻的意味使文本与曾风靡中国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浪潮遥相呼应,同时也形象地阐示了藏文化其本质上与现代文明的不同,那就是:在把握历史,言说世界时,藏人往往是以神话的传说的种种神迹和预兆的途径完成的,他们更愿意以“梦”解释现实,以心象抵达物象。
不仅如此,神子“我”的设置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形象读者再一次深陷于哲学的痛苦:存在是尴尬的。神子穿越一切,观古知今,但他无法获得肉体和语言,对于他人,对于世界,“我”是不存在的,而一旦“我”幻化为一个叫“夏超晋美”的俗世中人,所有的前世记忆便完全割断,对于今生的他,曾经的“我”也是不存在的,成了难以言说的他者。肉身和灵魂的交融永无完成之时,那么,“哪里才能找到我最终的歇脚之地?何处是我灵魂孤旅的归宿?”
因此,藏人对信仰生命一般执着的追求或可得出答案,短暂的肉体生命其实是在黑暗的混沌中,只有以灵魂不灭的信仰贯穿肉体生命,肉身才能安妥,才能澄明,同时,灵魂有了肉身的依托,才不至于像漂浮的幻影,才能成为可以言说的存在。
与哲学的高度相匹配,《隐蔽的脸》有宏阔的写实结构,它以“风轮”“风语”“风马”三篇章分别记述了藏区历史的三个重要阶段:土司统治时期,解放和解放后的革命时期,经济开放时期。定姆河谷是封闭而偏远的,但正如广大藏区许多的村镇一样,它并不因为地域和文化的双重边缘而幸免于现代化车轮的碾压和冲击,它已经历过苦难伤痛的震动,如今又走进了别样的惶惑和迷茫。如何展示一个民族一路踉跄而来的伤痛历史,对此格绒追美的态度是不做回避,也未虚化。他对政治权力介入导致的藏人价值体系的动摇,经济浪潮冲击引起的信仰体系危机,民族的边缘文化生存状态在强势的外力作用下已经发生和还要发生的一切,都表现出了深刻的认识,他的历史反思是审慎的,内蕴的,但也是鲜明的,富有批判性的。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活佛、头人、僧人还是村民,都经历了属于自己的苦难,苦难远非一人一事,而是从个体心灵延伸到整个群体的民族命运,是雪域高原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下的欲望、挣扎、毁灭、堕落、重生的故事,是在旷古的苍凉和无奈中,百年的痛苦与寂寞中,寻找家园的流浪长旅。
难能可贵的是,格绒追美在小说中直面苦难,袒露伤痛,但他并没有止步于表现苦难,陷入到苦难叙事的泥潭中;面对一段独特幽暗的历史,他也没有以肤浅的愤激的控诉,宣泄自己的话语权,充当时间的审判官。任何人都无力拨开历史的重重烟雾,还以本来面目,指明康庄正道。既如此,与其做愚蠢而徒劳的虚设与推断,不如从已经完成的时间和事件中,发现那些历经劫难但颠扑不破的恒定的美和活力,那些历久弥新的精神和信念。格绒追美正是这样做的,他以涅槃般的文化反思,建构了对一个民族个体苦难的超越。小说中所有郁结的忧伤、疼痛、苦难,最后都在面对浩瀚文化历史时空的憧憬中,被升华为一种向上的力量。这正是藏族文化的精神质地,它在外来暴力下确曾有过萎缩,它在金钱迷惑中也许正在蜕变,但没有什么可以从根本上动摇藏人对自然、人性、神性、信仰的追求。
正因如此,格绒追美是焦虑的、伤感的,但却不是虚无的,颓丧的,他以一颗刚性而柔软的悲悯之心抚摸着母族故土的疼痛。太多的山川河流千疮百孔,然而不灭的是大地上生命元初的美,轮回中必然会生长更美好更合理的梦想和现实。虽然“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但对精神彼岸的探寻将永无止境,这是一个村庄生生不息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繁衍生长的命脉。就这样,《隐蔽的脸》用贯穿文本的大叙事和随处可见的鲜活的小细节完成了诗化的历史建构。
读《隐蔽的脸》,最不能忽略的最扑面而来的就是语言。这倒不是指它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华丽、空灵、铺排、雍容,而是说这样的华美形式所蕴含着的独特意味,这种意味所表达的精神质地。阿来评价《隐蔽的脸》说:“用汉语写藏人生活,常痛惜于那些似乎用藏话才能表达的意味的消减。这部小说却用汉语把藏人对自然、对神性、对人性的知与觉表达得如此细致真切,让我深受鼓舞。”这话甚为恰当地说明了《隐蔽的脸》语言运用的妙处所在。这使我相信,在藏族作家中取得了最高文学荣誉的阿来确是懂藏语的。是的,几乎只能用藏语才能表达的意味,用精妙的汉语表达出来,这就是格绒追美不同于其他涉藏题材的作家的地方。他的语言里有血浓于水的母族记忆,有无法抹杀的民族胎痕,有无法仿制的康巴地域特色,汉语的汪洋大海丝毫没有淹没他一个藏人的口吻语气,这种口吻语气的地道娴熟和精妙每每让我在阅读中忍俊不禁,掩卷而笑,但这种会心一笑却不足以与外人道也——有时候,那些令我唇齿生香的话句其实根本就是母语的直译。我是多么欣喜地看到,原来,母语可以这样的形式走进汉语,使之最纯粹的意味奇妙地存活在另一种语言载体中。同时,不用担心外族读者会对这样从母语“直译”、“意译”而来的汉语产生阅读隔膜,实际上恰恰相反,好的东西总是共通的,连接最广泛的人性的。《隐蔽的脸》以其精湛的藏、汉语的化用和汇通,激活的是更多的人久违的乡土记忆,它本身的优美、华丽、流畅、准确更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语言,格绒追美自己讲过来自民族的传承:“数千年来,从祖先嘴里流淌出的是山泉、珍珠般充满诗意的语言。这语言据说得到过神灵的加持。充满了弹性、灵动,如珠玉扑溅,似鲜花缤纷,常常让人心醉神迷。特别是说唱雄狮大王格萨尔的传奇故事时,那语言的魔性像一片云雾罩在你整个身心之上,使你飘盈在神话的云烟中。”读完《隐蔽的脸》,我相信格绒追美“珠玉扑溅、鲜花缤纷”的语言也是接受了神灵的赐助的。
评论《隐蔽的脸》是一次对我来说多少显得奇怪的写作过程,我把我心领神会的感受写下来时,却发现它与我之所思其实相去甚远,在这样一部藏人视角、藏人知觉的著作面前,我仿佛第一次对自己的汉语表达产生了怀疑,我无力用手中之笔撩开蒙在《隐蔽的脸》上的迷雾。但我又想,谁又能真正看清那张完整的“脸”呢,或许,我的无力也正是作者格绒追美的迷惘?他极力想要厘清历史,抓住真相,然而,旧的迷雾弥漫不散,新的还正在滋生着,被创造着。更或者,现世并不需要你揭露幻影背后的真实,恰恰相反,“隐蔽的脸”才是外界的期待。这正如小说中所写道,改革开放开辟旅游业后,定姆河谷被打造成了全球盛传的“香格里拉”,外面的人不断涌来追寻香格里拉。“这使活佛和村民们疑惑、不安:天上的香巴拉怎么会是现实的存在,它什么时候来到了人间?那我们是不是已经生活在佛的净土了?”
是的,还怎能言说这无法言说的尴尬?到底是谁,给雪域高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为什么一方面热衷于自欺欺人地制造幻象,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地想要寻找真实?
小说的结尾,神子经历了尘世轮回后,终于又抛弃肉身躯壳,远走高飞了,因为“我”“不想听到凄楚的哭泣,不愿看见有人在偷情在盗窃在寻欢作乐,甚至还有人计划着谋财害命,诡计多端者的脸上笑意正浓——”“我”对自己说“我要远离这是非不分、罪恶渊薮之地”。
神子可以逃离,但人间永远炊烟正浓。“如果天空倾斜起来,你没有办法找到一根撑木,将它擎起。如果人心离人走远了,那么,也没有办法找到一根撑柱吧?就像天空自己变回来,走向平衡,人心也要靠自己走回来吧。”
白玛娜珍:《西藏的月光》
被西藏的月光照耀着的人有福了。我无可抑制地写下这句话,因为这是我读藏族女作家白玛娜珍的散文集《西藏的月光》时不断涌上脑海的一句话,不断激荡着心灵的一个感受。娜珍说:“此生我老了,我的余生,将在拉萨结束,就像之初,在拉萨诞生。这是每个热爱拉萨的人,自始至终的心愿。”她说:“无论去任何地方,捧着我的心,我只想回到西藏。”
从她的月光撩人中抬起头,我的窗外是城市日夜不息的喧嚣,和一年比一年更猖獗的酷热。那么多匆匆的人流车流,他们要去向哪里?他们是捧着心,去向一个能给灵魂以清凉慰藉的地方吗?在他们心里,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吗?
在我的心里,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吗?为什么,太多的港口,最后都成了驿站?为什么,终点又成了起点,归人终是过客?为什么,没有一处风景,一片海,一座山,是最后的眼睛和心灵想要看到、皈依的家园?也或者,不是没有,而是它还在前方某个未知处,等着我们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完成惟一的相遇,惟一的停靠?
像一只倦飞的鸟鹊,绕树三匝,却无枝可依。这是太多的现代人共同的心痛。
但白玛娜珍却可以说:“啊,西藏!我已洗净身上的尘土,请你伸开手臂!”
是的,在西藏的阳光照耀下,在西藏的月光沐浴下,一点点地洗掉身上的尘土,让灵魂焕发出原本的洁净和光亮,让生命拥有该有的欢畅和意义。这就是白玛娜珍的《西藏的月光》所娓娓道来的心愿。
白玛娜珍是无比热爱西藏的,她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西藏之美,写了在西藏生活的幸福感,安全感,西藏之美,美在慈悲、豁达、纯真,美在简单、快乐、自由。她多个角度不同侧面写了唯美唯善唯乐的西藏的人们:历经坎坷而又无比美好、豁达,善良的外婆,快乐无羁的女友黛啦,公交车上扭着身子跳舞的司机和售票员,保护误入男厕所的女孩的康巴汉子,劳动中唱歌嬉戏的藏族民工,以及在游戏中快乐地学习的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美好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些西藏的土地和文化滋养出来的人们,他们生活在缺氧的高地,但获得快乐和幸福感的心灵能力却是独有的。他们的健康和阳光让人看到了最心怡的绿色和希望,所以娜珍发出了不无天真的感慨:“张爱玲如果在这里,在拉萨的人群中,她的人生也会被感染得笑逐颜开吧?”
然而,虽然充满艳羡,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全部的西藏。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西藏”,这是生活在西藏的人们日日所感知的现实,也是作家必须要冲破所谓“最后一片净土”的思维惯性所要面对的真实。娜珍热爱西藏,但她对此保持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她并没有沉浸在千年的牧歌想象中,假装看不见被现代洪流裹挟着的西藏。《西藏的月光》尽情展现了西藏的“净土”之美,但同时,也对今日西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她在《百灵鸟,我们的爱》中沉痛地叹息:“没有酷暑,没有蚊虫,没有贼的拉萨,消失了。”《被红尘裹胁的洛桑和曲珍》中她直面物欲横流的现实所导致的藏族青年的信仰危机和人性迷失,写了洛桑和曲珍离开故乡在拉萨的红尘欲海中随波逐流,挣扎毁灭的故事。《央拉和央金》叙述了同样来自牧区的两姐妹到拉萨打工谋生的经历。当古老的牧业生活与城市文明已成为一种对立,这些乡下的女孩子进退两难,二者无法兼得。其实,她们的梦想很简单:想要像城里人一样洗上热水澡,看电视、穿时尚的衣服,想有钱替父母治病而不必因此去乞讨……进城后,央金积极学汉语找到了外面的活,央拉做了保姆去往成都。但她并不开心,她困惑于城市生活的冷漠和疲惫,她说:“他们穿得很好,这里冬天也开花,为什么他们不会笑呀?”她开始想念拉萨的太阳,想念牧场的空旷和遍山的花儿,想念童年那自由自在的放牧生活。回到拉萨后,央拉表示再也不去成都了。她形容城市是让人身体流汗,心脏结冰的地方。这个单纯快乐的牧羊女,最终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无法在其中展开自己的新生活。
最后,央拉辞别拉萨回到了高山牧场的家中。但问题是,在那里,她还能重新开始曾经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生活吗?还有那样的生活,驻留在她今天的家乡吗?白玛娜珍感慨道:“也许央拉、央金和我,我们今生只能在城市和牧场之间,在心灵的安详和城市的浮华,在传统生活和现代文明之间痛苦徘徊。假如有一天,我们内心的信仰,我们世世代代对生命的理解,人们的习俗,能够被发展的社会所维护,幸福一定会降临如同瑞雪和甘露……”
《村庄里的魔鬼》里写:“城市文明,像潮水般涌来。但挣钱付出的代价是告别一种自然而人性的生活方式。”这类主题中,《没有歌声的劳作》是最见力度的一篇散文,白玛娜珍的笔触直指时下,关注底层,对藏族人赖以生存的传统的文化习俗和劳动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阵痛、裂变,对藏人在现下社会生活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表现了深切的忧患意识。
在市场经济的狂潮袭来之前,拉萨的所有藏式建筑都是由本地藏族人承建的。娜珍写到藏族民工干活干得很细致漂亮,同时“他们干得悠然自得,每天中午坐下来吃饭喝茶就要花去近两个小时,劳动时,他们当然还要唱歌。那些歌声和着潺潺溪水,时高时低,仿佛预示着我向往已久的那舒展的生活。劳动的快乐像一首诗,史诗,使这个民族拥有高贵的精神”。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逐渐地,拉萨的建筑工程基本由外来工程队承包,而藏族民工由于缺乏新技术和干活的松散状态,开始找不着活干,就算找上了,也是打下手。2007年,一个内地民工一天最低的工钱为一百元,一个藏族民工的日工资最高才四十元。如今在建筑工地和其他劳动场所,藏族人和外来人一样不苟言笑,甚至有着更战战兢兢的面孔。娜珍沉重地感慨:“市场经济,正在以它简单粗暴和急功近利的方式,将所有的劳动门类,沦丧为一种纯粹的生计,我们每个人,不觉中也已变成了组成它的一部分。伴随这种遥远的期望,动听的歌谣将永远消失。而没有歌声的劳动,剩下的,只有劳动的残酷;同样,从劳作中分离的那些歌谣,保护下来以后,复原的只能是一种假装的表演,而非一个民族快乐的智慧。那么,我们该要什么呢?是底层人们的活路,还是他们欢乐的歌谣?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两者竟然成为一种对立,而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的全部真实与荒谬。”
是的,这是今日西藏所面对的真实与荒谬,也是当下极具普遍性的一个社会境遇:放眼望去,神州大地处处充斥着煞有介事的文化保护和虚假的民俗表演,而文化、民俗之所以存在的根基却已被抽空,田园乡村一日日荒芜,传统的劳动越来越不能给劳动者带来物质的满足和心灵的安逸,更奢谈什么劳作过程中的欢愉。也许,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面临的尴尬境遇,富足和进步总是要以付出优美的传统、以人心的满目疮痍为代价。任何人无力在现阶段内使其二者兼得齐美,作家要做的可能只是以手中之笔尽力捕捉心灵之痛,为山川河流千疮百孔的今日之现实留下一份文字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在近二十年来绵延不绝地出现,在当下常见得几乎成了文学的又一母题,但在白玛娜珍的笔下,因其特有的藏地特色,更因其感情的忧愤沉潜,对转型期社会的文化反思充满了一种苍凉的人生况味和历史惆怅,显得尤为深沉有力。
白玛娜珍就是这样一个富有写作使命的作家,她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书写表现了自己的现实关怀立场。西藏的月光给予她的不仅是清洁单纯的心地,更有敏锐多思的头脑,和执着进取的精神。虽然在《西藏的月光》一书中,她也娓娓细述了种花养狗的经历,与子嬉戏的快乐,女友来往的情谊,“爱欲如虹”的痛苦,但她从未落入一些女性散文写作风花雪月的窠臼,而是深层地表现了一个女人生命中最真实的喜乐和隐痛,也表现了一个生活在西藏的现代人在当今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复杂思绪。娜珍以饱含着生命汁液的文字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内心的困惑、纠结和忧戚,她发问,她思考,她真诚地记录了自己与时代同步的心路历程。也许,在当今涉猎青藏题材的诸多作品中,她的《西藏的月光》算不上是深刻的,在姹紫嫣红的女性写作园地里,她也远未形成圆熟的个人风格,然而她是独特的,她的可贵就在于她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作家,她捧着一颗心行走在一种对永恒困境的探索之路上。
白玛娜珍说:“我的作品在纯情中潜伏沧桑,在沉淀中青春依然摇曳。我喜欢这样的创作状态和人生状态。《西藏的月光》就是这样一本文集。”她的自我评价是中肯的。因为有生命的投入,有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西藏的月光》字里行间潜伏着沧桑,渗透着饱含生命真情的忧思,又因为有西藏所赐予的简单洁净和明朗乐天,娜珍的创作更表现出了纯情的质地。她的文字促人深思,但不会使人悲观,她表现更多更用力的依然是西藏的阳光灿烂,西藏的月色纯净,是生活在西藏这片神圣古老的土地上的人们不灭的精神和信仰。她的写作为今日西藏留下了纯美的文字留影,也为西藏外的红尘世界提供了一份有参照价值的心灵生活的坐标,是西藏书写中有重要意义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