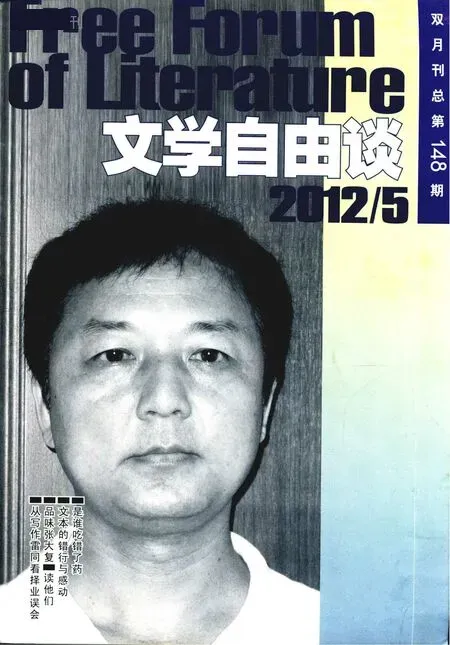文本的错行与感动
●文 谭 湘
文学作为一种抒发与表达,在文体形式上的细致差别不过是一种所谓成熟的艺术形式必备的格式化的渠道或者习惯,在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情绪、挥洒某种情愫,宣泄胸中诸般块垒,抑或演绎头脑里始终在意识与潜意识边缘上的白日梦样的症结的时候,实际上采用什么约定俗成的具体格式,经常存在着相当的偶然,时代的偶然,个人气质的偶然与经验的偶然。这些偶然的综合造就了作者在彼时彼地孕育而出的文学文本的叙述脉络与语言样式,以文字凝固住了他一向在流动与转换之中的印象与情怀。正是因为这种文本选择中的偶然性,当读者反过来以文本为开端去反向揣摩作者创作动机与情感特征的时候,文学文本的文体意味,所能提供出来的线索,就既是重要也是被限制的了。
一个在童年时光里暗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的女主角米拉的中国男人,在几十年以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转换的动荡中,不期然地回到了那电影的拍摄现场与历史故事的发生现场,他如梦方醒,他百感交集,他心旌摇荡,他恍然大悟。恍惚、朦胧与确认的发现过程与喜悦心情,使他像是在现实里做了一次打通自己前世今生的时空漫游,他将他真实的感慨与思绪用小说的形式做了一次抒发,形成了一个小说文本。
这是陈河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所能提供出来的让读者可以进行揣摩的反向索引,这个文本对于我们去怀想与体味作者的米拉情结,去实证主义地分析他童年梦中电影与事实的对位与错位,可谓重要,又远非惟一。在这异域场景中的新奇感受被老套的故事结构涂抹并存有不少陈旧气息的时候,我们马上会考虑一个仿佛是属于阅读文本意义之外的问题:作者为什么用了小说而不是散文的形式?
这种貌似蛮横的疑问实际上也是有自己内在的合理性的,那就是在现在的小说文本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实证主义的记录,看到了为了将自己实际的经验容纳到小说这么一种形式中去而不无勉强地去制造情节的费劲与努力。这个其实更适合用散文讲述的文学地理学、电影地理学的体验,以作者曾经在内地当过专业文学创作者的习惯,被用小说传达出来,像是在一件淳朴的情感场上罩上了一层娴熟的恋爱老手、暴力战士的外衣,这件外衣虽然符合商业化的阅读要求,但是却比较普通,看起来某种眼熟而并不十分新鲜,也可以说是并不完全合身;在既有的童年情结之上附加上去爱情与性,附加上去战争与牺牲,这种好莱坞式流行文本的编剧路数,实际上妨碍甚至冲淡了作者对自己那种童年情怀的珍视,也使得平淡生活中令人震惊的死亡在故事里变得仿佛水到渠成一样失去了张力。作者在创作自述里说现实中女药剂师的死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他将寄托着他的诸多情怀的伊丽达的死亡写成了不出所料的正常(我在惋惜之余宁愿相信那是一种叙事语调,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漫不经心或者曾经沧海)。
《宁死不屈》的故事是一个英雄的悲剧。阿尔巴尼亚这一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确曾被我们一厢情愿地视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意义上的兄弟,“小独裁者”恩维尔·霍查也确乎曾经和中国很近后来又很远;但是,二战中的苦难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承受得更为深重,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无私地援助过太多太多的阿尔巴尼亚也绝没有我们饿死的人多!中国人自己的苦难,比阿尔巴尼亚人从德国人那里承受得要大得多,惨烈得多。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资本去怜悯别人的。一些时候,怜悯确实是一种奢侈。我们在自己的可怜中所施予怜悯的对象,不仅占有了我们当年极其稀缺的物质,也更占有了我们当年的少年儿童的精神,乃至在时过境迁以后的这种偶然发现还能给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的作者带来发现之后的欣喜与激动。在那样既奢侈又混沌盲目的社会氛围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作者及由此而来的作者的童年情结,形成了这一族群作为成年人的白日梦中的一种。这样在质地上属于散文品质的真实情怀,妨碍或者来不及更深入打磨的小说文本,从作者的创作自述里,我们都能看到端倪。
散文化的真实感情是陈河这部小说最原始的创作源泉,游记式的景象记录与日记式的默对内心,是陈河这一艺术创作的最真实的出发点。此外的小说语言、人物对话、小说结构和小说情节,甚至小说中的人物关系,都并非是这部小说最出彩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呈现一种比较平庸的面目。苛刻一点说,实现童年梦想的偶然带来的激动之情,文学地理学、电影地理学的发现,表达一种发现了自己的前缘今世般的激动,选择用小说这一文体实在并不是最讨好的形式。以为单纯叙说实际的经验似乎不足以支撑要有相当长度的细节呈现的需要,但却无意中让小说的情节伤害了最初的情绪与激情,让有点老套、媚俗的男女关系与战火噱头冲淡了作为创作动机的怀旧的心绪。事实上,小说中最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的部分是来源于现场的景色与感怀,这个阿尔巴尼亚小城在一个又一个晨昏中的细节,马路上的被磨得光光的石头的细节,石头墙壁上错落有致的缝隙中的茅草的细节,等等,才是这部小说最具有神采的刻画。作者心目中的阿尔巴尼亚女英雄的形象和现实中他接触过的阿尔巴尼亚女药剂师的形象的重叠与交叉,正配合了他在这小城的现实与历史中所望见的景致的相合与相异。这样的情致,用站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的散文笔致书写出来的话,也许比所谓小说会更有力量得多。在这里,小说的传奇性的结构需要和情节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作者充沛的现实情感的表达。
在现实中确有所感,在文学的真实契机启动的时刻,是用实话实说的散文,还是用结构故事的小说,文本形式的选择完全出于个人的习惯,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更合适于当下这篇东西,也是作者自己的判断;不过,那种以为小说比散文大,小说的空间比散文要广阔得多,小说也才更艺术的观念在中国文坛上也是广有市场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很多人,好像要搞文学就要搞小说,不搞小说就始终距离文学还远。情感与情怀的文学表达,即使再勉为其难也要用小说来装点一番,其后果之一就是小说的读者群急剧萎缩。实际上在很多文学大家那里,文本的样式在很多时候都是模糊的,博尔赫斯、黑塞的许多写作,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再给他直接戴上小说或者散文这么简单的帽子了。关键是它出之于作者生命的真情,而不矫揉造作,不为了所谓结构而牺牲内容,不勉为其难,只依循自然而然。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还在正常的艺术之为艺术、文学之为文学的范畴之内。事情只要还在这一步上,就至少说明这种表达在最基本的原始动力意义上是完全符合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初意义的。作者的确是有话要说,而不是无病呻吟,不是闭门造车,不是我们所谓的文学现实中屡见不鲜的远离文学本质的现实功利主义之作。陈河等海外华文作家们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为国内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他们身置海外,用以生活的钱是自己挣得而不是国家发给的工资,也不存有通过写作谋个一官半职的念想,远离了这诸多的功名利禄,再从事文学,应当说,更容易回到文学的本意上。这也是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比较值得一读的价值所在。他们的技巧和语言也许并不特别出色,但是他们至少是确有所感,没有许多内地专业作家们那种小说腔,没有商品订货式的制造气,也没有无病呻吟写不出硬写每年必须发表多少字才能完成任务之类的“压力”。
陈河们之所以近年被特别关注,其背景是中国内地文坛一些越来越背离文学本意的专业创作的苍白。相比之下,陈河们的创作倒像是文学写作者们源于生活的习作,虽然形式上或有不成熟乃至远离当下生活之虞,但是在本质上却属于文学的纯正品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如果不苛求陈河这篇小说中的传奇性和那些可有可无的对话,不特别纠缠性或暴力的噱头,其真实的文学情怀还是相当审美享受的。这是一个男人与生俱来就要经历的灵魂的冒险,更像浪漫的冒险。我们感动在中国文学的阅读经验中,能有陈河这样的文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