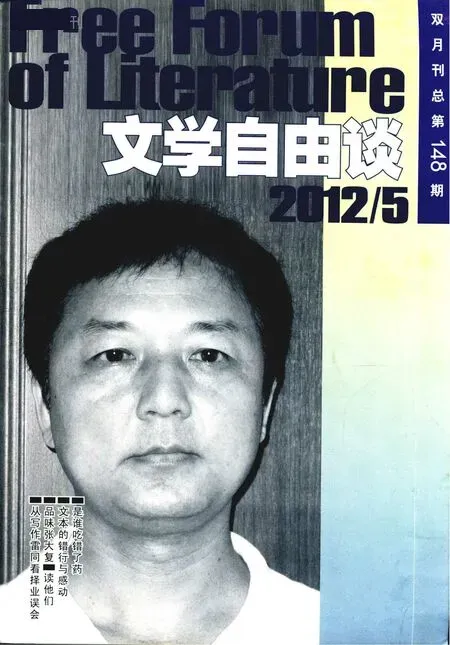品味张大复
●文/李国文
晚明文人张大复,字元长,江苏昆山人。生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死于崇祯三年(1630),享年77岁。
他的前半生,为戏曲作家。当时,在江南一带的梨园行里,此人举足轻重。因为戏剧界都熟知“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剧本的好坏,往往决定一出戏的成败。所以,好剧本难求,好剧作家更难得。演艺界人,虽谙熟声律,但不精通文史,下笔不了;一般文人,学问可以,对剧场艺术,却未必能通其门径而登堂入室,同样,也难下笔。因此,要求剧本既具戏剧性,又具文学性,这是磨合难度很高的创作。于是,作为文章高手,又是戏剧行家,堪称两全其美的张大复,便成为最佳人选。
《世海总目提要》称他:“粗知书,好填词,不治生产。性淳朴,亦颇知释曲。”由于他擅长编写传奇杂剧,颇有票房卖点,很受业者青睐。故尔四十岁前,他一共写了三十多部戏曲,平均一年两出,总量超过英国的莎士比亚。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些红过,火过的剧目,现在多不被提及,除专门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冷门学者,他是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剧作家。
这就是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了,文学也好,艺术也好,谁也不能自外于这个历史规律。严格讲,小说诗歌,戏剧影视,都是时令货,新鲜上市,光顾者多,时过境迁,拉架的黄瓜,就不值三文两文了。你自己觉得好,敝帚自珍,也许果然是好,字字珠玑,可时光不饶人,新陈代谢,物竞天择,后浪奔逐,前浪隐没,读者不买账,观众要退票的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也许你还活着,你的作品先你寿终正寝,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因岁月无情的淘汰,而渐渐式微,而终于完蛋,而被人遗忘,而画上句号,是中外古今作家的常规命运,谁也逃脱不了,谁也无可奈何。
西方有一个莎士比亚,东方有一个汤显祖,也就足够足够了,太多的不朽,其实倒是不朽的大减价,大甩卖。于是,作为戏曲作家的张大复,被人忘得干干净净,也属正常,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不过,幸而他的散文著作《嘘云轩文字》之中,一部十四卷,收文八百五十三篇的《梅花草堂笔记》,还真的被历史记住了。这部书时下不难找到,尚有人阅读,有人评介,有人褒贬,还有人争论,这样,他在晚明文学史上,认可也好,否定也好,得有一席之地。
四百年前的张大复,对当下那些崇尚浅阅读,喜好快餐化读物的人来说,恐怕是相当陌生的名字了。
应该说,这位作家,值得一顾,这部作品,值得一读。顾了,读了,能有多大的得,不敢保证,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得,是肯定的。何况此书不长,用一天工夫,可以通读三遍。第一遍,也许感觉一般;第二遍,你就会对他这些随兴而来,尽兴而止,自由开阖,率意放松,由数十字到百多字写成的小品,感到兴趣,感到亲切;第三遍,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漂亮文字,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张力,那“东关酸风射眸子”的动情篇章,那“风雨飘将去不回”的肆张意境,会让你欣然共鸣,击节赞赏的。
总之,他说不上是当时最好的作家,但也绝不是一个不值得一顾的等外品。
论文学水平,他无法与写《牡丹亭》的汤显祖比肩,论名声地位,也不能与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陈继儒相比。但在这部《梅花草堂笔记》中,我们读出他文章之潇洒飘逸,笔墨之本色自然,绝无晚明文人中间那股招人讨厌的腐儒味,拘泥迂拙的方巾气;其品格之高狷自好,其心地之质朴孤直,既非同时代那些标榜清高,灵魂萎琐的野狐禅,也无佯装超脱,行止卑鄙的山人气。他是个不结帮不结派,只有三两文友的作家,无人为他抬轿子吹喇叭,无人为他开研讨会众口一声阿弥陀佛,更无人为他出整版马屁文章赔钱赚吆喝。因之,他活着时就不怎么景气,死后当然益发萧条。再说他这个人,既无名震文坛的野心,也无追赶主流的壮志,能够无欲无求,远离热闹,躲避名士,枯守茅庐,写自己的小文章,圆自己的写作梦,也就足矣足矣了。
这等人,有谁会在意?有谁会在乎?小报记者挖不出他的桃色新闻,评论家估计也拿不到他的红包,各级领导很害怕他伸手讨要救济,当红作家生怕沾上了他惹来霉运,都拼命远离他。好在他知道自己是老几,心态也颇安然,这是我最钦服他的一点。其实,这也未必不好,人分三六九等,货分高中低档,作家也是存在等级差异的,名片上印上国家一级作家,你的作品该狗屎还是狗屎。是什么就是什么,本色才是最自然的。任何朝代,出类拔萃的精英文人,终究是少之又少的。若是像菜市场的萝卜白菜,论堆处理,那这个“类”,这个“萃”,基本上等于目前流行的这个文学奖,那个文学奖一样,多了,滥了,也就没有什么含金量了。
要知道,明末文坛之码头林立,之互相倾轧,之狗咬狗一嘴毛,之撕破脸相寇仇,之勾肩搭背抱团取暖,之淫靡成风色情泛滥……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不像话的一代,你想象有多紊乱,就多紊乱,你想象有多糟糕,就多糟糕,末日王朝所有一切败象,无不在这些文人身上充分表现。《金瓶梅》在万历年间应运而生,绝不是偶然的,正是那具形将朽坏的热尸上,才能滋生出来这种空前绝后的“恶之花”。
这样一来,在昆山兴贤里片玉坊的旧宅里,镇日枯坐着的张大复,你就不能不为之而生一份敬意。处于如此喧嚣的社会里,一个文人能做到不为所动,心无旁骛,进自己的门,走自己的路,该是多么的不容易。
有时候,上帝偏不让你做一件事,其实倒是在成全你,正是这种难得的冷遇,使他能够潜心于字句,凝思于文章,造就出与李梦阳、王世贞前后七子的主流意识不同,与耿定向、焦竑的儒学正宗不同,与公安三袁的性灵放肆,与竟陵派锺惺、谭元春的复古冷涩不同,与李贽疯疯癫癫的反儒率性不同,与屠隆的声色犬马浪荡成性不同,甚至与他心仪的好友汤显祖宏大抱负不同,当然与他时有来往的陈继儒“飞来飞去宰相衙”更不同的,属于他张大复的独特道路。
他的独特之一,就在于他不同于别人,他的独特之二,还在于别人休想同于他,他就是他,他是惟一的他,所以他了不起。
文学史的任务,就是把相同相似的作家诗人,合并在一个科目下概而论之。握笔一辈子的文人,最害怕什么呢?就是怕成为一个毫无特色,只能概而论之的同类项。长期以来,视张大复为明代万历年间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普通作家,多少有点低估,也太委屈他了。这位活着时默默无闻,弃世后接近湮灭的张大复,应该是明代晚期一位有份量,有创造,有个性,有才气的散文作家。因为他不追风趋时,不随波逐流,不邀名骛远,不经营造势,四十岁以后,恍若顿悟,放下戏剧,拾起散文,写出自由自在,写出心灵韵动,写出物我两忘,写出天人感应,写出大自然的色彩,写出小社会的斑驳,点点滴滴,流水往事,断断续续,浮云记忆……一句话,写别人不写之写,为别人不为之为,或许就是这位晚明文人最耐品味之处了。
然而,“五四”以后的周作人,对张大复评价很低,认为他在晚明文人中间,算不得一碗能够充饥的大米饭,而是一把用来闲嗑消磨时间的瓜子。
这等不伦不类的村妇式比喻,出自这位名流之口,实在好笑。但瓜子不敌米饭的评价,不看好张大复的情绪,昭然若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明清小品,行市见涨,一是《论语》派林语堂推崇英国绅士式的幽默,鼓吹袁中郎三兄弟之性灵,形成潮流;一是苦雨斋主周作人,其平实风格的文字,言简意赅的笔法,在文坛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及对明清散文的推介引导,不遗余力,遂蔚为风气,大行于时。在他看来,似满天星斗的明清文人中间,张大复的实力,实属平平,一般一般的作家而已。若以历史的大角度来考量,出类拔萃者从来是屈指可数的,因此,他的论断也不无道理。
在小品文写作和评论方面,周为重磅人物,毫无疑义。所以他的话,能起到语惊四座,一言九鼎的重磅作用,也是毫无疑义的。他不大喜欢这个张大复,视他与写《幽帘梦》的清人张潮,号仲子,字心来者,同属一路货色。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开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钱钟书,在天津《益世报》上拜读这篇讲演以后,写了一篇书评,对周作人不是无心而是有意的忽略,将晚明这位重要文人张大复,排斥在视线之外,对其创造性的文学成就,置若罔闻,表明他的歧义:“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映入眼帘);这个人便是张大复。记得钱牧斋《初学集》里有为他作的状或碑铭。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
那时的钱钟书还未成为扛鼎人物,不至于把他吓住。周作人没有作声,不等于他认输,没有马上回应,也是名流的一种矜持。隔了三年,1936年,他作了一篇《‘梅花草堂笔谈’等》文章,算是反应也好,算是答复也好,不指名地将此公案了结。当时,周作人为北大教授,钱钟书为清华学生,辈分之隔,名望之差,对于这位年轻人的质疑,既不能在意,又不能不在意。在意,那就等于视其为对手,太抬高了他;不在意,似乎默认自己确实理亏,才掩旗歇鼓的。
这就是中国大人物的弊端了,常常以为自己是皇帝,好武断,好大言,好一鎚定音,好说了就算。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你是陛下,你是金口玉言,你怎么说怎么是。可问题在于错了以后,这些大人物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认错。不认错,倒也罢了,可怕的,知道错了还坚持继续错下去,更可怕的,知道错了还坚持认为即使错也错得正确,一直错到死,哪怕错到棺材里,在盖上棺材板的那一刻,还要伸出一支手,翘起一根手指头,表示他的错,说到底,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你说,这要命不要命?所以,设想一下,政治领袖,经济首脑,军事统帅,地方诸侯,坚持错误,倒行逆施,害国误民,遗患无穷的话,老百姓该要用多少生命为代价,来为之救赎啊!
相比之下,周作人这桩文学公案,是小而焉之的花絮了。
周作人在这篇收进《风雨谈》一书中的文章中,反驳说:“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指张大复)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
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很难与一个明白却揣着糊涂的人讲理。明白人极好讲理,因为他明白;而明白人揣着糊涂,那就是一条不可理喻的犟驴。只是因为“他(指张大复)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只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于是,张大复被否定掉了。这使人不禁纳闷,我们评价一个作者,评论一部作品,究竟依据什么标准?个人喜恶,能成为一种接受和排斥的理由吗?
我同样也不喜欢这位以汉奸罪在南京国民政府老虎桥监狱坐过牢的周作人,但我从不因此不承认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散文成就。明人王世贞对有杀父之仇的严嵩,那应该是够不喜欢到极点的程度,但这位权奸的《钤山堂诗集》,在王弇州眼里,还能得到一个“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的客观评价。
看来,周作人对于这位晚明文人张大复的挑剔,近乎苛刻。
从他将其划入李北地一流,从他将其与张心来相提并论,说明周作人对张大复这部佳作的阅读,浅尝辄止的粗疏,是有的,皮毛之见的草率,是有的。这三个人,李梦阳(1472-1530),他死,张大复生,张潮(1650-?),他生,张大复死,可谓互不搭界。前者为政治色彩特强的官员,壁垒意识特强的诗人,非常之原教旨;后者为门第出身特棒的名士,兴趣爱好特广的玩家,相当的嬉皮士。而张大复,一个勉强考得的穷酸秀才,一个贫病交加的孤寒弱者,硬把他们三个捏在一块儿,真是老子与韩非同传,风马牛不相及。所以钱钟书说的未入尊目(’swim into his ken’),让周作人很不受用,可想而知。
钱钟书认为张大复在晚明文人之中,是个堪与张岱比肩媲美的人物。而“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这句话,本是周作人对张宗子,即张岱所著《梦忆》的评价,钱钟书将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记》,抬爱到可与之平分这荣誉的高度,自然不合周作人之意,他说,“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一口回绝了钱钟书。
写《陶庵梦忆》的张岱,比之写《梅花草堂笔记》的张大复,确实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得到更多的读者认可。但是,生于1597,死于1679的张岱,与生于1554,死于1630的张大复,相差半个世纪。时代不同,家国不同,命运不同,活法不同,对作家文章的优劣,对作家思想之高低,存在着无法计量的影响。我们可以将鲁迅与周作人放在一起讨论,因为他们曾经生活在同一天空下;但张大复和张岱却无法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一死于崇祯三年,明尚存在,一死于康熙十八年,明已灭亡。国之亡,国之未亡,对有心有肝,有血有肉的中国作家来讲,大有干系。这大环境的变化,非同小可,对于作家来讲,做顺民还是殉国,性命攸关;对于作家的写作来讲,谄媚新朝还是效忠故国,生死攸关。正是明清鼎革的危亡意识,使得张岱的形象思维得以高度升华,论文学水准,论文字功力,张大复未必不能与张岱旗鼓相当。要求张大复生出张岱那种家破国亡的黍离之感,改朝换代的亡国之恨,晚景凄苦的失家之苦,穷愁暮路的悲怆之情,那是荒谬的,这就是自视甚高的周作人,自信太过的偏见了。
作为随笔,求其精,作为小品,求其短,当然是第一位的考虑。但是,为了精萃,而忽略华腴,难免削足适履;为了短小,而不敢铺陈,那就是方凿圆枘了。所以,螺蛳壳里做道场,应该有举重若轻,吝墨似金的用心,应该有浓而不酽,淡而不白的本领。张大复在这个方面,一直受到当时人的认可和尊重。汤显祖评价他的嘘云轩文字》,为“近吴之文得为龙者”;钱谦益称赞张大复,“其为文空明骀荡,汪洋漫衍,极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诡于矩度,吴中才笔之士,莫敢以雁行进者”。
试举其写雨的两文为例,一曰《南庭》:“云情靉靆,石楚流滋。麦鸟骇飞,蝼蟈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草下,张口噤舌,若候雷鸣。狂飚忽卷万马奔沸,疏雨堕瓦,忽複鸣琅。百道金蛇,迅霆如裂。气散溽收,浮腻亦敛。灯火青煌,南庭寐寂。撑颐解眠,故自悠然。”不足百字,将一场大雷雨的始末,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景。其壮观的来势,其强烈的动静,其陡然的结束,其晚净的淡定,使人产生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现场感。
一曰《雨势》:“大雨狂骤,如黄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鸣水底,砰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龙漫吟,如伐湿鼓。电光闪闪,如列炬郊行,来著门户,明灭不定。仰视暗云,垂垂欲坠,道上无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长啼深林,鬼啸云个而裂垣败屋之声,隐隐远近间。雨势益恣,每倾注食许时,天辄明,旋即昏暗,如盛怒狂走,气尽忿舒,稍稍喘息,而后益纵其所如者。此时胸中亦绝无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风波之民欤?”同样一场雷雨,前者是雨在人外,得以从容观察,心态安然,后者是人在雨中,仓卒应对,狼狈不堪。前者是轰然而至,欣然而去的一场轻喜剧,后者是恶神天降,灾难临头,不知伊于胡底的悲剧。张大复的笔下,数十字,百把字,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引人入胜,而且,用字措词,平白如话,无一字可易,无一字多余,堪称绝活。
假如,你要知道他是一位盲人的话,我想你更会为之动容。
在中国所有故去的和还健在的文人中间,他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活得最为艰难者,大概也是生存状态极不佳之人了。一个要拿笔写字的文人,眼睛突然瞎了,没有阳光,没有色彩,当然也就没有白昼,只剩下无穷的和永远的黑夜,你说他怎么办?谁都想不到,我估计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这个张元长,既不自杀,也不搁笔,而是一天一天地坚持着活下去,活得有滋有味,而是一字一字地坚持着写下去,写得精彩纷呈。虽然,你可以想象他该有多难,该有多苦,但是,这个看起来极弱的人,实际却是个极强的人。我觉得他的生命力,够结实,够坚韧,哪怕人被拧成麻花,心被碾成面饼,也不认输,更不断气,不但挺住了生理和心理的压力,更经住了精神和物质的煎熬,而且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在晚明文学史上留下自己深刻的脚印。
据汤显祖《张氏纪略》:张大复“为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废。至云母子之间,徒以声相闻者十四年。母病时,以手按母肌肉消减,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犹喘喘好语曰,恨儿不见吾面,犹未有死理也。斯语也,闻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与无长目,不可得矣。有子铁儿而殇,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晓书传大义。所谓闺阁中钟子期也。为孟家妇,几年而复殇。天之困元长也,不愈悲乎?凡此数端者,客以为何如也?”
张大复,老天实在够虐待他的。四十岁前,他就以多病著称,认识他的人,他认识的人,都视他为病秧子或药篓子,据他《病居士自述》中所陈述的病情,至少罹患着以下数种慢性病:一,心脏系统有点问题,房颤或是心律不齐的“病悸”。二,血液循环系统代谢失调的“病肿”。三,胃肠消化系统炎症的“病下血”。四,以及“病肾水竭”的肾炎或者肝炎。而五,最为可怕的视网膜退化,多年以来“目昏昏不能视”,最终导致失明。于是,四十岁后,张大复,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盲人了。
然而,他挺得住。自号病居士,以乐观精神对待自己的疾患。客谓居士曰:‘子病奈何?’居士曰:‘固也!吾闻之师:造化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未老而化物者,且息我,我则幸矣,又何病焉?居士块处一室,梦游千古,以此终其身。’”然后,自号病居士”的他,更进一步阐述:“木之有瘿,石之有鸜鹆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天。随生有言,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传其形。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吾每与圆熟之人处,则膠舌不能言,与骛时者处则唾,与迂癖者则忘。至于歌谑巧捷之长,无所不处,亦无所不忘。盖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怜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与为友,将从其少者观之。”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眼虽失明,只要魂还在,心不死,文学就不会亡。冲这一点,对这位盲人作家,值得我们脱帽礼拜。
他是弱者,然而他比强者更强地打点着他的文学,诚如西谚所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的同时,也会给你打开一道门。这个张大复,眼虽失明,心却明亮。以他写的有关蔷薇两题,就可以看到这位盲人作家,是怎么样用心来感知这个世界的:
一曰《读酒经》:“数朵蔷薇,嫋嫋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气浓远,举酒五酌,颓然竟醉。命儿子快读《酒经》一过。”
一曰《蔷薇》:“三日前将入郡,架上有蔷薇数枝,嫣然欲笑,心其怜之。比归,则萎红寂寞,向雨随风尽矣。胜地名园,满幕如锦。故不如空庭袅娜,若儿女骄痴婉恋,未免有自我之情也。”
他失明的眼睛,看不到蔷薇叠彩,但“香气浓远”,飘然袭来的芬芳,却能使他感到蔷薇的“嫣然欲笑”,“嫋嫋欲笑”,感到蔷薇的“骄痴婉恋”,“自我之情”,“感到”和“看到”,是两回事,看到的,是平面,感到的,是立体,这种应目会心,神与物游的通灵境界,这种着墨不多,言意不尽的缱绻文字,你会觉得,他的双目失去了视力,他的心灵却无微不至地伸展到方方面面,延长着他的味觉、嗅觉、听觉、触觉,扩大到足以覆盖他体外所有的枝枝节节。现在你所捧着这部《梅花草堂笔记》,分不清其中篇目,哪些是失明前写的,哪些是半失明状态下写的,哪些是他失明以后口授而他人笔录的。浑然一体,难分轩轾。
我一直在想,张大复所坚持的纯美自然,所追求的质朴本色,所在意的洁身自好,以及汤显祖赞他的“天下有真文章矣”的“真”,成为他的人生信仰,成为他的行动指南,虽百病缠身不低头,虽一片漆黑不自馁,也许是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明末那个极失败的社会,那个极不可救药的文坛,在精神上的唾弃和行动上的决绝吧!他有两篇写月的文字,可以进一步地读到他的内心,他的向往,他所要构筑的文学天地,他所要达到的文学目标。
一曰《独坐》:“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无触之风,何声既烬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一曰《月能移世界》:“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今夜严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华可爱。旦视之,酱盎纷然,瓦石布地而已。戏书此,以信茂齐之语。时十月十六日,万历丙午三十四年也。”
也许因为这生活太沉重,这日子太琐碎,这现实太困惑,这人间太复杂,所以,月明之夜,给人们带来朦胧的美,隐约的美,含蓄的美,恬静的美,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美,不仅遮住丑恶,隐去肮脏,不仅化腐朽为神奇,使平凡成瑰丽,还能使我们“忘我之为我”,生出虚无缥缈的幻觉,得到美的享受,美的满足。张大复在明末文人当中,别树一帜,走的这条唯美主义的文学道路,岂是那些当时的,后来的,蝇营狗苟的凡庸之流,追名逐利的干谒之辈,淫佚无耻的声色之徒,阿附权贵的文彘之类,所能理解,所能企及的。
汤显祖也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他的《牡丹亭》,就是一部唯美主义的杰作,所以,其实来往很少的这两位文人,却是真正的心灵上的知音。
虽然,他的努力,他的追求,他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世界,你也许并不羡慕,因为收入和支出简直不成比例。当代中国作家,贼尖贼精,才不肯做这档亏本买卖。但是,他的这部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梅花草堂笔记》,所达到的美学高度,却是我等视觉很好的文学人,使出吃奶的劲,也休想望其项背的。
因为第一,相当草包的我等,腹中实在很空。
因为第二,相当脓包的我等,骨头实在很软。
还因为第三,设若我等落到张大复这种举步维艰的无尽黑夜之中,能自强而且体面,能安之若素而且从容不迫,写出来一部洋洋洒洒的《梅花草堂笔记》吗?恐怕先就被那永远的无穷的黑暗,压倒压垮了。
现在终于弄懂,周作人之所以不认可这位明末的文学大师,观察此公一生行止,也就了解其坚不认可的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