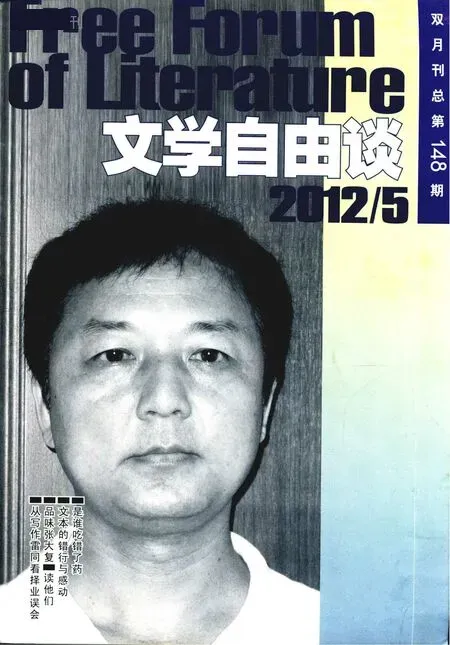从 写作的雷同,看 择业的误会
●文 唐小林
读罢2012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佚贺集辑的《“英雄所见略同”又一例》和该刊2012年第4期上发表的倪红《〈“英雄所见略同”又一例〉之我见》两篇文章,我真的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作为原甘肃省作协主席的高平和原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的晓雪,均是中国文坛上级别不低,享誉一时的著名诗人。但两文引录的这些“诗作”,让人怀疑,二位老先生是不是年轻时就入错了行,以为自己拥有诗人的才华,而误入了文学圈。我真的想说,本已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二位诗人一定要注意身体。以目前这样枯涩的文笔,拜托你们就千万不要再这样劳神费力,冥思苦想地写什么诗,自己为难自己了。要知道,写诗不是演戏。真正的诗人,并非要像娱乐明星那样,随时都必须保持频繁的出镜率,才不会被读者遗忘。写不出就大可不必去硬写,诗人并非老中医,头发越白,胡须越长,就越受追捧,顶礼膜拜来问诊挂号的人就越多;更不会像地里生长的辣椒,越老就理所当然地越红。如果自己本是一个写了几十年诗歌的平庸的诗人,就千万不要“不甘平庸”,以为自己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能跟年轻人一样激情喷发地写诗。“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当今的中国文坛,有几个文人能够有庾信这样的天赋和文才?
从倪红的文章中,笔者得知,晓雪与高平近年来写了许多首“两行诗”,并先后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由此看来,二位先生都似乎是笔耕不辍,非常勤奋,产量甚丰的诗人。但通过倪红在文章中的对比和说明,我们才知道,两位在诗歌写作时往往又像是在投机取巧。这就是,互相“学习”,并将自己若干年前发表过的一些诗作,稍加整容就又拿出来重新示人,发表在各种报刊上。这种自我重复,相互复制,简直成为了二位乐此不疲的一种诗歌“创作”游戏。照这样的方式来创作的诗歌,无异于就像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工业化生产。好诗本是心中出,试想,倘若他们不是曾经的省作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在文坛上浸染了那么多年,而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诗歌写作者,像这种既无生命激情,又无艺术性可言的“诗歌”,能够轻而易举,并且接二连三地在报刊上发表吗?如:“开了会落的花才是真的鲜花,永不凋谢的花肯定是假的。”如此枯燥拙劣,如同废话,毫无文采的文字,哪里谈得上是什么诗歌?这分明就是对邓丽君的歌曲《何日君再来》中“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拙劣的移花接木。在我看来,高平和晓雪诗歌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现象,恰恰说明高平和晓雪两位诗人已经陷入了一个近乎荒唐的写作怪圈。他们错误地把写诗当成了克隆技术的表演。在他们的笔下,流露出的往往不是诗人的激情和才情,而是毫无诗歌写作水平的人摆弄出来的一连串僵死的克隆文字。这里不妨来对比一下他们的如下四首两行诗:一、不在于到达终点,而在于途中的风景(高平)。不要只想着目的地,而忽略了途中的无限风光(晓雪)。二、没有奇思,不会有妙语(高平)。没有奇思妙想,哪会有佳作杰构、格言警句(晓雪)?三、如果回应犬吠,就加入了犬的行列(高平)。如果你回答疯狗的狂吠,自己岂不降为它的同类了(晓雪)。四、大人的语言是社论,儿童的语言是诗(高平)。所有的大人都不如一个孩子,因为他讲的是真话,是诗(晓雪)。
作为走南闯北的人来说,大概会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在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山谷中,沿途的风景非常优美,但许多来此旅行的人,总是来不及仔细欣赏就匆匆而过。于是,当地人就在山谷的路旁竖起了一块路牌,提醒人们说:“慢慢走,欣赏啊!”想不到,这样的句子,被高平和晓雪两位著名诗人共同克隆成了自己的诗。在第二首诗中,我们分明一眼就看到了古人诗歌的影子。唐代的黄蘖禅师在其《上堂开示颂》诗中写道:“尘劳回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在第三首诗中,高平和晓雪就像进行车辆改装一样,将汉语成语中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稍稍一变,就成为了他们的所谓诗歌作品了。在第四首诗中我们看到,他们几乎是把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的故事搬将过来,就成了在各种报刊上通吃的两行诗。由此看来,高平和晓雪,在当代的诗人中,的确称得上是在克隆技术方面灵犀相通的两位高手。他们在毫无商量的情况下,竟然能不约而同地克隆出相同的内容,恕我直言,如此方法写诗,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像样的句子来?
至于像高平的“爱说谎的老师,没有资格骂学生说谎”和晓雪的“如果老师说谎,能教育学生讲真话吗?”这样糟蹋诗歌的文字,与其说是诗歌,倒不如说更像是某个学生家长在与那些冤枉自己孩子不诚实的老师大声吵架。我以为,高平和晓雪写了一辈子的诗,居然把诗歌写成这个样子,这至少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诗歌。他们虽然写了一辈子的诗,但却始终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倘若他们稍微懂得诗歌不但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且是文学中的文学,他们就会羞于将自己瞎折腾出来的那些让人大倒胃口的劣质文字,沾沾自喜地拿出来发表在各种报刊上。没有金刚钻,却偏要去揽瓷器活,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数十年写作生涯的巨大失败和令人痛心的择业误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水平的两位诗人,却居然能够当上省作协主席和省文联副主席。我不知道,这背后究竟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奥秘?这多年的媳妇究竟是怎样熬成婆的?在我看来,一个省的作协主席或者文联副主席,至少应该是那个省文学写作的佼佼者。他的写作,无疑应该代表着其所在省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而像高平和晓雪这样的写作状态,难道能够真正代表甘肃和云南两省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吗?从高平和晓雪的这些诗歌来看,二位老先生虽然被称之为著名诗人,但他们究竟写出过什么像样的好诗?或许,高平和晓雪对别人的模仿纯属是无意的,他们只是在缺乏灵动的思维中一直走不出其创作的怪圈。久而久之,他们就把别人的东西稀里糊涂地当成了自己创作出的东西,并且堂而皇之地发表在了众多的报刊上。这种惰性的写作一旦被诗人当成了习惯,并且感觉良好地照此一路写下去,报刊杂志上无疑将会产生更多的文字垃圾。我真不知道,各地报刊的编辑们为什么会把如此工业化生产,糟蹋诗歌的诗当成了香饽饽,接二连三地争相发表出来?我始终搞不明白,这些诗歌究竟是人情稿,还是因为这些报刊的编辑们鉴赏能力确实是太低,分不清鱼目和珍珠?多年前,某著名作家居然将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江湖夜雨十年灯”说成是自己在梦中所得的佳句,并写成文章拿出来显摆。这种与高平和晓雪如出一辙的创作,成为了文坛上传颂一时的笑柄。我以为,高平和晓雪的这些两行诗,文字水平之低,甚至还远不如那些没有经过专门的诗歌训练的商家们的广告写得有灵气和富有诗意。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钻石广告),“牛奶香浓,丝般感觉”(巧克力广告),“孔府家酒,让人想家”(酒广告),“喝汇源果汁,走健康之路”(饮料广告),“不为诱惑谁,只为呵护美”(护肤品广告),“多一些润滑,少一些摩擦”(润滑油广告)。
在我看来,高平和晓雪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写作,暴露出的只不过是当代文坛作家们惰性写作,偷懒取巧的冰山一角。如果仔细阅读当代文坛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类似这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克隆”现象可说是屡见不鲜。想当年,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的那个经典的开头,不知被多少中国作家邯郸学步地克隆过。我们看到,即便是当今如日中天的个别“茅奖”作家,在其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同样大量采用了高平和晓雪诗歌创作中这样的克隆技术。如,某位作家一篇广为文学批评家们称道,并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散文,就明显克隆了安徒生的著名童话《丑小鸭》。在安徒生的童话中,那只长得非常难看的小鸭,仅仅是因为丑,就经常受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和谩骂。而在这位“茅奖”作家的这篇散文中,只不过是将安徒生笔下那只丑陋的小鸭生搬硬套地变成了一块丑陋的石头。在《丑小鸭》的最后,那只丑陋的小鸭最终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而这位作家的笔下,那块曾经老是被小伙伴们莫名其妙地辱骂,看似什么用都没有的丑石,却是一块罕见的,具有极大天文价值的陨石。在该作家的一部获得“茅奖”的长篇小说中,有一段看似非常精彩的吃芝麻的描写。这段描写,在他本人的多部长篇小说中都曾先后出现过。然而,这只不过是克隆了晚清小说家吴趼仁的著名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一段经典描写。也许,在反复的克隆中,作家早已把别人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当成了自己的东西。
而在另一位“茅奖”作家的某一部长篇小说里,其中一段关于土匪的叙述,却与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中的一段描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沈从文的笔下,湘军军营中,有一天突然吹响了哨子,违反了军规的刘云亭怎么也想不到引来了杀身之祸。当他哭喊着向司令求饶说,求求司令官的恩典,他跟随司令多年,没有做错过一件事,他的太太还在公馆里侍候司令太太。然而执法如山的司令却毫不为私情所动,为了湘军的名声,他不惜挥泪斩首自己的心腹。他对刘云亭说:“刘云亭,不要再说什么话丢你的丑。做男子的作错了事,就应当正正经经的死去,这是我们军中的规矩。我们在这里做客,你黑夜里到监牢里去奸淫女犯(一个长得体面标致,为人毒辣的女土匪),我念你跟我几年来做人的好处,为你记下一笔账,暂且不提。如今又想为非作歹,预备把良家妇女拐走,且想回家去拖队伍。我想想放你回乡去做坏事,作孽一生,尽人怨恨你,不如杀了你,为地方除一害。现在不要再说空话,你女人和小孩子我会照料,自己勇敢做一个男子吧。”这时,当刘云亭绝望地对司令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杀你,我还不干!”然而,铁面无私的司令官却像丝毫也没有听见刘云亭的话一样,把头掉向了一边,嘱咐副官买副好点的棺木。想不到,沈从文先生这段精彩的描写,却被这位“茅奖”作家克隆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在这位作家的小说中,十七岁的玲子姑娘是村中的第一号美女,玲子姑娘有一天大着胆子去找任副官,却误入了军需股长的房子。军需股长是余司令的亲叔余大牙,贪财好色的余大牙借着酒劲将玲子姑娘强暴了。当土匪头目余司令知道后,立即将自己的亲叔叔绑了起来,说:“叔,我要枪毙你。”余司令的叔叔余大牙愤怒地吼叫着说:“杂种,你敢毙你亲叔?想想叔叔待你的恩情,你爹死得早,是叔叔挣钱养活你娘俩,要是没了我,你小子早就喂狗啦!”然而,余司令却扬手一鞭,打在了余大牙的脸上,骂一声:“混账!”接着便双膝跪地说:“叔,占鳌永远不忘你的养育之恩,你死之后,我给你披麻戴孝,逢年过节,我给你祭扫坟墓。”想想看,这样的文字与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描写难道仅仅是英雄所见略同和偶然的巧合?
号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的男士、女士们,你们何时才会收手“拿来”式的写作,而呈现给读者诚实的作家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