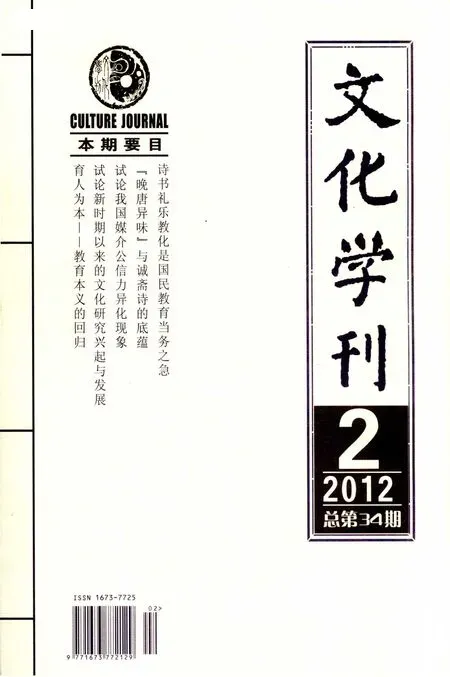基于实地调查与民族志“厚描”的语言民俗研究——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
张举文
(作者系美国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黄涛著 《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立足于实地调查这一民俗学核心研究方法来为语言民俗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做开拓性研究,不仅其学术创见难能可贵,而且其研究范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贡献是多学科的,但可从方法、理论以及范例作用三个方面来概括。
在方法论上,实地调查是民俗学,也包括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在内的质性研究学科必不可少的学科根基。《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依靠对一个村落(河北景县黄庄)的实地调查和充分了解才在问题讨论中有理有据,也使得该书不同于诸多相关题目的以文本或史料为中心的研究,为研究语言民俗树立了一个范例。该书从亲属称谓(分为血亲与姻亲)、拟亲属称谓、人名(分为姓名、乳名、绰号)、咒语等四大方面在方法论与理论体系上深入探讨。这当然不是语言民俗可能有的全部类型,语言民俗的分类也不是本书的宗旨。但作者在附录中包括了 “民谣”和 “民间故事”,并在再版中又包括了谐音、流行语等语言民俗类别,这表明作者并没有忽视语言民俗类别的丰富性。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希望的,对正文中的类别的探讨将在方法论上有助于对其他类别的进一步研究。的确,对黄庄的调查研究与分类方法完全可以用于对其他群体的研究,如某一特定职业或性别群体。附录所含的校园群体便是例证。当然,这些方法上的探索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论上的挖掘。
在此基础上,作者展开了理论方面的讨论。作者界定了“语言民俗”这一基本概念,并探索和尝试建立相应的理论谱系,将其区分于前人的“民俗语言”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作为社会语言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点,语言民俗学是有着广阔前景的。当然,对此题目的研究也体现了语言民俗在中国文化中的具体语境问题。民俗学在很多国家或语言中的别名是“口头文学”或“口头艺术”,抑或“民族志学”。如今,愈来愈多的学科将“口头”言语也视为“文本”,这也说明对活生生的语言民俗的重视。同时,这种从民俗生活中提取的言语样本又不同于从史料文献或第二手资料获得的文本。虽然因篇幅所限,该书不能像有些民俗志那样提供更多完整的描述,但这已足够表明所讨论的语言民俗在日常生活中的蓬勃活力。
有关咒语的探讨凸显了作者的一些独特看法,这是因为作者有着实地调查的鲜活语言证据来思辨那些统治学科的已有理论,也是因为“通行”的有关理论,几乎没有是基于中国文化实践归纳出来的。虽然因该书的宗旨所限,也因为国内有关理论著作的译介与讨论话语有限,作者没能充分探讨巫术与宗教等问题,但读者可以看出一些咒语所表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巫术——宗教观。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语言灵力观。而黄庄人所持有的有关“神”、“道”和“咒”的传统观念与行为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信仰体系。作者不是去套用西方理论,而是有批判性的比较,为今后有关讨论提供了健康的榜样。
该书的写作充分展示了作者在整个调查中的角色作用,具有反思性和“写文化”的新视角。此外,通过对“语境”的文化与社会层面的讨论,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个概念。读者不但可以了解作者在课题设计、调查和写作中的思想,而且还可以将该课题的研究置于当时(包括现在)的较广的学术和社会“语境”来认识本书在理论思想与方法上的思考与贡献。例如,作者坦诚地公开了当时在公众场合的评语和私下的议论,以及当时的个人感受,从一个层面记述了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历程。
更有意义的是,该书充分体现了格尔茨所提出的民族(俗)志的“厚描”,即不但提供了那些民俗语言应用的场景,也交代了历史背景和演变情况,还展开了学术话语。例如,在记述亲属称谓时,作者更多地论述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大的社会变化的影响。此外,通过探究“哥们儿”这一称谓的应用,作者将村落内部互动机制联系到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机制。其他如关于“干嘛去”、“吃了吗”、“家来坐坐”等俗语的基于实地调查的探讨,也同样为读者开阔了理论视野。
由此可见,《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一书不但为研究语言民俗,也为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民族 (俗)志研究和写作提供了可贵的范例。作为开拓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努力,本书应该是每位对语言民俗感兴趣的学生与学者都不可错过的。 该书的扩充再版,更证明作者仍在继续探索这个课题。相信作者还会有机会在下一个版本中进一步完善有关语言民俗的理论框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