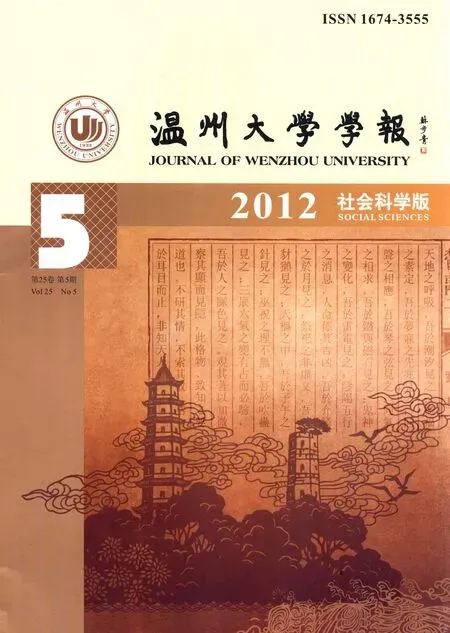论同文馆之争与洋务运动的困境
胡联洋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 100091)
论同文馆之争与洋务运动的困境
胡联洋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 100091)
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是洋务派与顽固派就洋务运动进行的一次较为激烈的争论。争论开始于奕等人要求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出身者入馆学习这一提议。顽固派认为洋务派这一提议有违于传统治国之道,事实上则是担心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会危及自身的政治地位。慈禧太后的态度及其产生的作用则更多地表现为对洋务运动的阻碍。虽然从表面上看争论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但是这次争论反映了在晚清政治背景下,洋务派在深入推进洋务运动这一问题上所面临的强大阻力。
同文馆之争;洋务运动;困境
1867年同文馆之争是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后洋务派与顽固派第一次直接而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直接检验了洋务运动开始后洋务派、顽固派以及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等各方对变革的态度和力量对比。针对同文馆之争以及顽固派与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期间的其他争论,人们往往简单地从阶级属性上对之做出解释,这里笔者试图将同文馆之争放到中国近代化演进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力图透过同文馆之争进一步分析影响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一些具体因素。
一、同文馆之争的背景与缘起
从鸦片战争开始,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王朝连连失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奕、李鸿章等清朝高级官员与西方列强始有较为深入的接触,部分清朝官员开始进一步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洋务派发现培养一定数量的外国语人才是开展洋务和对外交涉的重要前提。1858年6月26日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1]条约中的这一规定使得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不得不尽快将培养一定的外国语人才提上日程。另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北京政务的恭亲王奕对由于外国语人才的缺乏带来的困难印象深刻。因此,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等上奏清廷要求仿照俄罗斯馆旧例培养一批外国语人才以备中外交涉中的不时之用。在奏折中奕等认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5754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了奕等人的这一要求,但是由于缺乏适合的外国语教习,直到1862年6月11日,京师同文馆所招收的学生才正式上课。
二、争论背后洋务派面临的压力
大致来说,针对增开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馆学习这一问题,顽固派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与西学相比,中学更为优秀,学习西洋天文、算术的主要目的在于用西法以印证中法;救国的根本方法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洋人为中国人的仇敌,断不会真正传授其技能,而以夷为师不但不能救国,还将进一步加剧洋人对中国的侵略;允许科甲正途人士入馆学习天文、算学最终只能导致道德堕落以及士人之间党争不断,危害甚大。
由于自明清以来,中国长期受闭关锁国政策以及传统文化中重修身、轻器物思想的影响,顽固派的以上理由在一般士人看来是颇具有说服力的。对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馆学习这一行为首先发难的是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张盛藻,他在1867年3月5日的奏折中指出:“我朝颁行宪书,一遵御制数理精蕴,不爽毫厘,可谓超轶前古矣;即使或参用洋人算术,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耳。”[4]4540这里张盛藻首先指出其反对的前提是中法高于西法,洋人的天文、算学只是用来证明中法的精确。因此,他进一步认为救国的方法仍然应当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寻找,即“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4]4541。而对于张盛藻的谏阻,虽然清廷在当天给予的驳斥中认为“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5],但是,就招收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这一问题,清廷亦强调其目的在于“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5]。虽然在第一轮论战中,顽固派的进攻被清廷强力压制下去,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给顽固派新的反击提供了理由:既然招收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是为了用西法印证中法,那么中法应该是什么?应不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印证?
1867年3月20日顽固派的代表大学士倭仁继续上疏反对洋务派就同文馆内增添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馆学习这一做法。其在奏疏中一开始便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6]4557他认为用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天文、算学馆学习这种方式解救清政府面临的困境危害甚大,必然导致以夷变夏,加剧西人对中国的侵略,即所谓“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6]4559而对于倭仁的这一观点,通政使于凌辰又于1867年5月1日的奏折中加以补充,在奏折中他极力陈述招收科甲正途士人入馆学习可能带来的朋党之祸,他认为设立同文馆已经造成“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互相攻击之不已,因而互相倾复,异日之势所必至也”[7]。同时,在该奏折中,他还以历代的朋党之争作为警示。因此,无论是倭仁的华夷之辨还是于凌辰的所谓朋党隐患,都是打着传统治国方法的幌子来反对洋务派的革新。单单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他们的说法似乎有论有据,颇具说服力。其理论的前提是:与西学相比,中学并不落后,学习西法只不过是用西法以佐证中法,而在同文馆设置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士人学习天文、算学会造成西法对中法的挑战,对传统的治国之道带来损害。
由于顽固派在反对革新的问题上往往是以忧国忧民面目出现,特别是倭仁奏折中的华夷之辨又将这一时期西方宗教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这一客观现实和洋务派要求科甲正途人士学习西方天文、算学联系起来,并将其危害上升到亡国、亡天下的高度,从而更容易激发一般士人的忧愤之情和盲目排外情绪,遂引起顽固派对洋务派更为猛烈的攻击。他们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行为看作是投降媚外,正如翁同龢亦在1867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辨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京师口语籍籍。或黏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8]521而1867年6月23日直隶州候补知州杨廷熙在其条陈中,更是将当时的自然灾异和同文馆问题联系起来。
事实上,就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洋务派和顽固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1867年1月28日的折子中,奕就顽固派对洋务派舍中法而以夷为师这一攻击做出回应,然而奕的解释是:“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9]当然奕的这番话更为直接的目的是为了缓解来自顽固派的阻挠和非议,并且在奏折中,奕也列举了一些学习西法的必要性,但总体来说,奕的观点却为顽固派的进一步阻挠提供了借口,即问题的焦点仍然集中于西法和中法的关系上。张盛藻、倭仁等人随后提出的反对理由正是建立在中法高于西法这一基础之上。而在这一前提下,顽固派从中国传统的治国经验出发亦有自己的一整套说辞,这就使得洋务派进行的每一次革新尝试都陷于无休止的论战之中,效果大打折扣。
三、争论背后的权力之争
对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们来说,他们获取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对封建道统进行解释的能力和权力,他们往往通过对封建道统的维护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任用,从而获取政治权力。在同文馆之争中,张盛藻、倭仁等提出的反对理由正是这种封建道统在政治运作中的体现。表面上看,顽固派反对的理由是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天文、算学馆学习不符合传统的治国之道,危害甚多,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试图继续维护清王朝在传统治国理念下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特别是防止传统的官员选拔制度遭到挑战,从而维护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以及保证自身得以晋升的机会。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清政府对洋务人才的需求更为急迫。1866年2月,就派遣同文馆学生随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出使英国一事,奕就曾要求清廷对出使学生在品级上进行擢升,并且得到清廷同意。毫无疑问,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必将对传统士大夫的选用和擢升产生威胁。而就本次同文馆之争来说,洋务派进一步要求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并且待遇优厚,这在顽固派看来不能不是一个更为直接的挑战。如果洋务派的这种做法得到更多中下层传统士子的认可并且从根本上影响到清廷用人制度的话,那么倭仁等传统卫道士在朝廷中的号召力必然会进一步下降。在1867年3月5日的奏折中,张盛藻就不无讽刺地认为,洋务派为了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馆学习而给入馆者优厚条件可谓“诱掖奖劝,用心苦矣”[4]4540,而张盛藻的话也包含了他对洋务派一方势力更为壮大、传统阵营力量则逐步缩小这一状况的担忧。1867年5月16日,崇实的折子则进一步道出了顽固派的意图,他在奏折中认为:清政府可以对在天文、算学方面有特长的人员给以嘉奖,但是朝廷不必设馆教习,而是可以令各地督抚进行荐举,并强调“器数之末学,不过取效之一端。即推类以尽其余,当由艺以至于道”[10]。其意图仍然在于保证传统的官员选拔方式以及传统士大夫在官员选任方面的垄断地位。而针对奕等奏折中提到的开设天文、算学馆得到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支持这一事实,杨廷熙于1867年6月23日奏折中的反对意见则更耐人寻味,他认为搞洋务“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学之犹可,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兵弁子弟学之不过成其艺事,科甲官员学之即可寝成风俗也。盖科甲官员,四民之瞻仰,天下所崇奉者也”[11]。事实上,杨廷熙在奏折中对清廷的批评主要目的则在于要求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保证传统的官吏选拔制度不被改变,因为这和遇缺即选的直隶州候补知州杨廷熙自身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
四、慈禧太后对争论的态度
由于两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因此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倾向对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革新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天文、算学馆争论发生的 1867年,慈禧太后已取得事实上的统治权力,因此她在争论中的态度对争论的解决以及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无疑是希望清王朝免受外来侵略的,并且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所进行的革新措施也大都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但是就同文馆之争来看,慈禧太后的态度及其产生的作用则更多地表现为对洋务运动的阻碍。
在同文馆之争中,对于首先起来发难的顽固派士大夫张盛藻的奏折,慈禧太后当天即将折子驳回,慈禧太后的这种态度显然对处于同文馆之争中的洋务派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奕曾在1867年4月23日的折子中指出:“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其人。”[12]然而对于3月20日倭仁的折子,慈禧太后于当天既对倭仁进行了召见,而据翁同龢当时的日记记载,两宫太后“询同文馆事,倭相对,未能悉畅”[8]519。尽管在与两宫的对话中,倭仁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慈禧太后,但是慈禧太后的批示却是让总理衙门与倭仁进行辩论,事实上是纵容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对洋务活动进行攻击。而对于慈禧太后的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奕在4月23日折子亦指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报考者。”[12]从表面上看,由于张盛藻品位低,而倭仁则属于朝廷重臣、理学领袖,慈禧这样做既有兼听之明,又有尊重朝廷重臣之意,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慈禧太后的这种做法造成的客观后果就是使洋务派的努力大打折扣。在随后的争论中,虽然慈禧太后对前述杨廷熙对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及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馆学习进行的攻击大为震怒,但从慈禧太后就前述杨廷熙的折子所发的上谕看,慈禧太后最为震怒的是顽固派敢于将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以及顽固派在这次争论中的结党现象,这不能被理解为是她对洋务运动的坚决支持。因此,在同文馆之争中,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应对中国如何向近代化转变这一大问题上,采取的却是传统帝王的驭臣之道,客观上阻碍了洋务运动的进展。
五、结 论
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是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第一次激烈交锋,虽然这场争论最终在最高统治者的干预下得到平息,但是透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洞见近代中国在其早期的近代化尝试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秉承这一观念的顽固派士大夫人数众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他们竭力阻挠任何近代化的革新行动;而洋务派大多也是从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观点上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这就使得洋务派在面对顽固派的攻击时难以做出有力的回应。在新旧力量的交锋中,掌握帝国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则采取了游离于争论之外的态度,不能给予洋务运动坚决而有力的支持,事实上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因此从 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可以看出,在晚清政治格局下,洋务派试图通过采取渐进的方式扭转近代中国落后状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1]褚德新, 粱德.中外约章会要(1689 – 1949) [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309.
[4]张盛藻.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奏[C]//宝鋆, 载龄, 沈桂芬, 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四十七).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5]爱新觉罗·载淳.上谕(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C]//宝鋆, 载龄, 沈桂芬, 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四十七).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4542.
[6]倭仁.大学士倭仁奏[C]//宝鋆, 载龄, 沈桂芬, 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四十七).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6.
[7]于凌辰.请无庸开设二馆以弥朋党之祸折[C]//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16.
[8]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第一册[M].陈义杰, 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0]崇实.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无需限定正途折[C]//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18-19.
[11]杨廷熙.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条[C]//宝鋆, 载龄, 沈桂芬, 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四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4689-4690.
Study on Debate about Beijing Translation School and Dilemmas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HU Lianya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China 100091)
In 1867, there was a bitter argument o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roused between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and the Conservatives, historically called the Debate about Beijing Translation School.The dispute originated from the proposal, urged by Yixin and his followers, of establishing Astronomy and Arithmetic Department in the school and enrolling students who passed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The Conservatives believed the proposal of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was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governing the nation.The Conservatives’ worry about the proposal was, in fact, the afraid of their political status being threatened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ing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Empress Dowager Cixi’s attitude to the proposal and its influence were mainly reflected on setting obstacles to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Although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won the argument seemingly, the argument reflected the strong resistance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faced in further push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under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Late Qing Dynasty.
Debate about Beijing Translation School;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Dilemma
K252
A
1674-3555(2012)05-0030-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5.00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1-10-23
胡联洋(1982- ),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