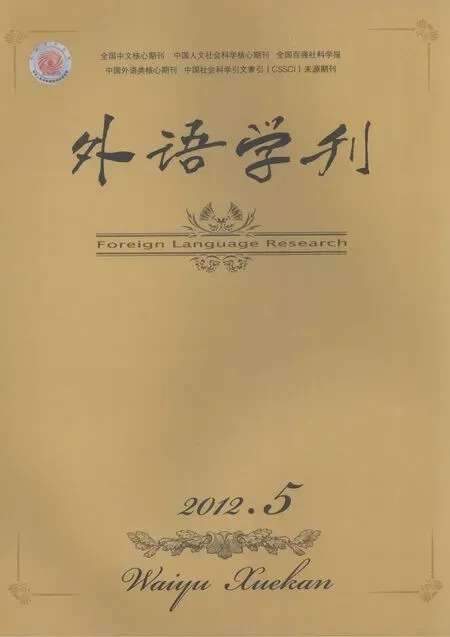语言转向和语言关怀*
冯光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420)
●语言哲学
○专题研究
语言转向和语言关怀*
冯光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420)
语言转向始于弗雷格还是维特根斯坦?我们认为是后者,但同时强调语言转向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经历孕育、萌芽和实现3个阶段。维特根斯坦的“一切哲学都是语言批判”的思想离不开弗雷格数理逻辑思想的滋养、意义和指称理论的启发以及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供的分析范例。具体说,语言转向孕育于弗雷格构建数理逻辑时对数的意义追问,萌芽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实现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与实在同构的论断,完成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哲学对语言的关怀可以上溯到西方哲学的黎明时期,但与语言转向不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都未将语言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都没有认识到语言对世界的投射作用。
语言转向;分析哲学;语言关怀
1 引言
“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一说最早由伯格曼(Bergmann)提出。他认为这种以语言为手段的哲学方法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io-Philosophicus)。然而,自达米特的《弗雷格:语言哲学》(Frege:PhilosophyofLanguage)(Dummet 1973)问世以来,语言转向又常和弗雷格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接受达米特 “语言转向开始之时就是分析哲学诞生之日”(Dummet 1993: 5)一说,这固然和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研究中的地位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将注意力过多集中于弗雷格的《论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 reference)一文从而未能充分认识到该文在弗雷格构建数理逻辑体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倾向于伯格曼和哈克的立场,即语言转向由维特根斯坦实现,但同时强调维特根斯坦的“一切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的思想离不开弗雷格数理逻辑思想的滋养、意义和指称理论的启发以及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供的分析范例。本文将围绕语言转向的本质和特征,分析、评价弗雷格、罗素以及维特根斯坦在这一决定20世纪西方哲学走向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语言转向孕育于弗雷格构建数理逻辑时对数的意义追问,萌芽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实现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与实在同构的论断,完成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哲学对语言的关怀可以上溯到西方哲学的黎明时期,但与语言转向不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都未将语言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都没有认识到语言对世界的投射作用。
2 语言转向和分析哲学
2.1 “语言转向”的由来
“语言转向”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伯格曼 1953年发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和形而上学的重构”(Logical positivism, languag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taphysics)一文。他指出,逻辑实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风格,那便是接受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开启的语言转向。后来,他在《逻辑与实在》(LogicandReality)一书中将这种风格明确解释为“通过讨论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讨论世界”(Bergmann 1964:177)。尽管术语“语言转向”是伯格曼首创,但该术语能广为传播却要归功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Rorty)。1967年由他主编的《语言转向——最新哲学方法选集》(TheLinguisticTurn:RecentEssaysinPhilosophicalMethod)出版后,“语言转向”作为哲学术语才开始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研究文献中频繁亮相。
“语言转向”指什么?
伯格曼明确指出语言转向是一种哲学研究策略的转变,即从主体(人)到客体(世界)的直达策略转向通过分析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认识客体的间接策略(Bergmann 1964)。换句话说,哲学从追问“X是什么?”转向先追问“‘X’的意思是什么?”对于这种转变是有基本共识的,分歧只在“什么语言才是合适的?”这一问题上。伯格曼还分析语言转向的3个原因。首先,语言转向之前哲学家未区分词语的日常用法和哲学用法,常把普通词语当哲学语汇使用,使它们晦涩难懂,需要用日常语言去解释,语言分析能提供这种解释;其次,许多哲学问题(悖论和语义含混等)与我们未将语言和关于语言的语言(元语言)区别开来有关,语言分析是避免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第三,语言不能表现世间万物,但有些事物难以表现并非这些事物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未能弄清语言的结构。罗蒂也认为语言转向是一种哲学方法,它要求通过观察语言去揭示事物的本质。罗蒂指出语言转向的认识基础是:“哲学问题能够通过改造语言或更多地认识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而得到解决(或化解)”(Rorty 1967:3)。他同时指出,语言转向是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哲学纷争不断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出发点是反对哲学的伪科学论辩。从罗蒂收录的文章看,“语言转向”是一个概括性术语,涉及英美理想语言学派(ideal language philosophy)和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欧洲大陆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cism),时间跨越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的30多年。
伯格曼和罗蒂给语言转向划定的范围不尽相同,但基本认识一致:语言转向是通过语言分析去认识世界的一种哲学方法,这种方法充分强调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大致体现在两个层面:语言结构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分析语言结构能帮助澄清思想和世界的结构。
2.2 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罗蒂的《语言转向——最新哲学方法选集》问世后,“语言转向”和“分析哲学”可谓形影不离,普遍认为语言转向是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基本特征。尽管目前对分析哲学所涉范围仍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它是以拒斥唯心主义(idealism)为背景、以分析为手段的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它以对事物或事实进行逻辑分析和科学描述为目标。根据哈克(2007)的梳理,分析哲学始于19末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后逐渐步入衰落。分析哲学发端于剑桥大学。在那里,以摩尔(Moore)和罗素(Russell)为代表的哲学家在弗雷格(Frege)数理逻辑思想的启发下,从处于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转向现实主义(realism)。这是分析哲学的第一个阶段,但这一阶段的最高成就不属于摩尔和罗素,而是属于前期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他的《逻辑哲学论》无疑是这一阶段的巅峰。分析哲学的第二阶段(约20世纪20和30年代)属于以拉姆塞(Ramsey)为代表的剑桥哲学家。由于受摩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很深,这一阶段随着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思想的修正以及拉姆塞本人的英年早逝而迅速终结。分析哲学的第三阶段属于二战前后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时期,以石里克(Schlick)为代表的哲学家崇尚语言意义的逻辑分析,提出语言意义的证实原则(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二战以后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Oxford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可谓分析哲学的第四阶段,这一时期赖尔(Ryle)、奥斯汀(Austin)、斯特劳森(Strawson)和格赖斯(Grice)等将注意力转向日常语言,认为日常语言是哲学分析的理想语言。他们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和分析给整个英语世界甚至全球带来巨大影响。当然,这一阶段的真正巨人还是剑桥的维特根斯坦,他后期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是分析哲学的一座丰碑。分析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步入衰落,除了其本身的缺陷外,也和以剻因(Quine)、戴维森(Davidson)和达米特(Dummett)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logical pragmatism)在北美的兴起有很大关系。
从摩尔和罗素到维特根斯坦再到赖尔和奥斯汀,他们都摈弃哲学的综合方法而采用分析方法,将复杂概念分解为简单要素,因此他们的哲学被冠以“分析哲学”之名。摩尔早在1903年就有“哲学概念的分析”(analysis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一说,罗素则在1914年就提到“逻辑分析法”(logical analytic method)。可见,“分析”之名和分析哲学的兴起同时出现,而“语言转向”则出现在分析哲学诞生半个世纪之后。仅从这个意上讲,把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出现的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去辨明世界的结构的哲学方法称为“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更为贴切。
3 语言转向的孕育与萌芽
3.1 弗雷格
伯格曼和罗蒂在讨论语言转向时都未提到弗雷格,但达米特宣称弗雷格是语言转向的第一人(Dummett 1993)。达米特的这一结论基于他的两种认识:其一,弗雷格提出哲学的任务是分析人的思想,而分析思想的最佳(甚至唯一)手段就是分析语言;其二,弗雷格的“论意义和指称”(Frege 1892)是语言意义理论的最早版本。达米特的这两种认识影响广泛,但说服力不够。首先,“分析哲学的诞生之日就是语言转向开始之时”(Dummett 1993: 5)一说值得商榷。我们知道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有分解(decompositional)或转换(transformative)之义,前者是将对象分解为构成成分,不一定涉及语言,摩尔和罗素的早期分析属于此类。第二,弗雷格关注的是数学基础而不是语言,他倡导的不是语言分析而是将数学归化为逻辑,他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完美的数理逻辑体系而不是一个语言意义体系,他追求的是为数学提供可靠的逻辑基础而不是为语言意义提供理论框架;他创建的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完全是为了满足逻辑推理的严密性需要,与自然语言有极大不同;他的《算数基础》(DieGrundlagenderArithmetik)几乎不涉及语言问题。第三,弗雷格1892年的“论意义和指称”一文确实直接涉及语言并有大量篇幅讨论词语和句子的意义,但是其主题是逻辑中的同一性问题(equality/identity)。弗雷格开宗明义:“同一性引发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它是一种关系吗?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还是事物名称之间的关系?在《概念文字》中我认为是后者”(Frege 1984:157)。文章结尾又进一步呼应同一性这一主题。只要将该文置于弗雷格学术追求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和解读,便不难理解他区分意义和指称并用大量篇幅讨论句子的真假值完全是为了验证他早期在《概念文字》中提出的同一性的可替换原理。弗雷格明确表示,意义和指称只是逻辑区分,这一区分能使他的逻辑体系日臻完善、趋于成熟(Frege 1892)。第四,对于究竟是谁开启了语言转向这一问题,达米特本人也底气不足,他在坚持弗雷格为语言转向第一人的同时,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如果把语言转向看成分析哲学的起点,那么不管弗雷格、摩尔和罗素培植了多少土壤,关键的一步是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的《逻辑哲学论》中迈出的”(Dummett 1993:127)。显然,至于语言转向的起始问题,达米特在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徘徊。
众所周知,弗雷格一生追求将算数建立在严格的逻辑基础之上,并为此创建现代数理逻辑。但是,与其他数学家不同,弗雷格的算术基础充满哲学思考,他的数理逻辑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是确定思想的客观性,思想具有潜在的逻辑结构,哲学家应该去寻找这个结构,而要找到这个结构就必须以逻辑为基础,因为思想结构只能反映在一种高于自然语言的逻辑语言之中。应该说,弗雷格在构建逻辑体系时涉及的语言分析孕育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第一,弗雷格的数理逻辑是表现命题和逻辑推理的手段,但是由于该体系必须以自然语言能够彻底转换为形式逻辑为前提,注定会引发他对语言意义的追问,而转换过程中频繁出现的“内容”(content)、“含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等概念又必然引起人们对这些概念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兴趣,进而意识到语言的使用。
第二,弗雷格并无构建一种将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语义理论的意图,但是他的概念文字为分析语言提供了形式手段,他在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的构建过程中进行的语言分析不仅克服了传统语法依据主谓结构分析句子的诸多缺陷,而且为全方位分析语言提供了范例。
第三,尽管弗雷格的语境原则——要在句子中(而不是孤立地)寻求一个词的意义——是为了辨明数的意义而提出的,但这一思想却大大拓宽了语言意义研究的视野。维特根斯坦就接过了这一原则,并将语境从句子扩展到了语言使用。
第四,弗雷格在验证同一性时对意义和指称的独到见地为以分析为手段的哲学研究指引了方向,而他倚重的合成性原则(compositionality principle)不仅能帮助解释我们创造和理解新的语言表达式的能力,而且最终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意义原则。
第五,弗雷格的逻辑分析排斥自然语言,但是没有否定自然语言的自身优势(如自然语言的灵活性)。这一思想为分析哲学从形式语言转向自然语言留下了路径。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弗雷格的逻辑分析给维特根斯坦以极大启发。应该说,正是在与弗雷格的交往过程中,在与弗雷格思想的碰撞、融合和进一步思索中,维特根斯坦构筑起了一个通过语言去思考世界的哲学体系,最终实现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3.2 罗素
罗素关心的也是逻辑,但他把弗雷格的逻辑分析方法完全应用于句子,尤其是含有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s)的句子,开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Ramsey 1931: 263)——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ve method)。据此,命题“当下的法国国王是秃头”可以分析为以下3个命题:“法国当下有国王”,“只有一个法国国王”以及“这个国王是秃头”。这种分析不仅区分句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而且表明分析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句子转换。
罗素还直接讨论语言的功能。他认为语言有3种功能:指示事实、表达说话人的心理状态和改变听话人的心理状态。罗素对语言的认识不仅和语言转向时期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一致,而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不谋而合。(Russell 1980:204)
罗素还强调自然语言的哲学意义。罗素说,“语言在哲学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是我们还未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会被这种影响引入歧途,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关注它并看看它究竟有都少合理性”(Russell 1924:367)。在罗素看来,自然语言并不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改造日常语言,使它的语法和句法形式与其逻辑形式契合,哲学就是要构建一种“理想语言”或“哲学语言”。
罗素也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铺设了道路,他的逻辑型态(logical type)和逻辑形式(logical form)以及哲学问题源自语法和逻辑形式的混淆的思想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很深,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基础。
罗素完全从句子出发去思考逻辑问题。这尽管与弗雷格从逻辑出发去分析句子有了很大不同,但是语言依然是配角。首先,罗素追问的是世界的本质以及知识和臆想的区别。他认为这种追问可以通过分析命题来实现,但他并不认为分析命题就是分析语言。罗素就曾抱怨哲学把分析句子当成自己的任务,抛弃其原本严肃而重要的任务——认识世界。基于这种认识,即便是在《意义和真理的探究》(AnInquiryintoMeaningandTruth)一书中,罗素也多次强调他关心的是认识论而不是语言。其实,在读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前,罗素一直坚信逻辑揭示的是世界的形式特征,不是语言的形式特征。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展示句子的逻辑形式也只是为了表明句子的逻辑形式和其语法形式之间的差异,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客观世界以及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种追求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直到他的兴趣从逻辑和数学转到心理学、物理学和认识论。
第二,罗素认识到语言的不同功能,但他只关注语言的指示功能,对语言的表达和成效功能视而不见。换句话说,罗素的心里只有逻辑。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打个比方,如果将逻辑看成事态的“脚手架”,那么罗素始终未能跳出脚手架上的护网(Wittgenstein 1974:76),而维特根斯坦不仅从中跳了出来而且步入语言游戏的运动场。
第三,和弗雷格一样,罗素也排斥自然语言,他认为自然语言的缺陷(如歧义和含混)只能通过分析去解决。他对句子进行转换分析为的是通过揭示命题的逻辑形式展现客观事态的结构,任何命题内容都可以分析转换为它的构成成分,但需要把自然语言转换为逻辑语言,逻辑语言的结构反映客观事态的结构,从而揭示事态的本质。但是后来的哲学发展脱离了他设计的轨道,从维特根斯坦到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大家都在展现自然语言的哲学价值。
4 语言转向的实现:维特根斯坦
尽管弗雷格和罗素的哲学思考都触及语言,但语言始终是配角。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的哲学思考完全通过语言批判展开,“一切哲学都是语言批判”的口号以及语言与实在同构的思想宣告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转向有两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前期的《逻辑哲学论》紧扣句子,后期的《哲学研究》紧扣语言使用。
4.1 《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全面确立语言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或实在是事实(不是事物)的总和,要呈现以复合的或原子的状态存在的客观实在需要表达式构成的命题,表达式是可分析或不可分析的名称,简单名称代表现实中的事物(名称的意义),名称将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初级命题是根据逻辑句法形成的名称串,语言和世界同构,所以可以透过语言窥见世界的结构,语言与实在之间的根本联系通过指称实现,即句子由指称表达式构成,指称表达式则通过命名各种实在而获得意义。基于这一逻辑原子主义立场,《逻辑哲学论》把哲学的使命明确划定为辨明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批判。语言批判是为了防止语言误用,消灭语言引发的误解,消除语言模糊和化解语言表层结构带来的哲学问题。这里,语言显然不再是哲学研究的配角而是中轴,哲学围绕语言展开。
《逻辑哲学论》明确语言批判的方法。语言批判以逻辑分析为基础,而逻辑分析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能辨明逻辑结构的符号系统来替代自然语言,也就是要找到那些模糊、含混和充满歧义的句子的替代形式,这种形式能将逻辑结构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达到消除误解的目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和罗素的数学原理在这一方面能有所作为,因为这种符号体系能显示、编码或者反映自然语言和思想的深层结构,也就能展示由语言和思想所再现的客观世界的深层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分析的是语言对客观世界的投射。
《逻辑哲学论》有明确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部分,它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传递思想;句子描绘世界万象,它由可分析和不可分析的表达式组成;不可分析的表达式叫做简单名称,它们的意义就是它们所表征的客观事物,简单名称将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这种语言观显现维特根斯坦早期以语言和世界同构为基础的语言意义思想,包括词语意义的指称论思想(名称的意义就是其指称)和句子意义的图像论思想(句子的意义是事实的图像)。
总之,《逻辑哲学论》探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并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标志着语言转向的实现,而维特根斯坦在阐述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过程中认定的自然语言在逻辑分析中的缺陷又为他日后重新审视自然语言,建立语言游戏理论埋下了种子。
4.2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一生从未停止语言反思。但有趣的是,他1929年返回剑桥后的语言批判发生极大的变化,他否定早期的指称论和图像论,认为它们建立在光滑的冰面上,因而缺少摩擦,前行困难,若要脚踏实地前行就需要回到粗糙的地面(Wittgenstein 1953: 107),这个地面就是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哲学研究》以自然语言的实际使用为基础建立的语言游戏理论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彻底转向对语言意义的追求。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绝不能干涉而只能描写语言的实际使用”(Wittgenstein 1953:48)。这一口号宣告分析哲学语言转向的完成。
《哲学研究》以拒斥奥古斯汀(Augustine)的指称论,摆出自己的语言游戏论开篇。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和人的生活实践紧密交织,比如名称的意义由命名活动及其情景生成;说话是一种生活形态,弄清一个词的意义就要弄清该词在某种生活形态里的使用情况;生活形态繁多,词语的用法也多彩多姿,词语不只用来命名,句子也不只用来描述,它们有多样的功能;语言的意义不由它的逻辑形式而由它的实际使用决定,因此解析语言的意义就是解释语言的使用规则。总之,语言不能和语境失去联系,不能失去自己最初的家园——语言游戏;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语言本身而是描述各种语言游戏,所以要从关心单一的逻辑语言转向关心各类语言,如科学语言、伦理语言和诗歌语言等;词语的意义和无意义没有明确的分界,它们随语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一个词语的意义只能在具体语言游戏中去定义,学会一个词语的使用就是学会在恰当的语境中使用它。
《哲学研究》不仅明确哲学的任务,而且暗示语言有一个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可供描述,这给后来的日常语言哲学家提供了启示和想象空间。斯特劳森和普特南(Putnam)都明确指出,不考察概念结构,哲学将无所作为。将哲学看成概念描写,有两层意思:分析语言就是展示语言的深层结构,语言的概念结构客观存在,不能人为构造。斯特劳森认为这两点就是分析哲学的特点(Strawson 1967)。艾尔认为研究语言的结构就是研究世界的结构(Ayer 1946)。戴维森把这种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世界的真实结构就体现在语言的语义结构里,而语义结构就是我们能判断哪些句子在什么条件下为真;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能发现我们已经间接地描述了客观世界,这就是了解现实结构的语义途径(Davidson 1965)。普特南也把语言的使用和对世界的理解联系起来,认为通过描写语言可以描写世界,因为世间事物和语言符号的描写体系一样。不管是斯特劳森、戴维森还是普特南,都在重申维特根斯坦的信念:使用语言和概念就是再现世界的本相。这便是语言转向的哲学精神所在。
显然,《哲学研究》和《逻辑哲学论》在“什么语言合适”上对立,但它们的方向却一致。维特根斯坦本人在评价《逻辑哲学论》时就说,它是一只报时不准的时钟,但并不是一包可以丢弃的废物(Anscombe 1971: 78)。其实,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始终致力于通过揭示语言的结构来“治疗”哲学问题,即澄清和化解哲学困惑,他一直在语言的语法中寻求“思想和实在之间的一致性”(Wittgenstein 1963:162)。这种努力不仅促使语言转向的实现和完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世纪西方哲学的走向。无论是维也纳学派还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都无不受到维特根斯坦的深刻影响,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不仅延续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而且促成一门新兴学科——语用学的诞生。
5 语言关怀
语言转向作为通过观察语言结构寻找解决哲学问题的一种途径,其历史并不久远,繁荣的时间也不长,但是语言关怀却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黎明时期。
语言关怀泛指哲学对语言的论述,这种论述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Plato)《克拉底鲁篇》(Cratylus)关于名称和事物关系的讨论。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名称表现事物的本质,名称的意义就是它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因此名称和事物之间是一种自然(natural)关系。赫谟根尼(Hermogenes)与苏格拉底的看法相反,认为名称和事物间的关系是约定的(conventional),是使用者的习惯。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给予语言的关怀更多,讨论更为深入,他的《解释篇》(DeInterpretatione)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语言是人类来自心灵的感情符号;词语的意义是约定产生的;陈述句是真假值的载体,但不是每一个陈述句都能判为真或者假;语言须要适应思想,比如,有些思想无所谓真假,有的则非真即假,语言也要有与这两种思想对应的形式。在中世纪,波伊提乌(Boethius)也有语言意义寄生于思想而思想则完全独立于语言的精彩论述,其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贯穿整个中世纪(Arens 1984: 174-6)。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humanists)注意到自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并对自然语言有新的认识,比如把语言看成分析的主要对象或认为语言对人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等。培根(Bacon)致力于构建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们通过谈话相联系,人们选择大家能够理解的语言,因为糟糕的词语是理解的障碍,会“使人陷入无数的争吵和捏造”(Bacon 2000:42)。到了现代,语言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洛克(Locke)在以观念为核心讨论人类知识的特质和局限时,认为词语指示观念,观念再现事物,所以人类才能追求和传播知识。语言的作用就是使我们迅捷、容易地传递知识。
显然,哲学对语言的关怀在第一哲学中就已存在,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语言转向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时期。主要原因是不管他们对语言有多么关心,有多少精彩的见地,语言始终是配角。其次,他们始终没有将语言视为解决哲学问题的途径,没有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视为同构关系,当然也就没有建立起一套通过澄清语言的结构去认识世界的系统方法。比如,苏格拉底根本没有谈及语言和知识的关系问题,而柏拉图在讨论语言后得出的结论是语言对知识获取没有任何作为,并坚持认为只能通过研究事物本身去认识事物;亚里斯多德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演绎推理中的肯定、否定、命题、矛盾和对立等基本要素,其终极关怀是形而上学,尽管他的逻辑追问出现了语言理论的心理痕迹,但是他并非要透过语言去更好地解读人的心灵;中世纪的波伊提乌坚持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从不认为哲学问题可以在语言那里找到解答;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目光投向语言也是为了批判经院逻辑(Scholastic logic)和满足公共演说家、政治家和布道者的需要,教他们如何使用词语以达到雄辩的目的,完全是一种非哲学的视角。总之,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之前,哲学对语言的思考林林总总,但始终只是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一部分,即使是弗雷格对意义和指称的精辟论述也只是为了解决他的算术基础问题,这与语言转向的精神旨趣还有不小距离。
6 结束语
本文从“语言转向”的源头谈起,强调语言转向通过构建人工语言或描写自然语言来寻求哲学问题的答案。这种哲学方法孕育于弗雷格构建数理逻辑时对数的意义的追问,萌芽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实现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与实在同构的论断,完成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哲学对语言的关怀可以上溯自西方哲学的黎明时期,但与语言转向不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都未将语言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都没有认识到语言对世界的投射作用。
维特根斯坦之后语言转向仍在继续,语言游戏论思想直接促成牛津日常语言分析的繁荣,最终成就日后称为“日常语言哲学”的牛津哲学。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兴起和繁荣又催生一门崭新的学科——语用学。语用学接过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等,并使它们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无论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还是当代语用学,都延续着维特根斯坦语言转向的哲学信念:分析语言的终极目的是了解人的思想和认识客观世界。
哲学对语言的关怀源远流长,但是直到20世纪,语言才成为哲学研究的中轴,不少哲学家为此兴奋不已,信心十足地以为已经寻找到了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途径,这种信心也随着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等哲人的思想的出台而达到顶峰。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信心大大减弱,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但即便是在哲学已经步入心智时代的今天,孕育于弗雷格,萌芽于罗素,最终由维特根斯坦开启的语言转向仍在延续。
阳小华. 西方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渊源演变[J]. 外语学刊, 2005(3).
Anscombe, G. E. S.AnIntroductiontoWittgenstein’sTractatus[M]. London: Hutchinson, 1971.
Arens, H. Aristotle’s Theory of Language and its Tradition[A].StudiesintheHistoryofLinguistics.Vol29[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4.
Ayer, A. J.Language,TruthandLogic[M].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46.
Bacon, F.TheNewOrgan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ergmann, G. (1953). Logical Positivism, Languag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taphysics.RivistaCriticadiStoriaDellaFilosophia, VIII: 453-81. Reprinted ( in a Truncated form)[A]. R. Rorty (ed.).TheLinguisticTurn:RcentEssaysinPhilosophicalMethod[C].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Bergmann, G.LogicandReality[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Davidson, D. Theories of Meaning and Learnable Languages[A]. In Y. Bar-Hillel (ed.).Logic,MethodologyandPhilosophyofScience:Proceedingsofthe1964InternationalCongress, 384-94[C].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5.
Dummet, M.Frege:PhilosophyofLanguage[M]. London: Duckworth, 1973.
Dummett, M.OriginsofAnalyticalPhilosophy[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ege, G. (1892). On Sense and Reference[A]. Reprinted in B. McGuinness (ed.).CollectedPapersonMathematics,LogicandPhilosophy[C]. Oxford: Blackwell, 1984.
Frege, G.TheFoundationsofArithmetics[M]. Oxford: Blackwell, 1959.
Frege, G.ConceptualNotationandRelatedArticl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Frege, G.CollectedPapersonMathematics,LogicandPhilosophy[M]. Oxford: Blackwell, 1984.
Hacker, P. M. S.Wittgenstein’sPlaceinTwentieth-centuryAnalyticPhilosophy[M]. Oxford: Blackwell, 1996.
Hacker, P. M. S. Analytic Philosophy: Beyon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ack Again[A]. In M. Beaney (ed.).TheAnalyticTurn:AnalysisinEarlyAnalytic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y[C]. London: Routledge, 2007.
Locke, J.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M]. Oxford: Oxfrod University Press,1975.
Moor, G. E. 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J].Mind, New Series, 1903(12).
Plato.TheCollectedDialoguesofPlato[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Ramsey, F. P.TheFoundationsofMathematic[M]. London: Routledge, 1931.
Rorty,R.TheLinguisticTurn:RcentEssaysinPhilosophicalMethod[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Russell, B.OurKnowledgeoftheExternalWorldasaFieldforScientificMethodinPhilosophy[M]. Chicago: Open Court, Lecture II, 1914.
Russell, B.Icarus,orTheFutureofScience[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4.
Russell, B.MyPhilosophicalDevelopment[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9.
Russell, B.AnInquiryintoMeaningandTruth[M]. London: Unwin Paperbacks, 1980.
Sluga, H. Frege on Meaning. In H. J. Glock (ed.).TheRiseofAnalytic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1997.
Strawson, P.PhilosophicalLogic[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Textor, M.FregeonSenseandReference[M]. London: Routledge, 2011.
Wittgenstein, L.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1.
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53.
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Grammar[M]. Oxford:Blackwell, 1974.
【责任编辑李洪儒】
TheLinguisticTurnandConcernforLanguage
Feng Guang-w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China)
There have been two competing arguments as to who inaugurated The Linguistic Turn. Bergmann(1953) and Hacker (1996) both claim that Wittgenstein is the first to execute the Linguistic Turn, while Dummet (1973, 1993) maintains that it begins with Frege’s discussion of the meaning of numbers inTheFoundationsofArithmetic. This article argues in favour of the former view that the Linguistic Turn started with Wittgenstein’s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and completed with his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 But unlike Bergmann, who seems to have ignored Frege and Russell, we argue that Wittgenstein’s doctrine that all philosophy is a critique of language does not come about in complete autonomy. Rather, it grows notably out of the ground prepared by Frege’s quantificational logic and Russell’s theory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 It is also noted that concern for language is nothing new in first philosophy or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but it is hardly in the same spirit or with the same purpose that characterizes the Linguistic Turn, which is a philosophical method adopted by a group of philosophers after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0thcentury to approach metaphys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through analysis of language, formal or natural.
The linguistic Turn;analytic philosophy;concern with language
B089
A
1000-0100(2012)05-0002-7
*本研究得到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资助,在此鸣谢。
2012-07-03
编者按:综观国际学术界,当今的语言哲学依然专注于著名学者、经典文献和基本论题的理解和消化。也就是说,该学科的发展还处于量变阶段。因此,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虽然着眼点各异,但是都以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语言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无论从维特根斯坦到弗雷格还是从维特根斯坦到格莱斯,本刊旨在向学界申明,语言哲学经典的探幽还须要通过探索不同语言哲学家相关思想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不同思想、不同学派之间的整合。这是该学科实现质变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