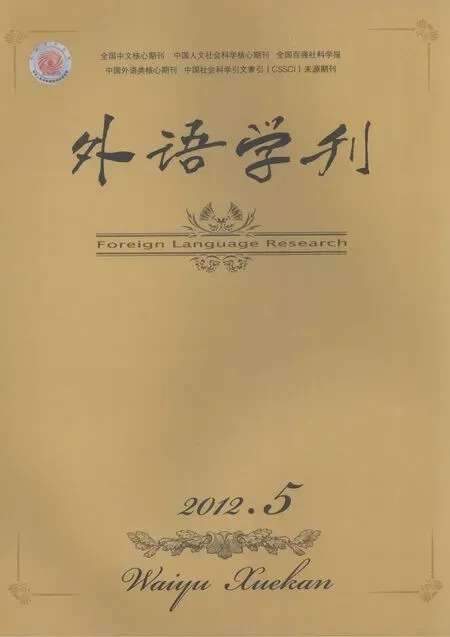语言的不确定性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模糊性
封宗信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〇语言的功能维度
语言的不确定性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模糊性
封宗信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不确定性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特征。韩礼德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理论特有的许多范畴概念描写语法和语法系统里的不确定性;90年代以来,他从“以语法方式思考”的语法学角度更细致地分析了语言各个层面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并明确提到了模糊逻辑概念。本文通过讨论语言(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和韩礼德对模糊性的正视和深入分析,指出系统功能语法和语法学理论直接触及到逻辑学领域和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关心的问题。
不确定性;模糊性;功能语法;语法逻辑;语法学
1 引言
“语言的不确定性”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特征。Halliday在早期系统功能语法描写中提出了“盖然性”/“近似性”的概念说明词汇的开放集合特征(1966)、方言学里两个因素的特征(1978)、两极归一性方法不能准确处理的语言事实,如人际功能系统的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里的多层次、多级别、多选项特征(1985)。90年代以来,Halliday (1996, 2002)多次强调,功能语法是语法理论也是语法学(grammatics)理论。他发现语言的不确定性存在于语法和语法学两个层面,提出了一系列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写语言的不确定性;在对语言各个层面的分析和描写上,以语法逻辑为本,由隐到显地借鉴了逻辑学方法和概念;对自然语言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分析和描写,直接触及了逻辑学许多领域关心的重要问题。
2 语言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源于哲学界关心的“无常、不确知、含糊”(uncertainty)概念。因为不确定的事物都无法量化和验证,所以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尽可能在争论中排除不确定的术语。但客观世界是复杂多样和模糊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推理、判断、预测和决策大多是在信息不完整、不确定、不精确或模糊的条件下进行的。试图对客观事物进行清晰和条理分明的范畴化和系统化描述,会因为描述这些复杂过程的自然语言本身无法达到清晰和精确而无法实现。
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导致了语言学范畴和概念的不确定性。“Linguistic indeterminacy”有双重含义,既指“语言”层面的不确定性,也指“语言学”层面的不确定性。普通意义上的语言不确定性指语义解释和“定义”(definition)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现代汉语词典》2002:298)。但在任何一部词典里,任何一个词条的定义都不是“确切而简要的说明”,而是别的词汇的组合表意,只有在该词典里连续检索一串词汇才能逐渐接近被定义的词的意义,这是词汇层面的语言不确定性。Saussure指出,“语言里只有差异,没有肯定性的词”(Saussure 1959:120)。概念纯粹是差异性的(differential),不是由肯定性内容界定,而是通过在系统中与其他词项的关系以否定性手段界定的(Saussure 1959:117)。因此,在许多学科里,最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种差+属”,即把要界定的概念放在包含它的属范畴中,用同一属范畴内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来揭示其特征。
在文本层面,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指出,表意(signification)总是一个指称其他符号的过程,没有仅指一个符号本身的符号(Derrida 1976: 43)。指称这个过程是无尽头的参照过程,永远找不到意义本身。德里达在索绪尔的“差异关系”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衍异”(différance)的概念,融空间上的差异(difference)和时间上的延迟(deferring)于一体来说明:意义是透过词与词之间的差异进行的游戏创造出来的,该游戏是“无限的”、“无穷的”和“不确定的”。
在类型学研究中,类和范畴的不确定性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Lyons在讨论类逻辑(logic of classes)时指出,语言里除了开放型和封闭型两类,还有一类是我们不知道其归属的、“不确定的”类 (Lyons 1977:154-155)。Lyons所讨论的“类”与数学集合论(set theory)之“集合”没有区别,是借用数理逻辑来说明语言学问题。Källgren (1996)发现,词类的不确定性是计算语言学上标记出错的主要根源。美国心理学家Heider (1971)曾指出,一个范畴有核心成分也有外围边缘成分,被试在判断含有范畴与类属成分的句子(如A chicken is a bird)正误时,对含有核心成分(范畴内的典型成分)的句子比含有外围成分(范畴内的非典型成分)的句子反应更快,从而认为儿童学习语言时在外围成分上比成年人更容易出错(Lakoff 1973: 459)。Lakoff在模糊论的框架下发现,自然语言中有一类被形式语义学忽视、但可用模糊集合的从属函数(membership functions)来描述的词,并指出这种“隐性涉及模糊性、能使事物更模糊或者不大模糊的词语”提出了一些最有趣的问题(Lakoff 1973: 471)。
Halliday指出,成年人的语言系统里有很多不稳定的东西(如英语的及物系统),儿童所设法接近(approximate)的东西不是固定和协调的,而是游离、飘忽不定和充满不确定性的(Halliday 1978:116-117)。虽然有语场、语旨和语式来确定各种意义范围,把语言分别确定在概念功能、人际功能、篇章功能里,但有很多不确定的区域。比如儿童对物体的评估就处在语场和语旨之间的地带,意态系统在语言的概念和人际部分之间。他又指出,“篇章”的概念也有不确定性(Halliday 1978:136)。虽然小句或音节都相对很好界定,但正常情况下一个篇章则很难界定,它可长可短,也并非有始有终,而且没有明确的边界。甚至“书面”与“口头”范畴本身也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或指一个语篇最初生成所依靠的媒介,或要送达别人的媒介,或要具体使用的媒介,或指语篇的其他代表性特征或属性。对语言描写得越细致,建立的概念越多,就会发现不确定的情况也越多。语法有内部组织,是概念功能;它有一些特殊目的的子语法(sub-grammars),有大量的不确定性。而语言学理论还是处在重视把微粒状(particulateness)当做规范的阶段,对非微粒状的东西则用截然不同的、甚至明显毫无关系的概念去对付。就篇章研究和篇章意义而言,我们不能把不确定性放置脑后。
胡壮麟(1984)总结的“韩礼德语言学的六个核心思想”中,最后一个是语言的近似性或盖然性。胡指出,韩礼德从信息理论中汲取了“近似的”(approximative)或“盖然的”(probabilistic)思想。虽然盖然性是语言故有的特征之一,而且这种规律性特征在人们选择词汇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很少有人把盖然性原则“类推到对语法系统的描写上”。例如“I shall go”与“I will go”之间,同一个陈述的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之间是盖然性关系。语言中存在“程度大小”和“频率高低”的现象,并非有些合乎语法而有些不合乎语法。那么对Halliday来说, “合乎语法性”(grammaticality)也是个不确定的概念。
Halliday在《走向盖然性解释》一文中指出,用盖然性解释语言,作为“语法学”的语法必须是聚合性的,必须能把语言表达成选项,因为盖然性是无意识的选A而不选B的概率(Halliday 1991:42)。他在《语料库研究与盖然性语法》中指出,懂英语的人都知道,在词汇出现频率上go > walk > stroll.人除了懂语法概念和范畴,还同样懂语法。讲英语的人会发现主动语态的频率高于被动语态,肯定式高于否定式,陈述式高于疑问式,the高于this或that,简单时态高于复杂时态。但他们没法确定单数与复数、this与that, 过去时与现在时之间的相对频率孰高孰低。这说明有些系统趋向于等概率(equiprobable),并因此有较高的信息价值;而有些系统则明显失衡并因此显得信息冗余程度更高(Halliday 2005:68)。
胡壮麟指出,Halliday是最早把盖然性原则类推到描写语法系统的学者。“近似性”或“盖然性”语言学思想,在于通过“精确地区别语义与特定情景语境的关系”来掌握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通过精密阶(scale of delicacy),由一般趋向具体,越分越细,可对系统中每个选择点的可选项给以近似值。这一思想不但能更准确地描写语义成分和词汇语法项等的分类,而且能明确展现不同语篇中语言现象出现的频率(如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在普通语篇与科技语篇中的不同分布)或近似值。胡文总结道,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能说明不同语域之间的差别很可能是它们在词汇语法层上的盖然率的不同,而这又受制于所要表达的不同语义的精密度。
语言描写自古就有规则与不规则之争。Halliday指出,语言学现在似乎不怕“不纯”(impurity),而且开始认真对待语言里的“模糊性”(Halliday 1978:114)。但这是个逻辑学概念而非社会学概念,是指偏离了理想的规则所要求的整齐规范,而非社会符号系统里的一个有机属性。语言的“模糊”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制度的动态和张力的一种表达。
3 语法与语法学中的不确定性
Halliday在《如何表意?》(1992/2002)一文中指出,语法是“经验的理论”(a theory of experience),而语法学是“语法之语法,经验的理论之理论”(a theory of theories of experience)。在这个层面就能看清,经验是有序与无序或混沌之间的一种交错(interplay)。科学家用科学术语来解释现实,但他们已经发现自己使用的工具语言(metalanguage)太僵化、太确定,因此在寻求两全其美的方法,即一种话语,从不确定性、连续性和不稳定性来解释经验(Halliday 2002:365-366)。Halliday曾指出,当语言学家势必要关心人的状况(human condition)。
在《论语法与语法学》(1996/2002)一文中,Halliday在第十节和第十六节分别讨论了“语法中的不确定性”和“语法学中的不确定性”。他写道,想把语法归纳整齐的努力说明,语法是不确定的或“模糊的”,即Zadeh的“模糊逻辑”(fuzzy logic)术语之意。形式逻辑和数学都可以被看做是把自然语言语法中的不确定性归结整理的一个结果而已(Halliday 2002:399)。他从类型学研究遇到的不确定性问题与“盖然性”之间的关系指出,盖然性与界定语法范畴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确定性的类型学研究本身就有些不确定,因此他分析出了3个类型:“层级渐变连续体”(clines)、“混合”(blends)、“互补性”(complementarities),外加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盖然性”作为第四个类型(Halliday 2002:399)。在“混合”与歧义之间也有不确定性,因为在一个语境下明显歧义的措辞在另一个语境里可能是混合。严格地说,盖然性不是一个“模糊”概念,但它在语法里给范畴的定义增加了不确定性(Halliday 2002:400)。
Halliday认为语法学应该容纳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是语法的一个本质和必要特征”,是“语法学应该解释和重视的东西”。语法提供了一种人工确定性,以间断点(discontinuities)的形式来体现(Halliday 2002:409)。语法学对不确定性的包容,就是接受“近似值”。在数学上,近似值是接近标准、接近完全正确的一个数字(表示近似值近似的程度,叫做近似数的精确度)。他通过分析指出,语法学是复杂性管理(complexity management)。一方面它有具体策略来消除模糊性,使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界限(如用系统网络处理系统内和系统之间的定性关系,把系统明确地识解为A或B,不存在盖然性;同时也可以使系统之间相互依赖或相互独立,不存在局部关联的程度问题);但另一方面,语法学又把各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当做复杂性管理的资源来开发。
Halliday重视从社会秩序角度来解释语言(学)过程。他早就说过,他在构建的这种语言学的“语法”是一组规则,其概念框架来自逻辑学,因此衍生自逻辑学语言模式中的组织概念就是结构概念(Halliday 1978:3-4)。由于结构功能受逻辑关系(如主语与谓语)限定,语言关系被看做是类(class)——如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形式关系。他承认Chomsky视自然语言为形式系统的巨大贡献,也不否认,如果说话者与句子都在理想状态下,语言不仅可以被表达为规则,而且可以被表达为有序的规则。但他指出,社会人(the social man)进入这幅图景之时,规则不再有序,甚至规则的概念也要受到质疑(Halliday 1978:4)。因此他提出了语法理论的4个最基本范畴:单位(unit)、结构(structure)、类(class)、系统(system),并指出最基本范畴是抽象化级别最高的范畴,只有4个,不多不少,这是由语言的本质决定的。
这4个范畴都与传统语言学不同。“单位”指具有语法形式并能在其中作出语法选择的语言片段;“类”是任何一组在结构上具有相同操作可能性的成分;“结构”是用来解释一个句法单位是如何由低一级的单位组成的;“系统”指在有聚合关系、在“类”里起作用的相关成分构成的有限集合,是韩礼德后来把语言整体当做“系统之系统”的关键概念。韩礼德曾指出,这4个范畴之间有联系,且有逻辑衍生关系(logically derivable),但在逻辑顺序上不分先后。同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与语料的关系又涉及另外三个不同的抽象层面:级阶(rank)、释示(exponence)、精密度(delicacy)。“释示”来自层级语言学分析(hierarchical linguistic analysis),指“较高分析层面与较低分析层面语言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Crystal 2008:180)。“级阶”和“精密度”专属于“韩礼德语言学”,分别指“范畴相互联系起来的分析阶,即同一平面上各语言单位(unit)的层级排列(hierarchical arrangement)”(Crystal 2008:402)和“把理论各范畴相互联系起来的分析阶(scales of analysis)之一,即分析的精度不断增加的维度”(Crystal 2008:134)。Halliday (1961)解释道,他在讨论这些关系时使用了更具普遍性的类型概念——层级(hierarchy)、分类法(taxonomy)、层级渐变连续体(cline)。这几个概念来自生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等级”用来强调单维度上相关成分组成的系统之“逻辑”顺序,“分类”作为一个特别“等级”来突出两种逻辑关系。“Cline”在生态学上指“渐变群”,被Crystal定义为特指“韩礼德语言学中潜在的无穷多等级分级渐变”的术语(Crystal 2008: 80)。
Halliday (1963)早在描述语调的研究中就指出,“标准”英式英语里的自然会话可以表示为涉及5个语调里的“连续性选择”。他在功能语法中使用的“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概念,是为了说明由“最大语法性”到“最大词汇性”之间的渐变、混合与互补。语法范畴的创新和对系统网络中系统选择趋于精确的描写,一直是语法与语法学中处理语言不确定性的核心。
4 功能语法对模糊性的描写
《功能语法导论》第一版(1985)里,只有两处提到模糊性,而且是一般意义上的模糊。Halliday在分析命题(proposition)与提议(proposal)的结构关系时指出,两者都可以有言语投射和心理投射。命题(信息交换)可以通过有引述功能的言语过程小句来并列投射(转述),而被投射的小句大多是限定性小句,但也有非限定性小句。提议也可以被并列投射(转述),被投射的小句可以是限定性小句,也可以是非限定性小句。这样,我们会以为,任何表示言语行为的动词都可以用来投射。因此,带非限定性从属小句的言语过程会被解释为投射。如果非限定性从属小句可以被带有意态的限定性小句替换,就更加肯定的是投射了。例如He promised || to make her happy可以替换为He promised || he would make her happy,就这排除了目的性小句。它与He promised, (in order) to make her happy的明显区别在于,后者是扩展(expansion)关系,而非投射关系。使役动词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它们并非言语过程,而且通常没有对等的限定性形式,例如我们不说*I’ll make that you should regret this!
表面上看,提议只可通过言语来投射,不大可能有对等于命题的心理投射过程。Halliday指出,不能通过“认为”使某事发生(think sth. to happen),但完全可以通过“祝愿”使某事发生(wish sth. to happen)。提议是被心理过程投射的,但与命题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作为符号交换的不同形式之本质特征。在心理投射中,命题是看法(以表示认知过程的“认为”、“知道”、“明白”等来体现),提议是愿望(以表示感情反应过程的“希望”、“喜欢”、“害怕”等来体现),但两个类别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Halliday 1985:236-237)。这是Halliday在功能语法描写中首次使用fuzzy一词。他还指出,关联与并列扩展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Halliday 1985:318),因为有许多可以任意解释的情况。实际写作中,“.... So, ...”和“..., so ...”都有可能,前者应该解释为关联,后者为并列,两个不同结构在意义上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过分细致的区分,遍布于语言系统,尤其在有关扩展和投射的基本语义关系语法里,到处都有。
在《功能语法导论》第二版(1994)里,Halliday增加了两处模糊性分析:一个是表示特质的修饰词(Epithet)与分类词(Classifier)之间的关系(Halliday 1994:184-185),另一个是扩展与投射重叠区域里使动(cause...to be done)与意动(want...to be done)之间的关系(Halliday 1994:289)。他指出,表示特质的修饰词与分类词之间的“界限不明显”(Halliday 1994:184),但区别非常大。表示特质的修饰词说明相关事物的子集合(subset)的某些性状(如old, long, blue, fast),既可以是事物本身的客观性质,也可以是说话人对所谈对象的主观态度表达(如splendid, silly, fantastic)。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但前者在功能上属于经验型的,而后者在名词词组的意义里代表人际成分,而且以不同形式反映在语法里。根本区别在于,经验型的特质词具有定义的功能,而人际型的特质词不具有定义功能。用文体学术语,前者是客观描述性的,后者是主观评价性的。
分类词说明相关事物子集合或子类(subclass)的某些性状(如electric trains, passenger trains, wooden trains, toy trains),有时候或是修饰词或是分类词,要根据意义判断:比如fast trains有时候指“快的车”,有时候特指“快车”,因此修饰词与分类词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区别(Halliday 1994:185)。分类词没有比较级形式(如*a more electric train),也没有强调形式(如*a very electric train),而是用排他性和穷尽性的集合来表示(如电车、汽车、内燃机车)。而且分类词的语义范畴相当广,包括材料、比例、范围、目的、功能、等级地位、来源、运行方式以及任何能把事物的集合区分成更小集合的系统之特征。“分类词+物质”的关系有时候很紧密,常常被当做复合词,尤其当表示物质的词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类或集合时。由于复合词与“分类词+物质”的名词词组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而且变化不定,因此很多人才感到书写时难以确定到底是按一个词、两个词还是用连字符处理(如walkingstick, walking stick, walking-stick)。
在分析动词词组投射的从属关系时,Halliday写道,want与to go之间的关系是投射关系(Halliday 1994:289)。“Do it”的投射,如在(She) wants to do it中,只是意义,表示“要做”,并无“做”(does it)的含义。而扩展则不同,如(She) tries to do it和(She) starts to do it确实有“做”(does it)的含义,即使此“做”有只做一部分或并未做完的可能。Halliday的观点是,表示情感的心理过程投射的是“商品与服务”类型的交换,即提议。如果该投射的主语与心理过程小句的主语一致,该提议就是说话者提出做事(offer),如She wants to do it.如果投射的主语与心理过程小句的主语不一致,该提议就是命令,如She wants YOU to do it.在第一种类型里,主语不用重复出现,但由表示情感的小句来执行(可用反身代词来明确表达,如She wants to do it herself)。因此,可以把所有此类投射看做小句联结(clause nexuses):
She wants || to do it.
She wants || him to do it.
但在很多方面,它们与动词词组很相似。(1)被投射的成分(典型的完成式非限定性)像扩展类型一样,产生了动词时态,如will和be going to两种将来形式。(2)用问句检验,应该是What does she want to do?而不是What does she want?(3)主语不同的命令形式与一些使役扩展(causative expansions)相似:
She wants him to do it.
She causes/gets him to do it.
He is wanted to do it.
He is caused/got to do it.
She wants it (to be) done.
She causes it to be done/gets it done.
扩展与投射正好在这个地带相遇并发生重叠。“使动”表示有外部执行者的“做”。“意动”表示这件事被设想或被投射,但不一定能发生。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却是“模糊的”(Halliday 1994:289)。总的来说,如果可以用一个限定性的that小句表示(如She wished that he would come),那么原则上这个关系就是投射关系。但这里又有个“灰色”区域:She wanted that he should come的说法是可能的,但不常见;She allowed that he should come的说法不常见,却是可能的(Halliday 1994:289-290)。Halliday接着指出,虽然有灰色地带的模糊个案,但投射与扩展是不同的类型。
《功能语法导论》第三版(2004)里对模糊性的分析和论述比前两版更多,如词与词之间的模糊界限,书写词与语法词范畴之间的模糊,聚合轴上词汇集合的模糊,语法视角下的模糊封闭系统与词汇层面的确定与有限开放集的矛盾。
第三版里描写的“成分结构”(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7)是沿用Halliday (1985)的路子,用“拼写”(字母组合成词)和标点(特殊符号及上下标表示分界)的结合。Halliday & Matthiessen指出,该系统比他们解释出得更为复杂,其中一个方面是,词的边缘界限有些“模糊”,因此只好用连字符来处理不确定性(如frying pan, fryingpan, frying-pan)。这正是把第二版中讨论过的普通人书写时遇到的普遍问题提到系统描写的高度。他们接着指出,写语法的人是在谈论书写单位还是语法单位,常常“不确定”,因此他们用“句”和“子句”(sub-sentence)来指书写单位。对于语法单位,仍沿用“小句”;许多小句通过语法关系连接在一起时,叫“小句复合体”。但在小于小句的层次上,情况则很不同。从书写角度看,子句由词构成,因为在子句与词之间没有书写单位。“词”也是语法单位,只好一“词”两用,既指语法单位又指书写单位。其原因是,书写词与语法词两个范畴“同等模糊”(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8-9)。
在讨论聚合系统和词汇系统时,他们写道,词汇项在具有相同语义学特征和共同搭配模式的“集合”里发挥作用(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40)。因此,“树、花、草”都有“植物”这一类属名称的共同特征;语料库显示,这些词汇的共同趋势是与颜色名称和grow词项的各种形式搭配。这些集合由于一些不确定性的词项(如shrub, blossom)而非常“模糊”。在讨论词汇语法连续体时,他们指出,如果把语法和词汇当做一个连续体的两端,那么就要问,介于它们之间的中间部分是什么?正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才把词项放置在聚合轴上描述,并从两个视角来看其形成的序列,从语法角度看做庞大、“模糊”的封闭系统,或从词汇角度看做确定的有限开放集合(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45)。
Halliday认为,过程类型(如物质过程、行为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关系过程、存在过程)是符号学空间,不同的区域代表不同的过程类型。区域有核心地区,代表过程类型的“原型”(prototypical)组成成分。但是区域之间是连续的,相互重叠,构成阴影部分。这些界限边缘区说明,过程类型是“模糊范畴”(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172)。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的术语是模糊范畴,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模糊范畴代表“模糊集合”,并非准确、清晰、界限分明的集合(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174)。Halliday指出,语法以自己的不确定特质去处理语法的不确定性,因此语法理论的范畴就像语法本身所解释的范畴一样模糊(Halliday 1996/ 2002:402)。
5 功能语法的逻辑
Halliday在语法学中所做的事情是对自然语言进行建模(modeling)。他认为,这样做也可以为别的东西提供参考,即把语言当做一种“逻辑”。逻辑分数理逻辑和语法逻辑,它们都是符号系统,但有互补关系。在有些情况下,需要语法派生的自然逻辑而“不需要,或也需要”人工设计的数理逻辑(Halliday 1996/2002:416)。
语言系统里的逻辑成分,其独特之处是通过递归性结构来表达,而所有其他功能都是通过非递归性结构来表达的(Halliday 1978:48)。逻辑语义学是个单一系统,而社会语义学是(也必须是)一个多重系统,即意义选项集合之集合,每一个集合都与具体的社会语境、语境类型或域(domain)相关(Halliday 1978:79)。虽然语言关系可以被看做类之间的形式关系,但语法是“系统思考”而非“组装式思考”(compositional thinking),是语法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是模糊的和盖然的范畴而不是清晰、分明、确定的范畴(Halliday 2002:3)。Matthiessen总结道,语法逻辑是自然语言衍生的逻辑,与专门设计的(而非衍生的)人工符号学系统——符号逻辑和形式逻辑完全不同。语法逻辑与现代符号逻辑的主要区别有3条:(1)把不确定性描写为一个有积极价值的特征;(2)逻辑语义范围比命题逻辑中的逻辑连接符范围广;(3)建立在共识(consensus)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真值上(Matthiessen 2010:109)。
Halliday创造的“语法学”术语,是要避免“语法既指现象本身(语言里的一个具体层面)又指对现象的研究”的模棱两可概念。他用了一个比例关系来说明:语法学:语法::语言学:语言。他的语法学是“对语法理论的一个具体看法”,因此不只是有关语言的理论而是“用语法进行思考的一个方法”。从《功能语法导论》第一版开始,Halliday一直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称做“语法”。后来指出,他的语法既是语法理论也是语法学理论。他的语法学核心是“用以思考语法本身”、“用语法方式思维”、“把语言作为其元语言”(Halliday 1992/2002:366)。他指出,语法学在解释语法时有模仿性质,建立在语法逻辑之上。这种语法学,尽管缺少数理逻辑的严密性,其优势却正在于此,不但可以理解语言艺术符号,而且可以理解非语言艺术形式的符号系统(Halliday 2002:402)。
菅野道夫(Sugeno, 1995)在自然语言上提出了“智能模糊计算”概念,或称“以词计算”。Halliday (1996)提到这项研究时强调菅野道夫的“智能计算”,淡化其“模糊”,并认为其实是“以意义计算”。菅野道夫的观点是:计算机要达到真正智能的程度,必须通过自然语言用人的方式运作。这一思路来自Zadeh模糊逻辑,依靠模糊集合和模糊匹配过程来推理和推测。Halliday指出,系统理论已经广泛使用于计算语言学领域,但更重要的是,系统语法学并不排斥模糊性。虽然因此招致批判,但语法学要对智能计算有点价值就必须有这一基本特点(Halliday 1996: 34-35)。
模糊逻辑学的核心思想是,个体是否属于某个集合,只是程度问题,如介于0与1之间的某个实数。虽然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里没有明确提到过模糊逻辑,但他早就隐性地借鉴了模糊逻辑学和模态逻辑学思想,从两极归一性出发分析了系统选择中大量的是与否、允许与禁止等之间的中介区域、模糊地带和选项。他构建的情态系统是对正负两极之间不确定性的完美表达,从人际关系角度构建了yes与no之间不确定的各种语义区域,如命题涉及的“盖然性”、“通常性”(usuality)和提议涉及的“职责”(obligation)、“倾向”(inclination)的意义等级。“情态”与模态逻辑学里的“模态”(modality)同源,也涉及模糊逻辑问题。关于情态系统的模态逻辑学性质,笔者已作过分析和讨论(封宗信 2011)。从Halliday (1970)早期对情态的描写到后期完整详细的描写可以看出,他的情态系统框架既包括了传统逻辑学的3种模态逻辑形式(可能性、盖然性、必然性),也包括了与现代模态逻辑学相关的扩展概念。在描述情态的扩展概念(如It is probably right = I think it is right)过程中,创造性地总结了语言系统里“语法隐喻”(语法变异)意义上的情态隐喻,从而把看似模糊的情态明确表示为两种不同的状况——主观的心理投射和客观的被投射事实,揭示了人对客观世界进行评价、判断和操控的潜能(封宗信 2011, 2012)。
从《功能语法导论》第一版(1985)到第三版(2004)的将近二十年间,Halliday从“语法”理论到“语法学”理论,从第一、二版中“逻辑功能”归属三元功能之一的“概念功能”到第三版中凸显“逻辑功能”为四大元功能之首(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63),从强调语法逻辑排斥形式逻辑到承认数理逻辑的用处,再到明确提到模糊逻辑概念,整个发展过程是逐渐丰富、不断提升和趋于完善的逻辑化过程。
6 结束语
语言学理论追求最大可能的规范和精确描写。然而,客观世界和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与人的愿望相悖。虽然Halliday承认语言是不可穷尽的(Halliday 1985:xiii),但他强调系统的完整性和对语言事实描写的相对准确性。随着分析沿着精密阶越来越细致,Halliday发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问题越来越多,功能语法理论的模糊逻辑学成分越来越明显,用最大的近似值描写最接近语言事实的语法理论,把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本质与功能语法所追求的精密和准确巧妙地结合在“以语法方式思考”的层面。他在语法学理念下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包容、正面分析和深入描写,不但直接触及到逻辑学许多领域关心的问题,而且对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相关领域也有重要价值。
封宗信. 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封宗信.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系统:逻辑、语义、语用[J].外语教学, 2011(6).
封宗信.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逻辑学性质[A]. 语言研究与外语教学[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胡壮麟. 韩礼德语言学的六个核心思想[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4(1).
胡壮麟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胡壮麟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Crystal, D.ADictionaryofLinguisticsandPhonetics(6th ed.)[M]. Oxford: Blackwell, 2008.
Derrida, J.OfGrammatolog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Halliday, M.A.K.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J].Word, 1961(3).
Halliday, M.A.K. The Tones of English[J].ArchivumLinguisticum, 1963(1).
Halliday, M.A.K. Lexis as a Linguistic Level [A]. In C. E. Bazell,et.al., (eds.).InMemoryofJ.R.Firth[C]. London: Longman, 1966.
Halliday, M.A.K.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Language as Seen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Modality and Mood in English[J].FoundationsofLanguage, 1970(3).
Halliday, M.A.K.LanguageasSocialSemiotic[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Halliday, M.A.K.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1994.
Halliday, M.A.K. Towards Probabilistic Interpretations [A]. In E. Ventola (ed.).FunctionalandSystemicLinguistics:ApproachesandUses[C].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1.
Halliday, M.A.K. A Recent View of “Missteps” in Linguistic Theory [J].FunctionsofLanguage, 1995(2).
Halliday, M.A.K. On Grammar and Grammatics [A]. In R. Hasan, C. Cloran, and D. Butt (eds.).FunctionalDescriptions:TheoryinPractice[C].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6.
Halliday, M.A.K. How Do You Mean? [A]. In J. Webster (ed.).OnGrammar[C]. London: Continuum, 2002.
Halliday, M.A.K. Introduction: A Personal Perspective [A]. In J. Webster (ed.).OnGrammar[C]. London: Continuum, 2002.
Halliday, M.A.K. Corpus Studies and Probabilistic Grammar [A]. In J. Webster (ed.).ComputationalandQuantitativeStudies[C]. London: Continuum, 2005.
Halliday, M.A.K. & C.M.I.M. Matthiessen.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3rd ed.) [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Källgren, G. Linguistic Indeterminacy as a Source of Errors in Tagging[A].COLING’96Proceedingsofthe16thConferenceonComputationalLinguistics(Vol. 2) [C]. Stroudsburg, PA: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6.
Lakoff, G.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J].JournalofPhilosophicalLogic, 1973(2).
Lyons, J.Semantics(Vol. 1)[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Matthiessen, C.M.I.M.KeyTermsin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Saussure, F. de.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M]. 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Sugeno, M. Intelligent Fuzzy Computing[A]. Paper Presented to PACLING II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Pacific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C].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5.
【责任编辑郑 丹】
LinguisticIndeterminacyandFuzzinessin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
Feng Zong-xi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Indeterminacy is a universal feature in natural language. Halliday has invented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specific to his systemic-functional description of indeterminacies in both the grammar and the grammatical system. Since the 1990s, in developing a theory of grammatics that “thinks grammatically”, Hallida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fuzziness, with explicit reference to fuzzy logic. This paper discusses issues in linguistic indeterminacies, presents some details of Halliday’s analyses and descriptions of indeterminacies and fuzziness, and points out that such serious treatment has touched upon crucial issues in several fields of logic and in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nguistic indeterminacy; fuzziness; Functional Grammar; grammatical logic; grammatics
H0-06
A
1000-0100(2012)05-0041-7
2012-07-10
编者按:功能是所有语言必须具备的标志性特征,因此是语言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栏目包括两个论题:前三篇文章集中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相关思想,后两篇则关注语篇模式和思维对语篇的影响。前者与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主流相契合;后者虽然处于功能语言学的边缘,却是该分支学科十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