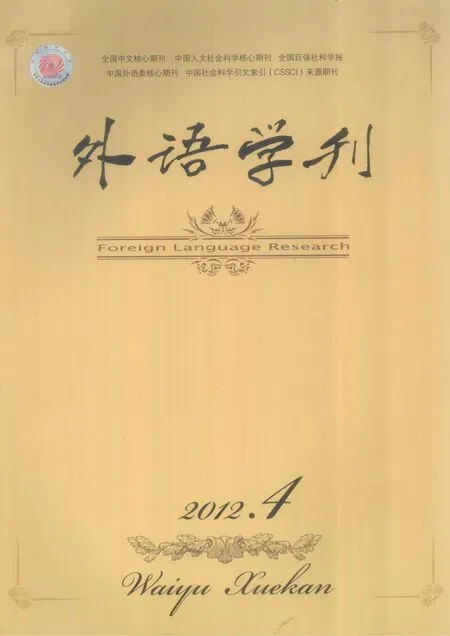乔姆斯基语言模块的理论蕴含及其困难*
——兼议语言模块观念的未来取向
奚家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518055)
乔姆斯基是语言模块、乃至心理模块性假说的最初倡导者。1957年,他的《句法结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新的语言学范式对传统的行为主义、经验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叛离。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乔姆斯基把自己的理论从最初的“普遍语法”概念的提出发展成为一个言说整个心智活动特征的认知心理学体系——心理模块性理论,并进一步向神经生理学领域进发,力图在物质的层面上寻找语言模块以及心理模块的构成方式。来自神经病理学的临床观察也显示某些脑区损伤和某种语言能力的缺失有明确的关系,关于一些具有超常语言学习能力但是一般智力却极为低下的“白痴天才”的研究似乎也在支持语言模块理论。由于不断有实证的和理论的证据出现,乔姆斯基的语言模块或模块化语言机制的基本假设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已经成为当今语言认知研究的主流思想。
但是,当我们深入考察乔姆斯基式语言模块的时候,一些不可回避而又无法克服的困难出现了。例如,语言模块是人所独有的还是在多种动物中普遍存在的?人的语言模块是如何形成的?虽然已经发现某些脑区和特定语言能力有关,但是如何将语言模块和特定的神经结构对应起来?这些问题正是不同意见者提出质疑的焦点。本文将指出,乔姆斯基模块的困难源自其用以界定模块的理论预设:(1)在结构心智观视野下,将模块看作是一种结构性存在;(2)在离身心智观视野下,将模块看作是一种“离身”的心理机制。我们认为,语言模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超越乔姆斯基模块的理论预设。
1 乔姆斯基模块思想的源流和理论预设
“乔姆斯基模块”(Chomskian modules)是根据乔姆斯基的模块观而命名的一种模块。乔姆斯基以语言机制的模块性为起点,进而对整个心智提出模块性的规划,指出人的心理(或认知)实质上是许多结构上独立的单元(即模块)相互作用的产物,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最初的“普遍语法”概念为核心展开的。
1957年,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提出了“普遍语法”的概念。这是一套儿童与生俱来的、可以适应于任何一种人类现实语言的语言反应规则。普遍语法本身不包含语言的经验内容,但它可以受语言经验激活而成为儿童学习母语的认知基础。乔姆斯基对普遍语法的定义方式沿袭了康德“先天范畴”的思想。即,为了使经验认识成为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完全脱离经验并先于经验而存在的认识框架。因此,乔姆斯基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了“官能”(Faculty)这个概念。(熊哲宏2005:742)
乔姆斯基还受到洪堡特的普通语言学思想的影响。洪堡特(W.Humboldt)提出,既然全人类都具有统一的思想本性和一致的精神趋向,那么他们表现出来的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后面一定有某种统一不变的支撑。也就是说,他希望寻求隐藏在文化差异背后的语言的普遍性。因此,他认为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在心理动作底层的、恒常不变的系统,这种心理动作把有结构的组织连接好的信号提升为一种对思想的表达”;语言是“一个递归的生成系统,其中的生成法则是固定不变的”(洪堡特2002:55-78)。
在普遍语法理论的基础上,从《句法理论诸方面》,经过《对语言的思考》、《规则与表征》、《管约理论》,到《关于心理研究的模块方法》和《语言知识:其性质、来源与使用》,再到《语言与知识问题》等著作的发表,乔姆斯基的模块理论已形成系统。(奚家文2009)。他确认,人类的语言能力实际上就是一组普遍语法,它是我们的自然语言的内部表征,并由语言官能内部的模块性结构来实现。通过对语言模块的讨论,乔姆斯基进一步指出,心理是由“具有其自己特性的分离的系统(如语言官能、视觉系统、面孔识别模块等)组成”(Chomsky 1988:161)。乔姆斯基在普遍语法假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宏大的关于语言模块、乃至所有心理机制的模块性理论。
通过简要回顾乔姆斯基模块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进一步解读他的语言模块思想的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结构心智观和“离身”心智观。结构心智观是乔姆斯基模块的第一个理论预设。乔姆斯基认为,和语言一样,所有的心理机制都由一些先天的、相互独立的“信息体”(body of information)来执行。比如,语言模块是一套先天的内部表征体系,即所谓的“普遍语法”,它规定儿童习得语言的可能性,它受语言的刺激而被激活,并迅速发展成为儿童母语的语法规则;除了语言模块之外,还可能有:数学模块、面孔识别模块等等。简而言之,乔姆斯基模块实际上是一种领域特殊的知识或信息实体,它是一种表征系统。(熊哲宏2002,2005)以“普遍语法”为例,乔姆斯基指出,这是一套先天的语言反应规则,如前所述,它实际上是一个康德式的“先天范畴”。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先天范畴具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第一,康德用范畴表界定了每一种范畴的执行领域,先天范畴因此具有空间性特征。第二,先天范畴是先于经验的逻辑存在,这是一个时间性特征。尽管康德竭力解释这里的先后应该是一种逻辑顺序,但是当先天范畴的概念被运用于解读认识过程时,这种逻辑顺序便自然地迁移到认识过程的发生次序中。例如,皮亚杰以康德的理论建构起来的“发生认识论”充分显示出这种微妙的次序关系的意义:正是认知图式和认识经验的次序关系的交替变化,才产生“平衡化-去平衡化”的认知发展动力。(熊哲宏2000)因此,康德的先天范畴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乔姆斯基显然继承了康德的这种概念建构方式,把“普遍语法”和其它种类的心理模块也表述为结构性概念。这更体现在他对心理模块的隐喻性描述中,“我们可以有效地将语言官能、数字官能等等视为‘心理器官’,类似于心脏、视觉系统或运动协调系统。身体器官、知觉和运动系统以及认知官能之间在目前讨论的范围内不存在区别”(Chomsky 1980:217-254)。
乔姆斯基甚至还进一步精确描绘出语言模块的3个层次性结构:第一个层次包括内化语言(I-Language)和外化语言(E-Language)两个部分,它们分别对应于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第二个层次为内化语言所包括的一个运算程序(Computational procedure)和一个词库(Lexicon),其中,运算程序从词库中选择词项构成更复杂的特征序列,即表达式。第三个层次可指由运算程序中的“合并”(merge)机制所结合成的层阶性树形结构,而“合并”机制是乔姆斯基强调的最为重要的句法操作。
“离身”心智观是乔姆斯基模块的第二个理论预设。离身的心智观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理论预设。(李其维2008)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心智观基于计算机隐喻把心智当作是对符号(环境输入)进行计算的程序,这套程序可以在人身上实现,也可以在其它的任何结构(如电脑)上实现,因而心智“与硬件无关”。这就是离身的心智观。
洪堡特是乔姆斯基模块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依据。洪堡特提出“在人类各种自然语言现象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思想表达系统”(姚小平1992)。这个表意系统是独立于各种自然语言之外,它和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具体表达内容无关,它是一个递归生成法则。乔姆斯基几乎完全地接受洪堡特的这个观念,并用它来建构自己的“普遍语法”学说。既然“普遍语法”作为一种语言规则可以生成任意的语言经验,那么它实际上就可以和具体的语言经验相分离。就像形式逻辑作为一套纯粹的思维规则可以将思维与经验分离一样。既然“普遍语法”可以和语言经验分离,这也就意味着它也可以和语言的经验者分离,因为语言经验和经验者是浑然一体的。
此外,从模块的结构性特征出发也必然推出模块的“离身”性结果。因为结构就是一种时空关系。一个结构性存在一方面表述它内部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特定时空关联,同时还需要表达它自身的存在与周围环境的时空关系。只有当它能够表现出和周围环境稳定的时空属性的区分和联系时,它自身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也意味着独立或可分离。把“普遍语法”或语言模块当作一种结构就意味着它可以和它的载体分离。即语言模块作为一种结构,在逻辑上可以和语言经验的主体分离。乔姆斯基关于“普遍语法”的界定必然导致“离身”心智观的选择。
2 乔姆斯基模块的理论困难
乔姆斯基从“普遍语法”到语言模块乃至心理模块的理论建构可谓洋洋大观,但是他的实际研究却止步于对词语和句子结构的形式化分析。正如Pinker的评论,乔姆斯基模块只是一个“深奥而空洞的形式主义”(Pinker 2005)。我们认为,正是乔姆斯基模块的两个理论预设阻碍其理论的现实化进程。
首先,语言模块的结构性存在使乔姆斯基在“语言模块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上陷入两难。
对于持有神论的哲学家而言,结构的起源不是问题。但是乔姆斯基希望在科学的语境中言说语言模块的起源,这就为他的理论建构造成巨大的困难。因为在当今的科学中,自然选择学说应是解释起源问题的有效的理论支撑。但是要注意,自然选择的对象是“功能”而不是“结构”。如果某种功能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能够提高生存和繁殖效率,这种功能就可能在自然选择中获得优势而传播后世。虽然可观察的自然选择结果体现为结构,如形态、器官等,但是这些结构的形成是依据它们能够执行某种功能。结构只是功能进化过程中的附属产品。进化心理学称之为“拱肩”,即罗马建筑中两个拱门之间的三角形区域,因为它往往具有很强的装饰性而更引人注意。但实际上拱肩只是拱门建设的附属产物。相对于功能而言结构犹如拱肩。因为结构本身不是自然选择的对象,所以它就不能得到进化论的理论惠顾。于是,乔姆斯基只能为他的结构性模块选择“突变论”的起源说。(代天善2007)虽然自然选择学说也认可进化过程中的突变,但是脱离自然选择这个进化动力的突变论依然是当代科学难以接受的。因而乔姆斯基的突变论实际上是说,在人类早期生存的某个时期,语言模块的结构突然形成,这个结构正好能够完美地实现人类语言交流的功能。在没有自然选择法则指导的情况下,一个结构的变异刚好匹配某种功能的需求,这是一个极度的小概率事件。就好比“将一只猴子放在打字机上乱蹦,而它打印出了《莎士比亚全集》”一样,让小概率事件成为现实往往需要意志的干预。如此看来,乔姆斯基模块似乎并没有彻底脱离有神论的藩篱,所以它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底气不足。
乔姆斯基模块的结构性特征带来的第二个理论障碍是“身心问题”的困扰。
乔姆斯基不希望像笛卡尔那样陷入二元论的争端。他说道,“人们为了解释行为现象或知识习得,假设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心理机制,但这种抽象机制所对应的物质结构是什么?——我完全没有定见。但我们并不像笛卡儿那样,在处理那些不能用他所说的物质运动的概念来表达的现象时,不得不假定一种第二类实体”(乔姆斯基1988:106,112-113)。为了避免身心二元对立,乔姆斯基走向还原论,他坚信语言模块是一个生理结构。如果语言模块真是一种生理结构,就像身体中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一样,那么语言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关于语言的研究任务就变成在身体中找到实现语言功能的器官。而这种工作应该主要由生理学家或解剖学家来完成。但是,我们再回顾乔姆斯基关于语言模块结构的描述就会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乔姆斯基描述的语言模块其实“是一个表征系统,是一个‘信息体’”。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存在。为了避免陷入二元论,乔姆斯基必须要把作为心理学存在的语言模块映射到生理结构中。这使得他再次回到“身心问题”的困扰之中。
乔姆斯基模块的结构性特征使得“身心问题”的困扰愈加严重。因为乔姆斯基把语言模块看作是一种结构,所以语言模块和生理结构的关系就成为了两个结构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就不能说是生理结构实现了语言模块,因为一个结构只可能实现某些功能而不能实现另一个结构。比如消化系统作为一个生理结构,它能够实现消化食物、整合营养的功能,但我们很难想象消化系统实现了另一个“消化”的结构。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生理结构和语言模块之间寻求因果解释呢?当我们要用一个结构去解释另一个结构的活动时,必须把这两个结构都放在一个统摄两者的更高级的结构中。例如,每当我操作开关就发现灯亮了。即使这两个动作无一例外地相伴随发生,我也不能对两者做出因果性解释。只有在开关、灯、电源、线路等要素组成的结构中,我们才能了解灯和开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样,我们发现大脑某个区域受损伤的病人会失去某种特殊的言语能力,这样的发现并不足以在逻辑上构成该脑区是形成这种言语能力的原因。要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统摄两者的更高级的结构。这个能够统摄生理存在和心理存在的更高级的结构应该是什么呢?显然,在自然科学的语境中没有描述这种存在的语汇。
由此可以看出,乔姆斯基模块的结构性预设使得乔姆斯基的理论不时地游走于自然科学的疆域的边沿,这是促使他的理论难以在生理学的实证研究中获得支持的一个原因。此外,乔姆斯基模块的“离身”性预设与“心理模块的构成标准”之间也存在理论上的矛盾。
由于乔姆斯基把心理模块界定为一种离身存在,即心理模块可以和具体的经验分离,这也意味着可以和经验主体分离。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既然每个模块对应一种任务,人拥有多种不同的模块,而模块和人自身以及人的经验是分离的,那么,当人面临一个特定问题的时候,他必然要面临应该用哪个模块来应付当前问题的选择。因为有这个选择,于是又必须派生出另外一个帮助人进行这种选择的机制。这个机制把人的反应和各种模块连接起来,它只能是领域一般的。在领域特殊的心理模块和人的反应之间又插入一个领域一般的机制,那么领域特殊的心理模块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心理模块最核心的构成标准是领域特殊性。领域特殊性是指心理模块只对特定领域的刺激做出反应,而非领域内的刺激则不会激活该模块。需要指出的是,刺激的领域属性是通过经验主体来建构的,是经验主体对刺激相对于自身的需求而做出的评价。关于推理问题的领域特殊性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推理内容对于主体而言具有自身卷入性时,某种特定的推理机制就会被激活而将推理结果引向某个固定的方向;相反,没有主体的自身卷入时,针对同样的推理内容,人的推理就会表现出另外的特征。(Cosmides 1989:187-276)这些证据说明,主体自身卷入与否是领域特殊性的反应机制是否被激活的前提,因此,领域特殊性的机制不可能“离身”存在。
乔姆斯基把他的语言模块界定为一个与经验以及经验主体分离的存在,是一种离身的机制,因此,乔姆斯基模块不可能具备“领域特殊性”的特征,而当语言模块的最核心构成意义被抽离之后,乔姆斯基模块还能成立吗?乔姆斯基模块面临的一些貌似阶段性问题或技术性问题的困难,实际上都源于乔姆斯基模块的结构性与离身性两个理论预设和心理模块的核心内容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这些冲突将极有可能给乔姆斯基模块理论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3 语言模块的理论趋势
通过分析乔姆斯基模块的理论困难,我们发现,乔姆斯基模块的结构性和离身性心智观最终导致模块理论的根本矛盾,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的语言模块(以及其它心理模块)的理论建构应超越乔姆斯基模块的理论预设,在功能性模块和具身性模块的方向上展开。
功能性模块是进化心理学倡导的一种模块观,其观念直接源于达尔文的“本能”概念。达尔文将本能定义为:由自然选择塑造的、有机体的固定反应模式。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本能是一种反应模式,而不等于行为本身,即在遭遇特定刺激时,它规定了有机体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第二,本能是通过生理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本能可以遗传。(达尔文2005)
达尔文定义的本能其实是可遗传的生理结构表现出来的功能。当代进化心理学家继承达尔文的观念来建构功能性模块。(巴斯 2007,张雷2007,Cosmides&Tooby 1994)功能性模块的界定不依赖任何物质化存在,也无所谓结构,而是依据它所能执行的功能。例如,Cosmides考察发现,人可能拥有一个用于指导社会交换行为的“骗子侦查”模块。(Cosmides 1989)她的理由是,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要善于和他人合作和进行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人会采取欺骗行为,即收取利益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有效地判断那些欺骗行为是具有适应性意义的,于是,经过世代的自然选择促使人获得一种专门用以侦查骗子的反应模式。每当遭遇社会交换情景的时候,这套反应模式就会自动激活引导人快速识别他人是否有欺骗行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进化心理学家考察的是:人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生存问题?人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应对这些问题?以及这个机制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机制的功能,并不强调它的结构。这就是进化心理学的功能性模块观。围绕这种模块观,进化心理学采取的是“功能分析”的研究方法(熊哲宏2005a),即分析为了应对生存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功能;以及为了实现这些功能需要什么样的机制。(蒋柯2010)
由于其本身是一种功能而非另一个独立的结构,功能性模块和生理结构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如前所述,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对接需要依赖于一个更高级的统摄性的结构,而结构却能够直接实现某种功能。所以,功能性模块不会遭遇乔姆斯基模块那样的尴尬:在技术上既希望能够和生理结构建立对应关系,在逻辑上又不能和目的论或决定论划清界限。功能和生理结构的兼容并不等于将功能还原到结构中并一一对应。也就是说,我们将功能定义为相互独立的模块,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功能的生理结构也必须相互独立。生理学的例子更能够直观地表达这层含义。比如,消化功能可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模块,由从嘴到肛门的若干生理器官来实现,它们一同构成所谓的“消化系统”,这些生理结构在执行消化功能时,各自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差距,但是都能够统摄到消化这个功能中。同时,这些器官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必须和消化系统之外的其它器官产生联系。它们可能还参与其它功能的实现。因此,当我们希望在神经层面上寻求语言模块的生理支持的时候,就不能采用割离大脑的方式,即将语言功能对应于某一个脑区,而是考虑某一组神经结构的活动按照特定时空序列的组合实现了某种语言功能,而这些神经结构的其它组合方式则可能实现他种功能。
心智的具身性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特征。心智的具身性是指:心智有赖于身体的生理的、神经的结构和活动方式。如果说“活动”实际上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也可以把心智理解为深植于人的身体结构及身体与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李其维2008)。因此,具身性模块就是在脑、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反应模式。这种反应模式不能和人以及人对环境的经验相分离。只有具身性模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模块。功能性模块观也必然导致对模块的具身性界定,因为功能须要通过身心结构来实现,不可能有脱离身心结构的功能。消化功能必须在咀嚼、胃肠的蠕动等器官活动中体现,语言功能也必须在神经活动、肺、咽、唇、舌等肌肉活动中体现出来。总之,“语言模块是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万晋红2009)。因此,关于语言模块的研究就是要把研究对象置于现实的经验中,而乔姆斯基式的形式化研究策略不能揭示语言模块的特征,因为形式化运算被悬置于身心与经验之外,未曾通达语言模块的活动。只有当我们回归身体,内观方可实现语言认知中“内在的主客统一”和“脑-身体”的统一,外观则可把握语言认知中“脑-身体”与环境的“耦合”关系,内外结合,从而实现“脑-身体-环境的统一”,这也是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观”的核心所在。(奚家文2009:70)
巴斯.D.M.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达尔文.物种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代天善.普遍语法与语言范式——从哲学、心理学到生物学的历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
李其维.“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心理学报,2008(12).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蒋 柯.从《语言本能》到进化心理学的华丽转身——平克的语言模块思想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
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万晋红.语言与身体[J].外语学刊,2009(6).
奚家文.从乔姆斯基到平克——语言心理研究的模块化之路[J].心理科学,2009(1).
奚家文.语言模块的具身性考察——“第二代认知科学”视野下语言心理研究的新进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2).
熊哲宏.“Mentalese”是否存在?——福多“心理语言”理论的几个难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熊哲宏.论“心理模块性”研究的理论心理学意义[J].心理学探新,2002(1).
熊哲宏.“模块心理学”的理论建构论纲[J].心理科学,2005(3).
熊哲宏.“模块心理学”的挑战:反“文化心理观”[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姚小平.洪堡特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J].外语学刊,1992(5).
张 雷.进化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Chomsky,N.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Chomsky,N.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8.
Cosmides,L.The Logic of Social Exchange[J].Cognition,1989(31).
Cosmides,L.& J.Tooby.Origins of Domain Specificity: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Organization[A].In Hirechfield & Gelman(eds.).Mapping the Mind[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inker,S.& R.Jackendoff.The Faculty of Language:What’s Special About it[J].Cognition,200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