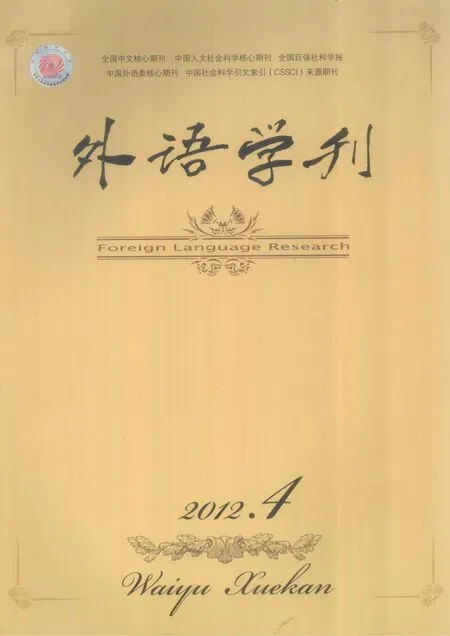人类语言学的研究视域分析*
王 旸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150001)
1 引言
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也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自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宏观语言学理论体系,其研究进展和成就是人类学其他分支领域有效工作的先决条件。探索人类语言的人类学家早期的拓展性工作,为其研究人类文明的行为方式及其潜在的内部模式奠定了基础,因为这两者构成人类文明,并在其语言中以种种方式明显地体现出来。人类学家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同时也为研讨人际关系的学者们提供重要线索和有效工具。此外,人类的行为方式及相互关系常由语言进行调节,并以其赖以运作的语言内部属性为特征,从而进一步按类型加以分类。
2 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及途径
人类学(anthropology)与语言学(linguistics)不论从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是从研究途径和方法上,都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二者既重叠、交错,又相互影响。语言学的研究素材是人类主要的交际工具——语言。语言是人类思维和自我表达的主要手段。然而,不论思维或表达,人类都不仅是作为具有行为的个人,也是作为一名社会成员及群体的积极参与者。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或载体,社会个体成员本能地促使其他成员分享其思想、感受、经历、情感乃至其所属文化,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较大区域跨度的同一群体,一个具有同质文化的独特交际集团。不仅如此,上述一切还会被自发地传给后代,从而促成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因此,可以说,语言通过其纵向和横向的交际,已成为人体基因之外的人类另一重要的遗传根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细而言之,即人的身体和身体行为,并透过其行为的各种具体外部表现去探索它们对他人及其所在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人行为的外部表现包括人的表情、姿态、动作及其对他人行为的反应和对他人周围物质和现象造成的影响。人类作为最高级智能动物,其外部行为的最特殊层面是极其复杂多变的发声活动。这种由大脑引发的活动涉及肺、声带、鼻、嘴等部位,其中嘴的最活跃部分是舌,因此,整个发声活动称之为Lingua,即英文tongue,其全部过程均属语言学的研究素材。
对人类语言学家来说,分析复杂多样的语言并非易事。惯常的做法是,把语言流(linguistic stream)初步切割成若干零散的单位,剖析隐藏于语言流内部或背后的诸成分的结构和模式,并在大的结构框架内将上述成分定位,进而探寻某一语言支流(sub-stream)或分系统(subsystem)的结构与另一支流或分系统的结构联系,并归纳出其间的模式和规律。多年来,为上述目的,语言分析家们设计和使用了多种技巧,其中行之有效者已成为其他人类学家分析人类文化和社会关系其它层面的模式。这些技巧在语言分析中的成功使用,给人们增强了希望与信心,即可借助语言类比法(analogy)帮助人类学家分析所面临的其他问题。
3 人类语言学研究视域的发展
由于在研究体制上深刻的内在联系,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方。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萨丕尔(Edward Sapir)、克罗伯尔(Alfred Kroeber)以及克拉克霍恩(Clyde Kluckhohn)等在这方面做出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并通过他们的研究与教学,发展和开辟了这一范围更广、内容更独特的研究领域 ——人类语言学。就语言的种族渊源(ethnic origin)和方言的研究而言,该学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当时古希腊历史学家赫罗多斯(Herodotus)曾对小亚细亚西南部卡亚人(Carians)和考努斯人(Caunians)的种族起源及其方言简略地进行过论述。他的研究恐怕是人类语言学方面最早的尝试。在美洲大陆的开拓时期,欧洲移民中的一些学者,其中包括医生、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律师、牧师等,对土著印第安部落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到19世纪,一些学者开始收集和发表关于印第安语言和文化的资料。1911年,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美洲印第安语手册》(第1卷),这部著作已成为现代人类语言学(Moder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的里程碑。按哈姆斯(Hymes 1964:12)的说法,它“近乎于一部现代美国语言人类学的奠基作品”。二战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被公认为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之一。与主流语言学不同,人类语言学的宗旨是“研究人类学范畴内的语言”,其基本前提是“语言主要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应以此给予理解”。“人类(语言)学家与语言学家不同,他们从来不认为语言隔离于社会生活,而是坚信其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依赖性。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技术性语言分析只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是能够从中就更重大人类学问题做出推测的数据。为此,人类学家在‘语言与文化’这样的题目下研究了诸如世界观之间的关系、语法类型与语义场、话语对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社区的互动……”(Giglioli 1972:9-10)人类语言学也如人类学其他领域一样,受到人种语义学(ethno-semantics)和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影响,重视以特定文化内具体社会事件大量记述为基础的形式化人种学描述。因此,最初人们是以人种学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对语言进行研究,即调查单一文化或社会特定环境中的语言,并通过直接观察和亲身经历收集资料。调研者们重视土著人究竟如何说和做,然后将其直观资料作为研究素材,进而对一种土著语加以解释。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从不同文化中收集语料,以增强研究课题的可比性。
3.1 关注语言的社会变体
人类语言学家从研究土著语言到探讨欧洲、南亚、东亚文明国家语言的社会变体(social variety),是令人瞩目的重心转移。它有助于了解一些语言,如英语、法语等移植到新的社会环境(多为原殖民地)过程中的演变和促进演变的种种文化因素。60年代人们开始重视具有社会意义的语言变体,一些人类语言学家把调研中心从印度和北非的社会方言转向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大都市中心的社会方言或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的社会方言。
人类语言的庞大结构变体和社会方言变体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这些繁复的差异迫使人们要对语言分析采用更复杂精密的方法,为语言材料的大规模处理开发更快捷有效的手段。在此方面,其他学科对语言研究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自50年代起,计算机的运用使信息的快速处理成为现实,计算机专家们还为语篇分析及据此分析编纂词典设计了机械电子程序,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们帮助探索出语言结构的更理想模式,机器翻译也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在设计语言分析和大量语言素材处理的方式上取得的这些丰硕成果,不仅对人类语言学的深入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推动了人类语言学家从语言素材中有效地提炼文化内涵和从社会文化行为中摸索出其他合理的模式。人们曾运用语言分析法和以语言为基础的计算机程序对菲律宾苏巴农人(Subanun)的疾病类型、玛雅策尔塔尔(Maya-Tzeltal)的柴火选择方法、日本和朝鲜人的动词选择形式等作过具有文化含义的分类。
3.2 对话语模式和副语言的微观分析
研究人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关系,虽有多种途径,但最离不开的是对言语交际的观察。因为通过这种观察,人类语言学家不仅能了解交际双方在说什么、为何说以及为何那样说,而且也能透过某些表面或潜在的话语模式(mode of discourse)察觉到讲话者乃至其民族的一种无形、特有的传统文明,发现支配他们文化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些相对固定的模式。人类语言学家还注意到,话语表达往往有身体各部位的活动相伴随。而这些所谓的体态语(body language),如眼神、手势、距离等,在交际中虽不能喧宾夺主地取代话语,却可表意、传情,对话语起到衬托和强化的作用。不仅如此,体态同话语一样受制于固有文化和传统社会关系,也有某些模式可循。为获取证据,近年来人类语言学家做了大量试验,如把一些典型会见:病患与医生、求职者与雇主、人类学实习生与信息提供者等,拍成电影或摄入录像,然后对其一一进行微观分析(microanalysis)。分析结果为人们提供了话语和体态方面的重要线索,如病人病情的发展及其疗程,求职者的个性和文化特征以及未来雇主可能提供的职务、实习者规划的分析框架和信息提供者回答中透露出的具体文化含义等。总之,这些线索对研究文化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进行微型分析中,还出现了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behaviour)这一新领域,它为话语分析乃至语言分析增加了新课题。所谓交际行为,是指语言之外的一种交际手段,它同体态一样对表情达意也起着辅助作用。在交际中,每位说话者在使用语言(元音与辅音、词与词组、句子与段落等)的同时,还利用着另一套符号系统,即副语言(para-language)。
副语言也称为辅助语言,它包括发声系统的各个要素:音质、音幅、音调、音色等。语言有真有假,副语言如语调、面容等作为思想感情的表现却较为真实,因为它往往是不自觉的。副语言沟通是通过非语词的声音,如重音、声调的变化,以及哭、笑、停顿来实现。心理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副语言在沟通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句话的含义不仅取决于其字面意思,还取决于它的弦外之音。语音表达方式的变化,尤其是语调的变化,可以使字面相同的一句话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例如,低音频与抑郁、烦恼、悲伤的情绪相联系,而高音频则表示恐惧、惊奇或气愤。因此,副语言是人类语言传输信息和交流感情不可或缺的表意手段,具有表明态度、抒发感情的语用功能。
然而,对典型化和固定化的交流行为进行分析是相当困难的,要有针对语言、副语言和体态剖析的一整套机械和电子辅助手段,如录音机、摄像机。这些设施具有控制速度、固定单放和前后倒放的功能,还能多画面地把稍纵即逝的多类素材展现出来,然后分段地对话语和体态进行微观分析。这种复杂的综合操纵过程往往因技术问题和缺乏对个人或群体文化背景的了解而受到阻碍,而且还有许多相关的理论问题尚未得以解决,如描写语言学家(descriptivists)还未透彻考证过英语或其他语言的各种小变体(subvariety),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最新调查成果也尚未将某些群体定性等。再者,交流行为零星或整块信息的内涵(import)——心理的、宗教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公共关系的,即使被分割开,也还是难以摸透,要等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到那时,通过对这类行为的小型样板的研究,人们才能较精确地揭示个人或群体的心理、社会心态、文化趋向,才能准确地刻画其内心世界并有效地进行监测。
3.3 语言间的异同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人类语言学涉猎虽广,但世界各种语言间的通性和差异却是难以或缺的研究课题,因为它们不仅反映语言本身的状况,而且也透视着其背后的人类社会与文化根基。在这种意义上,人类语言学家需透过语言的多层面来探索人类文明。例如,在发音方面,所有人类语言都是通过声波(sound waves)体现于外部环境中,这种声波产生于活动的发声器官对空气的作用。发声和传声的内在组织往往都具有数量有限的特征,如压缩(compact)、扩散(diffuse)、平和(flat)、尖高(sharp)、松弛(lax)、紧张(tense)等。各种语言都以元音或辅音组成的音链(sound string)形式出现,其数量均有限定,它们可以切分出低层声音单位,如音节(syllable)、词(word)、短语(phrase)和句子(sentence),也可串联成高层声音结构,如段落(paragraph)和语篇(text)。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声音的可能数目和音链结构,在所有语言中虽大致相同,而声音和音链高低层结构的具体选择及其内在结构却不一而足。在音素的数目上,差距就更加悬殊,有些语言只有15个左右,如夏威夷波利尼西亚语(日语也只有20多个);有的语言多达50个,如印第安纳瓦霍语,苏格兰盖尔语;有的语言甚至有75个,如哥萨克阿布哈兹语。
在结构上,各种语言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而这些差异则构成了民族间交际的障碍。就句法规则而言,几乎所有语言都有主语、谓语和宾语,但这些成分的语序却相去甚远,有些语言采用SVO,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有些语言遵守SOV,如日语、朝鲜语、德语;有些语言依照VSO,如希伯来语和威尔士语;个别语言,如马达加斯加的马拉加西语,还有以VOS为基本结构的。在语态方面,许多语言都具有主动(active)结构,但也同时存在被动(passive)结构。在这些语言中,The girl broke the cup与The cup was broken by the girl有着相同的意思,它们只是一种结构的转换(conversion)。但并非所有语言都具有主谓的这种主动与被动的相关结构,有的语言难以用A was broken by B与B broke A相搭配,而只能以A was the object of breaking from B来替代。在词性上,虽说多数语言有名词和动词词性,但其内涵却相互有别。在拉丁语中名词和形容词都属于名词性词(substantives),在日语中动作词和质量词都视为动词。
从而人类语言学研究的兴趣领域也十分广泛。在二战之后的10年间,哈姆斯(Hymes)的一项专题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步演绎成学术界的兴趣中心,这就是语言与世界观(world view)的问题。其阐述的核心观点是,人类所运用的语言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其感知(perceive)世界和思考(conceive)世界的方式。围绕着语言运作与思维方式之间关系的广泛研讨,无形中认证了30年代语言学界争论不断的萨丕尔-沃尔夫设想(Sapir-Whorf Hypothesis)。这种设想主要以语言相对论的传统理念为依据,由德国哲学家哈曼(Hamann)和赫尔德(Herder)最先提出。沃尔夫曾于30年代提出,语言结构对世界概念的构想方式有着强烈的影响。比如,一种语言的语法划分和构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模式,必然影响和决定说此语言者谈论时间的方式,即人们的思维决定于其语言结构,不同形式的思维产生于不同结构的语言,所要探讨的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例如,有的民族善于抽象思维,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具有众多的抽象词语和与之相关的结构。
60到70年代间,该学科的研究领域又有所拓展,一些新提法或新观念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2年哈姆斯提出了“话语人种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将其确定为人类语言学的一个独特领域。哈姆斯把言谈或说话(speaking)看作一个“谈话事件”、“传信事件”,对它作了非常细微的分析,区分说话的参与者、说话所用的代码、说话的体裁、语调、渠道等等。种种“说话、传信事件”及其组织因言语集团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话语策略的不同,是言语集团不同的明显标志。1964年哈姆斯又提出了一个至今还被人们反复论证的新观念:话语行为(speech act)。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哈姆斯、甘柏兹(Gumperz)及其合作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力图从人类学角度对社会语言做出新的论述,他们的研究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赞许,并因后者的加盟而得到加强。
4 人类语言学的研究意义
人类语言学不仅涉及到当前的一些重要人文学科,如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学等,而且也将诸如语言的起源与发展、语言习得、语言的比较、语言的描述与分析、方言学等一些语言学中的重大领域集于一身。特别是,它摆脱了纯语言形式研究模式的束缚,把语言置于其赖以生存的人类文化之中加以探析,无疑使语言研究具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及更丰腴的土壤。
加强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各国国情、民俗、价值观、行为模式、思维逻辑等,而且对探讨语言本身的结构和语义,特别是对研究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大有裨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语言学也必然会促使普通语言学向纵深和多样化方向发展,而其拓展也势必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和思潮[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田 华.副语言在话语中的言语特性[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3).
王 扬李永生.英语副语言特征探析[J].山东外语教学,1999(1).
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周流溪.语言起源的一源论读后[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2)
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Alter,S.G.Darwinism & the Linguistic Image:Language,Race&National Th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Asher,R.E.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Oxford:Pergamon Press,1994.
Bright,W.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Coleman,D.Speculative Notes on Human Linguistics[J].OL,2002(1).
Giglioli,Pier Paolo.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C].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1972.
Johnson,J.& Huebner,T.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Papers on Linguistics in Society(1959-1994)[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Von Glaserfeld.Radical Construction:A Way of Knowing and Learning[M].London:The Falmer 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