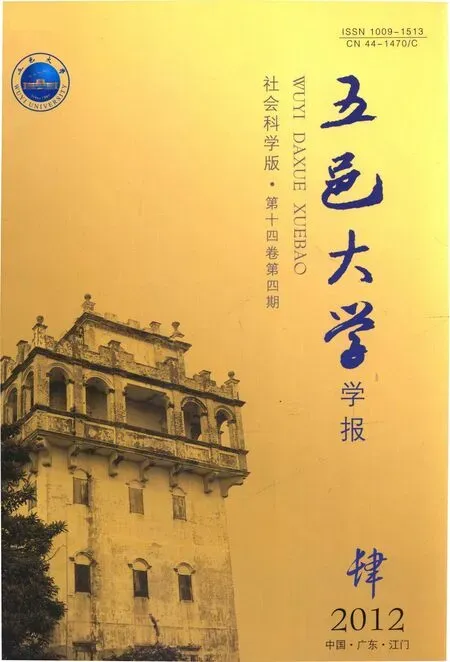庞太太:在故国 “文化孤岛”上老去——雷祖威小说 《爱的痛苦》母亲形象赏析
李夕菲
(五邑大学 学报编辑部,广东 江门 529020)
近30多年来,有关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渐成国际 “显学”,一批成长于美国本土、用英文写作的美国华裔作家如黄玉雪、赵健秀、汤亭亭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国国内学者张子清更将雷祖威①与汤亭亭、赵健秀、徐忠雄、谭恩美、李健孙、任璧莲等作家并称为 “当下华美小说界的七大台柱”[1]。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者吴冰、徐颖果、薛玉凤等对雷祖威作品的评价都相当高。
雷祖威 (David Wong Louie)的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 (Pangs of Love)[2]自1991年出版后,为他赢得了广泛关注与好评。《出版家周刊》指出:“雷祖威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勾勒出亚裔美国人那种疏离感,塑造出一系列在情感上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人物形象。”[3]从文本上看,小说行文简洁优美,文风典雅,多用动词,语带双关,让人读来欲罢不能,读后回味唏嘘。笔者在通读原作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对作品进行赏析。笔者所采用的这篇小说的英文版本,来源于原天津理工大学徐颖果教授编著的 《美国华裔文学选读》[4]第248-276页。以下引文的翻译和分析,均据此版本。
故事以第一人称 “我”——化学芳香剂公司的技师 “阿威”(Ah-Vee-ah)的视角展开。作者通过 “我”和母亲庞太太参与活动的几个生活场合,串联起人物间的身份和关系,细致描述了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两代人在文化和代沟等方面的问题。
75岁的庞太太是典型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家庭妇女形象:她因为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无法真正融入美国世界,无法理解已经美国化了的几个子女的婚恋观和各自面临的现实困境,只能带着舐犊情深的痛苦,固守在中国传统文化孤岛上渐渐老去。有评论家指出: “标题 《爱的痛苦》中的 ‘痛苦’(Pangs)与移民母亲庞太太的姓 ‘庞’ (Pang)相暗合,这一双关语象征了故事里人物的处境以及他们内心的痛苦。”[3]以下即从文化冲突和代沟入手,对庞太太这位母亲形象进行重点分析。
一、语言文化的冲突:母子同处一室却无法交流
“每天晚上,母亲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看上几小时的电视。她爱看露西和卡罗尔·伯内特的节目,然后再换有线电视的中文频道,但总是在看完本地新闻和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后才罢休。她根本听不懂约翰尼在说些什么,但每当电视里的观众发出笑声时,她也跟着笑了,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电线连接着她和电视机似的。
母亲在这个国家里已经生活了四十年了。可是她一定出于某种极大的意志力,居然坚持不学英语。……”[4]248
小说一开始便为读者展示了一位华人移民母亲的形象:活泼开朗,爱看电视,尤其爱看露西和卡罗尔·伯内特主持的搞笑类节目以及约翰尼·卡森主持的 “今夜秀”(Tonight)节目 (后者以轻松幽默的形式访谈名人,是NBA最赚钱的工具之一),但她居然四十几年不学英语,只从主持人的动作、表情中揣测理解电视内容,努力而艰难地适应着美国社会及其文化。
而跟母亲一起住在纽约唐人街的 “我” (阿威),今年35岁,是一家中型化学芳香剂公司的技师。父亲过世后,几位兄弟姊妹便将母亲从长岛送到 “我”的住地,让 “我”担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在守着看电视的母亲、读报纸打发时间的 “我”的眼里,母亲庞太太 “是一个随和、厚道,人们通常很喜欢的女性。她经常操着广东话跟朋友们闲聊,把柜橱和冰箱塞得像一个 ‘迷你型’杂货店——她在为长时间的饥荒或被包围而准备”[4]249。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庞太太是一个典型的广东妇女,并保留着她那一代中国人独有的思维行为方式——经历过中日战争的人,知道战争和饥荒时食物的重要性。
庞太太性格天真可爱,看电视脱口秀高兴时“喉咙里响起报警器似的笑声”[4]250,满口金牙让她的笑容更加灿烂生辉。“什么事让你这么乐?!”感到儿子目光的刺戳时,她会控制住笑声,像学生妹一样用手捂住嘴,眼波流转,透出狡黠的光芒。但庞太太与近在身边的儿子阿威却很难沟通。因为她从不关心政治,而且只能讲中文。阿威关心的是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儿,当他为战争、饥荒、无家可归者增多等现实的不幸而陷入忧虑时,母亲却对着电视上的三人脱口秀笑得肩膀乱颤。儿子想用读报纸标题的形式对母亲解释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却发现 “自打我去了学校,我的中文便自动停止增长了。在跟妈妈交流时我是一个语言矮子。当我说中文时,最多像一个早熟的5岁孩子的水平”[4]251。当阿威指着报纸上在阿富汗战争中战死士兵的图片,想告诉母亲,那不是她认为的 “一只猴子”[4]251而是一具尸体、世界充斥着杀戮时,她却声音颤抖地反驳: “你以为我不懂。你爸爸刚刚去世了……”[4]251“人们在杀戮,而你却只关心你的下一餐”[4]251,儿子责备道,并想跟母亲谈谈自由、谈谈民族自决,却发现 “用自己的中文词汇,那任务相当于不用铁锹去挖一个坑”[4]251,而且母亲根本不懂,也没有兴趣,并且因为联想到丈夫去世的伤心事而激起了对抗情绪。阿威只得用看电视打断这次谈话,并发出被迫的、假装的笑声,以冲淡与母亲发生口角的不快气氛,“母亲却仍然伤心地坐在那儿,控制着自己,像一个青铜佛像。”[4]251
这段场景,揭示了庞太太自从老伴去世后无法与子女真正沟通的心境。她的孩子们是在美国成长或出生的,更习惯于讲英语,在美国社会中学习生存技巧和与人交往之道,已经成了 “黄皮白人”,因此与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是难以交流的。在老伴去世后,庞太太与儿子之间虽然有亲情,却因为语言和代沟隔阂,等于是被困在了一个文化孤岛上,渐渐老去。她只能用对着电视傻笑,来掩盖这种孤独和痛苦。当儿子试图把她拉回到现实世界时,她表现出的是忧伤和抗拒。
二、婚恋观念的冲突:为什么不娶个中国太太?
这位只关心家庭和食物的老妇人,还有一件闹心的事:两个小儿子都没按她的愿望,娶个中国媳妇。庞太太有四个子女,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要三个儿子回香港娶妻,只有长子阿瑞 (Ray)接受了这个建议,阿威 (Ah-Vee-ah)和伯格 (Bagel)都置之不理。
阿威的女友都是白人。前一任女友曼迪(Mandy)由于会说中国话,跟妈妈一起庆祝中国春节,衣着装扮有淑女风范,满足了妈妈的中国幻觉,因此深得老人的欢心。深爱着曼迪的阿威也用尽了办法来弥补与曼迪之间的差异,比如用公司制作的能激发情欲的 “第i9144375941-3e号838型麝香”喷剂来制造温柔浪漫的情调。可是能满足妈妈 “中国式儿媳妇替代品”[4]258愿望的曼迪,最后却爱上了一个日本人,取消了跟阿威的婚约。这成了阿威和母亲共同的伤心往事。
庞太太对阿威的现任女友德博拉 (Deborah)则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除了认为 “她没味道”外,还看不惯年轻人不以结婚为目的同居。德博拉则责怪阿威像是母亲的小男孩,总是听妈妈的话,希望他搬出去住。在一同前往探视小弟弟伯格(Bagel)的路途中,由于语言不通,母子俩的谈话被德博拉误认为是嚼她的舌头,于是气恼地向阿威表达对母子俩的不满:“这太让人讨厌了。我不喜欢你们的秘密,当着我的面说长道短。”[4]259庞太太听不懂德博拉讲什么,但可以感到她的不快,于是不再讲话,把目光投向窗外。注意到了妈妈迷茫目光的阿威感到:来自于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时间的母亲似乎与汽车文化不相称,虽然接近机器,却更适合于生活在穿针走线和放牧着猪、马的农业社会中。“当想到妈妈75岁的身体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向前冲时,我联想到了我国第一位太空旅行者,被捆绑在水星号宇宙舱内的一只猴子,满身都是电线、约束以及电力,尖叫着被射向太空。”[4]259
阿威的这段内心活动,反映了他作为儿子,力图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寻求调和,表达了对母亲饱含同情、却无力帮助她适应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和异域文化的感伤。
更让庞太太难过的是小儿子伯格 (Bagel)。她无法明白伯格和他的同性朋友们,有着体面的职业,住着好房子,经济条件优越,谈着美国好莱坞明星,认同美国主流价值观,却为什么都没有女朋友。当伯格明确拒绝跟女性交往,表示 “我已经跟我的猫结婚了”时,庞太太气昏了:“讲这种混账话,那是一种什么生活,整天抱一只猫?她会给你生仔?”[4]261“你在杀我,”她说, “不久我就要躺在你父亲身边了。你这根昏竹笋②,照我的话做。乘还不太晚,找一个中国女孩结婚。她将会记得我的坟墓,带着食物和纸钱来看我。依靠你,我死了以后就要挨饿。”[4]261
中国人讲究子孙延绵,讲究慎终追远,无论在现世享福还是受苦,都盼望到阴间后有人祭拜追忆。庞太太游说儿子,一是找中国媳妇,二是留下后代,目的还是希望他们能继承中华孝亲敬祖传统,让自己和老伴去世后有人烧香祭祀。可老太太的愿望,在两个至爱的儿子那里都落空了。谁还能为这个家庭延续香火,谁还会为她 “送阴票子”呢?所以在小儿子家的聚会,本以欢乐期待开始,最后却是她无限伤心地说道:“如果没有人听我的,我怎么还能做你们的妈妈呢?”[4]271
华裔老人的这种愿望,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共性,而且这种共性更被华人妇女继承和弘扬。不仅雷祖威笔下的庞太太有,另一位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笔下 《无名女人》中的 “姑姑”也有,她在生下 “野种”并决定投井自尽将孩子带走时,也非常担心死后成为被家族遗忘、没有人给她上香敬供,从而成为总是挨饿、总是要从其它鬼那里乞讨、抢掠和盗取供品的野鬼。[5]
作为哥哥的 “我”,自然明白弟弟是个同性恋者,可 “我”不能跟母亲说透。“我”自己的婚恋也是不称母亲心的,“我”也无法向母亲解释自己和弟弟在表面成功的背后,仍然要面对肤色歧视等种种 “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指隐秘的、无形的偏见)[6]。明知母亲在美国的最后一点幻想都破灭了,却无法安慰她,只能任她陷入沮丧和痛苦之中。
三、边缘创作与文化焦虑
很显然,小说中的 “我”有雷祖威自己的影子。“我”的感伤,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华裔作家雷祖威对华裔父辈、对自己的顾影自伤。这一点,无论是研究雷祖威作品的学者还是雷祖威自己,都有指出。
出生在纽约长岛一个华人洗衣工家庭的雷祖威,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走红于美国文坛,被中国国内学者张子清称为 “当下华美小说界的七大台柱”之一,却仍然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美国主流文化的疏离感。他在解释创作宗旨时说:“亚裔美国人依然处于边缘。我深感我得从那些边缘的角度创作,传达边缘人物的经历。”[7]而雷祖威在接受张子清访谈时,也提到:“我写这些短篇小说时,我想像自己是第一人称的亚裔美国人。”[8]另一位学者薛玉凤指出:“雷祖威之所以如此关注婚恋问题并且如此悲观,与他自己的遭遇不无关系。……在写作短篇 《爱的痛苦》的过程中,雷祖威自己正面临着婚姻危机,苦于不知如何向母亲报告这件事,这种焦虑情绪直接影响了创作的主题。”[9]
据此,笔者认为,小说中的 “阿威”可以视同作者的情感替身 (作者中文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叫“威”,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匠心的安排)。作者感同身受地写出了阿威所经历的失恋挫折和华裔身份挫折,清醒地看到了这种中美文化冲突和老少代沟给亲情、爱情造成的伤害,却无力去填平沟壑,只能寄希望于用人生幽默和化学制剂来化解这人世间的种种痛苦。小说中的 “我” (阿威)和弟弟伯格,虽然已经是 “美国人”,却仍然会在事实上遭受到种族肤色歧视,进而影响到工作、婚恋等问题,无法真正快乐起来。例如,“我”的老板Kyot,“每次我们见面,他总会上下打量我,眼光爬过我的身体,大多数时候是斜着眼。”[4]252而伯格则羞于让他的白人朋友们知道,他的母亲的爱好只是摔跤这类低档游戏。
雷祖威特别用 “我”陪母亲在伯格家看电视摔跤比赛这个生活片断,来说明 “美国梦”是上演在眼前的真实谎言:母亲无法明白规则是美国人事先制定好了的,胜负早已决定,不以她的愿望为转移。而 “我”,却因为借此场合向母亲说明了前女友不再爱自己、不会再回来的真相而觉得无限负疚——因为母亲一下子变得 “不再有问题,不再有鼓舞,不再有愤怒,不再有希望”[4]270。“我剥夺了母亲的快乐,剥夺了她对美国人、对美国、对于我的那脆弱的信仰。并且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歉意,或者用好的句子让她恢复信心,让事情回到原有状态。我成了母亲鞋里的砂子、肾脏上的石头……”[4]270“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知道,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就很容易并经常哭泣。我听到过深夜里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4]270这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只是 “把手放在她的背上,像一只温热多肉的圆海龟”[4]271。
这段平实而带有控制的白描写法,让人内心升起对母亲无限怜悯却无可奈何的情愫。这种精神痛苦,如果作者本人没有经历过,是很难写得这么痛彻心扉的。
故事最后,是 “我”息事宁人地从口袋里拿出几块能化苦为甜的安慰剂似的东西,分发给参加聚会的人,寄望于它能消弥大家特别是母亲心中的隐痛。这也正是雷祖威的幽默所在:他把化解生活矛盾和人生痛苦的手段简化为了各种化学香味剂,并在小说中几处出现。而事实上,这些稀奇古怪的香味制剂,只是逃避生活矛盾的 “烟幕弹”而已。
杰夫·特威切尔-沃斯在为 《爱的痛苦》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评论道:“雷祖威的小说总是带有神经质的幽默。……这种自我意识的小说风格是过去几十年美国许多重要的优秀作家的典型风格,有效地表现了当代美国生活表面成功之下后现代的焦虑。”[3]或许,这正是作品更深一层的主题。
注释:
①雷祖威 (David Wong Louie,1955—),出生在纽约,1977年毕业于瓦萨学院,1981年获爱荷华大学美术硕士,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英文和亚美文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畅销短篇小说集 《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1991)被 《纽约时报》列为 “1991年名著”,被《声音文学副刊》列为 “1991年受读者欢迎的小说”,获《洛杉矶时报》“小说一等奖”、《犁铧》“小说图书一等奖”。该短篇小说集中的 《情感错位》曾被选入 《1989年最佳短篇小说选》。2000年发表长篇小说 《野蛮人来啦》(The Barbarians Are Coming),畅销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获2002年兰南基金创作奖。雷祖威、任璧莲和李健孙是20世纪90年代初走红美国文坛的华裔美国小说家,美国 《时代》周刊 (1991年6月3日)撰文,称他们是 “越过喧闹的新声”。
②据徐颖果女士的后文注释,美国华人把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叫竹笋,指像空心竹子一样没用。
[1]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2000 (1):93-103.
[2]WONG L D.Pangs of Love[M].New York:Plume,1991.
[3]杰夫·特威切尔-沃斯.序 [M]//雷祖威.爱的痛苦.吴宝康,王轶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4]徐颖果.美国华裔文学选读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5]KINGSTON M H.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9:15-16
[6]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 [M].徐颖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212
[7]SIMPSON J C.Fresh Voice Above the Noisy Din [J]Times,1991-06-03.
[8]张子清.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族裔性的强化与软化——雷祖威访谈录 [M]//雷祖威.爱的痛苦.吴宝康,王轶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9]薛玉凤.后现代文化焦虑——论 《爱的痛苦》的艺术风格 [J].外国文学,2005 (5):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