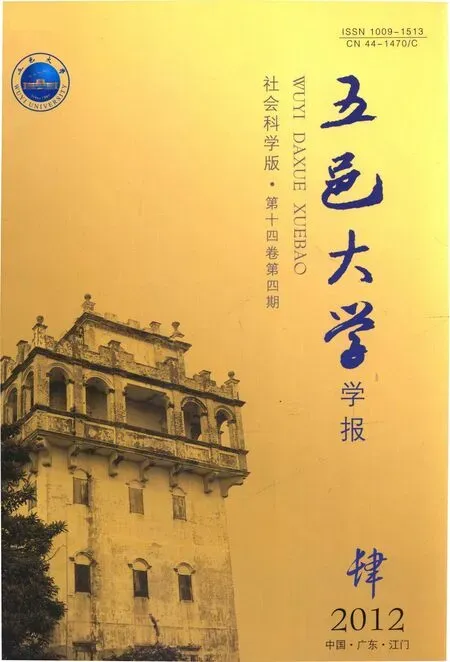未必樵歌响亦沉——论汪瑔的闲适诗与闲适心态
左 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汪瑔 (1828~1891),字玉泉,号芙生,晚号越人,所居名谷庵,学者称谷庵先生。本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以先世入粤,居久不归。汪瑔以游幕为生,足迹不逾广东。两广总督刘坤一、裕宽、张树声、曾国荃先后延之为幕客,主洋务;后捐纳国子监生同知职衔。晚年移居广州府番禺县。
汪瑔著述颇丰,有 《随山馆猥稿》十二卷、《随山馆丛稿》四卷、《随山馆词稿》二卷、《随山馆尺牍》二卷、 《无闻子》一卷、 《旅谭》五卷、《松烟小录》六卷。汪瑔工骈体文,诗词俱佳,尤长于诗,因词与叶衍兰、沈世良齐名,并称 “粤东三家”,诗名为词名所掩。汪瑔诗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博得众多诗坛名家的赞誉,如张维屏称汪瑔诗 “清圆如春莺啭树,矫健如秋隼盘空,言情写景,妙出性灵,慨乱伤离,时露风骨”[1]卷首。林昌彝 《海天琴思录》称:“山阴汪芙生山人瑔,胸次高旷,诗才清越。”[2]卷四,87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称:“芙生游幕岭海,颇有才名。诗亮拔自喜,晚趋婉约,乃多可取。”[3]四册,254汪瑔在晚清岭南诗坛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其作深入研究。
《随山馆猥稿》十二卷 (含续稿二卷)录诗一千零九十九首,其中同治十一年 (1872)定居广州后的诗作占593首。可以说,从此汪瑔进入了诗歌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
而汪瑔这一阶段的大部分诗作,是公事余暇和退职居家时创作的闲适诗,计430余首,占这一时期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三。闲适诗在中国传统诗文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因为它与 “言志”、“载道”的文学思想和价值观念是不尽相符的。一般说来,在时势艰难的晚清,西方列强的炮火,惊醒了中国读书人饮酒酬唱、游园赋诗的好梦,他们往往在诗中抒发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心;而身处鸦片战争前哨站、农民起义频发的广州,长期担任两广总督幕客、熟悉地方政治的汪瑔,居然创作了如此多的闲适诗,这使得汪瑔其人及其诗都显现出了耐人寻味的涵蕴。
一、“旅人”与知足心态
汪瑔诗中自称 “旅人”:“旅人感遥夕,秋气入虚堂”(《立秋后一夕雨》)[1]卷七、“知己泪白发,旅人心落叶”(《沉吟》)[1]卷十、“旅人闭户幸无事,惟祝瀛堧长太平”(《立春后阴雨浃旬排闷戏成》)[1]卷八,原因是汪瑔幼时即随父客游于粤,后来子承父业,继续在广东游幕,数十年饱尝人间冷暖,备受颠沛流离、骨肉分别之苦。同治十一年 (1872),汪瑔定居广州府,先后进入广东布政使和两广总督幕,经济状况大有改善。广州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繁华富庶,气候温润,历来是南粤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活环境较为舒适。汪瑔属于幕主延聘而来,幕主能以宾客之礼待之,故其心情较为自在。而全家团聚且安然无恙,更令他感到无限欣慰。早年忧劳惊悸的漂泊生活与之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饱经沧桑的 “旅人”来说,内心总有一种极度渴望稳定安逸生活的补偿意识。一旦获得安定的生活,便会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欣喜和满足感。
知足者常乐。虽然生活并不十分如意,“旬日来暑热殊甚,而官文书杂沓填委,如风如火,急勿可缓,伏几作书,书不止,汗亦不止,意颇苦之”[1]卷六,但当晚年摆脱了长期游幕生活后,汪瑔对眼前的安定生活无比珍惜,一切皆觉快然自足,并暂时忘记生活和身体上的种种不适:
旅食都无负郭田,治生难蓄卖文钱。只应三月茅斋住,成就湖州泊宅编。近效宋人说部作 《松烟小录》,已得数卷。
(《城南消夏杂咏》之十)
草堂著藜床,适意非尚俭。贫居效豪侈,勉强亦惭忝。微飔入帘凉,凉意生枕簟。北窗跂脚眠,偃息谢拘检。褦襶彼何人,见笑徒自点。敢曰矢勿过,庶几志无慊。
(《睡起读书用彭城集中南窗诗韵二首》之一)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知晓,汪瑔在日常生活中极简朴节约,馀暇以读书、著述为乐。在有限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汪瑔忙里偷闲,苦中作乐,追求平淡有味的生活和高雅的情趣,并将这种生活愉快、精神充实之感,以细腻的笔触写来,自是轻松洒脱。
这种饱经沧桑后的知足保和心态,与 “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不无关系。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广州饱经战争创伤,经济地位大不如以前。同治年间,清政府采取一系列调整政策,包括内部统治秩序的修补、中外和局的形成、自强运动的兴起,全国上下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期;而且,广州也努力发展本地的商业性农业和出口加工业,城市商业大为繁荣,有 “中国伯明翰”之称。这一“中兴气象”感染着汪瑔,在其诗中,几乎见不到发牢骚说世道不好,反倒是常常心怀感激:
近郭耕桑地,清时畎亩民。颇能占岁时,都解颂皇仁。时诏蠲逋赋。 (《村行杂诗之八》)
老农头似白,相见语欣然。细说承平乐,乾隆六十年。 (《村行杂诗》之九)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个饱经沧桑者对海内稍定的欣然感发,并不完全是粉饰太平。
不过,这种知足保和的乐观心态,对于汪瑔只是一种自我调试的方式,仅能给历经磨难、“性警敏事”[4]75-82的汪瑔一种暂时的缓解,而不能给他长久的心理归属感。身处对全国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广总督幕下、且被幕主倚重的汪瑔,仍然会产生羁旅他乡的客愁、对生命易逝的焦虑、对国势日渐衰微的担忧。如何保持一份平和淡泊的心态,成了安身立命的关键。
二、“幕友之贤者”与道家人生观
翻阅 《随山馆猥稿》便会发现,汪瑔年纪轻轻就已具备一种安贫乐道、自甘寂寞的超然心态:
闭关谢尘世,幽梦到烟萝。坏壁堆红叶,空庭暗绿莎。风怀因病减,诗思入秋多。赖有羊求在,新寒载酒过。 (《闭关》)
秋意和愁写,廉钩落日余。凉花双蝶小,古树一蝉疏。客到尝携酒,人闲欲著书。此中幽寂境,何似子云居。 (《新秋偶兴》)
这两首诗分别写于汪瑔十八岁和十九岁,诗中所透露出的超然物外的恬淡心态,实在很难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而此类诗在 《随山馆猥稿》随处可见。这种根深蒂固的 “出世”情结,源于汪瑔对 “幕友之贤者”的体认。
汪氏家族原籍浙江绍兴府,绍兴游幕风气之盛,全国首屈一指。汪瑔的父亲汪鼎为谋生计,曾在广东顺德、清远、南澳、信宜等地为幕客。幕客是地方官自行聘请的佐治人员,非官非吏,无品无位,须退居幕后,成幕主之美,往往名不见经传,因而有为人作嫁的失落感。然而,汪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茹素守真,可泯没以终世,勿夸耀以干人”[5]61,即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淡泊名利,不与物迁,隐约可见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这种追求也包含了下层幕客对于前景无望的无奈心态。岭南大儒陈澧认为汪鼎这一精神追求值得大力表彰,“以劝幕友之贤者,知立名之可以传于世也”[5]61。换句话说,幕客如能达到 “幕友之贤者”的精神境界,同样可以获得不朽的名声。
汪瑔自幼随父四处游幕,在父亲的引导下,对“幕友之贤者”有了深刻体认,并奠定了初步的道家文化思想基础,而 “羊求”、“子云”这样的高逸之士自然成了他的理想人格模范。由于家境寒素,加之受家庭氛围的影响,汪瑔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是子承父业,继续在广东各地游幕,“所至有声,既得先生治状尤著”[4]75-82。这一阶段,汪瑔引淡泊名利的名士盛宪、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以自况,如 “盛宪留吴非得已,鲁连居赵本无求”(《重有感四首》之四),亦可看作这一阶段 “幕友之贤者”的具体化。汪瑔常教导弟子 “幕客治事当如身居此官,善则归于主者,不当居其名也”[4]75-82,虽然也有徒劳无功的痛苦,但 “幕友之贤者”的自我认同,使其能够远离功名的诱惑,从道家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中找到归宿。
如果说,早期汪瑔服膺道家精神,还颇有些“求道”的意味,那么,定居广州后则明显偏向“避世”。因 “山资不足,家食未能虚”(《述怀十二韵序》),退隐还乡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汪瑔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在繁华都会中作个 “从来市隐心不嚣,岂必山居迹方屏”[6]卷上的 “中隐”之士。汪瑔只是将作幕客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对于纷繁浮嚣的幕府生活没有丝毫留恋,反映幕府的诗寥寥无几。光绪十年 (1884),57岁的汪瑔正式结束幕府生涯,移居广州番禺,名正言顺地做隐士了:
新凉招不来,残暑推不去。黄花时节过重阳,未始西风在何处。日日临风脱角巾,科头跣足恣闲身。地僻虽阙三分水,墙矮能遮十丈尘。名流无复秋声馆,解渴惟凭茶七碗。察幸衰颓白发翁,不曾欣羡清凉伞。相午柴扉且未开,小眠斋里小徘徊。藤床竹枕容高卧,自信今无热客来。 (《秋暑甚剧戏成短歌》)
晚年汪瑔的自我形象活脱脱是一个飘逸潇洒的柴桑翁,内心充满了无挂碍的快活。因厌弃官场而毅然决然归隐的陶渊明,自然是厌倦作幕的汪瑔追慕不已的偶象。虽然所追怀的 “幕友之贤者”的具体对象不断变化,但道家自由的境界始终是汪瑔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而写作反映这一心境的闲适诗对于汪瑔来说,正是 “当行本色”。诗人以一颗晶莹剔透之心去感受天地万物之灵性,抒发闲适萧散的情致,在清贫的生活中体味悠闲自在,并从中流露出对人生的理解和对哲理的思考。
然而,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宜闲适的时代,追求闲适的汪瑔其实很难回避现实政治。看到形色美观、口味鲜美的西餐,心里很不是滋味,“手掰琼酥饼,颜酡玉色醪。此中夸饮啖,吾意亦萧骚”(《江楼早集》);登楼凭栏,举目望去,尽是 “朔风旌旆连江戍,极浦帆樯异域船”(《冬日登镇海楼短歌》);面对国势日渐衰微的现实,沉溺于山水庭院之乐的汪瑔其实是无法忘怀时事的,“腐儒今白首,一意祝升平”(《偶感二首之二》),“尚有区区私愿在,海疆无事岁年丰”(《九月二十日复还故居即事成咏》)。在汪瑔心目中的自我形象定位是熟读史书、看透时局、又无法力挽狂澜、只得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的杜牧,如 “野夫对酒方行乐,惭愧樊川作罪言”(《早春感兴》);“载酒江湖今老矣,鬓丝惆怅杜樊川”(《春感》)。汪瑔在去世前一年,写了一首 《次韵答文芸阁编修廷式》给挚友文廷式,最后两句自称“衰翁不解苏门啸,未必樵歌响亦沉”[6]卷下。 “苏门啸”指阮籍的啸咏,比喻高士的情趣,“樵歌”即朱敦儒的词集名,该集反映了朱氏寓沉痛于隐逸的思想。汪瑔借此表达自己虽无贤人逸士之高致,却也另有孤怀幽抱。可以说,汪瑔的闲适诗中包含了其人生的沉重悲凉和痛苦挣扎。
三、“一言冷冰雪,万象豁云雾”
光绪了二年 (1876),汪瑔在 《杂诗十首》之九中表达自己的诗歌主张:
为诗道性情,初不假题署。奈何事标榜,骚坛竞攀附。西江自为宗,北地固多助。当时蜉蝣辈,相率作膻慕。惬心嗟未然,借面苦无具。未得夷光颦,已失寿陵步。我诗固不工,名氏亦不著。要为自怡悦,非以博声誉。一言冷冰雪,万象豁云雾。置之勿复道,识者解其故。
这里,汪瑔以一种异常清醒的眼光,看待风靡一时的 “宋诗派”。汪瑔认为,“宋诗派”之所以能居诗坛领袖,诗派自身的魅力固不待言,但提倡者的位高权重也与之大有关系。汪瑔还以诗歌应真实地抒发真我性情为标准,批评了 “宋诗派”之末流雕琢过甚、亦步亦趋的缺点,而将自己的诗歌创作看作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的游戏,并形象勾画出自己的创作特征:“一言冷冰雪,万象豁云雾”,即以清新秀丽的笔触,描绘天地万物呼之欲出的自然真率境界。
这一艺术特征与汪瑔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还与他师法的对象有直接关系。汪瑔博采众家,而最为推崇的还是善于表现日常生活和平凡景色,并发掘其所蕴藏的美的诗人。《漫成四首》之三云:
半世摹诗格,吾乡老放翁。别裁廷秀上,托兴杜陵同。
就闲适诗而言,汪瑔主要师法陆游平淡自然、空明透彻的诗风,融通杨万里的”活法”和杜甫的比兴寄托,同时吸收各种诗体的养分,变化镕铸,形成了 “一言冷冰雪,万象豁云雾”以造境为主的创作特点。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汪瑔的闲适诗众体皆备,特别是将多用于叙事的五、七言长篇古诗引入写景,并以贴近事物本身的时空自然流程为线索,不务错综复杂,掺以工整精致而又新鲜活泼的对偶句,因而显得自然轻快,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难得的是,汪瑔的闲适诗还以诗歌中的边缘体式——六言诗见胜。定居广州之后,汪瑔共做六言诗42首,几乎都是闲适诗。六言诗节奏变化较少,音节短促单调,容易流于平淡生硬。汪瑔工骈文和词,为他的六言诗创作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六言诗历来只是被诗人偶尔拿来抒写闲适心境,而志在林泉的汪瑔正好藉此展露才情和襟怀。他的六言诗随笔戏谑、轻逸明快、对偶精工、情辞相称,如 《颐园小集分体成六言一章》就情景宛然,甚有风致:
绮筵未妨卜夜,画槛犹可移春。花引倩兮一笑,月窥粲者三人。红牙一曲两曲,蓝尾三巡五巡。老我已无佳句,那堪题上罗巾。
其次,在语言上,汪瑔保持了闲适诗平淡自然的基本特色,同时吸收 “宫体诗”、“义山体”、“长吉体”一路的形式工巧、声律严整、辞藻秾丽的语言特点,由此形成了灵动圆润、韶秀淡逸的语言风格。这也恰好与岭南花团锦簇、纷繁玲珑的风貌相契合,充分展现了岭南的风物之美:
紫晃玻璃日,青开玳瑁天。晴光连大地,和气溢新年。岭海春原早,云霞曙更鲜。因之识元化,花柳共欣然。 (《立春后三日作》)
汪瑔的郊游诗多为春光明媚之景,这与岭南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有关。较之白居易喜欢将一切琐碎的事情都如实记录下来的倾向,汪瑔更追求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记录,用字炼意上多有讲究,绝不拖泥带水。
再次,诗人在表现自然物象时,善用动词和拟人手法,赋予天地万物以自然之灵性,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东西,在他的笔下都显得灵动自然、趣味横生。只有热爱生活,又心无尘俗欲念的人,才能有如此体贴入微的惜物之情。如:
长空急雨过,斜日透林明。云作烂银色,雷余湿鼓声。从教变凉燠,未用卜阴晴。只喜沟塍绿,田蛙时一鸣。 (《雨后闲眺戏成》)
诗中通过使用动词,让雨后的自然景物、动植物神态毕现,寥寥数语便描绘出气象万千的景象。另外,汪瑔为了追求自然天成的意境,极少用典使事。当需要用典时,又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多用熟典常字,融典入景,力避险怪。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文化背景,使得汪瑔凭借其闲适诗在推崇 “学人之诗”的同光诗坛上能够另出手眼、独树一帜,为略显沉重的晚清诗坛增添了一抹温馨的亮色。
注释:
①在中国诗史上,以 “闲适诗”为诗命名首见于白居易。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中说:“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见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第279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文对于 “闲适诗”的定义采用白居易 《与元九书》的界定。
[1]汪瑔.随山馆猥稿 [M].清光绪十七年随山馆全集本.
[2]林昌彝.海天琴思录 [M].王镇远,林虞生,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M].中国书店影印退耕堂本.1988.
[4]朱启连.汪先生行状 [M]//汪兆镛,等.山阴汪氏谱.民国三十六年汪氏敬德堂印本.
[5]陈澧.山阴汪君墓表 [M]//汪兆镛,等.山阴汪氏谱.民国三十六年汪氏敬德堂印本.
[6]汪瑔.随山馆续稿[M].清光绪十七年随山馆全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