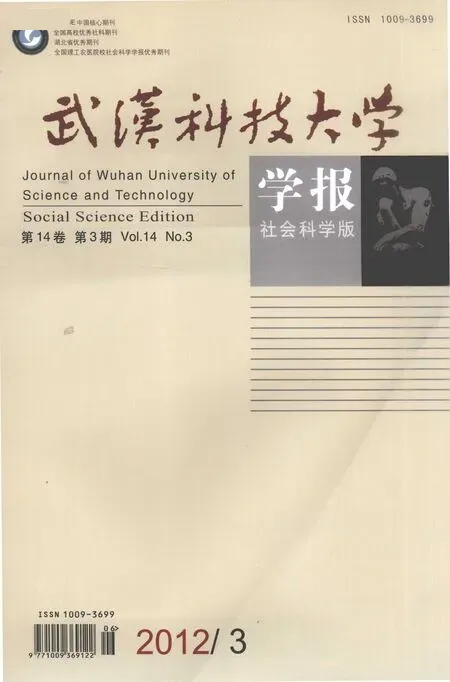主体间性——和谐伦理的构建基础
张学义 刘胜梅
(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江苏 南京211189)
近代以来,主体性道德哲学由辉煌走向衰落,加之呈现出的现代性道德分化样态,人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严峻的现实客观上吁求一种新的道德哲学范型来拯救人们的精神世界,规约人们的伦理行为,和谐伦理的理论建构正是这种趋势下的有益探索。
一、主体性道德哲学之困境:从“凯旋”走向“黄昏”
主体性道德哲学之困境是主体性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弊端在道德哲学领域的展现。所谓主体性(subjectivity)是指“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为根据等等含义”[1]65。这里所说的“主体性”主要指的是以自我意识之“自我”为出发点来规定一切存在的观念[2]3。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主体性不断建构的历史: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神祇“认识你自己”、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回归,再到帕斯卡尔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直至后来,康德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费希特的“绝对的自我”以及费尔巴哈的“我欲故我在”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建构和强化了主体性哲学理念。尤其是近代以来,主体性思想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历经了启蒙运动的洗礼,火山喷涌般在西方社会爆发出来,一度成为西方思想领域的主导,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人性之解放和全面人格之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月满即亏、否极泰来,主体性思想凯旋之际,也逐渐迫近了黄昏。主体性思维在高歌猛进之时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以及主体性道德哲学的“囚徒困境”。
(一)理想与现实的断裂
自古希腊以降至黑格尔,从寻求“万物的始基”到建构“绝对精神”,主体性哲学家孜孜以求的是世界的本原、最高实体以及超验本质,只有把握到这个稳固的根基,主体之存在才能具有先天超验、永恒不变、同一不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循此路径,主体之存在必然从现实、历史中不断被抽离出来,超越一切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化身为单向度的抽象化的幽灵。主体性哲学思想投射于道德哲学领域,便生成了无法自拔的内在矛盾。主体性道德哲学试图构建一个事先预设的、永恒超验的、同一的道德哲学体系,该体系编织了一个远在彼岸的五彩梦幻:它追求具有同一性本质的至善、至仁、至爱与永恒超验本质的合一,追求终极存在与终极价值的合一。究其因,它源于人类对自己有限生命的困惑以及对这种有限进行突破的雄心,源于从“存在者”到“存在”、从“定在”到“在”、从“是者”到“是”进行超越的信念。然而,这其中却蕴涵着深层悖论:这种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本意旨在思考生与死、天与地、苦难与拯救,思考人之生活意义与生存困境,实则在客观上忽视了真实生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忽视了活生生的生命样态,它成了一种“漠视生命”、“肢解生命”甚至是“敌视生命”的“无生命”哲学。这种远在彼岸、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让现实生灵唯其是从却又无法攀爬至救赎的道德天国,这种内在的悖论与冲突也昭示着它必然走向瓦解和完结[3]。
(二)主体与客体的分离
主体性哲学试图要克服传统哲学中主客不分的混沌状况,强调主体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导性、能动性和积极性,主张人是客观世界的主人,可以而且能够利用各种手段认识世界、控制世界和征服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人类的这种主体性思维愈加膨胀,于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就是追求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分明,主体对客体的强势支配,以至于心灵世界与物质世界、灵魂与肉体的明显分离。然而,这种主体性思想在根本上凸显的是个体的、“单子式”的主体性,个人之外皆为客体,不管人还是物,并倾向于以客体为主体实现的手段,这势必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分疏和异化。而以此理念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关系也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诸如霍布斯的利己主义、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等伦理形态。总体而言,主体性道德哲学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人们生活在一种“狼与狼”的丛林之中,乃至形成“他人便是地狱”的局面[2]19-20。
(三)人与人的物化
人们发现,人越是追求自身的主体性,人们对于物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物化”。人类在科学技术的武装下充分彰显着自己的主体性,不断地侵蚀、占有、消费着他物,但也更加依赖于他物。正如弗洛姆所言:“今天,在全面发达的工业国度里,人们把占有的范围扩大了,对朋友、亲人、健康、旅游艺术品都可以占有,就连上帝和自我也不例外。……人变成了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占有的性质。在这种全面物的依赖关系中,一切都物化了,就连原本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也变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4]76-77在这种对物的占有 与 依 赖的关系中,人们常常会产生错觉,似乎觉得只有通过对他物的侵蚀、占有和消费,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人变成了依赖于物的物,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诉诸物来权衡。这样,世界就是一个异化了的物化世界;人在追求主体性的同时,却迷失了主体性,于是,诸如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乃至道德虚无主义沉渣泛起,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2]18,[5]159-160。
综上不难看出,当人的主体性发挥到极致时,其弊端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主体性哲学在充分彰显人之主体性的同时,却迷失了自己。如主体性哲学之命运一般,主体性道德哲学也在追求世界之同一、主体之和谐的梦想时,悖逆了其初衷,导致了主体的分离与消解,构成了现代性道德危机的重要诱因。
二、现代性道德分化之展布:由“冲突”迈向“和解”
在主体性道德哲学追求世界同一、主体和谐效果甚微之时,现代性道德却在不断走向分化。高技术体系、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作为“淘沥”现代性道德的三大现代性因子,却在以追求同一性之实现的方式进一步破除了道德同一性的梦想,呈现出现代性道德分化的各种样态,成为加剧现代性道德危机的又一利器——事实上,它们背后之理念与主体性道德哲学之思想彼此纠葛,或本身就是一体,或渗透于后者之中[6]。
(一)高技术张扬工具理性
技术本质上是一种解蔽方式,使存在变为存在者而进入开显之境,这体现了一种类生命的共通性和伦理普遍性,然而现代高技术体系“以信息方式和控制论图景为典型塑造”人类生活方式,即以一种促逼的方式招致着人与自然的汇聚,汇聚成一个座架,使得人与自然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敞开、展现于开明之处,自然遭受拷问,人类迫使自然做出回答,剥离了覆盖在自然之上的神秘面纱,而人也在此过程中被逼迫而变得不自由。高技术使得世界祛魅和整体性瓦解,从而偏离了人之生存共同性和伦理普遍性,昭示了工具理性的胜利和个体性的凯旋[7]。
(二)市场经济分化个体差异
现代经济秩序的变革,市场经济范例的兴起及其体系的确立,使得经济从传统文化中独立。物质生活的富庶和物质欲念的膨胀使得人们从高尚沦为世俗,从执著于自觉过高尚的精神生活下沉为以积极的态度追逐一种幸福的物质生活,“理性经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逼近的目标,趋乐避苦、计较利害得失、精打细算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现代人从根源上切断了神圣性以及与神圣性本质的联系。尤其进入资本市场经济阶段,资本以一种高海拔、高平原的状态进入市场,其高度的控制力和对资源的自由配置力,加之无孔不入的投机行径,颠覆了传统的市场游戏规则,对传统自由、平等、公平的原级市场理念与原则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以一种貌似正当的对自由的遵守、并“自由”地破坏自由的游戏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优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压盖了社会优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资本者或资本集团玩弄游戏规则于股掌,幸福、快乐建立在追逐欲望的基础之上,原本普遍的自由、平等、公平成为只适用于孤立的“这一个人”的规则,一个人的自由变成了大多数人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变成了众多者的不自由,规则成为资本精英的权柄,大众在无知的背景下“被规范”。这就颠覆了传统的“自由”理念和规则的神圣性,造成了“自由”的异化和对规则普适性的漠视,最终导致普遍性的消解和个体差异性的分化。
(三)全球化促逼地方性“置根”
“全球化”概念提出之时,西方学界以热烈的态度去拥抱,发展中国家学者也有步其后尘者,举双手以欢迎。然而,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时髦之物,其实质是所谓的“麦当劳化”,背后展现的是“理性的狡计”,是一种文化与经济分离后的冲突展现,是技术经济世界与符号价值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与分殊,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分化与较量,是一种话语权之争。全球化体系下,规则、规范成为手段,普遍、普世成为目标,然而目标的设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甚至手段超过目标。全球化视域下的普世伦理就成为其理论设定的目标,然而不同地域的人们又因各自依附于其地方性传统,在经济与文化分离和断裂的表征下又呼唤其传统的觉醒,从而在文化或道德上激起一种反向运动,即“置根”(embedded)运动,普世伦理只能作为一种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景在向善良的人们招手微笑罢了。
以上三种因子又常常是纠结在一起:全球化是以高技术和市场经济为先导,开创了以全球网络为背景的技术-经济范型,又加之西方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诉求,强推硬植某种超地域、超历史的、具有同一性表征的道德话语,试图以世界性的“大社会”取代地方性的“小社群”。然而实际上,它们却又在其各自的和共同的维度上加剧了现代性道德的分化或二元化: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殖民、地方与全球以及传统的丧失与回置,等等,最终导致全球背景下的“世界公民”彼此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或匿名的“邻居”,人们远离“道德乡土”而成为心灵上的“流浪者”[6]。
然而事情的另一极却是,现代性道德的分化使得道德主体又渴求着某种“道德对立面的和解”,加之主体性道德哲学陷入同一性破灭、主体分离的困境,现代性道德危机愈演愈烈,人们难以接受由此引发的“道德冲突”,希望走向和解,重回一种彼此和谐的生活境遇,于是客观上呼吁一种新型伦理范式的建构,来拯救危机的现实。
三、主体间性道德哲学之超越:历“黄昏”再现“黎明”
主体间性道德哲学范型的建构就是在主体性道德哲学式微和现代性道德呈现分化样态的背景下提出的,理论和现实都需要一种容道德同一性和道德主观性于一体的新型伦理范式。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由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理论初衷是为了摆脱“唯我论”的困扰,解决“他者”主体性问题,以及解决主体间构造世界的交互性问题,进而通过对他人主体性的先验构造和交互主体性对世界的构造来完成主体间共同的生活世界的建构。然而这种认识论层面的主体间性,还只是停留在纯粹意识当中,“我在‘这里’,他人始终在‘那里’,他人与我的统一”,只存在于想象和意识中[8]。海德格尔试图通过现象学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哲学建构来完成对胡塞尔狭隘的意识哲学超越,他以“此在”——具体生活境遇中的人为根本,通过对“此在”与他人的“共在”来达到主体间的共通。“此在”生活在他人、他物之中,与他人、他物交互和“共在”,并在这种交互和“共在”中同时显示出自我与他人、他物,体现出一种共主体性[9]。后来,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了主体间性问题。他认为语言本质上属于生活世界,世界体现在语言中,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理解和对话,超越个体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达到主体间的“视阈融合”[10]。20世纪的德国宗教学家马丁·布伯则着重从“我-你”的关系中试图探讨一种新的主体间性的对话模式。他的“你”包括所有除“我”之外的存在,“我-你”关系是世界的本体,处于原初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状态。我和“你”处在一种直接体认的关系中,彼此并不能完全融合为一,始终存在一个距离,布伯称之为“之间”,这种“之间”不在我中实现,也不在“你”中实现,而是在“我-你”的“对话”中体现。“对话”使得你我联系在一起,但又保持各自的特性和彼此差异的张力[11]。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则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着重阐述了他的主体间性思想,他以“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其实质就是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在一个理想的话语环境中,实现交往的理性化[12]。
综上可见,主体间性主要指涉自我与他我、他者的关系,这里既有我与他、我与你的关系,也有我与我的类——我们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共通性、共同性以及彼此间沟通的可能性。主体间性范畴内的主体——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具有相互平等的地位,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有机统一,体现了自我与他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充分融合,体现了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交往、沟通、对话与理解,体现了“自我与对象内在统一的生存境界”,在根本上体现了人类对自我、自身的“终极关怀”[13]。因此,主体间性道德哲学较之于主体性道德哲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一)手段到目的的转变
在主体间构造的关系链中,彼此双方所做的一切,既是本真的自我目的的展现,又是本真地为他人目的展现的;双方的目的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双方的活动虽然还保留着形式上的“手段”关系,但本质上却成了这统一目的性的展开形式。主体间性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且主体的范畴不仅是人与人,还扩展到动物、生物乃至非生物,并把主体间的目的统一起来而达成和谐共识。
(二)“相对”到“相与”的转变
主体性哲学失败的原因在于其遵循的逻辑是对象化的逻辑思维,是主体相对于客体和对象处于一种相对主导、统治的地位,彼此间主次分明,其他客体归属于另一主体,这背后实则隐含着一种统治、暴力,其极端就是集权,所以“相对”的主体性哲学始终进入不了主体间性的世界。而主体间性道德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提倡人与人、人与物的相容和相与,是一种“让……存在”、“与……生存”的模式,让他人、他物存在,与我共存,共同此在,彼此和谐共处于多样性的生活世界。
(三)主体间性的道德哲学建构并不需要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之外寻求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形态之一就是交往行为,这种交往行为为主体间的沟通提供了可能性前提,同时,现代性的合理化逻辑又为在交往中达成理性共识创造了条件。他认为相对式的主体性道德哲学是现代合理性的非均衡发展、工具理性极度扩张的结果,交往合理性受到了明显压制,一旦相与的交往合理性被解放、激发出来,那么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就成为可能[14]。
需要指出的是,主体间性是人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对象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维度”,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主体间关系的最终解决,需要在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得以完成。
四、主体间性的和谐伦理之可能:颠覆与重构
由上可知,主体间性道德哲学是对主体性道德哲学的批判,是对那种以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利我、排他为特征的个人主义的反思,更是试图对主体性哲学思想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淡漠、人与自然的排斥对峙、人与社会的矛盾对立的现实性超越,以及以此为表征的现代性道德危机的颠覆和重构[12]。因此,建构一种以主体间性为根基的道德哲学新范式成为时代的诉求,而国内学者适时提出并试图建构的和谐伦理体系正是这样一种主体间性的道德哲学进路。
首先,“和谐”思想体现主体间性。这从古代的“和”之思想可见一斑。儒家有“和而不同”、“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故牟宗三有评,“仁以感通为性”[15],感通即是主体间生命的交互融通;道家有“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意指人与他人、天道、自然和而为乐;墨家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故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睦共处;张载也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主体间共荣共生的思想,体现出多元主体下的“和而不同”。对于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亦有其资源。许慎《说文解字·人部》云:“伦,辈也”;杨琼《〈荀子·富国篇〉注》:“伦,类也”;赵歧《〈孟子·离下篇〉注》:“伦,序”;台湾学者黄健中经过详细的词源学考证后认为,“伦谓人群相待相倚之生活关系也”[16]。由此可见,伦是一种差别而有序的关系体系,是由众多差别而有序的单一物构成的普遍性体系;而“伦理”者“伦”之“理”也,是这种由单一性构成的普遍性体系的理念表征,它一方面具有伦理概念本性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黑格尔也同样说,“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17],伦理追求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实体认同,而实体又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体现出人与他人、他物现实的共通性。总之,“和谐伦理”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彼此的有机融合,是一种普遍性与多元性兼顾、实体性与主体性同一的伦理体系。
其次,所谓和谐伦理,其旨趣在于以一种自由的道德主观性发端,进而形成一种伦理普遍性,再又转化为一种相与的道德主观性,最终达成主体间对彼此相互关系的承认和认同。个体在本能上虽为本能和欲望所驱使,然而道德自由在主体维度中并不完全倾向于自利、自私与自保,否则其自身的存在会受到危及。和谐伦理承认个体自由与个人正当性,并以此为基础寻求彼此间的共通性,以寻求在“异质性”的个体丛林中达到普遍性的伦理皈依。
概言之,和谐伦理范型是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为思想资源,以和谐为内核,以主体间性为基石,在注重维护伦理实体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同时,又尊重道德主体的主观性和多样性;它既兼顾了传统形上道德哲学追求善、仁、爱的道德理想,又关照了现代性道德分化、道德多样性的现实,承认个体自由与个人权利的正当性,通过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契合,一个适恰的“阿基米德点”。同时,主体间性道德哲学对主体性道德哲学进行颠覆与改造,弥补了主体性道德哲学带来的诸多“囚徒困境”,重新开启了一扇道德哲学的希望之门。
[1]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5.
[2] 刘金萍.主体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 田海平.生命的大同与大异[J].江海学刊,2008(2):5-10.
[4] 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76-77.
[5]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6] 田海平.和谐伦理作为一种承认理论的四个论纲[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23-29.
[7]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25-932.
[8]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M].倪梁康,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890-894.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131-146.
[1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20-342.
[11]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刚,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6:186-199.
[12]高鸿.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间性及其困境[J].教学与研究,2006(12):53-59.
[13]吴桂韩.试论主体性的和谐伦理道德观[J].理论界,2007(5):166-167.
[14]唐士其.主体性、主体间性及道德实践中的言与行[J].道德与文明,2008(6):36-41.
[1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
[16]黄健中.比较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1-25.
[1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