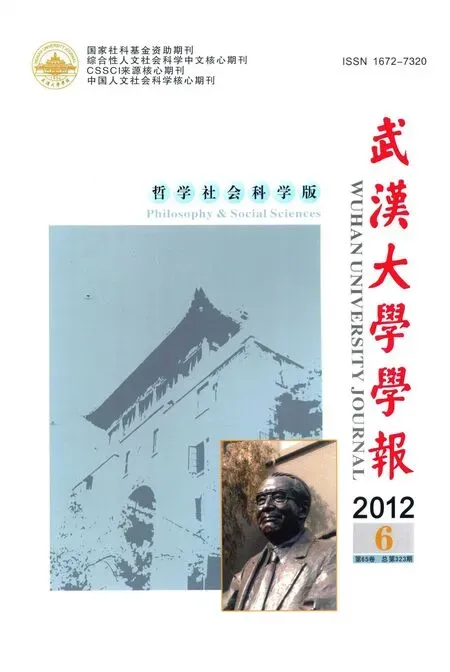商鞅之“法”及其刑名逻辑
吴保平 张晓芒
一、商鞅之“法”
商鞅是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其“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史记·商君列传》),继而说服秦孝公,开始实行“商鞅变法”,“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稿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其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变法成效之大、影响之广,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
(一)商鞅之“法”的起源
在法的起源问题上,商鞅认为“法”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上世,“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商君书·开塞》下引《商君书》只注篇名);“中世上贤而说仁”,即以道德观念的“仁”来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刑政不用而治”(同上);然而,到了“下世贵贵而尊官”(同上)阶段,人们“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同上),社会混乱,争夺激烈,必须“定分”、“立禁”、“立官”、“立君”。所谓“定分”,是为了达到“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同上)之目的。这实际上是确认了对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规定了夫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说明法律是为确定与保护财产所有权而产生的。因而,法学界称其为“定分止争”的法律起源论。所谓“立禁”,即制定惩罚侵犯私有财产行为的法律、禁令,确定了私有权、制定了法令,就要有人去掌管,这就需要设置官吏(“立官”)以及统辖官吏的国君(“立君”)。由是连环,国家和法律出现了。
较之传统天命观,商鞅关于“法”的起源论,应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二)商鞅之“法”的特征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对法的规范、公正、公开、平等性等都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系统的论述。
关于法的规范性。在对“法”的起源的认识基础之上,商鞅提出法的概念:“法者,国之权衡也。”(《修权》)在商鞅看来,“法”就是治理国家的标准,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以此将其比拟为度量衡:“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同上)此“法”即规范,其功用是明辨是非而加以赏刑。商鞅之所以强调法的规范性,目的在于用它来统一人心,使整个社会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在其利益所容许的范围内行动,以保持其统治秩序。
关于法的公正性。商鞅认为法应该体现公正无私,故而主张“任法去私”,而不能“释法任私”;因为凡是违法、“害法”、乱法、废法,都是由“任私”而起。他说:“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一君好法,则端正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巨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修权》)这里的“私议”是指国君周围近臣的建议。他认为,私议不仅不合乎法度,而且危害很大,是“法”顺利实施的大敌。因此,“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国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同上)商鞅“任法去私”的主张,在于反对包括国君在内的统治者枉法任私、玩弄法柄和权术的行为,表明对法的公正性的强调和重视。
关于法的公开性。商鞅继承了法家先驱者子产等人公布成文法的思想,主张公布成文法,坚持法的公开性。《定分》篇中说:“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在商鞅看来,统治者制定的法令不仅要布之于天下,而且还要让法令明白易懂,使人人都能够理解,这样才有利于法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公开法令的同时法也就随之具有了明确性的特征,人们以此即可有所规避或选择自己的行为。从当代的视角分析,法律的公示和普及意味着国家向民众明确确立了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同时,法律的强制性特征较儒家的“礼教”更有助于将这种外在的客观标准内化于人们的心中,由他律转化、积淀为自律,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整合,便于国家治理。按此,商鞅之“法”的公开性和明确性就为其“法”平等公正地实施奠定了基础。
关于法的平等性。商鞅认为“法”代表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应该具有平等性,刑罚的对象不能有贵贱等级的差别,也不能因人而异。司马迁“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法”的普遍适用的平等性特征的评价,即可上溯至商鞅的“壹刑”。即“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赏刑》)。其冷峻的言辞,似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感。但其一,商鞅“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之“壹刑”的对象是不包括“王”(君主)在内的。一定程度而言,“法”是“王令”的体现,若要让“法”顺利实施,从而实现对“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的统治,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树立“王”(君主)的绝对权威,把立法、执法等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王”(君主)的手中,操生杀予夺的大权,才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商鞅主张“君尊则令行”、“权制断于君则威”(《修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其二,司马迁对此进行评价时,也不无感慨地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名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因而,商鞅之“法”的公正性、平等性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既然“王”(君主)在“法”之上,那么,商鞅所希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无法实现。虽然如此,商鞅还是对执法的公正性给予了更多关注。因此,他用大量篇幅论证了依法施政、信赏必罚的重要性,并要求君主“任法而不任智”(《任法》),严格执法,公而无私。商鞅的两次变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坚持了这一原则。在商鞅那里,法在推行和严格执行过程中是一个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诚信问题。这是迈向“法治”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威慑力。一旦身处上层的权贵破法不罚,身处下层的民众就难以建立起对新法和国家的信赖。《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徙木立信”、“一诺千金”、“刑劓公子虔”、“黔太子师公孙贾”等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按《礼记·曲礼上》的“刑不上大夫”,是商周以来刑适用的阶级原则,大夫犯罪免受墨、劓等肉刑,所以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刑以治野人”、“刑以威四夷”之说。但商鞅 “刑无等级”主张的提出,以及上述举措的实施,应是对“刑不上大夫”的礼治惯例的大胆挑战,让“秦人皆趋令”(《史记·商君列传》)。平等性作为商鞅之“法”的重要特性之一,在秦国得到有效贯彻。这种体现“法”之平等思想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认识如何促使大家共同遵守一种强约束的规范问题。
(三)商鞅之“法”的作用
商鞅之“法”在具有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平等性等特征的同时,也随之具有了“定分止争”、“定赏分财”、“禁恶止乱”的作用,为其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和“富国强兵”的目标奠定基础。
“定分止争”语出《管子·七臣七主》“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定分”就是确定名分,“止争”就是止息纷争;法律中以此语表示要确定物的权属。《慎子·逸文》曾举例说明“定分止争”:“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之言时也有类似的故事,但都未在“法”之作用的层面上展开论述。商鞅在《定分》篇借用慎到这一故事,展开了对“名分”的分析,他说: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
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商鞅认为,“定分止争”是“法”的作用之一,一旦物的权属问题有了明确的界定,那么就不会有纷争发生。国家之事同物(兔子)的权属问题一样,如果名分不能确定,就会导致“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定分》)的恶果。因此,确定名分,是形势大治的方法;若名分不能确定,必然导致形势的混乱,甚至会有亡国的危险。该如何“定分”呢?还应从“法”入手,因为“法”是“国之权衡”,故可“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修权》)。法令定,名分就可以定,合于法令者给予赏赐,反之则予以惩罚。由此观之,商鞅关于“名分”的论述,当是对申不害的“循名责实”理论和尹文“刑名之术”在“法”之作用上更为直观的表述。因为他们强调的问题,都是“名分”的确定与否是国家“治”与“乱”的关键。在此基础之上,商鞅进一步把“名分”法律化:“立法明分”。即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所谓“公私之分”(《修权》)。这其实为法家一贯的“‘法、术、势’思想的发展与‘刑名之学’有密切联系”①谷 方:《论“法、术、势”的历史地位》,载《求索》1982年第3期。的推论提供了又一佐证。
对于“禁恶止乱”、“民治国安”,商鞅主张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严厉,即通过“严刑峻法”、“以刑去刑”,让“法”起到“禁恶止乱”的作用,达到“民治国安”的目的。商鞅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开塞》)商鞅依靠“重刑”实现“禁恶止乱”、“民治国安”的做法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可取的,他在秦国的两次变法都得以成功,以及司马迁的评价都说明了这点:“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对此《战国策·秦策》中也有类似记载:“商君治秦……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应该说,这种社会效果的取得与他采用“重刑”不无关系。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商鞅的“重刑”思想由于过于严苛,特别是诸如连坐等制度的实行,极易伤及无辜百姓;而诸如涉及户籍的一些变法举措,则极大地限制了民众自由。事实上,商鞅也恰是死于他自己所制定的“重刑”之下。其最终的“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记·商君列传》)的哀叹,或许是对自己之前所制“重刑”的追悔。然而,历史发展的代价现象表明,“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页。。只不过这些“巨大的历史灾难”在先秦时期是落在了邓析、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身上。司马迁在为他们作传时,也未因其个人感情的憎恶而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
态度决定方法,也直接导引研究的思想及价值趋向。钱穆在其著《国史大纲》的开篇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③钱 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全两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页。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也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①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由此,“温情与敬意”、“了解之同情”就是我们对待历史和研究历史所应持有的态度。按“逻辑与法学具有天然的联系”②张晓芒:《惠施、公孙龙与三晋名家》,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就逻辑学本身而言,它“作为研究推理有效性或论证有效性的工具性的思维科学,除具有最本质的求真功能外,还具有提高人文精神的求善功能。……任何解决问题的逻辑论证,都要求在求真的过程中既保有逻辑的求真态度与精神,又保有逻辑的求善的振世精神和人文关怀”③张晓芒、吴保平:《逻辑的求善功能》,载《光明日报》2011年8月3日第14版(理论学术版)。。这样,逻辑本身的求真、求善功能,也就势必“呼唤”我们要以“温情与敬意”、“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研究历史。唯有如此,才能“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才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④钱 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全两册),第7、8页。也才可“通过严谨而认真的研究,增强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增强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⑤张晓芒:《先秦诸子的论辩思想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3页。。商鞅之“法”中的刑名逻辑思想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一点。
二、商鞅之“法”中的刑名逻辑思想
作为先秦法家中重要政治改革家,商鞅之“法”完全是为其改革实践服务的。他在对“法”进行理论总结时,同韩非一样,也是以正名逻辑作为工具来论证他的刑名法术思想。所不同的是,商鞅在论述他的刑名法术思想时,不像韩非那样就“形”、“名”问题而论“刑名”,但却以此为工具加以运用。例如,《商君书》中对“审名”和“明分”都有涉及,但却没有像韩非那样明确提出“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的命题。然而,商鞅在论“法”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运用“审名”和“明分”。
(一)“名”与“实”
商鞅所言之“名”、“实”,常与“法”相提并论,这是法家论名的一个特点,也是刑名逻辑的特点之一。在《君臣》中,他说:“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名号”是先秦时期一个极具政治性的概念,这是因为,自孔子首提“正名”问题以后,无论对名的语义解释或语用运用,无不打上了政治伦理的色彩。而“号,名位也”(《国语·楚语下》),“号谓谥号也,一曰受天子之号令也”(《周礼·职表》),则以“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也”(《白虎通疏证·号》)的人的名位、事功表达,以“名谓尊卑职责之名号”(《国语·周语上》)的伦理诉求,显示了名号的重要性:“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形)名声号矣。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经法·道法》)故而墨子说“名参乎天地”(《墨子·非攻下》),《礼记·礼运》言“号者所以尊神显物也”。诸子各家纷纷论述“正名”、“制名”也就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正名”有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渊源。
由是观照商鞅之“名号”,既然为“圣人”所立,就既要以此区分清楚“君臣上下”的关系,也要惠及普通民众。商鞅正是从民之重“名”入手,在《算地》篇集中论述了名、实关系。“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这里的“名”就是上文所指能给人带来尊贵地位的“尊名”,它可以让民去以死相争的,足见当时民之重“名”程度。对于“利”,商鞅如是解释:“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这些“利”其实就是与民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物,也是可以让民去以死相争之“实”。因此,商鞅总结道:“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这也道明,作为人之常情,民若一味求利,就会摒弃礼法;若一味求名,就会违背常情。因此,过分求利和过分求名,就会使社会出现名、实相离的现象。商鞅对比了今世与上世两种社会,认为“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正是由于这两种社会现象都说明了名、实相离的问题,商鞅才会作出“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的结论。亦即只有把名、利统一起来,既能让人民在生活上衣食无忧,又能让他们在社会上有名分、有地位,人民才会跟从国君,拥戴国君,听命于国君。至于如何将名、利统一并合理分配,应是“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即名、利作为君主的权力之一,必须是要被审察清楚之后才可以将其合理分配给臣民。因此,“审”是统一和合理分配名、利的前提和关键,是真正的统治之术。
(二)“名分”
商鞅“名分”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联,战国时期“土地私有的国民富族正催促着以血族纽带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发生变化”①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1页。,出现了“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开塞》)。这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公权制度以及法律相为联带的关系”②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1页。,因而,在此关系之下,“分定→立禁→立官→立君”就构成了一个前后承接逻辑严密的政治体系。国君管理群臣,群臣执行法令,法令保障之下的土地、货财、男女等“名分”随之得以确立,也就止息了乱和争。
在《定法》篇,商鞅先是以“众人逐兔”的故事说明“定分”的目的是为了“止争”;接着指出了确定“名分”的方法为设置官吏,以吏为师;其意义在于可以使德行不良之人能够自治,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在此基础上,《修权》篇将“名分”法律化,称其为“立法明分”,借此以“公私之分明”。“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法”在这里即相当于“名”。
(三)“审名”与“明分”
如何“审名”和“明分”,《赏刑》篇中商鞅对国君治国的三种方法进行分类,接着逐一对其“审名”和分析:“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
《修权》篇中商鞅对治国的三大要素进行分类,并逐一对其“审名”:“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
此外,在《靳令》篇还有对“六虱”的分类,在《弱民》对“三官生虱六”的分类,等等。
综上,商鞅对“名”、“实”,“名分”以及“审名”和“明分”等逻辑方法的运用,均是作为一种工具,与其“法”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现出实践逻辑之特性。这些逻辑的实践活动,为其后的韩非形成“形名参同”、“参伍之验”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实践逻辑曾被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图尔敏(Stephen Toulnin)称之为“工作逻辑”或“操作逻辑”(working logic)。将这种形象化的表述映射于商鞅之“法”中的形名逻辑思想,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逻辑思想中找到它的历史文化的学理根据,亦即温公颐先生所言:“中国逻辑不纠缠于形式,而注重思维的实质性的研究,所以它可以避免西方或印度逻辑的繁琐之处。……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称之为‘内涵的逻辑’。”③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它对于当代社会“新法家”重申法律的意义与作用,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