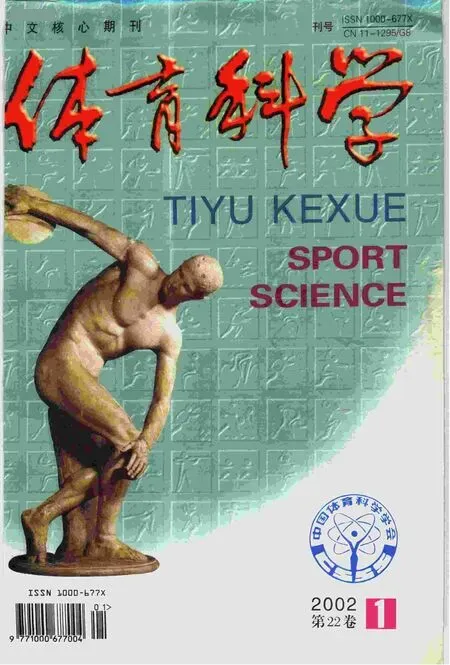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刘媛媛
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刘媛媛
从先秦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基本理论入手,探索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先秦时期,在不同的思想背景和治学传统下,形成了儒家社会化身体观、道家自然化身体观、医家实体化身体观;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各有千秋,共同筑造了中国古代先秦身体观的理论大厦,这三者分别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施加了社会化、自然化、和实体化的影响;诞生在这一片身体观土壤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社会伦理层面、万物自然层面及人体自身生命结构层面对当代体育文化有所补足。
身体观;先秦;古代体育;文化;中国
1 前言
身体是每一个人生而有之的存在,然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无论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身体都曾经历被压抑、被贬低、被蔑视的历史,如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东方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经过文艺复兴的启示、启蒙运动的觉醒及至当代西方哲学的兴起之后,身体才渐渐获得其本不该失去的地位,在学术理论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身体观成为世界学术关注重心的时代,中国思想文化视野中的身体观研究也渐渐浮出水面。有学者针对中国身体观研究曾言:“在多元文化论当令的今日,中国人文研究应深入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之特殊性的议题,并开发其普世意义与价值,以便与西方或其他文化互相参照……‘身体观’研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具有可观的发展潜力。”[20]可以说,中国身体观亦成为当前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和前进路向。
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讨论,首先要对先秦身体观进行说明,简单来说,身体观是指“对身体典型特征外貌与内在特性及本质内容所形具之意识”[17],具体到本文,就是指基本成形于我国先秦时期的人们对身体的基本意识与认知,本文在先秦身体观语境中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即对当代体育文化的意义。
2 概念解析
2.1 先秦身体观语境
先秦身体观是指基本形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人们对身体的基本意识与认知;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是因为先秦时期的身体观几乎奠定了之后全部中国古代身体观的基础①周与沉先生在其《身体:思想与修行》一书中明确表示此点,事实上,中文学界对先秦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原创地位早有共识,如余英时先生“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一文,杨适先生《希腊原创智慧》一书等。,特别是儒、道、医三家,其中以儒家思想为根底的儒家身体观更主宰了中国古代身体观的全部历程,在中国古代世界占据了主流地位。此外,道家身体观和医家身体观作为重要的中国古代身体观分支也在先秦时期形成系统的理论架构和运思路线。“这一时期的身体观虽然或有不详尽之处,然其基本规模已定,其后的身体观无论如何演化,在此处多能找到渊源与端倪”[18],更因为先秦身体观为始创期而未受日后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干涉,其理论形态是纯粹中国化古典化的,原创性非常强①杨适主编的《希腊原创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一书的前言中曾言,所谓“原创文化”,指的是在以往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影响最为重大深远的几种形态由以起源的创造原形,“轴心期文化为人类精神觉醒之第一次突破:为第一次,故为原;为突破,故为创”。,意义尤其重大。
语境本为语言学术语,“内部语境指一定的言语片断和一定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外部语境指存在于言语片断之外的语言的社会环境”[13]。近年来,随着“语境”在诸多学科中的运用其意义不断泛化与深化,指一事物赖以存在的某种社会文化形态(可以具体指环境、背景、氛围等),它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即在这一泛化条件下使用“语境”一词,与身体观结合在一起。先秦身体观语境具体是指由先秦时期的身体观理论体系所构成的一个讨论环境。
2.2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这一部分,需要处理一个理论问题,即中国古代有无体育的问题。
我国古代没有“体育”一词,对国人而言,甚至“体育”概念的引入都是相当晚近才有的事。因此,在“体育”概念引入国门之前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中国古代有无“体育”的讨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体育”一词,但一直存在着丰富的体育现象与体育内容,因为对身体的发现与养护是每个民族天赋的能力,身体活动和娱乐是人类自身的本性,在情绪迸发时便会“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古时代在欢庆丰收时,就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大型活动 ;自先秦伊始,我国古代诞生了许多和政治教化有关的体育项目,譬如射箭、御车等,均属于奴隶社会奴隶主教育子弟的“六艺”;此外,中国古人不断挖掘修养身心的方法,如导引行气、熊经鸟申、五禽戏、天竺按摩法、小劳术、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以及与军事活动紧密相联的一些军事体育项目,如蹴鞠、击鞠等。有学者曾将中国古代体育的内容分为四大类:一是,各种礼仪活动中的体育;二是,养生中的体育(中国古代养生理论与养生实践是中国古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三是,包括各种武术在内的军体项目;四是,各种体育娱乐项目,包括宫廷和民间的丰富多彩的节目活动等[2]。
由以上论述可知,我国古代虽无“体育”一词,但体育现象、体育文化还是存在的,不仅仅存在,而且还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本文在广义的层面上研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将中国古代身体活动与身体现象纳入“体育”研究的问题域内。
2.3 先秦身体观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之关系
本文以“身体观”立论并非一味迎合主流文化热潮,而是基于对身体观与体育文化关系的深刻认知。因为不管身体观研究多么流行,必须和体育发生联系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体育文化的研究视野。
将身体观与体育文化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化,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基本思路: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产生了不同的“身体观”,不同的“身体观”对“身体”提出不同的诉求,而体育作为人类有意识的身体实践活动,对这些身体诉求必然有所反馈,即身体观表达和传递了整个社会对身体的要求,这些要求影响了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体育价值取向又直接影响了体育实践活动,最终呈现出不同的体育文化风貌;在此,“身体观”就好比一座桥梁,沟通了整个社会生活与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上述联系成为本文选择在身体观语境下研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及其现实意义的基本前提。
3 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要研究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首先要对由儒、道、医三家身体观所构成的先秦身体观语境进行分析;其次,则需要分析在不同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质和面貌;最后,则从宏观的视角对先秦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全貌做一小结。
3.1 儒家身体观语境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3.1.1 儒家身体观之要义
1.身体承载了社会道德伦理价值
儒家思想是积极入世的思想,在晚周狼烟四起、分崩离析的混乱世界,儒家先师对人、对世界有着共同的关怀,关怀人生,亦关怀人身,肯定“人者,天地之心也”[6],以坚定的信仰情怀和实际的身体力行为儒家身体观营造了一个爱人生的温暖氛围。
儒家爱人生是没有疑问的,但儒家先师为人生和人身设置了一个“爱”的前提,这个“爱”的前提就是要践履社会对人的期许。孔子感叹“朝闻道,夕死可以”;孟子有“体”之贵贱大小之分;荀子以“有义”为人“最为天下贵”的理由,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提出了对人的社会化要求,只有社会化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完善的人、可爱的人,并最终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这一社会化要求聚焦于人的“身体”,就要求君子仁人能够严格遵守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要求,时时刻刻控制身体与生俱来的感觉与欲望并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在孔子要“戒血气”、重仁义;在孟子要“养浩然之气”,培养发自本心之“四端”;在荀子要“化性起伪”,遵守社会礼仪的规范。因此,儒家身体观的根本要义在于赋予身体以社会道德伦理价值。
2.身体的阶级差等性
如上所述,儒家所推崇的社会道德伦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这一社会秩序是有阶级差等的社会秩序。因此,身体的阶级差等性是从儒家社会化身体观中生发出来的必然结果。儒家社会化身体观的明显特色就是讲求身体的阶级差等性: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各的身体,各有各的规矩;所谓君子小人之分,不仅仅指人格,其身体亦蕴涵着不同的意义与价值;所谓大体与小体的区别,其“体”亦分别为不同的层次;所谓“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於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的圣人众人之分,也鲜明体现于圣人之体与众人之体的不同之中。学者李建民曾言:“礼的身体在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各有容”[7]。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更是儒家身体观看重阶级差等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儒家先圣从不同层面区分了人与人的相异,身体在其中的展现也充满了阶级差等的色彩,在具体的身体实践与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由这种阶级差等而生的规范与限制,这些规范与限制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阶级差等性是“身体”在儒家社会化身体观的又一要义。
3.社会化的身体观
孔、孟、荀等儒家往圣无一例外地对个体的物质性存在即身体进行了社会化的处理。孔子“戒”血气,重仁义,首先为儒家社会化身体观确立了立论基础。孟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培养内在“心性”的发展思路,将身体与人发自于内的良心四端即社会道德伦理紧密联系起来,“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通过“养浩然之气”这一心性充养的过程,人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充满社会道德伦理光辉的身体,从内在道德良知的层面上肯定了社会道德伦理意识与身体存在相关,进一步完成了儒家身体观的社会化建设。荀子则更重制度脉络,采用高标外在礼仪的态度在儒家身体观蓝图的描绘过程中浓墨重彩地为儒家身体观的社会化建设落下重要一笔,从外在礼仪即制度的层面进一步稳固了儒家社会化身体观,三者共同构成了儒家社会化身体观的基本语境。
3.1.2 儒家身体观语境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1.强调体育文化的社会作用,使体育活动呈现出鲜明的伦理色彩
强调体育文化的社会作用是儒家社会化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特色,譬如宫廷射礼、祭祀武舞、古老的“六艺”传授、近世的武艺指点、贵族子弟的射御技能培养、普通民众的蹴鞠、马球、娱乐等,从官方主流到民间市井,凡是处于儒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活动,莫不呈现出鲜明的社会伦理色彩。
2.凸现体育文化的事功价值,导致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夹杂缠绕的附着性
儒家身体观语境下的“身体”负担着促进个体道德养成和强化社会秩序的人的重任,如射礼中“射”与“礼”的结合、如田猎之“观德”、如投壶之“修身、观人”等,由此也导致了中国古代体育难以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身体”的活动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消弭体育文化的竞争意识,促使体育活动形成弱化竞技色彩的发展趋势
以“射不主皮,力不同科”为例,“射不主皮,力不同科”这一说法出自《论语》:“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16]“射”指的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射”,而是指演习礼乐的“射”;皮指古时箭靶用布或兽皮做成,故用皮代指箭靶子。“射不主皮”,即不以射破箭靶子为主,而以射中为主。整句话意思是说,射艺,主要不在于射透箭靶子,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是不同的,这是从古以来的规矩。孔子在这里认为,人为主导射箭比赛的主要是规范即“礼”,而不是射箭的技术。从中可以看出,在以儒家思想为思想主流的中国古代,重视的是仁、义、礼、乐等社会道德伦理而非身体运动本身;倡导的是“身体”之间以礼相待的规范而非突出个体力量的平等竞争对抗精神;追求的是人(君子)在社会秩序中和谐安处而非唯我独尊的超越追求,从而消弭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竞争意识,促使体育活动形成由对抗朝向表演的发展趋势。
3.2 道家身体观语境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3.2.1 道家身体观之要义
1.身体承载了自然的意义
与儒家思想相比,道家思想的显著特色就在于弃绝了儒家所强调的社会道德伦理,主张“道法自然”,不仅老子有“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的感慨,庄子文本中也出现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的说法。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家蔑视的是人为设置的种种违反自然法则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对儒家所推崇的阶级差等的否定(在道家思想中隐含有“人人生来平等”的理念,因此不论美丑、残全,在人格上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摒弃的是儒家所提倡的社会道德伦理,推崇的是“道”的自然而然、无为而为,标榜的是“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3]的自由自在的神人人格。道家身体观也遵循着这样一种反对社会约束崇尚自然大道的原则,道家身体观语境中的“身体”承载了自然的意义,讲求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大化流行。老子驱除一切有可能对身体进行额外添加和刻意为之的干涉与矫饰,致虚守静,复归于“道”;庄子则更进一步,在“忘身”的状态中“爱身”,通过“心斋”和“坐忘”等手段来追求生命的自然而然和自由自在。
2.身体的个体超越性
如果说身体的阶级差等性是从儒家社会化身体观中生发出的必然结果;那么,身体的个体超越性则是从道家自然化身体观中衍生出的必然产物。
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道家自然论反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对人的束缚,由此否定了儒家以阶级差等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追求人法“道”而得来的解放。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体现出了个体超越的特性。“超越”是一个当代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经常用到的词,其意涵丰富,本文取安乐哲在其《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一书中的“超越”意,即“超越的意义:如果B的存在、意义和重要性只有依靠A才能获得充分的说明,然而反之则不然,那么,对于B来说,A是超越的”,“超越的意识表达了富有成效的独立性和自足”[1]。这个超越的定义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即谈“超越”一定是相对于某一参照体系的“超越”。此外,能够被称之为“超越”一定是其自身能够达到圆满自足。在道家思想中,这种“超越”首先就表现在“道”,即“自然”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漠视和对儒家社会秩序的严厉批判中,在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和理想社会秩序的否定中突出“道”,即“自然”的存在、意义和重要性;其次,“道”即“自然”表现出其自身的圆满自足,无须任何其他倚靠。
本文在此所强调的个体超越就是指在摒弃了人的社会性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对个体与自然冥合能力的充分信任。就老子而言,个体超越是指个体通过与“自然”即“道”的冥合而超越了社会制约和社会控制,人的生命,包括人的身体,就在对自然的遵守中而具有了“独立性”和“自足”,这个对“自然”的冥合过程在老子就是靠“致虚守静”的功夫使“体”合于“道”的过程,通过“体”合于“道”实现“没身不殆”,这个“没身不殆”是追求个体生命的长久与永恒。就庄子而言,个体超越不仅是指不受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制约和儒家社会秩序的控制,更是一种逍遥和自由的超越,因为个体超越的意义在于超越社会的评价,即不是为社会或他人活着,强调个体自身的感受,即为自己而活,从而强调了个体行为的逍遥与自由,独自寻求自身内在力量的培养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个体通过“心斋”、“坐忘”[3]等一系列实践操作,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自然自由的逍遥境界,即“同于大通”的境界,以“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的态度将个体生命超拔到一个自然自由的全新高度。
3.自然化的身体观
综上所述,道家先哲从不同程度上都希望人能复归大道,并且在复归大道的过程中实现个体超越。这个“道”就是指万事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复归大道就是顺应“道”的规律,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会给个体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不利的后果。在这一条复归大道的路上,面对身体这样一种人生而有之的存在,老子主张摒弃欲望,要求人“致虚极守静笃”,不使身体受到外物的干扰而有任何妄动与作用;庄子更是忘却身体物质基础的存亡与身体物理结构的美丑,要求人“心斋”、“坐忘”,借此排除社会或生存环境带来的各种烦扰,来消解“物累”,实现“爱身”。复归于“道”的身体得以不受一切外在规范的束缚,复归于“道”的身体就是个体超越的身体,这就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传统中身体活动的个体化倾向埋下伏笔。
道家先哲将身体置放于自然化的场域,老子以“道”开辟了道家自然论的园地,又使出“致虚守静”的功夫,为道家身体观指明了自然化的方向;庄子在“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前提下,采用“心斋”和“坐忘”的办法,使身体更加超越于平凡肉身而处于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逍遥境界,在身体复归于“道”的道路上实现了身体的个体超越性,进一步深入发展了道家自然化身体观,形成了不同于儒家社会化身体观的道家自然化身体观语境。
3.2.2 道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1.强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自然特质,生成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理想境界
在道家思维传统中,“人法道、道法天、天法自然”,万事万物都以复归自然为要旨,人的身体运动也体现出这一自然而然的本质特征。在道家自然化身体观语境下,熏染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天行”的自然特质,并由此生成了体育活动技进乎艺、艺进乎“道”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道家养生活动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2.强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促进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自在自为
道家身体观强调身体的个体超越性,超越于社会规范,超越于外界束缚,因此,强调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促进体育活动的自在自为,如道教修炼、气功、导引等运动方式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可以说,在道家身体观语境下,任何活动都是个体自我的选择,出于个体自适的需要,体育活动也不例外,毋须顾虑儒家身体观语境下对身体设置的层层社会制约和秩序控制,只需倚靠复归自然大道而达到超越与自由。
3.主张体育文化的虚静气质,彰显养生活动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儒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特质之一是弱化竞争色彩,体育运动中的竞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问题的讨论域中,道家身体观则因其对自然大道的追求,促使中国古代体育发展过程中则完全不着竞争的色彩,走上一条趋于虚静的养生之路。
“道家宗旨,清静冲虚而已”[10],道家自然化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重在以虚静养生,要求身体处在一种虚静的状态下去深深体味自然大道神奇的流转运化,在虚静的状态下体会个体的超越,因此才有“《老子》‘静以养性’,《庄子》‘虚以养神’”[21]。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虚静养生的手段方法不在少数,非但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逝,反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构成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趋势的另一大方向,与道家思想乃至各派思想融为一炉,愈积累愈雄厚,形成了以道家为主体的“清虚派”养生观,延续至今很多以“虚静”为要旨的养生锻炼方法多得其精髓。
3.3 医家身体观语境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3.3.1 医家身体观之要义
在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治学传统中,医家思想多被视为仅牵涉技术层面的知识系统,“《汉书·艺文志》曾将‘诸子’与‘百家’作基本的区别,以为前者才是学术思想的探讨,后者仅流于方技之书”[4],医家就属于“百家”之列,因此,人们往往忽视其中所蕴涵的丰富思想资源,对身体观的讨论亦不例外。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如果说儒家身体观附着了浓厚的社会化色彩,道家身体观沾染了飘逸的自然化气质,那唯有医家,是最关注人的身体本身的。“医家的态度显然更为‘切身’……医家关切人身体结构、运营、健康诸方面,对形躯之身的态度确较儒、道二家更加现实、也更为积极主动。”[20]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医家身体观补足了儒、道两家身体观的不足与偏漏,是先秦身体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就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而论,医家身体观不仅仅是补漏,更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建构的主要理论基础。
本文将医家身体观命名为实体化身体观。实体概念出自于洛克《人类理解论》。洛克说:“我们所有的各种实体观念,只是一些简单观念的集合体……同时,我们还假设有一种东西是这些观念所依属所寄托的。”[8]洛克的实体观念首先强调了对象的物质属性,因为这些“简单观念”是有“所依属所寄托”的,是由可感物质所形成的,它们通常指向的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可见的有形实体;其次,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了“实体”的基础作用,他所指明的实体的含义更主要是人们设想出来的本质性的存在。在这里,实体这一观念最接近医家身体观的言说视角,首先从人的生命结构即物质属性方面认识人的身体即将身体视为实体性存在,同时强调,这一实体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和本质,即将身体本身视为认识、研究的对象,而不只是作为认识的起点。
医家前贤在面对人的生命的时候,通过实践与思维两方面资源的艰苦积累,对身体的意识与认知更富有理性精神,突出将人的身体本身作为认识对象,走出了一条实体化的身体观道路。相较之于儒、道二家,医家从人体生命结构入手看待身体,从发生论上肯定了人的物质基础,将人的躯体看做天地化生的宝贵存在而倍感珍惜;从阴阳互动的角度解析生命的动力;提倡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建构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人体生命组织结构模式,采用形神兼顾的养生策略,构成了先秦身体观中的实体化身体观。医家实体化身体观不仅从生理层面上肯定了身体的重要价值,而且更具有生命关怀的终极意义,为后世对人的认识奠定了比较科学的基础,为人类寻求更美好、更健康的人生探索了一条源远流长的道路,与儒家社会化身体观、道家自然化身体观相比,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中国先秦古人对身体的意识与认知,是先秦身体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3.3.2 医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医家实体化身体观以最贴近“形躯之身”的态度,以对人有限生命的关怀为目标,对身体有着明确的意识与认知,采取多种手段维护人的身体健康,追求延年益寿。医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特质突出表现为:
1.强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健身价值,形成了众多用以健身强身的体育活动形式
《吕氏春秋·尽数》篇提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9]的以“动”养生,精、气、神兼养的路数,颇具健身价值。唐人养生延续医家辩证之身体意识,以天地阴阳万变比附人身,认识到“及其失也”的人生脆弱,但更有“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身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12]的坚定自信。孙思邈以医家胸怀著《千金方》,涵括诸多具体方便的养生实践手段,如“正东坐,收手抱心,一人于前据蹑其两膝,一人后捧其头,徐牵,令偃卧,头到地,三起三卧,久久效。两手相捉扭捩,如洗手法。……大坐伸两脚用当相手勾所伸脚着膝中以手按之,左右同。上十八势,但是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11]。蒲虔贯《保生要录》虽为道教著作,但其中对人身保养的认识亦怀踏实的医家态度认识人的形神身心。一言以蔽之,从先秦至清末,在医家实体化身体观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领域始终有这样一片用以承载人“永赐难老”美好愿望的园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2.凸显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整体性,构建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生理理论基础
在医家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表现出整体性的特征。所谓整体性,即将人体视为一个由脏腑、经络、精、气、神等元素构成的整体,人的健康是脏腑的完善,经络的畅通,精、气、神的统一自足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从当代生理解剖角度出发将人体视为分裂的细胞、肌肉、骨胳、器官等组成部分。并由此构建出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独有的生理理论基础,不仅今天我们所称之为的医疗体育如此,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诸多方面,如中华武术、中华养生等都以医家人体生命认知为基础,讲求人的形神兼备,身心统一,武术文化中一些拳派拳种特别讲求练功先练气,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养生文化更是以医家人体生命认知为底色描绘人体保健画卷,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3.4 小结
综上所述,儒家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认识人的身体,从社会价值层面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历程进行了社会化的干预;道家从万物自然的角度来认识人的身体,从个体行为层面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历程进行了自然化的干预;医家从人体生命结构自身的角度来认识人的身体,从身体运动规律层面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历程进行了实体化的干预。有必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三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侧重于不同层面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施加了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诞生的丰厚土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培育和滋养着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施加影响,诠释着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4 现实关怀与时代意识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以日新月异之势飞速发展,但始终不变的是每一次的进步都必须参照前人的轨迹,或者会继承,或者会突破,但总有对人类诞生初民时代的遥遥回望。因此,任何一种以古代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其关注目光绝不应该就古论古,而是加入时间的坐标,将古代世界的路径延续至今,从中总结归纳出于今人有益之物情事理,方可赋予此研究以现实关怀与时代意识。
4.1 儒家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伦理层面而言,儒家社会化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强调社会道德伦理价值在体育文化中的控制作用,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民胞物与”式的和谐与平衡状态。孔子对《诗》“思无邪”,对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及对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16]的要求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的赞叹,诸如此类莫不强调了为时人所渴盼仰慕的社会道德伦理理想。
以最具普适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随着时代更迭、社会变迁,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伦理理想虽然会有不同的标准,甚或后世都会反抗批驳前代的社会道德伦理理想,但在得以掌握社会权利后一定会发扬符合当时时代发展规律的社会道德伦理理想。因为无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社会而言,政府所提倡、民众所遵循的社会道德伦理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毕竟“每一个社会都会面对一个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19]。在这个前提下,儒家思想传统所孕育的社会化身体观语境及儒家社会化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毋庸置疑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即便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可以说,儒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以社会价值为旨归,重道德、崇事功,是实现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理想的重要手段,而当这些社会道德伦理理想由对人进行被动控制转化为人的主动遵守,当规范内化为人对自身自觉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体育文化内部的规范与调整。当今时代,面对当代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中各种行为失范现象,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追问未必不能够成为走出这些价值混乱困境的良途。
4.2 道家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与国人延续至今的儒家积极入世的主流路线相比,道家文化可以成为今人身处嘈杂繁华的现代世界时进行人生选择、生命体悟的另类路径,体育文化亦包括其中。
从万物自然层面而言,道家自然化身体观以其对自然大道的追求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沐浴在一片大道普施、周流万物的自然自由之境。老子开创了遵循大“道”的道家自然论道路,强调寡情少欲,以对人生理欲望的摒弃来实现人与自然大道的相通;庄子以更逍遥的态度有意识、有方法地摆脱身体生理局限,在对“身”的忘却中折射出一种迷人的“神”的光彩。道家旨意“致虚极,守静笃”从而“没身不殆”;齐生死、一万物,“心斋”、“坐忘”,从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最终将个体带入一种无限无际的自然自由境界之中。
道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以复归自然大道为鹄的,弃人为、法自然,讲究个体超越,譬如道家养生活动,习者莫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道骨仙风的风度姿态,仿佛神人下凡,为个体有限的肉体生命找到值得珍惜的永恒理由;即便不是纯粹的养生活动,在其他身体运动中,道家仍然于其中寄予了“技进乎艺,艺进乎道”的大道理想。可以说,道家自然化身体观和在此身体观语境中诞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正是在“道”的高度与层次上令当今时代体育文化得以窥见那一片自由自然的陶潜桃园。道家身体观要求在有限的肉体生命中见出无限的自然大道,从这一理想出发,自然要求避免在运动过程中的功利性,相对于当今时代体育主流文化注重以运动效率额和运动技能至上的功利性追求而言未必不是一种超越。
4.3 医家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虽然以医家态度着眼,没有直接从中诞生出系统的体育文化模式,但这种观点直接促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普遍重视身心双修,灵肉共赢。
医家实体化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以健康长寿为导向,形神统一、身心双修,特重规律、针对性强。由是,它反映的是重视身体物理能量的挖掘与释放,最终追求不断超越生理极限的当代竞技体育文化传统;尊崇的是物我和顺、身心和谐、形神统一、性命双修的注重身心循环中内在潜力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精髓。从这两个层面而言,先秦医家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当今时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5 结语
“人类的普遍关怀是自身生存状态”[14],这种关怀历久弥新、亘古不变,而体育是人类重要的身体实践活动之一,对体育文化进行研究是这一关怀的生动体现。
大而观之,对体育文化的研究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视,小而视之,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对体育自身的进步发展也颇具意义。历来学人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做过很多探索,较之以往学术成果,作者选择在先秦身体观语境下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从先秦儒、道、医三家身体观入手,审视不同身体观语境下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
从现实关怀和时代意识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儒家从社会道德层面入手所形成的身体观,还是道家追求自然大道所形成的身体观,甚或医家切实关注身体自身所形成的身体观,古人这些明确针对人的身体而生发的意识与认知是影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元素,诞生在这一片身体观土壤中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当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和可借鉴的价值。
[1]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19.
[2]毕世明.中国古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4.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117.
[4]蔡璧名.身体与自然——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心论古代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M].台湾: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95:2.
[5]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3.
[6]李学勤.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98.
[7]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000:160.
[8]洛克.人类理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廖名春,陈兴安.吕氏春秋全译[M].成都:巴蜀书社,2004:386.
[10]体育史论文集[C].中国体育史学会,1985:64.
[11]体育研究资料4[M].成都:成都体育学院科学研究所,1962:113.
[12]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3]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谢松林,庞朴.阴阳五行与中医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179.
[1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4.
[1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9,61.
[17]杨荣丰.先秦儒家践礼之身体观[D].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
[18]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
[19]游任滨.离散的想象:生命科技论述中的身体展演[A].文化研究学会2003年会论文集[C].2004:9.
[20]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
[21]郑杰文.中国古代养生观说略[J].文史哲,1992,(2):19.
Study on the Sport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Body-thinking in the Pre-Qin Period
LIU Yuan-yuan
This paper,starting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Confucius,Taoism,and doctors materialized view of body in the pre-Qin Period,makes the research on sport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During the period of pre-Qin,under the different ideologic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tradition,the formation of Confucian social view of body,Taoist natural body view,doctors materialized view of body is made.The three body view of Confucianism,Tao,medicine each has its own merits,and commonly builds theory building of body-thinking in ancient China in pre-Qin period.The three exerts the social,natural and physical effects respectively on China ancient sport culture.Born in this piece of body view soils in China ancient sports culture in social ethics,all natural level and the body's own life structure level have certain supplement to modern sport culture.
thebody-thinking;pre-Qinperiod;ancientsport;culture;China
G80-05
A
1000-677X(2012)01-0081-07
2011-11-23;
2011-12-27
广州体育学院院管科研项目(QN1106)。
刘媛媛(1980-),女,新疆乌鲁木齐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研究,E-mail:jijing3710@163.com。
广州体育学院,广东广州510500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Guangzhou 510500,China.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