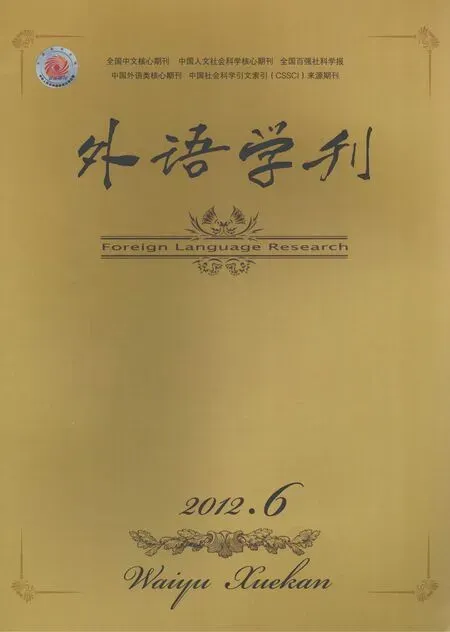“图像论”意义观的本体论解读*
——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拓展性研究之一
谢 萌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1 引言
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本文把他的前期思想“图像论”意义观作为研究对象。简单讲,前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作为意义生成机制。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图像”来显现。图像就是对思想的摹画。思想能动地反映世界和语言,它以形成图像的方式沟通命题与实在。这样,“图像论”意义观的内核就是以语言工具论为基础的意义指称论;命题在逻辑形式与指称内容上同实在是否相符就是判定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然而,命题的逻辑分析导致指称失效,这使“图像论”意义观陷入困境。可见,虽然“思想”这一特殊存在的引入使指称关系得以确立,但是工具论语言观对存在的实体性要求、意义指称论所携带的本体论承诺无法完全阐释意义的生成。由此,对“图像论”意义观的批判性研究不应该只在分析哲学内部进行,深入剖析这一理论须要进入本体论层面。
“本体论(存在论)就是研究在者(сущее)存在(бытие)的学说。”(李洪儒 2006:32)本体论语言哲学把语言视为本体(而非工具),通过研究这一本体的“在”与“是”将语言与人紧密结合,从而揭示语言的本质,探索人及人的世界(李洪儒2011)。这种语言本体观提供了考察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不同思路,即本体论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与意义本体观的研究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分析性语言哲学与本体论语言哲学存在相互融合的内在要求;“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分析和解释,而非两者中的任何一种”(李洪儒2011:4)。作为语言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分析”必然携带本体论承诺——可分析之物必然存在,分析终点必须是存在之物。从存在到分析、由分析述及存在,是一切知识得出的必然顺序,顾此失彼无法达到认识目的。因此,本体论诠释作为一种综合统一的思辨性研究方式,同分析一并作为语言哲学的两种研究工具。进一步讲,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分析”就意味着“定义”(江怡2009)。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分析的依据和方式就是下定义(维特根斯坦2003b)。下定义就是概念分析的过程,而“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合题。概念是思辨者的存在,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是思辨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存在和本质”(黑格尔1980:231)。可见,分析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前者以后者为目的。由此,本文将分析与解释相结合,并且以后者为基础,通过概念思辨方式考察“图像论”意义观的分析性研究。
在研究维度上,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对意义(语言的意义/人的意义)的研究须要将意义本身视为特殊“在者/是者”。本体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人的存在之所,语言的意义就是人的意义。海德格尔等语言哲学家把作为此在的“我”的意义视为哲学追问的本体;这种意义指一切存在的意义,尤其指语言的意义/人的意义。(海德格尔1987)进一步讲,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方式就好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认识语言,就要将语言视为本体,从语言本身出发,研究它“如何在、如何是”(李洪儒2011:)。意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能够不依赖语言的表达而存在于人的世界中,并且语言本身就是意义系统。我们既可以问“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也可以问“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并且后一个问题较前一个问题显然具有一种更为原初的意义。意义的自足性与复杂性决定,要研究意义,也要将它视为特殊“在者/是者”,进而通过追问这一“在者/是者”在语言和世界中“如何在/如何是”来达到认识目的。
当然,本文以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为研究对象,并非意在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贴上本体论的标签,而是力求通过引入本体论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把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纳入本体论语言哲学之中”(李洪儒2011:3),充分吸收分析哲学的合理因素并强调语言哲学的思辨本质。这样,本文把“图像论”意义观置于本体论语言哲学框架中,通过意义本体观的研究维度、分析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追问“图像论”意义观的理论优势与局限,反思这一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
2 “图像论”中的世界和语言
“图像论”分析、构造世界和语言的理论基础是逻辑原子主义。这一理论的诞生背景可追溯至古代本体论“从无到有”的创世观以及德谟克利特关于世界本原的“原子论”。逻辑原子主义是其创始人罗素“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抽象本体论的直接后果”(江怡 2009:90)。维特根斯坦继承罗素的这一思想;“图像论”的主旨就是通过逻辑分析揭示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进而澄清语言的意义。
2.1 世界
以逻辑原子主义为本体观,早期分析哲学把“分析”理解为“分解”;并且,以现代逻辑为依托,逻辑原子主义者认为“逻辑”就是构造世界的依据和框架。由此,维特根斯坦在“图像论”中把世界“分解”为“事实”、“事态”、“原子事实”、“简单对象”等各种逻辑成分。
具体讲,世界由事实构成;事实是诸事态的存在,事态是构成事实的基本单位。事态的存在就是肯定的事实,事态的不存在就是否定的事实。肯定的事实与否定的事实一起构成实在。这里的“实在”指涉逻辑中的可能世界,因此肯定的事实只构成可能世界的一部分,即现实世界。事态可进一步分析为基本事态,基本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构成基本事实,也叫原子事实,它们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逻辑原子,是思想能够描述的最小逻辑单位。然而,基本事实或事态并不是构成世界的实体,它们只是容纳这些实体的形式,真正的实体是维特根斯坦设定的逻辑分析的终点——“简单对象”(simple object)。它们是逻辑中的基本构成单元。对象与事态的关系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诸对象的结合(Verbindung)或配置(Konfiguration)”(韩林合2007:45)构成基本事态;事态是对象的存在形式;事态的存在与不存在构成事实;事实的总和就是世界。
在构成世界的各种逻辑成分中,对意义的生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原子事实和简单对象:简单对象是构成原子事实的实体,原子事实是思想描述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能够承载意义的最小单位。这样,简单对象就是构成意义的实体支撑。然而,随着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原子主义思想的进一步认识,他发现,“空间对象的复杂性是一种逻辑的复杂性,因为说一个事物是另一个事物的部分,永远是一个重言式”(维特根斯坦2003a:138)。可被分析的事物都是空间对象;空间的无限可分性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这样,空间对象的复杂性就等同于逻辑的复杂性:从逻辑上讲,一事物永远是另一事物的组成部分。由此,对象的简单性受到逻辑的质疑。其实,维特根斯坦认识到的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本体论语言哲学的研究方式得到更加确切地说明:所谓“简单”与“复杂”,都是针对不同标准或要求而言的,也就是说任何简单对象的存在都是相对的。从认识论角度讲,我们无法知道怎样才算是“简单的”。因此,“图像论”中的简单对象作为一种逻辑设定,无法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注定是不完善的。
简单对象的逻辑设定无法给予存在实体支撑,因此维特根斯坦把对存在的追问诉诸于人和语言。这样,“人”因素以形而上主体的方式被引入世界中:“5.62……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我所唯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就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5.621世界和人生是一回事”(Wittgenstein 1955:26)。我能够使用的语言为我所存在的世界划定界限;语言使我的世界成为我的人生。可见,脱离主体谈论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毫无意义——意义不是在“世界”中,而是在“人的世界”中。
2.2 语言
分析性语言哲学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就是把对存在的实体性研究转变为表达性研究;语言被当成认识工具。在“图像论”意义观中,语言被分析为分别与“事实/分子事实”、“原子事实”和“简单对象”相对应的“命题/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和“名称”。这些逻辑成分的设定就是构造命题的真值函项理论,进而得出命题意义的前提和基础。
在语言的各种逻辑成分中,通过描述原子事实直接触及实在的“原子命题”起到断言事态存在与否的关键作用。“分子命题不包含超出其原子所包含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它们并不在其原子所包含的知识之上增添任何实质性的知识”……“如果我们把一切可能的原子命题都做出来。如果我们能确定每个原子命题的真假,那么世界就会被完全地摹状”(维特根斯坦 2003a:12,19)。可以说,简单对象保障意义在世界中的存在,原子命题保障意义在语言中的存在。在“图像论”中,命题的意义通过真值函项理论生成并确定。真值函项理论成立的先决条件就是原子命题具有相互独立性,即一个原子命题的真值不依赖另一个原子命题就能被判定,从而通过对原子命题真值的逻辑运算就得出了分子命题的意义。然而,“原子命题”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图像论”意义观所使用的“原子事实”、“原子命题”、“命题极性”等概念是将物理学概念“移植”到哲学的产物。“原子、分子这些词本来是指物的,不是指事的,而事实却是事,不是物。”(陈嘉映3003:133)“可被喻为‘原子’或‘分子’的事物存在于事实中”的说法尚且合理,可是“事实”是复合概念,用“原子”作为“事实”的属性显然犯了混淆概念范畴的错误。命题是对事实的描述和建构,既然如“原子”般相互独立的事实并不存在,那么也不存在如“原子”般相互独立的命题。这样,通过概念分析和解释,“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的存在就被否定了。
其实,分析性语言哲学对意义的研究是有先天缺陷的:通过分析具有实体属性的“世界”和“语言”两大本体来追问意义是本末倒置,因为“意义”并非实体性存在,逻辑分析的结果必然会与实在产生龃龉,从而使意义失去本体论支撑,最终导致形式约束内容的教条。因此,对意义的研究须要从“意义”本身出发,通过意义本体观的研究维度揭示意义的存在方式,从而达到认识目的。此外,以语言工具论为背景,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的分析缺失主观因素作为通达经验世界的“灵媒”。本体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人创造语言,语言成为人的第二现实”(李洪儒2006:29)。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本人也认为“语言是我们机体的一部分,而且像我们的机体一样复杂”(维特根斯坦2003a:116)。这在强调语言与人血肉交融的同时告诉我们,对人而言,语言这一特殊本体具有“内在”属性。对意义的考察离不开语言,更离不开人。意义不是在“语言”中,而是在“人的语言”中。
3 意义——在语言与世界之间
既然意义存在于“人的语言”和“人的世界”中,那么对意义的研究自然要追问二者的“内在联系”——人。在逻辑原子主义思想和语言工具论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独创之处就是将“思想”或“逻辑图像”作为沟通语言和世界的途径。虽然这仍未跳出逻辑先验性的窠臼——“思想”只是“逻辑”的反映,但是“思想”作为主观因素的引入成功地帮助“图像论”从对世界的逻辑分析过渡到对语言的逻辑分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研究极少关注“图像论”中这一关键环节带给我们的反思和启示。
3.1 意义的产生
学界普遍认为“图像论”只讨论了一种“意义”,即产生于世界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生成方式遵循从世界到语言的顺序;它是依赖客观实在的、被语言所“反映”的意义。其实,如果进一步追问这种意义产生的根源,即思想,就会引出“图像论”提到的另一种“意义”,即语言所“显示”的意义;它产生于语言本身并依赖人的思想。
产生于世界的意义就是语言所“反映”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用“图像”喻指意义的生成方式,意义就是图像对世界的摹画;它是由图像显示出的“映射关系”——一种逻辑上的配置。前期维特根斯坦强调逻辑的先验性;他认为逻辑是构成世界的秩序,人的思想就是这种秩序的反映。因此,在“图像论”中,逻辑作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图像必然是逻辑图像;世界以图像的形式映入思想,思想以图像的形式被语言表达。“‘一个事态是可思的’(可想象的)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做出一幅关于它的图像”(Wittgenstein 1961:32);“3.01真的思想的总体就是一幅世界的图像”(Wittgenstein 1955:15)。这样,意义的生成方式可概括为:只要是可能世界中的事态(存在与不存在的事态)就是符合逻辑的,只要是符合逻辑的就是可思的,只要是可思的就可形成图像,只要是图像就可由语言表达。从而,“4.2命题的意义是它与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符合和不符合”(Wittgenstein 1955:19)。可以说,这种依赖客观实在的意义就是理想语言的意义,它体现为命题与实在之间的逻辑关系。
产生于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所“显示”的意义;它是与理想语言的意义相对应的日常语言的意义。并且,将逻辑分析引入日常语言是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独创之处(江怡2009:105)。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在意义的生成方式上刚好相反:在日常语言中,对意义的生成起到决定作用的不是逻辑,而是人的思想。“3.02思想包含它所思想的情况的可能性。可以思想的东西也就是可能的东西”(Wittgenstein 1955:15)。这就决定,日常语言的意义是“人的世界”和“人的语言”的意义。这种意义具有主体间性/社会属性,对它的考察需要追问语言的理解与表达,即语言的应用。“4.002人有能力构造语言,可以用它表达任何意义,而无须想到每一个词怎样具有指谓和指谓的是什么。——就像人们说话时无须知道每个声音是怎样发生的一样……人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懂得语言逻辑……语言掩饰着思想……理解日常语言所要依赖的种种默契是极其复杂的。”(维特根斯坦2003a:203)其实,这种“默契”对于理想语言的逻辑分析同样必要,因为命题本身就提供了分析语词(记号)的语境;从而“3.262记号不能表达的东西,其应用显示之。记号隐略了的东西,其应用清楚地说出之”(维特根斯坦2003a:198)。从本体论语言哲学角度讲,产生于语言的意义可将产生于世界的意义包含于其中,因为语言所“反映”的意义,即逻辑上的配置关系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从而“思想当然也是命题的一种逻辑图像”(Wittgenstein 1961:57);思想也是一种语言,“思维和言说是同一个东西”(同上);并且,我们知道思想是人的理性存在;这就得出了语言本体观的重要思想——语言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3.2 意义的确定
“图像论”意义观的内核是指称论,意义的确定性是指称论的内在要求。由此,“图像论”中理想语言的意义与日常语言的意义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前者的意义由逻辑来确定,后者的意义由语言本身或者“人”来确定。理想语言的意义由逻辑运算生成,运算规则意味着逻辑决定意义;日常语言中的逻辑不是运算规则而是逻辑概念,应用这些概念的前提是人规定了它们的意义。
对于理想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在于思想的逻辑本性。逻辑是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构造语言的方式;思想由语言表达,逻辑就是语法。语言具有意义或者逻辑真值的内在要求就是“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形式逻辑是命题的某种‘内在(internal)’属性”(Forster 2004:108)。这样,“具有意义意即是真的或假的,为真为假实际上构成了命题与实在的关系,我们说命题具有意义(Sinn),即指此而言”(维特根斯坦2003a:36)。“图像论”对命题意义的“确定”须要以逻辑为手段。简单对象的逻辑设定将命题与实在相联系,力求从外在世界确定命题意义。从语言本身来看,真值函项理论将命题看成原子命题的逻辑构架,命题意义借助真值运算得以确定。“……很明显,我们感到并使用语言的语词,把它们作为在逻辑上相互等值的单位。”(维特根斯坦2003a:108)由此,命题的真值通过“在逻辑上相互等值”的原子命题,即命题变项的真值运算得出。每个命题都是对原子命题作真值运算的结果。进而,“5.2341 P的真值函项的意义是P的意义的真值函项”(Wittgenstein 1955:23)。可见,在理想语言中,意义是可参与真值运算并由真值运算得出的逻辑实体;逻辑作为运算规则决定意义。
融入日常语言的逻辑不再是运算规则,而是日常应用中的逻辑概念(真、假、肯定、否定等)。“我们可能谈论这类和那类的函项,而并未想到其一定的应用。因为在我们使用Fx和所有其他形式变项指号时,并没有任何例子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用变项来摹绘事物、关系、特性,并从而指出,我们并非从我们所遇到的某种情况引出这些观念,而是以某种方式先天地具有它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能否正当地将逻辑(例如像《数学原理》中那样的逻辑)直接用之于普通的命题?”(维特根斯坦2003a:142-143)维特根斯坦发现,在日常语言中,作为一般概念的逻辑无法发挥其特殊功能,因为“我们不可忽视我们命题中用语尾、前缀、元音变化等等,等等,所表达的东西”(维特根斯坦2003a:143)。由此,“实际上,困难在于,即使我们想要表达一个完全确定的意义,也有可能未达到目的。因此,似乎可以说,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命题确实是实在的图像”(维特根斯坦2003a:145)。逻辑无法使日常语言的意义达到完全清晰,这是因为日常语言是应用中的语言,而“应用”这一概念必然离不开“人”的参与。日常语言的丰富性与模糊性就在于人对语言的诸多规定,逻辑概念的应用规则也只是包含在这诸多规定中。因此,日常语言的意义只能由语言本身或者“人”来确定。这样,“如果命题‘这本书放在桌子上’具有一种明白的意义,那么不论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能够说出这个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维特根斯坦2003a:145)。可见,日常语言中的逻辑不再是意义的决定性因素,意义才是得出命题真值的必要前提。意义既是语言的意义,又是语言和实在之间的真正联系。语言因意义而存在,意义就是语言的存在方式。
3.3 意义的反思
“图像论”意义观考察了两种“意义”,即逻辑语言所“反映”的意义与日常语言所“显示”的意义。对于两种意义的产生与确定,逻辑扮演不同角色(理想语言的逻辑规则、日常语言的逻辑概念),而思想始终是沟通语言和世界的纽带。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产物,所以被语言所“反映”或“显示”的意义归根结蒂产生于人的思想。思想是比语言更为广阔的领域,思想的内容比语言的内容更加丰富。意义作为特殊“在者/是者”承载思想的全部内容,表征人的理性存在。
“命题的逻辑是‘思想的法则’,因为它们给出了人类思想的本质——或者更准确地讲,因为它们道出或显示了人的思维方式,它们表明了思想是什么。”(Wittgenstein 1978:133)表面看来,逻辑在“图像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揭示思想并规定命题;然而,实际上,“命题的逻辑”必然是语言的成分,而语言就是思想的产物。语言因其是思想的产物而成为实在的逻辑建构;“逻辑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意义”的生成与表达。意义作为语言的存在方式远比逻辑形式复杂得多,这正是由思想/人和语言的复杂性造成的。“我们的语言的约定是异常复杂的。在每个命题中都有很多要思而未说的东西”……“因而对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命题‘表放在桌子上’的意义较之这个命题本身更复杂,也是很明显的。”(维特根斯坦2003a:148)思想/人和语言的复杂性决定,对意义的研究须要更加开阔的视野与更为宽广的思路。因此,研究语言和意义须要把“思想/人”(而非逻辑)作为出发点。弗雷格曾明确提出哲学应该在研究数理逻辑的基础上揭示思想;他在《论意义和意谓》中把命题意义当成思想,由此确立了“思想”在语言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江怡2009)。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进一步揭示了思想在语言中的表达。他甚至把思想中的意向内容引入关于意义的讨论,进而得出“事物只有通过其与我的意志的关系才获得‘意义’”(维特根斯坦2003a:171)。可见,以逻辑为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的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和意义的研究同样把“思想/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显然与本体论语言哲学的相关思想“不谋而合”。
本体论语言哲学是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主流。它从整体出发,以宏观的研究视角“将语言视为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成人思想的组成部分”(李洪儒2011:3)。语言本体论对意义的本体性研究与人紧密结合。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语言哲学家认为,哲学就是人对自我的存在的追问,语言哲学对意义的追问就是对人的存在的追问。这样,“意义”成为哲学追问的本体,“人的意义”就是主要研究对象。(海德格尔 1987,Gadamer 1975)本体论语言哲学通过研究语言探索人及人的世界最终是为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人与意义共生、共存;意义因人而存在,人因意义而生存。追寻意义是人生头等大事,从生到死就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寻求意义就是安顿人生,寻找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本。可见,人的存在就是对意义的诉求,意义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其实,“人/思想”和“意义”的重要地位同样体现在语言哲学的“近亲”——语言学中。关于语言的存在方式,语言学通常认为,语言在现实中以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为表现形式;语言本身作为意义系统具有内在属性,它以形成意义的方式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语言必然是以音响和文字作为表现形式的有意义的结构系统,无意义的符号和声音不是语言。(Saussure 2001)可见,意义就是语言的存在方式;语言的运作,即语言的外化与内化/编码与解码就是意义的生成与传递;人/思想就是主导语言运作的动因。因而,“言说”不但实现了语言的目的,而且实现了人的目的。这一思想在言语行为理论中得到了深刻和细致的阐释。“我们说出的每个句子都具有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的双重作用”……“要确定是什么样的以言行事的行为在起作用,我们就必须确定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在使用这种说话方式。”(Austin 1962:98)表义的目的是为了行事;意义包含并取决于人的目的/意向,以言行事就是通过语言的意义来实现人的意义。这一思想被塞尔进一步引入心灵哲学研究。可见,在语言学中,意义同样是语言和人的所在与所是。由此,为了更好地揭示意义这一“在者/是者”,须要进行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整合性研究。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意义本体观的研究维度、分析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把“图像论”意义观置于本体论语言哲学框架中;从本体论层面剖析这一理论的优势与局限。具体研究表明:
第一,“图像论”意义观对语言和世界的分析性研究以语言工具论为导向;脱离主观因素的逻辑分析的产物失去本体论支撑,意义无法通达经验世界。这就说明,通过语言认识世界须要主观因素作为媒介,因为“语言”是“意义系统”、“思想产物”、“心理实体”的同义表达式,是具有“内在”属性的“特殊本体”。由此,意义只在“人的世界”和“人的语言”中,对意义的研究须要把握意义产生的根源,即“思想/人”。这就要求,对“图像论”意义观的深入考察要关注逻辑语言的意义,更要关注日常语言的意义;因为对于后者,语言较逻辑具有更加基础的地位,人较语言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语言的意义决定逻辑,思想/人决定意义。可见,语言工具论无法深入语言内部实现对意义的综观,进一步洞悉意义的本质须要从本体论层面入手。
第二,本体论语言哲学和分析性语言哲学在研究方式上的融合能够引导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向纵深发展。将意义本体观的研究维度、分析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引入对分析性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考察可以更加有效地揭示意义的本质——对意义的追问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解释被引入人及人的世界。研究表明,在人的语言中,意义是语言的存在方式;对于语言这一特殊“在者/是者”,意义是“在者之所在/是者之所是”。在人的世界中,意义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生”与“存”就是意义的“在”与“是”。这样,意义既是语言的存在方式,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意义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使人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即语言人——语言和人唯有彼此融合才能实现意义。由此,在对意义的诉求中,“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李洪儒2007:11)。对意义的进一步研究须要揭示语言对人的表达/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即语言的主观意义——说话人意义 (李洪儒2010:27)。
第三,本文“拓展性研究”力求通过意义理论这一切入维度,把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纳入本体论语言哲学之中,从而促进整体性语言哲学发展。在此基础上,“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突破学科界限、实现整合,是另一种趋势。进一步讲,就是将通过对语言单位及其关系的分析来揭示语言本质的语言学与通过语言(包括其单位和单位间关系)分析、阐释来揭示语言外人及其世界的语言哲学结合起来”(李洪儒2006:29)。质言之,对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语言是共同的研究对象,人是共同的研究目的,意义(人/语言的存在方式)——语言的意义、人的意义、说话人意义就是共同的研究内容。由此,揭示语言的意义/语言的存在、人的意义/人的存在、说话人意义/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就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共同旨归。
通过学科整合,实现语言哲学研究的“开拓和创新”(李洪儒2011),是大势所趋。因此,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拓展性研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
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江 怡.分析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李洪儒.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二[J].外语学刊,2006(2).
李洪儒.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J].外语学刊,2007(4).
李洪儒.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J].外语学刊,2010(6).
李洪儒.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J].外语学刊,2011(6).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一卷逻辑哲学论以及其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a.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M].第二卷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1929-1931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b.
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Forster,M.N.Wittgenstein on the Arbitrariness of Grammar[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1975.
Saussure,F.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Wittgenstein,L.Notebooks,1914-1916[M].New York:Harper& Row Publishers,1961.
Wittgenstein,L.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 Ltd,1955.
Wittgenstein,L.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M],tr.G.E.M.Anscombe.Oxford:Basil Blackwell,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