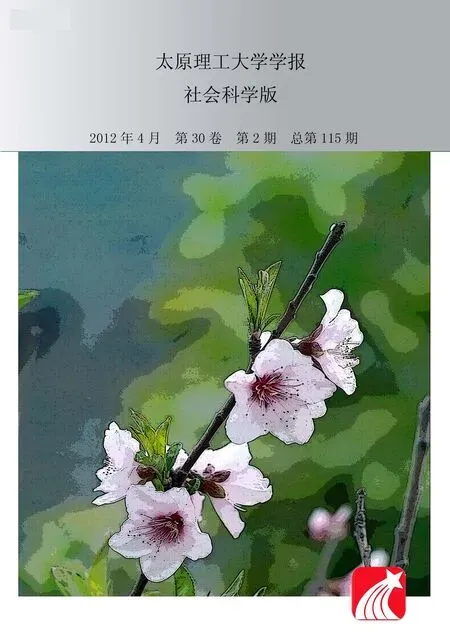平民的千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生悲剧与精神悲剧*1
胡 伟
(1.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1]1采用两段式结构,以“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分别讲述了吴摩西(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两代的经历。这部小说承袭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作者白描叙事的功夫达到上乘。小说中的社群、家庭和人物,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有关。小说叙述结构完整,内容翔实,严谨生动,文笔稳健。从吴摩西到牛爱国祖孙两代的寻找,不只是形成了一个轮回,更预示了中国平民的千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读后让人有悲凉的感觉,其更像一部乡村平民心灵的精神史。
一、平民人生的悲剧
《一句顶一万句》的线索是写跨越70年的两次寻找——“姥爷”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各自都曾寻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及其奸夫以报仇,一个出延津,一个回延津,但那只是一种“假找”,他们要找的是能跟自己说话的人。小说揭示了平民人生的悲剧。
(一)物是人非的悲剧
当曹青娥挺着肚子,到镇上拖拉机站找侯宝山的时候,拖拉机站和院子房屋的样式,一点没变。但侯宝山变了,侯宝山在拖拉机里坐着,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但拖拉机上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女的,怀里抱着一个半岁大的孩子;侯宝山在开拖拉机,那个女的在啃一根甘蔗,吃一口,吐一口。拖拉机到了地头,侯宝山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喝水,曹青娥看到他胖了,也黑了。那女的在拖拉机上喊:“娃他爹,把娃接下来,给他把泡尿。”曹青娥这时发现,那辆“东方红”拖拉机比前几年破了许多,侯宝山开拖拉机,也不戴白手套了。曹青娥突然明白,她找的侯宝山,不是这个侯宝山;她要找的侯宝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了。
(二)物非人非的悲剧
历史的长河在流淌,时间在变但空间不变,不变的地方物变人变。牛爱国和李克智说起小学时班上许多同学,二十多年过去,都各奔东西。其中一个叫王家成的已经死了,一个叫胡双利的疯了。当年教语文的魏老师,教地理的焦老师,前年也前后脚去了。小说中还写到,姜罗马告诉牛爱国当年吴摩西和吴香香蒸馒头的家,现在成了一家酱菜厂;转盘西北角,当年是意大利神父老詹的教堂,现在成了“金盆洗脚屋”;东街桥下当年有吴摩西挑水的井,现在成了一个卷烟厂。牛爱国想打探自己的情人的下落,结果“老李美食城”变成了“老马汽修厂”。曹青娥到了日思夜想的延津,发现延津变了,她小时候记得的延津,和三十三年后的延津,是两个地方,东街变了,西街变了,南街变了,北街变了,十字街头也变了,西街西头,当年吴摩西和吴香香蒸馒头的院子早没了。曹青娥记得爷爷家在南街,三十三年前叫“姜记”弹花铺;如今弹花铺还在,弹花却不用脚蹬了,装了一部柴油机,弹花锤“哐当”“哐当”在自己翻跟头;但她记得的人都死了。爷爷老姜死了,大伯姜龙死了,三叔姜狗也死了,剩下的皆是姜龙、姜狗的后代,见面都不认识。曹青娥离开延津,去了新乡,去找当年与爹爹吴摩西分手的东关汽车站旁边的鸡毛店。但到了东关,汽车站二十年前已搬到了西关;当年的汽车站,现在成了一座化肥厂。化肥厂占地几百亩,十几根大烟囱,突突往天上冒着白烟,哪里还有当年鸡毛店的踪影?
(三)自我迷失的悲剧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好像活的不是自己,也找不到自己。小说的前半部分“出延津记”找寻的是未来,也就是“到哪里去”的问题;小说的后半部分“回延津记”则是寻回根本,即“从哪里来”。杨百顺和牛爱国一直在寻找,但现实生活中却屡受打击,找不到自己。杨百顺变成了“杨摩西”,又变成了“吴摩西”,又改成了“罗长礼”。牛爱国思考:自己没了,自己的心思也没了,那牛爱国成了谁呢?芸芸众生,不知自己是谁,也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即使有人找到了自己,“事情想不明白,人的忧愁还少些;事情想明白了,反倒更加忧愁了”。
命运无法掌握的悲哀。从被拐卖到被嫁人,曹青娥从来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命运是什么?小说借瞎老贾之口说: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念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一切仿佛被安排好了。即使心非所愿,有时甚至生不如死,在疲于奔命中,苟活于世,有些荒诞和疯狂,然而这是小说人物无法摆脱的宿命。吴摩西出门找出逃的妻子竟然是出于面子和舆论压力的“假找”。牛爱国千山万水寻亲还乡,则是出于说不清楚的“无意识假找”,是为了转移和掩饰自己的“自我危机”的屈辱感、情感与生存的困惑感。为了找出七十年前的一句话,牛爱国千里辗转,最终也没找到。
生命轮回的无奈。牛爱国重复了外公杨百顺的流浪之路,人物的轨迹是重合的,遭遇是近似的,都经历了职业的失败,都是老婆跟别人跑了,需要假装去找老婆,都颠沛流离辗转远行等等。平民历经千百年,不变的仍是为了吃饭穿衣等生计而做事,结婚、生子、离婚、吵架、偷情、朋友断交等问题。
(四)不变与变的悲剧
时代在变迁,但千年不变的仍是孤独。话会变形,形成了流言。例如流言传得全县城人都知道,牛爱国要杀人。牛爱国酒醉时与冯文修说是要杀小蒋的儿子,要杀庞丽娜。经冯文修酒醉说出后,话再经过几张嘴说,皆成了清醒时的话;等话又经过几道嘴,传到牛爱国的耳朵里,成了牛爱国当时抄起把刀,就要杀人。这时不是去杀小蒋的儿子和庞丽娜,而是要杀冯文修。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头扎向了自己。这些话自己说过吗?说过。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但又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已无法解释。因为时候变了,场合变了,人也变了。话走了几道形,牛爱国没有杀人,但比杀了人心还毒,这话毒就毒在这个地方。
中国传统伦理关系的颠覆。父子反目,杨百顺与父亲老杨老死不相往来。兄弟不和,杨百顺和弟弟杨百利之间,姜家三兄弟姜龙、姜虎、姜狗之间,手足之情被各种利害关系所遮蔽。妻子出轨,传统夫妻之间“互敬互爱”的伦理关系显得如此脆弱。师徒有隙,杨百顺为了猪下水觉得师傅师母太小气,结果另谋生路。朋友反目,老韩和老丁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但是为了意外之财,二人最终分手成为陌路人;老韩欺骗了朋友老曹,使老曹的女儿曹青娥嫁给了牛书道。
二、平民精神的悲剧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在高层次的需要充分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适当的满足。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等。社交需求属于第三层次,社交的需要也叫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个人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和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社交的需要比生理和安全需要更细微、更难捉摸。它与个人性格、经历、生活区域、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有关系,这种需要是难以察悟,无法度量的。刘震云在谈及《一句顶一万句》时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1]50。刘震云说,“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1]65。刘震云通过小说主要描写了第三层次的需要,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于是人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温暖的抚慰。《一句顶一万句》是对民族内部精神存在状态的深层追问,它试图展示的是民族群体中个体的精神面貌。亲情、友情、爱情,支撑着一个人的精神,自古而然,但它历来难求。刘震云始终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他认为“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1]80。他是“中国平民心灵”的发现者与挖掘者。
(一)孤独与诉说对象的颠覆之悲剧
无人可说话。牛爱国不是怕庞丽娜,还是怕离开她;也不是非跟她在一起,而是离开她,连她也没有了;或者,连怕都没有了;与她说不上话,离开她,连话和说也没有了,怕的原来是这个。一切不在庞丽娜,全在自己。牛爱香要嫁给比自己大得多的宋解放:“给你说实话,姐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话。姐都四十二了,整天一个人,憋死我了。”百年时间中,家族在延续,但其孤独感却没有改变。
即使有说话的对象,说话的对象却不理解自己。吴香香与杨百顺说不来,牛爱国与庞丽娜也说不来。牛爱国不爱说话,他老婆庞丽娜也不爱说话,大家都觉得他俩对脾气,他们在一起相处两个月,也觉得对脾气,就结婚了,生了孩子,就开始见面没有话说了。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有话说是两回事。不爱说话时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心里干脆什么都没了。牛爱香嫁给宋解放的目的是找个说话的,可结婚之后,一天到晚,跟他一句说不来。而牛爱香没嫁宋解放之前,见他就笑;自嫁了他,一次也没笑过。
诉说对象的颠覆之悲。中国自古以来的平民婚姻,往往是对现实的妥协,或者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是老大不小了,随便凑合过日子,大多没有经历“说话”(精神交流)的洗礼。本该是自己的诉说对象却和别人说的上,吴摩西发现自己的老婆和人偷情,两个人办完事后,抱着说了一夜的话,先是气愤;等到俩人逃走后,吴摩西出远门又不巧遇见二人,眼见这对偷情的男女过的虽苦,却有说有笑,这才觉得自己悲哀——“他们一夜说的话,比和我一年说的都多”。庞丽娜跟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有了奸情,被小蒋老婆赵欣婷逮到了,赵欣婷跟牛爱国说,她在旅社房间外等了半夜,什么都听见了,“他们一夜说的话,比跟我一年说的话都多”。成年人杨百顺能说得着的对象是几岁的小孩子巧玲。小百慧与牛爱国说不着,与牛爱香说不着,与宋解放说得着。宋解放说:“过去我不会说话,自从有了百慧,我变得会说话了。”书中的朋友、夫妻,大多数要么说不对话,要么说不上话。两个人相对无语,闷不做声,寂静转化为寂寞。
(二)交流的对象“人是心非”的悲剧
牛爱国论其最好,不是李昆;不是崔立凡;不是……算来算去,还是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青海。但杜青海也不是过去的杜青海了,杜青海在部队时靠谱,两人分别几年,也开始给牛爱国出馊主意。牛爱国的情人章楚红说起她和丈夫李昆的事哭了,两人刚认识时,世上再没有两人说得着,不然她也不会二十出头,不顾爸妈反对,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从张家口来到泊头。谁知短短两年过去,两人就说不到一起,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三)角色替换的悲剧
“你看你,一年多不见,你咋成了我,我咋成了你呢?”这是文中常说的话。牛爱国与章楚红说完一段,要睡了,一个人说:“咱再说点别的。”另一个人说:“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这时牛爱国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山西沁源县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章楚红变成了庞丽娜。当初小蒋的老婆赵欣婷在长治“春晖旅社”捉奸,听到小蒋和庞丽娜在屋里说的就是这种话。
(四)非法与合情的悲剧
老婆偷情是非法的,但是偷情的原因是因为说的着,有共同语言,是精神上的正常需求,是合情的,吴香香和庞丽娜都有某种意义上“出走的娜拉”的意味,这也是一大悲剧。社会的不认可与人自由的需求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个问题在中国农村社会该如何处理呢?允许她们偷情,还是按传统规则办事?这是一个在当今还无法解决的难题。
三、平民哲学与平民语言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地深沉。刘震云正是对故乡延津和延津大地上的平民怀着深沉的爱才创作了这篇优秀的小说。小说表达了平民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典型的平民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刘震云发现了“说话”和“对谁说话”及“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的孤独状态的。
小说总结了平民生活的哲理: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事不拿人话拿人;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每件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中,又拐着好几道弯;知道自个儿是谁了,才能明白往哪里去;日子是过以后,并不是过从前。
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拿起就放不下。刘震云用民间最日常的大白话进行对话,不加任何文学的修饰,但是却又能够达到文学上的修辞效果。即使是作者的叙述,也基本上依照民众原生态的思维模式,一种自然的流动与述说,简洁朴实洗练,既与中国民间生活相一致,又夹杂着戏文韵白,两者结合起来,返璞归真,有内在的韵律与节奏。《一句顶一万句》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多用老百姓的日常说话,例如文中多次对有共同语言的人的语言描写就是:“咱们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语言带着乡土风情,短句居多,少有修饰。又如“说话办事,一方总想着另一方,就没了自己的心思”,“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头扎向了自己”。文中的语言也有很多幽默之处,再如老秦讲理的方式,老秦讲理是自个儿从来不讲,都是让人讲。别人讲,他在那里听;而且一切须从头讲起,一五一十,来龙去脉,哪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任何一件事,理都不是一面的,是多面的,讲着讲着就出了纰漏,一出纰漏就被老秦抓住了:“停停,这个地方我咋又糊涂了呢?你再讲讲。”等你把这个纰漏堵住,别的地方又出了纰漏;本来事情没那么多纰漏,也让你说得漏洞百出。一直讲到老秦听明白了,也就是你讲不下去了,老秦啥也没说,就已经得理了,老秦才作罢。所以老秦与人打交道,从来不动心思,都是别人讲着讲着改了心思。
四、与作者商榷
(一)文中有些地方不太真实
按照上文所说的马斯洛的理论,刘震云主要通过小说描写了第三层次的需要。但笔者感觉主人公前面两层的需要尚未满足。另外,还有对农民精神需要的夸大。根据笔者对农村人的了解,好好活着是他们的生活真谛,对精神需求也有但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夸大。
再如亲情缺失。对杨百顺和父亲老杨的描述好像根本没有父子之情。又如巧玲的母亲对巧玲独自抚养多年,但在文中好像没有母子深情。再如庞丽娜对百惠也是如此,百惠毕竟是庞丽娜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让人觉得文中描写与现实有点出入,不符合人之常情。文中对个人精神的需求描写的夸大压过了正常的人性需求。
文中打电话有些不真实。牛爱国第二天早起,去张家口之前,先给山西沁源县城东街酒厂的姐夫宋解放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暂时还回不了沁源,让宋解放先照料百慧上学。宋解放在电话里喊:“你在哪儿呢?”牛爱国:“远得很,在广州呢。”一般电话是有来电显示功能的,是否说成准备去广州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文中说到了延津县城,牛爱国才知道延津县城之大,比滑县和山西沁源县城大多了。笔者在延津和滑县住过,知道滑县县城大过延津。小说虽然是虚构,但符合真实情况可能更好些。
姜龙的孙女姜素荣该叫巧玲(曹青娥)“姑姑”,而不是文中所说的“姑奶奶”。文中是这样交代的,老姜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姜龙,二儿子叫姜虎,三儿子叫姜狗,姜虎有个女儿叫巧玲,姜素荣的爷爷叫姜龙。但文中说,姜素荣听说曹青娥去世了,感叹一番,说:“没跟这位姑奶奶见过。”
(二)一些描述有些“绕”,影响阅读的快感
小说第一部分有点“绕”,因为叙述的时空变化太快,让读者不容易接受。第一节只有几页,叙述中或曲里拐弯,或套中套,三五个故事结成一体,似乎相干,似乎又无需拐这么多弯,有些人物读后就忘了,如铁匠老李,这些人物可以删去或减少刻画。叙述由于太过“绕”,结果使得作品很多地方看似丰富,实则臃肿,有枝蔓横出的感觉。个人感觉第二部分“回延津记”更为流畅,更引人入胜,其主干突出,内容丰富,情节简洁,形象鲜明。例如以“找话”为悬念,情节跌宕起伏,叙述流畅。结尾也耐人意味:“但越是这样,牛爱国现在越想见到章楚红。不管她现在在干啥。找到她不是要从她嘴里打听七个月前她想说而没说的话,来泊头之前也许想知道这句话,现在突然明白,时过境迁,再找到这句话,这句话也已经变味儿了;他现在找到章楚红,不是要打听七个月前的老话,而是牛爱国有一句新话,要告诉章楚红。”
(三)沉迷于自我的叙述方式
句子“不是……也不是……而是……”出现的太频繁,有点转圈,影响了阅读的流畅性。例如文中说牛爱国他妈本不该姓曹,应该姓姜;本也不该姓姜,应该姓吴;本也不该姓吴,应该姓杨。又如但等孩子买下之后,老曹才知道,老婆要这个孩子,既不是为了孩子,也不是为了老曹两口,也不是为了造七级浮屠,而是为了跟二叔赌气。再如,牛爱国知道妈在安慰他,仍没说话。待到了路上,又想起妈的话。不是因为想起妈的话,而是妈说这话时歪着脖子,牛爱国不禁流下泪来。又如胖子担心一车豆腐坏了,也不是担心豆腐坏了,是怕豆腐运不到德州,德州的主顾,被别的卖豆腐的顶了窝。
参考文献:
[1]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