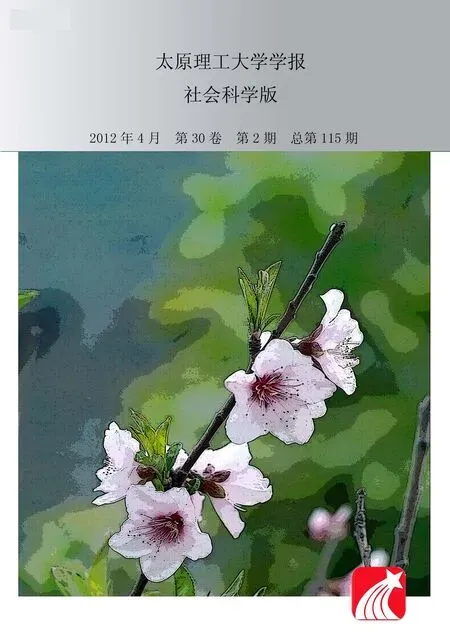《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1
付飞亮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严歌苓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版权被张艺谋在2007年买下,由刘恒进行了改编,经张艺谋拍成电影《金陵十三钗》,并于2011年12月15日全国公映。影片获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代表中国角逐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且是内地2011年公映影片中唯一拿到四次票房周冠军的影片[1]。张艺谋毫无保留地称赞道:“《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剧本,是我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2]编剧刘恒也很得意:“如果说,我完成了这个剧本是很幸运地走了一条钢丝,那么张艺谋完成这部电影就是走了十几条钢丝。”[3]但是,他们真的走过了所有的“钢丝”吗? 笔者拟对《金陵十三钗》从小说改编成电影后的得失成败,发表一点浅见。
一、战争与死亡
小说《金陵十三钗》[注]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6)。本文有关《金陵十三钗》小说内容的引述,皆参考自:严歌苓.金陵十三钗[J].名作欣赏,2006(7):3-31.文中用双引号标出,不再一一注明。描写了1937年南京城沦陷后,圣玛丽教堂(电影中改为文彻斯特教堂)收留了十四位秦淮河青楼女子,最后是这群受人轻贱的“香艳的洪水猛兽”挺身而出,暗藏锐器,抱着决绝之心,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侵华日军司令部在圣诞夜举行的“隆重庆典”。小说以“我”——故事中的一位教会女学生书娟的侄辈的口吻,通过“我姨妈书娟”的视角,来追忆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及这些秦淮河女人的事迹。叙述基调低沉而内敛,是那种极力压抑的无声的愤怒与悲痛。
原著中对战争场面基本上没有正面的描写,只是以极简略的几句话一带而过:“书娟收拾了自己之后,沿着走廊往回走的时候,不完全清楚她身处的这座美国天主教堂之外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这非常符合一位十四岁的少女的视角与心理。战乱时期,外面的世界如何残酷可怖,躲在教堂里的女学生们只能通过大人的言谈获得一点印象,而且那时,她们好像还没有太多的国难当头的概念,仍然为了一些琐事而与秦淮河女人们争吵,甚至打架。因为“我姨妈(书娟)此时并不知道,她所见所闻的正是后来被称为最丑恶、最残酷的大屠城中的一个细部。她那时还在黛玉般的小女儿情怀中,感伤自己的身世”。
而电影对小说进行的大幅度的改编,首先表现在对战争场景的正面铺陈上。电影几乎完全脱离小说原著,添加了战争的情节与场景,有几乎长达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对战争的正面表现,极力渲染了战争的残酷、血腥与中国抗日战士的悲壮精神。
原著中,中国军人没有怎么抵抗,就被日本人俘虏了上万人,据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几个伤兵说,他们是任由日本人“把手指粗的绳子绑在他们的手臂上,而他们一动不动,整整齐齐给绑成一串又一串”,赶到江边集体屠杀。这样的窝囊的死法,不仅当事人本身觉得耻辱,也令所有的中国人觉得心痛。小说中在教堂避难的中国士兵有五位,考虑到反抗会累及教堂,几乎都束手就擒,被日本人杀害,可谓死得令人觉得特憋屈。其中只有那位李全有上士以两手掐日军中尉的脖子,作了最后的一搏。惨痛的惋惜、压抑的悲愤,流露在小说的克制的叙述中,字里行间的那种低沉的、无声的怒吼,能令人感受到不可遏制的反抗情绪与惊人的力量。
电影没有照原著那样表现中国军人,而是赋予了他们宁死不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英勇气概。电影中把十多位教导队的中国士兵改编成为了保护女学生,而放弃了撤离出城的生机。这十几位战士浴血奋战,除李教官和浦生外,全都在没进教堂前就以惊人的英勇精神而壮烈牺牲了。电影还请来了以威廉姆斯(Joss Williams)领衔的好莱坞顶级战争特效团队,重金打造吸引眼球、刺激人腺上激素的电影大场面,其效果一点不亚于《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等战争大片。
这种对战争情节与场面的改编,可能主要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一是塑造中国军人的英勇形象,可以维护民族尊严,尊重民族情感,减少一些可能会对拍摄“南京大屠杀”这一敏感题材的批评;二是吸引观众,提升商业价值。制片人张伟平毫不讳言《金陵十三钗》“是商业片,而且是一部大投资的商业片”[4]。票房是这部影片最重视的终极目标。
这种改编,确实达到了上述两个目的,但是却违反了影片的叙事视角的统一性。小说中的叙事者置身于事件很多年后的想象性描述,她是凭借着胡书娟的记忆或讲述,加上一些历史档案资料与图片,力图还原当年南京城里的那段悲惨历史,显得真实可信自然。而影片一开始是以获救女学生书娟的回忆来展开的,以内聚焦限定型的第一人称叙述。如影片结束时,女学生的旁白告诉我们,她不知道那些秦淮河女人和男学生陈乔治的最终结局,这是明显的限制性叙述。这样的优点是以当事人现身说法,有更令人震撼的说服力,但是整部影片却并没有坚持这一视角,有很多地方用全知全能型的第三人称叙述。如影片一开始的那场枪战,还有中国士兵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行为,这种对残酷而逼真的战争场景的刻画,女学生书娟那时正躲在教堂里,根本不可能知道得如影片中表现的那么清楚。电影中的叙事视角的不一致,可能会使爱思考的观众产生疑惑。
二、爱情与色欲
电影对小说的第二个较大的改编是加入了美国入殓师约翰与秦淮河青楼女子玉墨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玉墨与书娟的父亲胡博士有过一段艳事,玉墨与戴教官之间的暧昧与调笑也描写得较传神,但是,电影中却把这两段情感纠葛全部删除,反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她与假神父约翰的情感戏。
电影为何要这样改编呢?笔者以为,电影改编是以假神父约翰为中心的。约翰作为影片的灵魂人物、重点刻画的英雄形象,不能没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于是影片发挥了好莱坞的浪漫爱情桥段,并且请来了第83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得主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来扮演约翰这个角色。不知道是为了迁就克里斯蒂安·贝尔不会中文,还是为了显得有所谓的“国际范”,电影将人物所操的语言作了较大的改变。原著中,除了与一位日本大佐讲英语外,里面的两位神父都是一口中国话,阿多尔多甚至还会讲一口地道的扬州方言,至于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出场人物,都是讲中国话。而电影中,将那个假神父约翰的语言定位为英语,几乎不懂中文,而且让陈乔治与那些女学生,全都陪着他讲英语。电影中,玉墨一口流利的英语,让她能与美国入殓师约翰直接交流调情,让人觉得特别矫情。
同时,为了成就玉墨与约翰的爱情,电影还把胡博士改编成了一位交通部的孟先生,为了拯救女儿孟书娟(即小说中的胡书娟)而留在南京,并被迫为日本人做事,成了一名“汉奸”。当然,他帮助了约翰修理汽车、获得通行证,最后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而这样的改编,使小说中的其他情节也不得不做相应的调整。原著中,书娟因为父亲与玉墨之间的关系,使她对玉墨非常仇视,甚至打算用烧红的火钳子报复玉墨,“在那婊子细皮嫩肉的瓜子脸上烧个纪念”。
电影里,如何对原著中书娟对玉墨的仇视作个合理的交代呢?为了延续小说中的书娟对玉墨的那种鄙夷与怨恨的情绪,电影又作出了一次“走钢丝”的行为。电影补充了一个替代情节,即通过玉墨之口来暗示书娟爱上了美国人约翰,而对玉墨的厌恶和憎恨是因为吃醋,是因为看到约翰对玉墨的献殷勤、求欢。这样的改编,好像合情合理,能自圆其说,但是却耐不住推敲。书娟与约翰只是一面之缘,而且是在那样凶险的一个环境,约翰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男性魅力。他,年纪可以做书娟的父亲,职业只是个卑贱的入殓师,而且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很难让人觉得信服。
电影中的李教官基本上可以说是小说中的戴教官的改编,对他的情感依托也作了调整。电影中的改编,让他少了小说中的那种放浪气,多了一份庄重与严肃。但是,他不仅几次舍身保护女学生书娟,甚至还能在生死悬于一线的危急关头,注意到书娟在奔逃中掉了一只鞋,并且在惨烈的巷战中为书娟捡回那只鞋,默默地送到教堂。这样的情节改编,好处是让李教官既保持了那种顶天立地英雄男儿的形象,又铁骨柔情,使人物形象一下子就生动饱满起来,感人至深,令人为之热泪盈眶,但是,仔细回味,却多多少少令人觉得有点不可信。在战友及自己随时可能牺牲的情况下,不太可能会为了一只鞋而冒险吧。如果说是一种朦胧而强大的爱情力量在驱动他如此鲁莽、如此多情,似乎也有点牵强,再联系到书娟对美国人约翰的朦胧情感,这种多角恋爱的情节更是让人觉得纠结。
由此,再加上约翰与玉墨的激情戏,难免会使人产生联想,电影好像对情色元素特别感兴趣。同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影片对豆蔻与香兰遇害场面的详细表现,其目的就有点可疑。对豆蔻回藏玉楼寻找琴弦被日本兵轮奸致疯的情节,小说中虽然也有描述,但没有正面表现。影片为何要这样详尽地展示豆蔻与香兰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呢?除了可以让观众仇视、痛恨日本兵外,是否还可以抓着一切机会展示女人的肉体,刺激观众的感官、满足观众隐藏的黑暗的欲望?
有人说过,在电影中,死亡是国王,性欲是王后[5]。这是视觉艺术一个秘而不宣的王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所说的人类两种本能冲动——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也为这一王道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影片为了表现情色,与渲染战争一样,也存在偏离影片整体视角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影片是以书娟的视角来开展的,对于两位秦淮河女人出教堂回妓院找琴弦和耳坠的遭遇,她不可能知道得如影片中所呈现得那么详细。影片中表现得如此具体,明显也是第三人称叙事,与整部影片的叙事视角相悖。
当然,电影在对情色的表现过程中,也偶见成功的一面。如在表现玉墨等人风姿与才艺的时候,改编了小说中的一些道具,比如对琵琶的运用。小说中的琵琶只有一根弦,在豆蔻没回藏玉楼找弦前,曾说这些窑姐们在一起将有点黄腔左调的“采茶调”唱得“像哭一样难听”。“贫贱俗媚的音符给弹得如此低沉,让书娟感到不伦不类。”小说中的这种压抑的悲伤,令人顿有乱世之叹,荒凉失所之感。电影却将这一情节改拍得风情万种。玉墨与众秦淮河女子准备去赴难的前夜,演唱了翠禧楼的招牌曲子《秦淮景》,其甜美的软声轻唱,恍若一下子将观众带进梦幻般的温柔富贵之乡,香艳而使人惆怅。这一改编的好处,是能表现这些青楼女子的才艺,增加她们的形象内蕴,激发人们对这些女子的同情。美好的事物被推毁,总是更能让人无限伤感。电影放大了琵琶这一道具的功能,既煽情,又催情,效果总体上来说不错。
三、“十三”与异装
电影对小说最复杂的一个大改编,是对 “十三”这数字进行了繁复的演绎,几经曲折,使情节起伏多变。小说名为《金陵十三钗》,是因为在原著中,教堂收留的妓女是十四个,而豆蔻独自去找琵琶弦,一去不回,就只剩下十三个了。至于为何正好是十三位,笔者推测,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与“金陵十二钗”形成差异,并达到惊奇的效果。“金陵十二钗”因为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缘故,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经典的习语,小说借用它,可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另一方面,严歌苓长期生活在西方,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可能借用了“十三”这个数字的特殊含义。“十三”这个数字代表不吉利,又令人联想到耶稣与十二位名徒。小说取名“十三”,既隐约让人嗅到一种不安,又可以暗示里面发生的侠肝义胆、牺牲自我、拯救他人的崇高行为。所以小说名为“金陵十三钗”,既有中国传统的灵气浸透,又有西方的悲悯的宗教情怀。
小说中的十三位秦淮河女子最后毅然地代替女学生去赴死,没有其他的波澜。电影可能嫌这样的情节还不够煽情,不够惊心动魄,也不够精彩好看,所以在“十三”这个数字上衍生出一系列紧张的情节,为了这个数字,对原著作了巨大的改编。
首先是对陈乔治的改编。小说中陈乔治是被英格曼神父收养的,已经二十四岁了,是教堂里的厨师,并与躲进教堂的妓女红菱相好,最后为了保护神父而被日本人枪杀。电影中,他被改编成一位十四岁左右的文弱男孩,受神父所托照顾那些女学生。小说中的陈乔治不是太显眼,但是电影中这个人物的戏份很大,而且极富张力。他男扮女装,演出了一段与其他的十二位秦淮河女子一起赴难的千古传奇。电影的这种改编,除了保留小说中的名字与收养经历外,完全重塑人物形象。
电影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把留在教堂里的女学生由小说中的四十四位减少至十四位(这个数字值得让人注意,因为来教堂里的秦淮河女人也正好是这个数)。为了向观众强调这一点,影片一开始,就让陈乔治反复数女学生的人数。小说中,教堂里的女学生没有一个死亡,但是在电影中,一位女学生在教堂里面被流弹击中,一位被日本兵追逐摔下楼身亡,这便剩下十二位了。小说中,豆蔻独自一人去翠禧楼找琵琶弦,但是在电影中,另一位妓女香兰陪她一起遇害。这一改编,有点不合情理。如果说豆蔻去是为了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香兰冒死回去,只不过是为了耳坠,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为了“十三”这个数字,电影在情节上还衍生出一个非常大的改写,那就是让日军大佐派兵看守教堂,禁止众人出入。而原著中,没有这一情节,教堂里的人基本上可以自由出入。因为日本当时还没有和美国撕破脸,不可能明目张胆包围美国人的教堂,所以电影的这种改编,有点牵强。同时,电影中豆蔻与香兰两人如何逃出重兵把守的教堂,影片中对此也是含糊其辞,成为不解之谜。
影片中小蚊子这个人物与她的宠物猫,也是为了数字“十三”而专门设置的。日本中尉一个一个清算女学生的人数,包括那位从地窖里跑上来寻猫的妓女小蚊子,正好是十三位。原著中根本没有这只猫,它是被强行塞入的,也没有提到小蚊子这个妓女,除了赵玉墨、豆蔻、红菱、喃呢、玉笙等人,其他的妓女都没有给她们取名字。电影中增加小蚊子的作用,除了是引出“十三”这个数字的一个工具,而且在结尾时她的反悔,更是为了反衬玉墨等其他十二人的慷慨赴难的精神。因为她的临阵变卦,使情节多了一份波澜,也多了一份惊险。小说抒情诗般的淡然从容或者说庸常真实,在电影里面也因之变得惊涛骇浪,充满强烈的传奇色彩。但是,让一个青楼女子冒生命危险去寻找一只猫,而且是在豆蔻等人刚遇害不久,较难令人信服。此外,当她临上车时哭着不去,约翰安慰她,塞给她的正好是日本人送的一只卡通猫,明显有点过于巧合,匠气太重。
电影中英格曼神父的死与约翰的职业,也是因为数字“十三”。小说中的英格曼神父是教堂的管理者,也是尽力保护教堂众人与日军周旋的神父。但是在电影中,他根本没有露面就已丧生于日军的一次空袭中。为何要这样安排呢?因为要使陈乔治男扮女装,凑足“十三钗”,除了必须让陈乔治有点女气外,为增加可信度,还需要有一位易容高手,于是入殓师约翰登场了。而一位美国入殓师的登场,最好的借口就是英格曼神父的死亡安葬。约翰的职业,使他有可能拥有高超的化装技术,把众秦淮河女子,甚至男子陈乔治化装成女学生。原著中,十三位女子在夜晚被当做女学生带走,较易令人信服。而电影中,在白天,而且里面还有一位是男子,要让日本人相信他们全部都是女学生,也要说服观众这是有可能的,对编剧及导演来说,不能不说是又一次“走钢丝”的行为。
可以说,影片中陈乔治男扮女装、女学生教堂身亡、香兰寻耳环、小蚊子寻猫,甚至英格曼神父的死、约翰的职业等各种改编,都和“十三”这个不祥的数字有若干关联,而且一环扣着一环,互相牵连。至于编剧是灵光一现,先有在数字“十三”上发挥的构想,还是先有让陈乔治男扮女装的主意,然后兴奋不已,再回过头来对原著进行全盘的改动调整,笔者就不得而知了。这些改编,确实使情节变得紧张曲折,使电影场面变得惊险刺激,但是,从情理上来讲,较难具有说服力。
当然,由数字“十三”所衍生出来的情节改编,也有一些是比较成功的,如约翰用卡车偷运十二位女学生出城。电影中这种改编,不得不提到对几个道具的运用。首先是卡车。小说中的卡车是福特牌,而且没有坏,而电影中,那辆卡车一开始是躺在教堂院子中不能动弹的一堆破旧的废铁,后来在美国人约翰的妙手下回春,载上女学生们逃出南京城。同时,这辆卡车起到隐喻作用,暗示那位玩世不恭的美国入殓师本人也从颓废消沉的人生状态走向重生,得到救赎。其次是酒。小说中的“女儿红”,是陈乔治用来讨好红菱的,那些秦淮河女人与伤兵们用来打发难熬境况的,而电影中,“女儿红”换成了红酒,并发挥了推进故事发展的重要功能。当入殓师约翰在教堂里找到红酒,喝得大醉,并借酒装疯,赤裸裸地向玉墨求欢时,酒是色媒,是害人之物。但是,当神父约翰拯救女学生,出城时遇到日本兵的路卡,靠送了几箱红酒给日本兵,从而蒙混出城时,酒又是救人之良药。这里面蕴含的悖论耐人寻味。
电影中对日本大佐的改编,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小说中的日本大佐,“戴金丝边眼镜,微笑极其文雅”,虽然可恶,但是给人印象不深,而电影中对长谷川大佐的塑造,却显得气场十足。他温文尔雅的外表和娴熟的英语,在教堂里弹奏日本童谣《故乡》时表达的思乡情怀,都给人以有教养的印象。电影中对风琴这一道具的运用,是神来之笔。小说在描写教会女学生用歌声来抗议或救赎战争中的灵魂时,提到了手风琴,也提到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日本士兵听了这歌声后心有所感,然而终究没能抵挡屠戮,反而引来了日本兵对洁净少女的邪恶的欲望。但是,电影中用它来表现日本军官如菊花般优雅的一面,比较高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中,曾形象地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两重人格,“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6]。影片中的日本军官形象,正是对日本人性格中的“菊”与“刀”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正如影片中约翰所说的,大佐是一位文明人,但是,当他强令女学生们去参加日本人所谓的庆功宴时,却暴露了他的野蛮残忍的一面。这种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同于过去一般的抗日影片中的对日军军官的简单塑造,既有深度,又真实可信。
四、结语
电影《金陵十三钗》与小说原著差别非常大。严歌苓看到电影时,觉得完全陌生,“屏幕上展现的是完全新鲜的,甚至我不敢相认的生命!它的丰美和惨烈,它的深广和力量,让我完全忘记自己跟这个艺术生命体还有什么关系”[7]。虽然严歌苓好像对电影的改编很满意,但是,正如她曾经表示过,“以后要写‘抗拍性’很强的作品,保持自己小说的文学性”[8]。言外之意,相信不难明白。
改编成电影后,《金陵十三钗》场面确实精彩了,血腥的杀戮与肉欲的情色确实达到了刺激观众腺上激素的效果,然而,却显得虚假矫情,破绽百出。正如张爱玲在《连环套》里曾经形容过一位女人,虽然眉眼长得不够精致,但是“她哪里容你看清楚这一切。她的美是流动的美,便是规规矩矩坐着,颈项也要动三动,真是俯仰百变,难画难描”[9]。电影《金陵十三钗》正是这样一位肉感的女子,拨动着你的欲望和神经,然而,要获得奥斯卡评委的青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海盗王.《金陵十三钗》内地四连冠 《那些年》获季军[EB/OL].[2012-01-10].http://news.mtime.com/2012/01/10/1479657.html.
[2] 张力韵.金陵十三钗:剧本打动人心 凸显人性光辉[N].城市导报,2011-12-19(8).
[3] 刘 玮.刘恒:电影是剧本的墓志铭[EB/OL].[2012-01-11].http://www.chinadaily.com.cn/zgrbjx/2012-01/11/content_14425497.htm.
[4] 佚 名.张艺谋《金陵十三钗》是商业大片 窦骁周冬雨有望出演[EB/OL].[2012-09-21].http://ent.ifeng.com/movie/special/szslove/news/detail_2010_09/21/2601919_0.shtml.
[5] [美]戴维·斯卡尔.魔鬼秀:恐怖电影的文化史[M].吴 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5.
[6]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
[7] 严歌苓.五写“十三钗”[EB/OL].[2011-12-28].http://www.cflac.org.cn/ys/xwy/201112/t20111228_68779.html.
[8] 康少琼.严歌苓:我要写“抗拍性”很强的作品[EB/OL].[2011-05-18].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1-05/18/content_7885758.htm.
[9] 张爱玲.连环套[M]//金宏达,于 青.张爱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