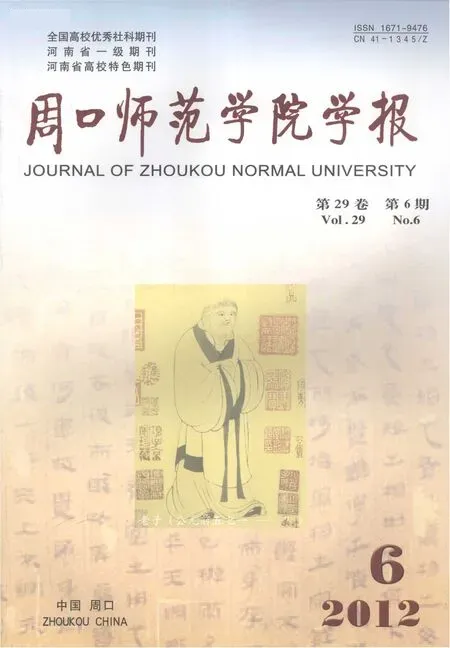姚鼐《老子章义》研究
赵 丹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历代注《老子》者众多,他们对《老子》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了一部丰富的老学思想史。老学,就像一面镜子,不仅投射出一个时代的背景,而且可以了解注老者把握《老子》的情况以及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清代,学术氛围由空洞无物的心性探索转向具体扎实的学科考证中,故清代学者普遍具有考据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清代学者注老,往往会对具体问题进行考证,如考证《老子》一书或者老子其人,不再单纯对《老子》进行义理诠释。《中国老学史》指出,在清代对《老子》之书的考证性著作多于前代,这是清代学术转向对老学研究造成的最大影响[1]。生活于乾嘉时代的姚鼐,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浓郁的乾嘉考据氛围还是对其产生了影响。他兼采义理、考证与词章,其《老子章义》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姚鼐与《老子章义》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前后绵延二百多年。桐城派恪守程、朱道统,标榜继承秦汉以至唐宋八家的文统。因其创始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得名。桐城派传人遍及全国,规模之大、历时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所谓“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桐城派在文坛上真正造成声势是在乾嘉时期,姚鼐则是集大成者。姚鼐(1731-1815年),字姬传,书斋名“惜抱轩”,世人称之“惜抱先生”。姚鼐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早亡,父亲终生未仕,家境贫寒。其自幼好学,分别向伯父姚范和同乡刘大櫆学习经学和古文义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选入《四库全书》馆,在馆不到两年,便辞官回故里。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起到他去世前近40年中,都以治学和教书为业。姚鼐一生著述很多,有《惜抱轩诗文集》、《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选编有《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抄》等。
徐世昌《清儒学案》说姚鼐在十三经、史记、汉书、通鉴、文选致力尤深,天文、地志、小学、训诂无不综贯,可见其治学广博。姚鼐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2]61义理、考证、词章三者均体现在姚鼐的作品中,《老子章义》就是一个代表。《老子章义》分上、下两篇,对今本《老子》的结构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将今本一章分出若干章,或把几章合为一章,姚鼐称这样“更求其实”。为求老子本意,在考证方面,他研究老子其人、老子与孔子的关系及《老子》文本;解老方面,融会儒道,尤其是程朱理学思想;文学理论方面,体会《老子》的美学思想,从而阐发自己的文学观。
二、考据特色
过去人们认为姚鼐只尊程朱义理之学,将其视作考据学家的对立面。其实,他反对的是“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2]61,不仅不反对考据,而且主张与义理、词章相济。加上他正逢乾嘉考据学大兴,汉学压制着宋学,兼采汉学,有助于融洽学术氛围,缓解学术纷争。他的《老子章义》正吸收了汉学之长。
(一)考证老子其人
关于老子的出生地,《史记》称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还有陈国相人之说,《庄子》则称孔子和杨朱都曾“南之沛见老子”,沛地在宋国。三种说法,姚鼐认为“《庄子》尤古,宜得其真”[3]780,老子应是宋国沛地人。关于老子的姓氏及有无谥号问题,姚鼐进行了考证,他说:
陆德明《音义》注老子,两处皆引《史记》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阳,不谓为《史记》之语,陆氏书最在唐初,所言《史记》真本盖如此,则后传本之非明矣。
当唐之兴,自谓老子之裔,于是移《史记列传》,以老子为首,而媚者遂因俗说以改司马之旧文,乃有字伯阳,谥曰聃之语,吾决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无谥,苟弟子欲以谥尊之,则必举其令德,乌得曰聃?[3]780
陆德明的老子注有两处引《史记》的“字聃”;河上公将《老子》托于神仙之说,称老子“字伯阳”。陆德明的老子注成书于唐初,所记载的《史记》本是对的,而唐代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就擅改太史公的原意,称老子“字伯阳,谥曰聃”,这是错误的。太史公称,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这才是正确的。姚鼐说,老子并没有谥号,若聃是老子的谥号,但聃却无法体现老子的德行。詹剑峰说,《史记》原文是“字聃”,“伯阳、谥曰”四字是后人妄加的,这是姚鼐和王念孙确切证明的[4]16。
关于《论语》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中的老彭,历来就存在歧义。一说是商代的贤大夫,其说出自《大戴礼·虞戴德》,很多注解《论语》者都采此说,朱熹就是代表;二说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彭祖是尧的臣下,是传说的人物,据说活了八百岁;三说是老彭、老聃、彭祖,同是一人,代表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姚鼐则在《老子章义序》里直接说:“老彭者,老子也。”[3]779老彭就是老子,又说“彭城近沛,意聃尝居之,故曰老彭”[3]780,彭城临近老子的故乡沛地,故称老子为老彭。
(二)关于老子与孔子的关系
关于老子与孔子的关系,姚鼐说:
夫孔子于老子,不可谓非授业解惑者,以有师友之谊,甚亲,故曰我老彭。
老聃论礼之说及《老子》书言以丧礼处战之义,其于礼精审,非信而好古能之乎?
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闻。……孔子遇老聃,问礼于其中年,而《老子》书成于晚岁,孔子盖不及知也[3]780。
姚鼐认为,孔子把老子视为老师和朋友,所以才亲切地说“窃比于我老彭”。孔子在老子中年时向他问礼,而《老子》一书成于老子晚年,可能孔子是没有见过《老子》一书的。而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是历史事实。《礼记·曾子问》和《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第四十》都有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情况。老子言礼,是“精审”的,包括“丧礼处战之义”。老子与孔子都信而好古,且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的礼的知识是非常具体的。
由于老子明确反礼,礼是在道、德、仁、义之下的,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故历来都有人怀疑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真实性。姚鼐认为,孔子问礼于老子与老子反对礼是不矛盾的,他说:
老聃之言礼,盖所谓求之过者矣。方其好学深思以求先王制礼之本意,得先王制礼之本意而观末世为礼者,循其迹而谬其意,苛其或而益其烦,假其名而悖其实,则不胜悁忿而恶之。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过,贬末世非礼之礼,其辞偏激而不平,则所谓君子驷不及古者与。且孔子固重礼之本然,使人宁俭宁戚,下学上达而已。……《老子》书所云绝圣弃智,盖谓圣智仁义之伪名,若臧武仲之为圣耳,非毁圣人也[3]779。
老子是深知先王治礼的本意,即统治者无为而治,百姓朴实无华。老子最初的愿望是与孔子一样的,追求礼之本然,下学上达。但末世的统治者以仁义礼乐来欺骗愚弄百姓,故仁义礼乐成了极虚伪的东西。老子比孔子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末世礼治的欺骗性,故他强烈批判礼治,实际上是揭露统治者“假其名而悖其实”的真实面目,激起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老子之所以“绝圣弃智”,也是因为圣和智都是统治者借仁义之名欺骗百姓的驭术,就像臧武仲徒有圣人的美名而无圣人的贤明。这正如詹剑锋所说,绝圣是反对术数的先知,弃智是反对统治者的巧伪,绝学是反对当时的官学[4]240。老子并非主张无知,而是主张有知的,明白事物之理,明白自然之道,回复清心寡欲的朴实面貌。庄子也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抨击借仁义之名来参与各种权力金钱争夺的假圣人,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上各种巧诈窃盗不断。
(三)关于《老子》文本
关于《老子》文本,首先是分章问题。姚鼐的弟子吴启昌《跋》云:
《老子》分章,世率依河上公注本。河上公注实流俗妄书,托于神仙之作,唐刘知几已辨之矣。世俗不察,猥守其本,于其章句误合误分者,皆缴绕穿凿,迂其辞以曲就之。虽高识如苏子由、王介甫者,皆不免焉[3]788-789。
世人多依河上公的注本,而河上公本宜合却分、宜分却合,谬故易见,唐人刘知几已指出该注本的缺陷。苏辙与王安石虽然都博学深思,仍守河上公本分章之失,在文义不可通处,就穿凿附会,辞不达义。故姚鼐注老,先为《老子》书重新分章,少则断数字,多则连字数百为章,使《老子》义明,训其旨于下。姚鼐把今本的几章合为一章,如把今本7、8章为一章,14、15 章为一章,20、21 章为一章,22、23、24 章为一章。他说,20章的“唯之与阿”以下是“求道者之状也”,21章的“道之为物”以下是“得道者之实也”,“此最是老子教人深切处,分为二章,则全失其旨”[3]782-783。除了合章外,姚鼐还将一章的几句分出来单独为一章,或者移到别章。例如,“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12字常被误置于30章“果而勿强”之后,其实应在55章“心使气曰强”之后。37章应置于32章末尾,37章的首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与32章的首句“道常无名”呼应。42章的“道生一”至“冲气以为和”25字应置于39章之首。39章的“贵以贱为本”至“此其以贱为本邪非乎”二19字应置于42章“人之所恶”之前。姚鼐的有些调整与后来出土的帛书本、楚简本相合,显示出他卓越的学术眼光。例如将45章“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分出,与帛书本、简本相合,只不过帛书本、简本将其置于54章“善建者不拔”之前,而姚鼐认为其与“以正治国”呼应,故置于57章之首。46章“天下有道”四句分出来,与帛书本、简本也是相合的,姚鼐将其置于57章“天下多忌讳”之前,而“罪莫大于可欲”以下在帛书本及简本里单独为一章。
其次,校字释义问题。姚鼐说,《庄子·天下篇》引老子语在今文里没有,可见今传本是有脱谬的,其前后错失的很多,姚鼐一一更正之,“以待世好学君子论焉”。在释义方面,亦多有可取之处。如“万物作焉而不辞”一句,姚鼐认为“作,使也。以身为万物使,不辞其劳,而亦不有其美”。“贵大患若身”,“贵”字作慎惜义。第57章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姚鼐说“世以奇谲解之,大谬”。姚鼐本着求实的精神,指出有的地方不可勉强解释,如63章的“大小多少,报怨以德”一句,“大小多少下有脱字耳,不可强解也”[3]789。姚鼐参照《韩非子》、王本、古本、王辅嗣本进行校字,例如“虚而不屈”应从王辅嗣本,改为“掘”字。“是谓盗夸”,《韩非子》作“盗竽”,姚鼐指出这是错误的,不必从之。类似这样的见解还很多,对正确理解《老子》文义,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以儒解老
姚鼐在考证方面是持之以据,本着求实的精神。但姚鼐不是考据学家,故《老子章义》也并非纯考证性的著作。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说:“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缺;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可见,姚鼐是以义理为主干的,在《老子》诠释方面也不乏洞见,而以儒家思想为旨归。
(一)会通儒学
以程朱理学为宗,是桐城派的特色。姚鼐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2]102可见,程、朱在姚鼐心中是父、师的地位,不可随意诋毁。但他认为不能盲目崇拜程、朱,其失当处应该给予纠正,以清醒的头脑看待其优劣得失。对《老子》,姚鼐也是这个立场。他说:
《老子》云:贵以身为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于吾身为快,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以是为自贵爱也。而杨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夫《老子》言诚有过焉,虽举其末学益谬,推原及老子以为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辞。然是有岂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谓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老子之行[3]779。
老子言“贵以身为天下”,主张以贵身的态度去对待天下。福光永司说,真正爱惜自己生命的人,才能珍重他人的生命,才能尊重他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把治天下的重任交给他[5]。杨朱在老子自爱思想的基础上宣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姚鼐认为杨朱只顾自身,与天下隔绝,的确无损于他人,但这是自保。一方面,姚鼐赞同老子所说的贵身思想,另一方面,姚鼐说,末学杨朱曲解了老子的原意,这是老子所未料想到的。但说“老子以为害天下之始”,这未免夸大了,不可取。姚鼐客观地看待《老子》,《老子》言“诚有过”,但儒者不肯认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老子的行为是不对的,儒者应肯定老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圣贤地位,老子、孔子都应是儒者心中的道德典范。
在姚鼐看来,儒道是互通的,在解释《老子》首章时说:
道,诚可道也。圣人之经纶,大经礼乐刑政,治天下之法,昔何尝不可道乎?然而非必常道之也,时异势殊,前之所用者,而后有不可施矣。名,诚可名也。人之事如是焉,名曰孝如是焉,名曰弟、曰慈、曰忠、曰信,昔何尝不当其实而可名乎?然而非可常名之也,人异而情变,彼行之而是者,此行之而固非矣。无道、无名,是名为天地之始;有道、有名,是名为万物之母。圣人反天地之始,故不系乎有之迹,而常无焉,以观其妙也。圣人循万物之母,故不因故迹,而常有焉,日生不穷,心达乎万物之极际,而观其徼焉[3]781。
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姚鼐以儒家的概念来解释老子的“道”和“名”,老子的“道”是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就像儒家圣人制定的治理天下的经纶礼乐刑政之法,是不能违背的。老子的“名”是“道”赋予的,就像儒家经纶下具体的道德伦常,如忠、孝、弟、慈、信各种道德规范。第二,“常道”、“常名”是恒常的,但蕴含变化之理。程颐说过“惟随时变易,乃常道也”,这是合老子意的。众人都以不变为“常”,殊不知能变也是“常”。但“常”也是要遵循“道”的,所谓时异势殊,人异情变,彼行此非,“常”是由道决定的。第三,以心性本体论来解老。“心达乎万物之极际,而观其徼”,只有悟出心之本体,心之无边无际,才能探寻到宇宙的本体和宇宙万物的无边无际,这一阐释有融会理学和老子之道的意味。总之,老子的道与名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道为体,名为用。而儒家解老,一般把道、名都圈定在伦理道德范畴里,姚鼐的高明之处在于把老子的自然逻辑与儒家的伦理逻辑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从注文还可看出,姚鼐尊奉程朱理学,尤其重视发挥理学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儒者,姚鼐并不守门户之见,主张学习各派思想之长。《老子章义序》就说:
天下道一而已,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夫恶知其始之一也[3]779。
这里的“道”并不特指儒家之道,而是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的法则。求道者各有各的探索之路,有的见识多,有的见识少,应兼采各家,从而达于道。求道者应拥有宽广的学术胸怀,兼收程朱理学、老庄学说以及佛教思想。在解老时,姚鼐发现有的地方是佛道相通的,如解释“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滌除玄览,能无疵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为:“能婴儿,能无疵,则无妄见。所谓知者,不待言,却又恐其未得真知也。禅家休去歇去,一条白练去,乃此意也。”[3]782《老子》这四句话是讲修养的工夫,精神和形体合一,集气到最柔和处,摒除掉一切杂念,返回到内心本明的状态。“无知”是“滌除玄览”、“天门开阖”、“明白四达”修养工夫之后的最高境界和最佳结果。“无知”便是得到了真知,不需言说的。老子本意未必言佛、言禅,但其理相通,“休去歇去”,真知就在心中,本然地了解,不需过多的追逐。当然,尊奉程朱理学的姚鼐,在解老时,还是以儒道相通为本的。
(二)借《老子》抒救世之志
桐城派是在道统最没落的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都试图在政统的枷锁下实现道统所赋予的使命,即使归隐,仍不忘身任天下的志向。姚鼐也是如此,生活在文字狱大兴的乾隆时期,君主以高压政策禁锢士人的思想。姚鼐说:“秦法本商鞅,日以虏使民。竟能威四海,诗书厝为薪。……盛衰益隆污,治道何由醇?焉知百世后,不有甚于秦?”[2]6秦朝禁锢思想是非常残酷的,而当朝君主非但不汲取教训,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姚鼐借古讽今,希望给朝廷以警醒作用。在解老中,也不忘抒救世之志,例如在解释“宠辱若惊”这章时说:
宠之为辱也,非宠之必为辱也。若以为惊者,辱矣,贵之为大患也,非贵之必为大患也,若以身与其间者,则大患矣。何也?彼以宠与我者,取我而下之也,得之何足喜而若惊焉,失之何不适而若惊焉,是谓为宠辱矣。贵之为大患者,吾以身赖其崇高之乐,则亦以身任其危峻之忧矣。苟无以身与焉,而何患载!以身赖其崇高之乐者,以身为天下者也,夫亦不自贵爱矣。惟能自贵爱而不为者,则有天下而不与矣,可以寄托天下矣[3]782。
老子说,得宠和受辱都会使人惊恐,得宠后会害怕殊荣被剥夺,便会在赐予者面前阿谀逢迎,可见得宠跟受辱一样会使人失去人格的尊严。姚鼐则说,受宠不一定会成为辱,若感到惊恐,便是辱,看重自身受宠便是大患。人们往往重视荣辱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老子呼吁大家要贵身和珍爱生命。而姚鼐希望众人追求“崇高之乐”,不必在乎身外的恩宠与毁誉。“崇高之乐”即儒家传统的积极向上,修己立德,“一箪食,以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以实际行动践行道德伦常原则,具有忧患意识,为天下百姓着想,珍爱生命同时又身任天下,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之。可见,姚氏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兴趣不在于探求理气、性命之类的哲学问题,他所强调的主要还是对纲常伦理道德的维护。姚鼐通过抒发救世情怀,表明自己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护卫者。
四、文学思想
姚鼐不仅训诂有序,阐释有理,而且以文学家的眼光注入老学新的特点。《老子》五千言,哲理深厚,少有人从文学角度去分析它,姚鼐的《老子章义》则暗含了古文艺术。姚鼐在解老过程中体会老子的美学思想,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解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为:
浊者与万物相浑于一也,故能浊,难静之而清,则分别生矣。于是其道不可安以久,心之纷扰,动之徐生,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保此道者,不欲以善自盈,不盈则不知己之善,冲然与物无间,是与天地相似不违者也,可以敝矣,不待吾新之而物成矣[3]782。
姚鼐认为,老子这句话是说明体道者的修养工夫,从“浊”到静,在动荡中,能静心自定,动极而静。从“安”到动,在长久安定中,能活跃起来,静极而动。之所以能做到此修养工夫,在于坚守道,坚守人格修养,故能不断去故创新。应用到文学理论中,第一,“浊”代表动和创生,“安”代表静和自定,如同阳刚与阴柔。姚鼐提出文学风格美是刚柔相济,所谓“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文章是合于天地之道,故文章之美合于刚柔之美。刚柔是对立的统一,相互依靠,不可偏废其一,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第二,人格修养将决定文章的风格,文人应把道德修养和高尚人格作为第一要务,就要“保此道”,要不自满,“冲然与物无间”,不违背天地之道,才能创生新的作品,从而达到姚鼐提出的“道与艺合”的境界。第三,老子的描写,素朴简单直接,其素材都是日常生活和自然风物所直接体现的。姚鼐赞同这种自然、朴实的文风。
姚鼐在读《老子》时,首先注重韵律。例如,第4章的“道冲”、“渊兮似万物之宗”,其中“道冲为句,与宗为韵,言道之体至冲也,而用之或有能不盈者乎?”第20章的“乘乘兮,若无所归”,王本的“儽儽兮”入韵。第57章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其中“正、兵合韵”;“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其中“贫、昏合韵”。其次注意文章的结构关系,如承接关系。第4章的“挫其锐”四句承“不盈”,“湛兮”句承“万物宗”;第64章的“欲不欲”承“无执”,“学不学”承“无为”。再次,解老的语言简短,贯彻了桐城派“文贵简”的原则。章太炎也说姚鼐文章有个特点为“谨”,即文章避免冗长烦琐,使文章尽量明白畅通。姚鼐的一些《老子》解释比较易懂,如解释第15章为“微妙者,成己者也,玄通者,成物者也,豫若冬涉川六句,以状微妙,浑兮其若浊,以状玄通”,简洁明了,从而有效传达了《老子》意思。作为一个散文大家,姚鼐提出著名的文章八大要素,即“神、理、气、味”是文之“精”,近于虚,是内在的要素,“格、律、声、色”是文之“粗”,近于实,是外在的要素。前者的审美层次比较高,必须通过后者显现出来。姚鼐之所以注重韵律、文章结构以及简洁的表达语句这些外在的形式,就是为了突显出文章的神韵。
五、结语
姚鼐顺应了乾嘉时代的学术风气,兼容义理、考据和词章之学。其《老子章义》一书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考据方面,探究老子其人、老子与孔子的关系、《老子》文本;在义理方面,以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解老;同时在文学方面,体会老子的美学思想,并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说:“自惜抱文出,桐城学者大抵奉以为宗师,然其才气之盛,学问之正,博大精深。”《老子章义》正体现了姚鼐才气之盛,学问之正,治学之博大,思想之精深。
[1]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424.
[2]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姚鼐.老子章义[M]//新编老子集成:第15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4]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