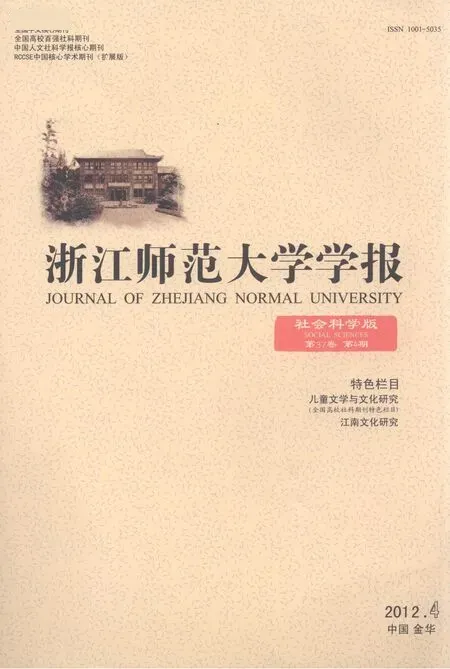大学章程:秩序规则的二元性
——一种历史角度的考察*
蒋季雅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1)
大学章程:秩序规则的二元性
——一种历史角度的考察*
蒋季雅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1)
大学章程体现了大学内部治理规则,是我国大学治理中引进的西方舶来品。引进大学章程的目的是既要解决我国大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状,又要使其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保驾护航。通过考察西方大学章程内容后可以发现,作为大学自治传统载体的大学章程体现出了秩序规则的二元性,其内生秩序决定了大学的本质,也成为其事业发展和传承的核心,其内化的秩序规则体现了大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内生秩序规则与内化秩序规则的变化对应了大学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兴衰,而历史的经验将对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学章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内部治理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领域中问题层出不穷而又难以解决,改革者将目光锁定了高教法中提到过,但却一直不为人重视的大学章程,从而使大学章程建设提上了我国高教改革的议程。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委员联组讨论会上提出了教育部要向地方放权的意向,并说,“我们多年来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现在是该放就放,但是每一个学校要有自律的基础,有自我配合的能力,否则放多了马上就会出问题”。[1]“学校要遵循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来管理教学,大学应有自己的章程。”[2]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改革“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能否得到解决的关键在于政府向大学放权时,大学要具备“自律”和“自我配合”的能力。“自律”与“自我配合”是对大学自我治理,内部机构运转协调有序的秩序描述。在法治国家,寻找秩序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实现规则之治。因此,在高等教育法律体系背景之下开启大学内部规则之治的重任将由大学章程来完成,大学章程制度的建设成功也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里程碑。“大学是12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纪产物”,[3]9大学章程也最早出现于那个时期。要了解章程与大学内部秩序的必然联系,我们必须追溯到大学产生之初,因为历史的作用在于“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4]
一、大学章程体现了大学秩序规则内生与内化的二元性质
众所周知,大学的产生与中世纪行会组织形式密不可分。行会是“为了保护本行业利益而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规定业务范围、保证经营稳定、解决业主困难而成立的一种组织”。[5]行会具有鲜明的职业技术性以及职业道德性,也正是在这两种特性的基础之上,每个行会内部有着特有的组织纪律与规章,可以制定自己的章程,对内实行封闭式的自我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会内部的规则是残酷而非人道的,与之相反,行会中洋溢着的是“平等、民主、互助友爱、相待如手足”的温情。[5]大学最初只是行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与普通世俗行会组织不同的是,它是人们以追求知识为共同目的聚集在一起之后形成的行会组织,因此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目标价值。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特性到今天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价值目标的超脱性。“如果大学只是作为一种追求物质利益和自由的法人团体,它本应与中世纪其他机构具有同样的命运,而这些机构已经销声匿迹了。”[3]25但如果大学仅仅只为了追求真理和研究学问,也并不能成其为大学,因为以这一目标为追求的学院组织早在中世纪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但它们都没有发展成为大学。在中世纪的复杂环境之下,没有外在权威对大学的保护,教师与学生们很难获得为追求真理而“沉思”的机会。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学院模式而成其为大学,就是因为它将保存、创造知识的内在诉求与运用知识服务社会的外在需要二者有机结合在了一起,或者说因为中世纪大学的知识传承方式①使其能够具有为政权组织以及社会服务的功能,因此外部权威通过赋予它各种各样的特权或权利促成其完成了价值功能实现与输出的组织形式建构。而机构与组织形式的创建是中世纪大学对于后世最大的贡献之一。
中世纪大学大多是以某个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当有著名学者跓足一个城市讲学时,往往周围其他城市、地区的学生们就被吸引到这个城市来跟随学习。所以通常的情况下,教师与学生们相对于这个城市而言都是外乡人(或外国人)。依据中世纪的法律规定,外乡人无法享受到城市市民的权利,但“教师和学生们不确定的社会地位,这才是早期大学确立的诱因”。[3]22新兴的大学行会组织在12世纪的前几十年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关注,这种局面在1155年腓特烈一世颁布《安全居住法》时而被首次打破。[3]85-86由于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博洛尼亚大学师生们利用腓特烈前往意大利接受加冕的机会向其恳求禁止市民对外国学生动用司法权以及保障师生自由迁徙的特权。腓特烈慷慨地在《安全居住法》中赋予了师生们这些特权,并认为知识是宝贵的,为知识离开故乡的人们是值得称道的。但腓特烈关心政治局势甚于关心师生们的法律权利,在其后师生权利受侵害要求其保护时他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反而是与其不和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随之认识到了大学价值,并通过颁发特许状为大学授予特权的方式大力提升大学的社会地位。[3]86-88亚历山大之后继任的教皇保留了这种扶持大学的传统,大学成为了教廷保护的对象,但同时也成为了监督的对象。教皇可以直接为大学制定章程或者对其章程进行修改,也可以为大学制定法令。与教会相似的是,世俗政权与城市政府也逐渐看到了大学的价值,在一些教权衰微的地方,世俗政权或城市政府利用权力对大学进行干预,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其制定章程。中世纪大学章程多数为教皇或国王、城市政府制定和颁发,章程中既有与教学相关的规则内容,也有所赋特权以及法令在大学中的实施内容。教会实行的是“对大学内部事务无所不在的干预政策”,[3]100但这只是从章程或教会为大学制定的法规命令内容中看到的表面现象,实际上除了对大学与城市政府、市民之间矛盾纠纷的赋权式干预之外,教会在中世纪前期为大学制定的内部管理措施大多符合大学教学规律,很多情况下就是对大学实践做法的确认。如教皇英诺森四世就曾“在自己的法律著作中充分研究了大学的本质和特点”,[3]100而据他对大学章程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大学内部的教学管理是相对独立于教会的。因此中世纪前期教会对大学内部组织纪律宽容化也是大学得以出现在历史上的重要外在原因。但毕竟对大学无所不在进行干预是大学外部权威机构的权力,因此当大学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权威机构对大学干预、压制的力度也加大了,从此大学也就难以再完全恢复到中世纪前期的辉煌。章程是中世纪大学得到外部权威组织承认的合法证明书,也是大学所处宏观与微观社会环境的缩影。中世纪大学的内部结构与运作通过其章程能够大概获知,而大学的使命与外部权威机构对它的定位在大学章程中分别转化成为内生秩序与内化秩序两种基本秩序规则的安排。
二、大学章程作为内生的秩序规则:大学学术组织、纪律的规范化成形
一般认为中世纪最早的两所大学是博洛尼亚大学与巴黎大学,这两所大学分别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行会组织与以教师为主体的行会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多以手工业为主,实行师徒制的传授方式,但学徒的人数受到限制。[6]同样的,大学在其产生之初也实行师徒制知识传授模式,文凭也是以教师个人名义发授。博洛尼亚大学形成的是学生行会,“那里的学生行会,在一开始聘请教授时,就通过罚款来监督教授是否良好地履行自己的教学职责,是否准时上课,是否上了足够课时,为了支付罚金,教授们必须事先存下一笔钱来支付保证金。”[3]23巴黎大学则形成教师行会,为教学与学习制定规则。在知识、教育为教会垄断的中世纪,大学由行会向教育机构转变,首先要得到教会的认可,其次就是要取得学术标准的评价权。因为在追溯大学起源的时候,“一直以来就存在一个标准规范,……使人们承认大学或与其类似的组织是高等教育机构。这就是将学位的授予建立在学术委员会决议的基础之上,学术委员会对这个决议负责。……大学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必然要求有衡量正当行为的最低标准和做出决定的材料和程序”。[3]25-26学术评价权是否掌握在大学手中决定了大学是否能由师徒制的行会组织向教育机构转变。这种学术评价权主要表现为考试权,但考试权曾一度被教会所控制。继腓特烈一世之后向大学伸出保护之手的亚历山大三世在颁布命令“宣布发布执教许可证和从事教学工作都是免费的同时,为评价教师资格候选人执教能力制定了程序,规定候选人必须要通过由‘杰出教士们’组织的考试后,其执教资格才能得到认可”。[3]88但如果考试权不由大学掌握,缺乏明确的教学与学习评价标准,大学就不会形成稳定的组织制度与学术规则。1213年巴黎教长颁发的“大学的大宪章”是考试权由教会把持向教师转移的一个标志,它限制了大学内部代表教会利益的教长的权力,规定在聘任神学和教会法的教师们,必须要经过教授投票。申请大学教职的候选人必须经过学院的考试。②随后巴黎大学以教师作为考试评价权的主体,围绕学术委员会评价机制建立起了内部学术组织规章制度并得到了教会的认可。在学术组织制度规范成形的情况下,1215年巴黎大学第一部章程制定,它“不仅意味着松散的大学组织得以重建,以前的章程③重新发生作用,而且意味着导致一所大学,或者章程,或者大学秩序的建立的行为”。[3]31而用教皇特使库尔松的罗伯特在1215年所说,则是确保大学的安宁。[3]32
中世纪大学即使有了统一的章程,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社团组织,如有着完善组织形式的同乡会就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但对于组织结构影响力延续至今的社团形式而言,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比同乡会要更为重要。博洛尼亚大学章程与巴黎大学章程是中世纪各大学借鉴的范本,仿照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大学通常依靠同乡会等社团组织进行内部管理,而仿照巴黎大学建立的大学,“大学的很多管理是通过学院进行的”。[3]124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联邦制中联邦与州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学院是大学内部根本的并带有某些自治权的实体,它们有自己的章程、评议会和院长。”[3]42院长通常就是大学的教师,他负责“管理和教学、辩论和考试”。[3]124学院是在学科基础上形成的团体组织,它以教师为中心将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中世纪学院之间的竞争关系更加强了学院内部的团结。相对于为维护大学共同利益而存在,因此行政事务日益增多的大学共同体而言,学院是一个更为浓缩的学术共同体。
中世纪大学的章程几乎都以巴黎大学或博洛尼亚大学为模本,主要原因在于这两所大学最早完成学术组织纪律规范化从而塑造出大学的模样。它们为教会以及后来的统治者“栽种大学”提供了便利,[3]56因为从功能运转而言,只需要复制这些大学的章程就可以制造出大学来。
三、大学章程作为(外生)内化的秩序规则:大学权力、权利的行使与监督
困扰整个中世纪大学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将其自身与周围社会、政治环境相协调。作为异乡人集合体的大学要想在一个城市立足下来,就必须要取得教皇或世俗政权的支持。只有得到他们的特许状,大学才能获得与外部干扰势力相抗衡的权利。中世纪大学因所处的城市不同而与世俗政权、教会的关系有所不同。如博洛尼亚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世俗权力远高于教会权力”[7]的城市,虽然教皇也“摆出一副‘学生自由’保护人的姿态”,[3]51但大学仍然处于城市为其制定的章程约束之下,约束的目的在于防止大学迁往其他与之竞争的城市。以学生为主体的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们为此与城市政权展开了斗争,最终与城市政府达成妥协:城市承认大学的独立,大学处于自己选举产生的校长管辖之下,同时城市赋予学生当时只有其市民才享有的各种特权保障。
与博洛尼亚大学不同的是,巴黎大学处于教会势力强大地区。教长作为主教的代理人是大学的首领,“对学生和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力”。[3]132由于教廷一贯持积极保护大学的态度,几乎每次大学与外界发生冲突后,教皇都会参与解决争端,并通过特许状的方式为大学赋予特权。作为特许状的衍生品,教皇对大学实行教皇学监制度,他们“自觉地维护教皇赐予大学的特权,以免受地方当局的限制和侵犯”。[3]18这些制度一方面起到保护大学特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使大学处于权力的控制之下。12世纪后期是大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巴黎,学生的人数出现了“几乎失控的快速增长”,[3]53教会对于法学这一世俗学科的发展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兴盛显得忧心忡忡,因为这与教会为了弘扬教义而支持大学的初衷相违背,而大学教师也“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力焦躁不安”。[3]53大学与教会之间展开了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231年”[3]54巴黎大学教师在教师中自行选举校长而告终。而教长的权力让位于大学选举产生的校长则开始成了13世纪的普遍现象,“教长都逐步丧失了实权,而流于形式”。[3]142教会或者是对大学选举校长不加严格限制,或者如“许多欧洲东部和中部的国家,教长是当地的主教或者大主教。把他的权力委托给官方选出的大学成员”。[3]143又或者如牛津、剑桥大学,从主教处获得选举教长的权利,将教长变为了大学内部而非外部官员。[3]135
校长由大学选举产生之后,校长成为了“大学的行政首领、学校议会所采纳的决议的执行者、特权和章程的执行者”。[3]132教师组成的评议会或者学生组织成为大学中最高治理机构,大学在与外部控制的斗争中取得了外界的支持与赋权,同时又通过对这些权利的运用摆脱了外部对大学不恰当的制约。这种局面的出现除去大学教师、学生们积极斗争这一原因外,与中世纪特有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使大学能够与干预者进行利益的博弈,最终使大学“成为教会与王室之外的第三种权力机构”。[3]20权威机构对大学各种权利与权力的赋予使得章程成为体现大学社会地位的外部秩序规则内化的载体。但大学并不甘心于外部秩序的简单施加,而是为自己积极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制度保障。最终在中世纪外部权力争斗的夹缝中,大学形成了以教师、学生团体为意志决策中心,与外部环境并存的自给自足的自治实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治地位带来了大学学术上的极度繁荣,它成为“知识活动的中心,是学者的家园,理智在这里启蒙,……新时代的曙光随之降临”。[8]
四、大学章程秩序规则:二元性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衰
如果没有中世纪大学教师与学生们同外界干预的不屈斗争,没有他们为大学宁静氛围主动争取权利保障的精神,大学的面貌与今天肯定大不相同:大学不会在人类进步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者大学早就如中世纪大多数的行会组织一样消失于历史之中。大学在人类历史中的首次亮相是以围绕知识传授与研究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的集合体形象出现,教学与研究是大学不变的核心事务,而人的集合所形成的精神也就是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既是中世纪行会组织中的民主、平等与互助,也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与追求而表现出的思想自由。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教师与学生们的精神就是大学出现的“原创精神”,而“如果这种原创精神消失的话,如果原发性乐观改变的话,事业就会衰亡”。[9]这种“原创精神”就是学术自由精神,“学术自由本质上是精神自由,它意味着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时所作的任何选择或学术结论,遵从的都是他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对真理的执著信念,而不是对任何权威的盲目遵从”。[10]大学章程中围绕着教学、研究这一核心任务而建立起来的内生秩序规则是学者学术自由在大学层面的制度安排,这种学术自由的团体性权利(an institutional right of academic freedom)④也可以表述为大学的学术自治。从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历史来看,内生秩序的出现表明了大学组织结构的初步成形,并与围绕着大学共同体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建立起来的内化秩序共同构成了大学内部的基本秩序。以学术事务、学术共同体成员为直接调整对象的内生秩序规则,只有学术共同体成员才最有权力将其表述出来,也只有学术共同体成员才最为珍视这些规则并尽心尽力地守护它。内生秩序生发的源泉以及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它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制度安排对大学的教学、研究活动予以规范,即使是统治者想将某种外在秩序强加于大学之时也不能无视其内部的规律,因为一旦这种内生秩序的规律受到损害,大学的精神以及大学的事业也就将受到破坏。中世纪后期国家政权势力对大学内部教学、研究活动进行了种种干扰,有的国家甚至将大学变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但大学教学、研究事务相对于国家行政活动的独立性仍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中世纪大学兴盛时期也是其自治权取得与维持期,这种局面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以下三个前提条件基础上:1.大学获得多项政治特权,从而可以形成权利自我供给的小王国。2.大学有着较强的经济后盾,如大多数大学依靠教会向教师发放薪金,给学生提供补助,且学生取得执教资格后有机会成为教会的牧师。3.阻断了外部对大学内部垂直的行政干预,大学自行选举校长,教师团体或学生团体是大学最高管理机构。这三个前提条件对大学而言实际上都非常脆弱,它们的出现主要取决于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大学是否宽松,而并不以或不完全以大学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同时这种完全的自治对大学而言也具有危险性,因为大学虽然取得了自由,却也同时隔绝了外部世界对大学功能变化要求的回应,因此当政权想要利用大学的功能为自己服务时,很可能直接采用剥离大学各种权利与权力的方式。实际上中世纪大学这种完全的自治只是短暂的,在大分裂时期,教会、国王都通过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将大学变为自己的思想阵地。大学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成为了政治冲突的牺牲品。在教廷——中世纪大学最大的支持后盾与世俗王权斗争失败后,大学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更是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是大学的特权被大量剥夺,其次就是大学在财政上不得不依赖于政府,同时政府权力随意干预大学内部事务。此时大学机构日益庞大,已失去了以迁徙方式对抗外界干预的可能。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充满了“过分腐败的抱怨以及常常是暴力性的学生选拔”。[11]237但“当政府的要求有时与大学传统的、有特权的、以社团为基础的自由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达成一种可接受的折中方案,……不能简单地丢弃那些源自中世纪的古老的特权”。这种情况下大学无法取得卓越,但由于核心事务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能够进行正常的组织运转,因此“尽管存在着政府或教会的监督,整个近代早期,大学仍保存了一种脆弱的却是有价值的独立性”。[11]131而对大学古老自治传统的回忆也为洪堡时代的到来以及大学精神的复兴提供了契机。
五、结 语
大学章程内生秩序规则发端于大学学术共同体自身的运行规律,内化秩序规则来源于外部政治权威对大学的赋权及对其社会地位的承认。二元化的秩序规则相互融合,共同服务于大学教学、研究的核心事务。但中世纪后期大学的衰落表明,大学内部秩序规则必须要在保证核心事务运行的基础之上具备回应外部环境对大学价值需求的功能,它既要守护起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又不能使大学成为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我国当前的大学章程建设是在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背景下展开的,大学的法人地位也通过《高等教育法》得到了明确,因此大学章程的任务就在于建立起适应大学内部教学、研究规律的学术治理规则,同时将教育法治精神融合到大学章程之中,政府则应当不断完善教育法律制度,将教育行政活动控制在法律范围之内,避免对大学内部治理的任意干预。
注释:
①中世纪大学通过提供亚里士多德式的沉思生活进行教师职业的训练,但这种训练其实提供了学员们胜任各种社会实务的能力,从而也培养了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而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很多并不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的目的。参见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5页。
②1231年“大学的大宪章”被选入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颁发的圣谕《知识之父》之中。参见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页。
③笔者认为这里的章程有可能指的是各学院的章程,或者是指巴黎大学以前存在的各种规章制度,抑或二者兼有。
④此权利为美国法院判例所认可,参见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1]袁贵仁.985、211不再增任何新成员[EB/OL].[2011-03-19].http://learning.sohu.com/20110318/n279889195.shtml.
[2]袁贵仁.教育部将向地方放权,前提学校要自律[EB/OL].[2011-03-19].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4086782.html.
[3]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4]伯顿·克拉克,等.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5.
[5]宝兴.中世纪欧洲的行会道德[J].道德与文明,1994(4):36-37.
[6]徐平利.中世纪行会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孕育[J].教育评论,2009(5):156-158.
[7]冯典.中世纪大学自治精神探析[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6-18.
[8]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98.
[9]迈克尔·夏托克.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M].范怡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10]周光礼.大学的自主性与现代大学制度[J].大学教育科学,2003(4):1-4.
[11]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二卷[M].贺国庆,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Dual Regular System of the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IANG Ji-ya
(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Introduced from western countries,the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 reflects university’s internal governance.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 in our country is not only to solve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that“tightening control results in stiffness while relaxing control brings about disorder”,but also to escort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By analyzing the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 in western countries we find that,as a carrier of the tradition of autonomy,the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 reflects the duality of regular system.The regular system which grows from inside decides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and becomes the core of its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The regular system which grows from outside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and the status university occupies in the society.The change of the dual regular system corresponds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university through history.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will provide insights for constructing the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 in our country.
the constitution of university;modern university system;internal governance of university
G640
A
1001-5035(2012)04-0083-06
2011-11-20
蒋季雅(1977-),女,湖南辰溪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级宪法行政法博士研究生。
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大学章程法律问题研究”(10AFX006)
(责任编辑 钟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