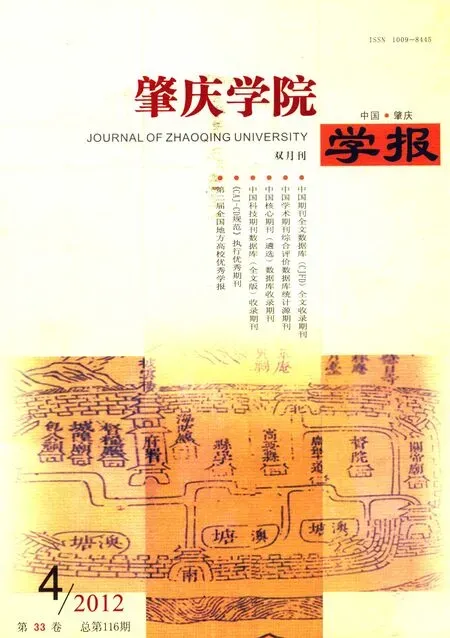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暴力”
徐法超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人们通常引述布尔迪厄和丹托来界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指试图“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或“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彻底颠覆将美学附属于伦理学的大众倾向”[1],也就是说,是一种把审美的态度引进原本应由理性和功利以至信仰把持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的倾向。而丹托则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可以描述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艺术家摆弄日常生活的物品,并把它们变成艺术的对象。第二,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以至将自身以及周围的环境看作是艺术的对象。
两种界定的旨趣有所不同,丹托的界定着意于器物层面,而布尔迪厄在此之外还包含了由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所开辟的审美的生存论含义。但他们都把日常生活的审美看作一种伴随着全球化、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文化形态,看作是对以生产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秩序的淆乱和僭越。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尚未在骨血中坚持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的中国人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起的淆乱和僭越,既可以拥戴,也可以反抗。
拥戴的理由一般是把对现代性价值秩序——尤其是所谓工具理性或功利主义态度——和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政治道德谱系的不合理性的证明,作为迎迓审美标准君临各种日常生活领域的理由。在这种意义上,审美化所引起的淆乱和僭越是造反、革命、救赎,或者在最起码的意义上,消解严肃精神、更加苛细地呵护大众的世俗欲望。而反对理由则指责它对真理、伦理政治、信仰的原有的严重性的侵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被认为很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内在意愿,戕害个体的自主性,等等。
显然,支持者们依据的是前现代的、古典的或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试图坚持某种惟一的、绝对的价值或社会秩序,或某种本真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因其与感性欲求的直接关联而被认为是不纯粹、缺乏超越性的。但另一方面,支持者们则拥戴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原则,一般性地解构美的纯粹性,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甚至倾向于放弃超越的向度(道德的、宗教的和社会的超越指向恰恰是被现代主义精神所破坏的),毫无保留地拥抱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这自然更能投合当代的民主和多元化等似乎毋庸置疑的价值。于是,一个担心被指责为绝对主义者,或者“是因为被剥脱了权威而心生怨恨”的现代性知识分子,在对各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评述中,也往往表现为“一方面如何,但另一方面又如何”的“辩证的”或“乡愿的”左右逢源与摇摆游移。
只是,这种“乡愿”是否是必然的?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某种评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的相对合理的标准?要搞清这些问题,需要对审美的本性以及它对人生及社会的功用进行更谨慎的评估。在此,我们选择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中最触目的一个方面,审美暴力,来透视审美的历史本性,并论证我们对待审美活动、对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应有的态度。
一、审美暴力与审美活动的本性
在资本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撑下,当代文化正试图把所有可能的东西都网络为审美消费的对象,不仅日常生活和周遭环境,而且,就连我们的“身体”以至心智都直接面对审美改造的要求。这样一种倾向,无疑为我们带来了感官和欲望的空前满足、解放或放纵,带来了情绪上的安逸或某种被预设为安全的刺激,也令我们感到自己似乎被文化千方百计地诱惑、迎合或娇宠着。但是,即便没有法兰克福的警示,人们也能在这种文化倾向背后感觉到某种隐隐的恐慌:比如,我们时时被提醒着要担心自己是否体面,是否入时;即使已经足够漂亮了,还要担心年华老去;我们乐于指责某某漂亮的明星没有内涵,报怨电影电视中过多地表现了暴力,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恐慌,通常是由那些不符合我们意愿(或者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生命的利益)的外在的强迫性的审美要求引起的,我们把这种外在的、强迫性的审美要求称作审美暴力。当然,这种恐慌在人类历史的所有形态中可能一直都存在,但无疑被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倾向加剧了,从而最终成为了问题,成为了促使人们对于古典以及现代美学观念进行反思的最有力的动因。
在由康德确立的古典美学观念中,审美被刻画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功利的,“道德的象征”,某种沟通有限和无限的心智活动;它与单纯的感官愉悦不同,使我们斩断与现实生活的功利链条的关联,进而趋向道德的完善。也就是说,它是超越性的、纯粹的。而无论法兰克福乃至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美学精神与古典美学在本质上有多大的不同,他们无疑已经在根本性情绪上接受了这一点,即认为审美可以完成某种救治社会异化的功能,然后才试图从政治的或其他的角度对审美活动有所剖判和节制。而后现代氛围中出现的“审美暴力”概念则直接暗示了审美的令人不安的一面。
具体地讲,所谓审美暴力,在当前的使用中起码包括三种意思:1.在最基本的或最表皮的层次上,审美暴力指的是把外观、形象,尤其是人的外貌作为社会评估、社会区隔或社会选择的最初(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依据,它所对应的英文概念是the violence of aesthticition,比如,相貌难看在升学、就业、婚姻和谋求较多的社会资源时造成的困难,对包装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等等。2.审美暴力的第二层意思是对暴力的审美化表现,即所谓的暴力美学,对应的英文概念应该是aestheticized violence,主要针对文艺领域中对暴力的形式化描述,当然,这种描述往往以超越道德评价甚至以反道德评价的方式刺激和取悦受众的感官。3.审美暴力的第三种使用方式是形而上层次的,指的是审美作为一种生存姿态所具有的括除对象的存在具体性和丰富性的特征。阿多诺曾用审美暴力的这种含义即aesthetic violence,表述人的主体性对于自然的丰富性的括除、祛魅和操纵。当然,这种意义上的审美暴力还体现在文学艺术、新闻媒体对现实的观照中,西方文化对东方文明的观照方式之中或者说体现在所有的文化际观照之中,最后,本雅明也曾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审美化了的政治,而把共产主义描述为政治化了的美学。
非常明显,第一层意义上的审美暴力并不是当前文化独有的现象。美饰美器、外观、形象自来都是社会区隔的重要依据,比如,容貌于古于今都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边际价值或文化资本。当然,它现在之所以被如此地关注,是因为它已经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了血统、政党、生产性价值,而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重要依据。然而,重要的是,只这一点就已经严重地违背了经典的古典美学观念,审美不再是无功利的,也不总是通常所说的无功利的功利性或者说某种为了生命的权益或人类整体的大功利。相反,它体现为确切的社会功利性:我们更多地只是因为认同某种有更多社会承诺的生活,而把这种生活的表现和选择认定为美的。我们欣赏三寸金莲或环肥燕瘦,并不因为它体现了某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是因为它是康德所讲的“道德的象征”,也不是恣肆的生命力的体现,我们只是在期盼某种历史性的社会认同。
对暴力的审美化表现实际上也有久远的历史。在高度理性化之前古代西方文明中,对暴力的表现和欣赏都是非常常见的。同时,可以看到,古代文艺作品对暴力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表现对命运或某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形而上的恐惧,并张扬、无所顾忌的生命强力。只是,这两种旨向显然都和近代启蒙精神冲突。对于要求对人类理性主体的信仰,要求在总体性的理性理想之下规范人类行为的启蒙性精神而言,(社会革命之外的)暴力恰正是一种违逆,而对暴力的审美化表现或将正面的美学价值赋予暴力本身,显然是不能被允许的。于是,近代文学作品虽然也表现暴力,却只是把它作为美的对立面来呈现。
但是,在现代主义将死亡、丑陋和荒诞奉上艺术殿堂的高位之后,当代文化却突兀地激发了对暴力的审美化表现的热情,除了在所谓“暴力美学”电影中对暴力的集中的审美化表现外,各种类型的商品化影视文艺类型也都乐于呈现暴力内容。不过,与高度理性化之前的时代相比,当代文艺作品对暴力的审美表现在动机和目的上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在通常可见的古代文艺作品中,对暴力的表现总是有意义的,即对暴力的表现是为了表达某种关于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但根据Bruder,当代文艺作品对暴力的审美化表现却容许对暴力的无意义的使用,即并不承担探求暴力和人生价值之间关系的目的,而只试图通过表现暴力自身刺激受众的感官[2]。当然,对暴力的无意义的使用却并非没有意味,它表达的是对强力的艳羡和某种抽象的反秩序或破坏的冲动,暴力的实施虽然没有现实的对应,只是一种抽象的情绪,但这情绪本身无疑是现实生活累积的。另一方面,当代文艺对暴力的有意义的使用,也不再表现对于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形而上恐惧(它当然也表现恐惧,只是这种恐惧是明确的、形而下的,比如灾难片和恐怖电影),而更多地表现为突破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冲动。这种冲动大多内在于道德承诺,即在不违背道德道义的原则下展示暴力,暴力的实施者往往同时是正义的代表者,暴力的对立面不是理性或道义秩序,而是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权力体系,因此,暴力的实施不但少了侵害性,而且最终实现了商品性影视作品所必须实现的伦理承诺。但,当代文艺对暴力的美学化处理中也不乏那种纯粹表现生命强力的张扬,从而要求人们对理性和道德秩序进行反思的意图,比如,《发条橙》和《低俗小说》等。这些作品,除了必须将现代社会既有的理性和道德秩序作为反讽的对象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阿喀琉斯式的生命意趣的回归。
总之,当代文化对暴力的热情是在对启蒙运动的价值和社会方案的合理性的怀疑中获得的。而且,无论人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热情的隐秘指向是以单子式的、放恣的审美主体代替背负着社会功利目的和道德义务的理性主体,以审美的原则代替伦理和社会功利原则。“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3]21,但是,这位酒神所依据的审美原则不再以成就道德或理性上的完善为目的,他是“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3]86。显然,就在这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核心的理念被论证并确立起来了。
但是,在审美暴力概念的最后一个意思中,这种把审美作为救治社会人生的手段的意图变得非常可疑。康德曾把审美刻画为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即在某种意义上“括除”功利性的或经验性的欲望的能力,因为这种括除,人类才能超越有限,成就道德上的完善。但也正是这种括除,提供了暂时地悬搁现实的道德、义务要求的可能性,人可以蜷缩成一个单子式的审美主体,世界因此似乎变得更柔软、更轻,但是,要获得这样一个(常常是脆弱的、离心的)更柔软更轻的世界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当自然因为审美的要求蜕变为景观之后,资本也就成功地掳夺了人们和自然的原本的亲熟关系和敬畏。在掠夺者的眼光中,印度神庙中的古佛不是敬畏和信仰,而是巨大的财富或艺术品。人们如此地关注显贵和明星们的隐私,也就是各种直接间接的情欲故事,而不是他们质实的头绪繁多的生活本身。我们首先在审美影像和故事中想象另一个国度,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通常安于把中国经验为大辫子、小脚、神秘,电影《卧虎藏龙》或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巩利或章子仪;我们留连于异域风情,甚至希望他们永远保持为一种贫困的原始的景观。还有非历史地将审美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规划,或将审美理想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诱饵。
当然,在当代文化中,最能凸显出审美括除的暴力本性的,是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制造出的仿真的“拟象”世界,一种超现实的“第二自然”,一种我们上面所提到了更柔软、更轻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它邀请并允许我们长时间地滞留其中,去体验某种虚拟的但集约的、纯粹的情绪,“它提供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然而,如此一来,“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现实对象对我们的现实性行为的直接要求被弱化了,能指挣破了与所指的稳固关联,自由流动,世界被夷平为意义或情绪的代码,情感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之前已经被“拟象”世界吸吮或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而这就是为什么媒体选择放弃琐屑的、无趣的具体事实甚至真实本身,倾向于把世界描述为一个富有情节的故事或一种浓密的情绪的原因。出于相同的原因,如同沃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观看第二次海湾战争的系列报导时,我们更多地感觉到是在观看一部长篇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感受到某种悲悯,实际上却无动于衷,不会果真因此想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也有人在现实生活中,像在电子游戏中一样轻忽生命。
至此,审美活动——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再纯粹是一种实现道德上完善的途径,带给我们审美体验的东西并不总是指向 “终极善”,而更多的是与个体的具体生存处境相关的生活理想的感性展现,它可以是形躯层次上的愉悦、舒适,也可以是社会认同,是个体生命意趣的实现,是历史性的伦理意愿的满足。更紧要的是,这些理想的生活方式可能是超越的、理性的、道德的,也可以是本能的、违背公共利益以至野蛮残酷的。因此,一味地拥抱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强调以审美的标准替代道德、真理等其他的标准,也就本然地包含了恐怖的意味。
那么,为了真正的生命利益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审美、对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呢?
二、审美、幸福及一种积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精神的可能性
哲学、宗教和艺术或人类理智的真正事业是论证、展示或促进一种可以达至幸福的生活方式。为此,它们需要区分、辨别各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事情被判定为是善的,有些事情则是恶的。其中,又有一些事情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价值,另一些则相反;有的价值被认为是相对的善恶,有的被认为是绝对的善恶;对这些价值的追求,也因此被区分为有限的目的和终极的目的,对个人而言这种终极目的即幸福。在此之上,人们也期待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拥有幸福,即普遍幸福。而相信人类可以达至幸福和普遍的幸福,并相信达至个体的和群体的幸福有确定和惟一的途径,要求万事万物以其应有的理序实现,并以这种理序或理念的感性显现来定义美,实际上是传统美学观念的普遍模型,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没有本质的区别。
个体的和普遍的幸福自然是人类理智的最终依归,也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理想。然而,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者,人类配享的幸福必定是有限的,并且,普遍幸福的可能性也不是自明的。在一种最奢侈的形态中,戴东原期待道德之隆盛,可以“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马尔库塞则要求人的爱欲本能的完满实现。这一切无疑是非常诱人的前景,也是所有乌托邦理想的核心内涵,但它们又显然是过分天真了,在道理上也讲不通:首先,我们不能期待全知全能和永生,我们不能期待自己成为神(而且,可以确定地论证,一种全知全能和永生的存在是无趣的,无所谓幸福与不幸);同时,人类所希求的各种生存向度或目的性的自由往往并不是圆融无间而是相反相对的,我们希求入世的健动也希求出世的悠游,我们希望把自己完全地交托于一个巨大的信仰或权威也希望自作主宰,我们必然像叔本华的钟摆一样在各种欲望之间摇摆不休,直至寂灭;最后,人类的欲望从来不只是原生的动物性本能,而是社会历史相关的,与他人的比较中产生的中介性的欲望,这种欲望是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因为总体的社会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即便人们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资源以实现基本的生存欲念,但总有些东西是稀缺的,比如荣耀、权力和奢华,我们可以期待共产主义——它并不许诺普遍的幸福,而只主张在物质资料充分富足的基础上,消除来自社会的奴役——但不应该期待在人间建立天堂。实际上,人们通常也只保守地把幸福理解为某种特定人生向度的实现,由德性和智慧把持的人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内心的平静(皮浪、伊壁鸠鲁、犬儒、小乘佛教和禅宗),富足健康和美无妄的生活(我等星斗小民),生命意趣的繁盛(部分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庄子、尼采、马尔库塞、福柯等等),巨大的社会成就或道德功业(儒家、功利主义者和马克思)等等。然而,根据Belliotti,上述所有的单一的生存向度的实现都不足以保障作为持久的、积极的、正面的心理状态的幸福感受[4]。因此,强调幸福是单一的人生向度的实现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不但忽略了人们对不同的人生向度的合理的执着,因此引发出各种不人道的禁欲主义和专制;而且,当它被宣布为社会的普遍要求或普遍幸福的目标时,往往意味着只有某些特殊的人群是配享幸福的,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无论在孔子人文化成或庄子的悠游超离的世界里,都没有为所有人留有坐席。
因此,幸福不能被期待为所有人生向度的完全实现,也不是某种单一的人生向度的实现。所有人实现其所有人生向度的普遍幸福,在逻辑上不成立,而试图把任何一种人生向度设定为社会的共同目标的作法也是危险的。就在这里,文化虚无主义者们会毫不迟疑地宣布,西方理性传统据以制定其总体性的社会人生规划的根基,都被挖除了。于是,没有达至个体和群体幸福的确定的和惟一的途径,没有了成就终极善的本质的理序,没有了总体性的理想,也没有了天国和上帝。于是,人们仓皇地逃亡到轻浅的审美愉悦之中,追逐那些没有更高精神指向的欲望碎片,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暴力,就在这里获得了其社会文化精神的依据。但是,这些文化虚无主义者,这些消极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最终发现,在背弃了传统理性的道德要求和理性要求之后的发足狂奔,只能使自己离幸福越来越远,因为,他们和理性传统所要求的纯粹的道德主体或国家政治利益的服从者——清教徒或红小兵——一样,都只生活在某种片面的人生向度之中。
实际上,上述意义上的幸福或普遍幸福理念之不可行,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失去了超越的方向。成就个体和群体的幸福感受,虽然不能是所有的或单一的生存向度的实现,也不能是一种无政府式的放任,一种被暂时的欲望驱使的、没有持续的意志力控驭的生命状态,而是境遇性的,由自我或社会群体确认的各种不同的人生向度的总体上的增进:首先,任何一种人生向度的缺欠都会导致痛苦;其次,任一生存向度的彻底实现都是无稽的,其现实的可能性只是境遇性的增进;另外,某种生存向度的增进总以减损其他某种或某些生存向度的实现为代价,对于一个餍足于城市的繁华喧嚣的人而言,质朴幽静的乡间是值得向往的,一个农人则会对灯红酒绿艳羡不已,但选择搬到乡村便失了繁华,反之则失了安宁。但我们必须选择,那么,只有促成我们在特定的生存处境中最关注的生存向度的增进的选择,才能促成幸福。当然,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在两个地方,则相对于只能居住于一地的人而言,无疑更为幸福,因为我们的目的性自由增加了。于是,对于一个具有健全理智的个体或社会而言,我们可以期待的个体和群体的幸福应该是境遇性地、相机地促成各种的人生向度总体上的增进。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美的本性是“境遇性的理想生活方式的感性显现”,而我们可以怀抱的最终理想是普遍的幸福,那么,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促成各种人生向度的总体性增进的目的,就成为评估一种审美理想境界高下的标准:我们认为浮士德的狂飙健硕有较高的美学品格(如果我们不急于把“不同的人生向度的总体性增进”理解为某种纯粹的道德评价),而沉迷于片面的欲望则较低下,就是基于这一标准。在同样的意义上,是否能够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各种人生向度的总体性增进,也是我们用以审视审美活动的价值的依据:一种使人们固执于片面生存的审美活动,在价值上自然不如那些创造性地开启了不同生存向度的总体性增进可能性的审美活动。
不过,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但往往被轻忽的问题:直接地展示与个体或普遍幸福理念相符合的美,并不必然是促成不同的人生向度的总体上的增进的最有效的手段。这实际上就是法兰克福在批判大众文化时所达到的洞见,“肯定性的文化用清白的灵魂抗议物化,但最终只能屈服于物化”,因为,这种美往往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过于遥远,根本没有直接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只能像一块飞地一样被怀想。而如果这种美被意识形态成功地利用,则我们就会只安于怀想,安于认同这种夹带着意识形态内涵的美的训诫和许诺,放弃反抗坚硬的现实的努力,放弃对其他正当的权利的要求。法兰克福要求艺术的自律性,批判大众文化,要求艺术对现实采取一种断然的否定性立场,拒绝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显然就是基于使美摆脱政治的不正当利用的意图。
于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呈现与普遍幸福的理念不相符、或者在品格上不高的审美理念,比如展示对于暴力和肉欲的痴迷,也并不必然无益于促成不同的人生向度的总体上的增进。当然,如果这种展示的唯一的目的或作用是使人沉迷于形躯欲望或攻击性冲动时,像我们经常在后现代的文化实践中看到的那样,它就是有害的。但如果在一个过分压制人的正当形躯欲望和个体政治权力的社会情形中,表现暴力和欲望本身是对增进自身目的性自由的要求,如我们在明清情色小说中的看到的那样;而当这种呈现创造性地提供了促成人生向度的总体性增进的具体方向时,它们会比单纯地描述乌托邦更现实地激发人们改变现实的意愿,它们可能表现为“破碎之声、粗俗之缘、投机之瘾”,但是,它们正因此更贴近人性,也因此具有更强烈的“现实的召唤力”[5],“一个人不可能只是生活在某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希望之中,一个人的希望只有在可能的王国里才能实现”[6]。同时,既然现代主义的彻底的否定性姿态无法避免被经典化或被意识形态利用,艺术的自律性并不保证其批判的力量,“自从艺术成为自律的,它就续存了从宗教而来的乌托邦”[7],那么,艺术不应固守自身的边界,不应执着于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希望,而应着意于是否现实地扩展了人的目的性自由,无论这种扩展是多么细微。这无疑就是后现代美学精神的革命性方面,或者说是一种积极的后现代美学精神:在一个没有本质、没有乌托邦理想的世界中,一种开放的、游戏的、行动的美学或许比现代主义更具有批判的震惊感,同时,只有境遇相关的、创造性地增进人的自由的生存可能性的活动才是真理性的。
综上所述,在理解审美活动本性及它与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时,有三种基本的倾向,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三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歧,但这种分歧不在于是否坚持美是幸福或终极善的理念(也即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感性显现,而在于人们所期待的幸福的内涵是什么,在于人们是否相信审美活动总是促进这种幸福的手段,以及审美活动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增进幸福。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自然会导致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同态度。
在悬设了上帝和天国之后,幸福被归于道德,因此,古典美学精神强调美对于道德的依附,而道德承诺的总是个体对于群体的义务,是以,个体的幸福,个体的其他合理的生存向度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在此基础上,人们要求无功利的审美和感官愉悦的严格区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过多地迁就感官欲望,自然不会得到古典美学精神的印可。现代美学在相反的意义上强调人的原始的生命意趣的张扬,强调人类生存的其他向度,也强调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革命的最终意义,但这种强调往往矫枉过正,以至于最终试图以审美的标准替代伦理的、理性的标准,或以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代替政治经济的或道德宗教的乌托邦;因此,法兰克福欢迎造反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反对那些制造虚假幸福与和谐的审美活动。后现代美学精神则放弃了乌托邦理想,消极的后现代主义甚至放弃了追求各种人生向度的整体性增进的理念,他们只关注具体的、切近的快乐,留连并满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营造的"超现实的"生存空间中,不足取法;但积极的后现代主义却关注并坚持各种人生向度的总体性增进,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现代美学精神的延续,只是它放弃了宏大的社会改革方案,试图在既有的社会秩序的罅隙间寻求改良的契机。于是,它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相对宽容,但也不衷心拥抱,而是把审美活动的价值放在现实的社会进程中加以考量,因此比古典和现代美学观念更为冷静和现实。
所以,我们所能期待于当代审美文化生产者和批判者的,正是一种积极的后现代精神:它是建立在对历史和人性的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实践智慧,它以消解对单一的人生向度的沉迷、促成人的不同的生存向度的总体性增进为目的,为了这一目的,它相机地表现暴力肉欲,或描绘乌托邦,它可以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和断然的否定姿态,也可以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要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如禅宗里的善接引者,他们知道单纯地描绘佛国并不足以使人参悟,应该根据参禅者的悟境予以点化,也不应执着于文字,可以当头棒喝,只为破除迷执,恬逗人机。当然,也不应一味棒喝,以打人为事。
[1]布尔迪厄.区分[M].黄伟,郭于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8.
[2]BRUDER M E.Aestheticizing Violence,or How To Do Things with Style[N/OL].http://www.gradnet.de/papers/pomo98.papers/mtbruder98.htm.
[3]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6.
[4]BELLIOTTI R A.Happiness is overrated,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
[5]张祥龙.当代西方哲学笔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6]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0-111.
[7]杨小滨.否定的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