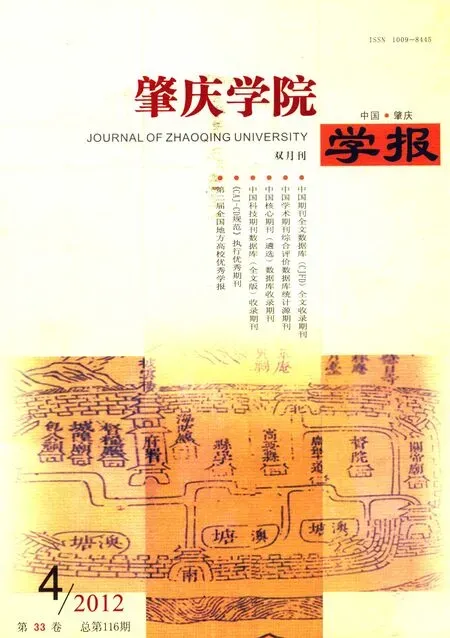缘合的碰撞——论《庄子》与佛教的关系演变
周黄琴
(肇庆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对于佛教的中国化,笔者一直存在着一个疑问,即外来佛教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国人所接受?对此,尽管学界已作了一定的阐释,如认为是统治者的推崇以及高僧们很好地迎合国人之需要。但毋庸置疑的是,统治者的推崇仅是一种外在因素,或表面现象,而异域之佛教如何能较好地迎合国人之需要?两种文化之间到底有没有更深层次性的契合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思想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地搭建起来?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一解析,以揭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内在交流的契合性。
一、思考基点的相通性
尽管庄子与佛陀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但从人类文明兴盛的时间轴上看,他们都处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而且都对人生问题做出过深入思考,如果摒除外在枝节的遮蔽,那他们内在思想的相通性就会豁然清晰。
首先,佛陀与庄子的思想都是起源于生命的内在体验。众所周知,佛陀与庄子思想的产生,既不是为了学术的发展,也不是为了外在世俗之目的,而是来源于对人生痛苦的反思。据佛教经典的描述,佛陀本是一位无忧无虑的王子,然却被“四门出游”的老、病、死之悲惨现象所震撼,而毅然放弃王子地位,选择出家生活。虽然,其间参杂了一些神奇性的描述,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佛陀的出家完全是出于对人类现实悲惨情状的内在触动。
对此,《中阿含经》亦作了相应的描述:“我本未觉无上正尽觉时,亦如是念:我自实病法,无辜求病法;我自实老法、死法、愁犹戚法、秽污法、无辜求秽污法,我今宁可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犹戚、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耶?”[1]即是说,佛陀感受到了人生的大量束缚与困惑,以及现实人生追求的内在矛盾性,因而,渴求一种全新的“涅槃”世界。正是基于对生命的体验与渴求新生命的内在意向,使佛陀在日后的修行中能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也使在日后的说法中,从未脱离实际生活而去建构理论体系。
对于庄子,现今的历史资料都无法确切地考证其具体的家庭背景,只是在《庄子》篇中偶尔提到其生活之窘迫,如“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甚至落到“往贷粟于监河侯”的悲惨境况。艰难的生存境遇,使庄子对人生有着切身之感受,再加上当时悲惨现象的大量存在,如“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2],“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人间世》)等,无不激起他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以及人生意义的追寻。故在《庄子》篇中,作者毫无建构理论体系的意向性,而是想通过大量来自生活的寓言故事来揭示人生哲理,以此警醒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
其次,都对生死问题做了探究。可以说,生死问题是一切宗教的核心问题,而佛教亦不例外,佛陀离家出走时就曾发誓要断掉人的生、老、病、死、忧伤与苦恼,否则终不回宫。事实上,只要断掉了生死烦恼,其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所以,憨山大师曾云:“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3]
庄子虽然不是一位宗教家,但他对于生死问题的探究,可谓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深刻的。在他看来,“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生命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无可奈何的,即“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正因生死的无奈性,所以世人产生了强烈的“悦生恶死”的心理,甚至连儒家大圣人孔子,在面对颜渊之死时,也免不了悲痛欲绝。
如何才能化解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生痛苦呢?这是佛陀与庄子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然而,在消解生死困惑的问题上,他们却找到了极为类似的方式,即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中去消解生与死的界限,从而获得永恒性。如佛陀将入灭时,对哭泣中的阿难说,不要悲痛哭泣,不要自寻烦恼,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的。而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本是气聚、气散持续不断的一个自然过程,生中有死,死中又蕴含新生,生死环环相扣,永不分离,就像昼夜之更替那样自然与相续不断,“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所以庄子能非常乐观地对待妻子的死亡,即鼓盆而歌。
最后,都力图摆脱世间束缚,追求无限自由或脱离苦海。在佛陀看来,世间无处不是苦,有“三苦”与“八苦”之说,而且对各苦存在的原因亦作了深入探究,力图把众生从苦中解救出来。他认为,不是事物本身导致我们痛苦,而是由于世人的“无明”,对生命“无常”、“无我”的实相缺乏洞察而误以为有我,从而产生执着而陷入痛苦之中。事实上,一切事物皆因缘合而生,缘散则灭,世间没有自性的永恒存在体,一切都必然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我”是什么?其实,“我”不过是“五蕴”和合的现象而已,只要破了心中的执着,就能证得“如来智慧德相”。故佛陀毅然放弃世俗中最令人羡慕的王子生活,选择出家,正是一种“追求永恒幸福、无限自由,抗拒死亡等束缚的向上意欲”[4]的表现。
而庄子尽管生活极其艰难,但面对高官厚禄之诱惑而毫不动心。据《史记》记载,楚威王听说庄子非常贤德,便派使者以“厚币迎之,许以为相”。然而,庄子却以“宁游戏污浊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为由,毅然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在庄子看来,对于精神自由来说,外在一切世俗功利目标都是一种束缚,人不应沦为功利的奴隶,而应是自由的主人,因而,对世人为各种名利而伤生害性之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尽管,佛陀与庄子的生存境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在面对世俗功利之时,他们却表现出极为相似的价值取向,即抛却世俗之累,寻求精神解脱。而且,庄子消解世俗执着的“齐物”思想与原始佛教的“无执”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庄子认为一切世俗观念都是相对的,只有摆脱这些世俗观念的束缚,才能认识世界以及人性的本然状态,从而获得自由。
虽然,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是,也存有大量之差异,如在消除执着的具体方式以及消解之目的等众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庄子是为了唤醒人的觉悟,从残暴、动乱的迷梦中走出来,回到生命的本真自由状态,而佛教则是为了人来世的美好生活。可以说,庄子关注今生的当下现实生活,而佛教关注后世的美好生活。然而,在佛教初传的过程中,这些差异性虽曾引起过一些讨论,但并未构成佛教中国化的巨大障碍,反而在相通性的基础上,佛教人士不断倡导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通性。如孙绰在《喻道论》中就运用了大量的庄子思想来佐证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而且,随着佛教传入的深入化,这些差异也在佛教日后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走向了消解,使两种文化之间真正走向了融合。
二、形式上的借用性
《庄子》与佛教的相遇,可谓是一种机缘。虽然,对于佛教的传入时间,学界存有多种看法,然而,对此,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逐一进行了考证,并给予了大量的否定,唯独对学界公认的汉明帝永平求法之说,给予了肯定之评价,即“汉明求法,吾人现虽不能明当时事实之真相。但其传说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5]可见,永平求法,虽有神话之意味,但不能全然断定为虚妄,其或是佛僧们在事实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神秘性,以此增强护教的力度而已。如若界定传法之初,为东汉时期,而此期又恰是中国文化处于谶纬思想与鬼神方术极为盛行的神学化时代。
为迎合时代之需要,当时的高僧们,不得不寻求一种契合中国世人心理需要的传播方式。据《高僧传》的记载,名僧们都会一些神道之术,如安世高是“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尝行见群燕,忽谓伴曰:‘燕云应有送食者。’顷之,果有致焉。众咸奇之,故俊异之声,早被西域。”[6]而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劾验。”[6]278因时势之使然,佛教传播之初,高僧们着重从神异之术上来着手,而非义学层面来宣传,即使期间译有《四十二章经》,然亦与道术相通,故而导致世人把佛道等同,出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之荒唐局面。
尽管,这种方术化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上层贵族求福求寿的心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但是,这种传播状态,并没有得到知识分子们所认可,因为,从佛教的呈现面貌上看,那不过是一种粗浅的方术而已,与当时其它方术并没有本质之差别,故“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云其辞说廓落难用,虚无难信。”[7]实质上,对于高僧们来说,亦不满足于此状态,摄摩腾就曾有强烈之忧患意识,即“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6]1事实上,这种方术化的传播状态,并不是佛教传播者的真正意指,其不过是为获取信众而使用的一种“方便”而已。
然随着魏晋玄风的兴起,高僧们的译经工作亦逐步向“依附玄理”的向度上迈进。如支谦把《老子》中的“知常曰明”与“复归于无极”之思想,运用于《般若波罗密经》的翻译上,即把《般若波罗密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可见,在支谦的眼中,“般若”与“大明”,“般若密”和“度无极”,其含义是相等同的。支道林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使用了大量的“众妙”、“至无”等道家用语。此现象无不展示出当时佛学对玄学的迎合性。因为印度梵语与中国汉语,在概念术语以及思维范式上都存在着较大之差异,故只能用“格义”化方法,即用中国思想术语来阐释佛教经典思想。在吕澂看来,不仅译者只能根据“各自所尊所懂的来传译”,而且翻译之外的讲习者,也只能“按照自己所学所知的来讲,听的人就不能不借助于自己原有的中国思想底子去理解和接受。换句话说,是将自己本土的学说与印度学说作比较,即所谓‘格量’(以中国学说尺度来衡量)的方法。”[8]确切地说,所有文化要进行异域传播的话,就必须经过一个“格义”化的阶段,而佛教就选择了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想,实质上,就是用老庄的思想术语以及思维方式来阐释佛教经典思想。如在张松辉看来,道安的“本无宗”思想,“与其说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不如说是来自中国的庄子。”不论是立论基础,还是立论目的,道安都是“继承了庄子思想”,并“与当时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一致。”[9]
虽然,学界认为,在“格义”化的过程中,高僧们仅是借用了老庄之术语与思想来推广佛教而已,而非把佛教完全等同于老庄思想。这一意图,也许在高僧们的心中是非常明白的,但对当时的中土之士来说,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意识,而是直接把它们进行类比思考。因为,在当时,中国学人无法理解与接受印度的思考范式,只好把它与中国的思维范式进行类同化。其实,到慧远讲法之时,还曾如此,即“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6]172而明末憨山大师亦作了相应的描述,即“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穷教典,苦于名相支离难于理会,至于酷嗜老庄为文章渊薮,及其言论指归,莫不望洋而叹也。”[3]329其实,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要对两种思想进行“格义”的话,实际上,在“格义”进行之前,就已经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是一种预定的假设,即佛教与老庄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否则“格义”难以进行。
正是基于此假定,当时许多高僧都是精通老庄之学,如支遁就注释过《庄子》,慧观亦精通庄老,注《法华经》时云“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且,当时高僧与玄学名士的关系亦非常密切,如支遁与王羲之、孙绰、何充、谢安等都有深交,而西晋僧人支孝龙与名士“陈留阮瞻、颍川庾凯,并结知音之友,世人呼为八达。”[6]124甚至,孙绰在《道贤论》中把竺法护等七位名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可以说,不论道安、支遁,还是在僧祐的《弘明集》中,凡是魏晋时期的佛学作品中,都充满了庄老式之思想。相对来说,东汉时期,佛教作品中对《老子》思想的引述要高于《庄子》,而到魏晋时期,引述《庄子》的几率要远远高于《老子》。因而,佛教思想恰是通过老庄化得到了快速传播,对此,道安亦作了相应的论说,“经流秦土,有自来矣。 ……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望相似,故因风易行也。”[10]
而且,早期译经中也强化了对神话故事的描述。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受道教的“长生久视”思想影响的结果。然而,从深层次上看,这些神异故事的描述,与其说是与道教有着契合之处,还不如说是与《庄子》中的“至人”、“神人”等思想有着契合之处。因为,一方面,《庄子》是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俗称《南华经》,而且道教吸纳了《庄子》中的大量思想;另一方面,从佛教自身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不愿意走向与道教相同的神通化道路。因为,这将抹杀佛教的独特精神,无法把自身与道教区别开来,所以,在《理惑论》中就存在着对道教方术之批判,即“都是虚诞之辞,不可置信。”
所以,在龚隽先生看来,当时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之所以能合流,就“在于当时学人们普遍误解了般、玄二学在理论形式上的相似性,简单地认为二者可以完全会通起来。”[11]“一方面,玄学名士们认为,般若学的抽象思辨和玄虚境界与自身学风颇为投合,便引以补充玄学旧义;另一方面,般若学者也力求依附于玄学的势力,发展自己的学说,对般若学的解释也是尽量着以玄学的色彩。”[11]84然而,佛教的玄学化,必然会导致对原始佛教思想的种种曲解,对此现象,道安早就意识到,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就指出,竺叔兰所译的《放光》,“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柄,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滕,每大简焉。”[10]82然而,竺法护的《光赞》,虽“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然“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复相明,又不显约也。”[10]82由此可见,当时佛教之简约与玄学化,实属无奈之举,完全是出于传播需要之考虑,故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之说。
然鸠摩罗什来华后,对“格义”化之缺陷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他说“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6]42因而,积极倡导用直译的方法来纠正原有般若学经典中的老庄化色彩,后经其高足僧肇的努力,般若学逐步恢复其原有之精神,即消解本体论观,恢复对空性的正确理解。可是,对于僧肇与玄学思想的关系,学界仍持有异议。如汤用彤、吕澂先生认为僧肇未跳出玄学之系统。瓦格纳先生认为僧肇是把“道家思想佛教化”。而龚隽先生认为僧肇与玄学不是“服从于一个同质性的体系”。[12]实质上,这些论说都是在试图从内在义理的层面,来划清僧肇与玄学的关系,即到底是属于哪个思想系统。但从形式上看,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僧肇在语言系统中仍没有脱离开玄学,还是 “假庄老之言”。虽假借庄老之语言,来阐释般若“空”性之思想,然而,对于中土之士来说,“空”性还是难以理解,僧叡在《喻疑》中作了论说,甚至连慧远都觉得法性之“空”,晦涩难明。
至隋唐时,为寻得佛教之真意,摆脱玄学之束缚,西行求法极为兴盛,义净曾云“西去者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13]而且,译经工作也达到了高潮,即演化为国家大事,不论在译经人才上,还是在译经原典以及规模上,都是其它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如在译经人才上,不论东晋道安,还是鸠摩罗什,都没达到梵汉融通之境地,而隋唐时期的译经大师,如彦综、玄奘、义净以及不空,都能“类华梵俱精,义学佳妙”。[13]75而且在译经的原典上也克服了初始时的口授以及借助西域之本的局限性,而是凭借华人直接从印度携来之原本。然而,尽管这种庞大与深奥的译经活动推动了隋唐佛教的兴盛,即宗派林立,可是,这种脱离实际生活体验而走向名相化的方式也预示着佛教即将走向衰落,虽然其后有会昌法难的破坏,但从佛教自身发展的机理来看,佛教不断走向经典繁琐化以及宗派相争的道路,就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而会昌法难只是加速了佛教的这种衰败而已。
三、内容上的融合性
然而,当其它宗派逐步衰落之时,禅宗却为佛教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局面,其中之奥妙,值得深思。据禅学资料的记载,早期禅是一种修行方法,而后逐渐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禅师群体”,即北方禅学注重禅数学修行,而南方注重义理。其中之缘由,在葛兆光先生看来,是由于“6世纪北方禅学的两个源头传入都是西来的胡僧;而南方禅学虽然多从北方而来,毕竟是在华人的思想氛围中,由汉族僧人来理解和阐释的,”[14]而南方又是“义学的重镇”,难以接受北方的苦修之禅数法。对此,《续高僧传》亦作了清晰的记载,即“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续高僧传》卷十七)。
汤用彤先生亦认为“南方的文化思想以魏晋以来的玄学最占优势,北方则仍多承汉朝阴阳,谶纬的学问,”致使“北方佛教重行为,修行,坐禅,造像,”而“南方佛教则不如此,着重它的玄理,表现在清谈上。”[15]这种差异性,亦导致南北禅师群体的冲突,因为,在早期强势的北方禅师们看来,南方之禅法更是一种背叛,故曾一度把达摩与慧可等都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与迫害。这种情感色彩,在《续高僧传》中亦有一定的流露,如“摩法虚宗,玄旨幽赜”,而慧可为“情事无寄,谓是魔语”。然而,实质上,从达摩的“二入四行”以及慧可的“兼奉头陀”的修行方式中,就可以看出,早期南方禅师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北方禅法思想的框架,仅为禅法思想注入了一点玄学思想而已,直至四祖道信才把苦修转向为“禅智合一”,使玄学思想进一步扩充到禅思想里。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就对修行者的不同层次作了分析,并认为不同慧根的人应有不同的修行方式,而那些高智慧之人不需要经过“念佛”、“坐禅”等繁琐的过程,可直接感悟佛的境界。因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修行的多维发展路向,迎合了不同层次人的需要,内在地推动了禅宗日后的发展,也使南方禅学逐步脱离了“印度禅学及其直系传承的北方禅学的牢笼开始在另一种思想之中成长。”[14]58到六祖慧能乃至其后,禅宗在破传统禅学方面走得更远,不仅打破传统“由定发慧”之修行路向,转向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瞬间顿悟,而且在破权威与名相方面亦有较大突破,而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达“无差别”的圆融境界。
实质上,禅宗在其创立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摒弃与中国不相适宜的印度特色,以此推动禅宗的发展壮大。所以,汤用彤先生认为“凡是印度性质多了,佛教终必衰落,而中国性质多的佛教渐趋兴盛。”[15]330甚至,他直接界定,“禅宗则为南方佛学的表现,和魏晋玄学有密切关系。”[15]330而吕溦先生也认为,“我们不能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佛学的单纯‘移植’,恰当地说,乃是‘嫁接’。两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是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8]4崔大华认为“禅宗‘顿悟本心’虽然独特,但是构成这一宗教思维方式独特性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因素——整体直观、实践体验,其观念背景,甚至是观念渊源仍然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于庄子思想中。”[16]
事实上,随着隋唐政治上的统一,禅学也不断地走向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南方的义理禅学不断地处于领先地位。这不仅是指禅师们在实际吸引信众的事实效果,更是从禅宗内在思想的长远发展。因为,北方禅学仅注重外在修行的行为,如坐禅、造像等,缺乏内在学理以及心灵上的转化与支撑,这必将导致禅学走向极为粗浅化的道路。而对于这些粗浅的修行方式,中国的文人墨客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也不太相信这些外在方式可以解救自己,在他们心中更渴望的是一种心灵的超越与自由,即“游心于玄冥”之中,其实,这也是庄子情怀在文人中的一种表现,而佛教要取得发展,就必须找到与中国文人的契合点。而且,禅宗四祖、五祖乃至六祖都拒绝皇帝的应诏,始终选择在民间默默传教,这种漠视名利的情怀,也迎合了中国文人的心灵需求,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对老庄与佛禅常常并不加以分别,对‘心灵的清净’与‘人生的自然’等同看待,并不去细细分辨其中更深层哲理理路的差异。 ”[14]342
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禅宗更多的是与玄学发生了关系。然而,透过这些文字上的表述,还是可以看出《庄子》与禅宗内在思想上的交融关系。 虽然,魏晋“三玄”是指《老子》、《周易》和《庄子》,然而,《老子》与《周易》对人内在深层次上的精神需求,缺乏精细与深入的探究,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语言,而在《庄子》篇中却对人生的境况作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究,并对世俗的人生之路也作了批判与反思,积极倡导人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快乐。
然而,不知是出于宗派的保护,还是其它发展之需要,禅宗人士一直强调禅宗与佛教的渊源关系,以致一直追溯到佛陀的捏花一笑,来论证禅宗的发展历史,很少谈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诚如铃木大拙在《禅与生活》中说“禅是中国人彻底把握佛教教义以后所得到的东西”,但又强调“佛教演变出禅宗以前,从来没有与中国本土思想发生过密切关系,”但又补充道“这里我所指的本土思想是儒家思想。”[17]那么其意指是否是想排斥儒学对禅宗的影响,而又不想明指道家与禅宗的关系呢?其实,在铃木大拙的其它论述中,仍不免可以看出庄子与禅宗的内在渊源关系。在《禅与生活》中,他指出了印度与中国两大民族的差异性,即一个精于思辨,幻想,而另一个则注重实用,关注世俗生活。那异质性的印度文化,又如何能在中国加以延续呢?文中,他认为“庄子和列子是中国古代两个最接近印度型的人”[17]38那么其意再清楚不过了,即庄子或列子是佛教中国化的桥梁,而从禅宗发展的历史轨迹上看,禅宗与《庄子》,不仅在形式上紧密相连,而且在破语言文字、破权威,追求当下解脱上都存在着内在的相联系。对此,美国学者默顿做了精彩的概括,“庄子思想和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是唐代的禅宗。……是庄子所代表的那种思想文化使得高度思辨的印度佛教变成幽默、反偶像、完全实践的佛教,这种佛教以禅宗之诸形式流行中国和日本。禅宗照明了庄子,庄子照明了禅宗。”[18]
[1]中阿含经(下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957.
[2]王先谦.庄子集解[M].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社,1996:82.
[3]曹越主编.憨山老人梦游集(上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2.
[4]陈兵.生与死——佛教轮回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19.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2.
[6]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4.
[7][粱]僧祐编撰,刘立夫译注.弘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51.
[8]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2.
[9]张松辉.庄子考辩[M].湖南:岳麓书社,1997:206-207.
[10]释道安著,胡中才译注.道安著作译注[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156.
[11]龚隽.佛——觉悟与迷情[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84.
[12]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6:96.
[13]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71.
[14]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58.
[15]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26.
[16]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536-537.
[17][日]铃木大拙.禅与生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40.
[18]何兆武主编.中国印象(下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