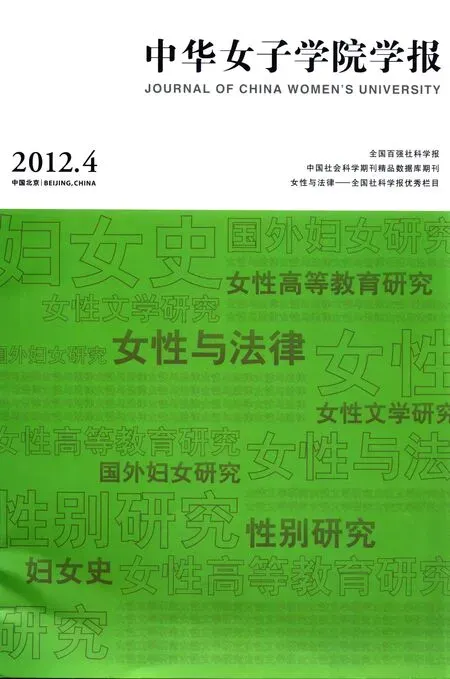差异与共生——《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评议
韩贺南
杨国才教授积累多年、撰修数载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该书的面世,使女性学学术园地又增佳作,可喜可贺!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作为一股颇具批判力、创造力的学术力量,异军突起。从学理方面来看,女性主义认识论(知识论)是女性主义学术的逻辑起点,而女性主义认识论又源于人们对女性现实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女性主义认为,知识再生产着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要推动性别平等必得改造知识。与一般的知识论关注“知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1]1不同,女性主义认识论关注谁是知识的主体,谁拥有知识,谁的知识可以成为知识等问题,注重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权力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和知识对权力关系的建构,质疑现存知识的真理性。女性主义认为现存知识存在系统的偏颇。因为,传统的知识是以男性为主体建构的,缺乏女性的立场和经验。女性主义的学术目标,就是要挑战传统,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
因此,女性主义学术秉承社会平等的价值观,使它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注重性别与阶级、民族和种族的“结盟”,或将性别、阶级、民族作为分析社会的重要范畴,关注它们之间纷杂交错的关系,强调社会变革中各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致力于促进社会平等。
中国妇女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学理上,主要承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传统。同时,借鉴在中国重建的社会学以及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理论;在实践上回应中国改革开放中凸显的性别歧视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性别(Gender)概念传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叶(’95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社会性别成为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与范畴,女权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女性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使用女性学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女权/女性主义学术逐渐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杨国才教授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一书,就是中国女性学和女性主义学术力量孕育的成果,是中国女性学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结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学术园地的绚丽奇葩。
二、作者其人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一书作者杨国才教授,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于云南大理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白族之家。大理美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民族文化滋养了她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热情奔放的个性。除良好的家教、学校教育以外,丰富的社会实践积淀了她的学术素养。她在后记中写道:“父亲从小让我读书,教育我‘打铁要本身硬’,让我读书要刻苦、做事要认真、做人要诚实。”[2]7多年以来,她一直保持白族女性热情、大方、诚恳、厚道、勤劳的风格,关注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她也正是在回到少数民族妇女中去推动少数民族妇女脱贫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少数民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和织绣产品走向市场的经验,进一步看到少数民族妇女工艺的精湛和作品的精美;正是在与少数民族妇女共同参与的社会性别培训中,她深切地感受到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并且,她不断为少数民族妇女的智慧与创造而感动,从而萌生起通过研究少数民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与服饰,探究其丰富的知识与悠久的文化之动机。
在学理层面上,她致力于少数民族女性学的建构与发展,理论积累与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她完成这部优秀成果的坚实基础。此外,作者历任云南省第九、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使她具有促进性别平等、社会平等的责任感:作为少数民族女性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代表为人民”是她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少数民族的女儿,她把为少数民族和妇女,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代言作为她参政议政的任务;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女性,她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与民族文化的自觉,把记录、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和文化,作为责无旁贷的责任和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些都是该著作诞生的重要原因。
就学术积累而言,杨国才教授善于借鉴先进理论与方法,勤于寻找各种资源。20世纪80—90年代,她涉猎的研究领域颇为宽泛,主要有少数民族哲学、妇女的生产与生活,逐渐进入对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生存与发展、伦理道德、生育健康、教育、权益保护等问题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她不断转变观念,更新方法,不再把少数民族女性作为变量,而是作为主体。她回到少数民族女性之中,倾听少数民族姐妹们的心声,记录她们的知识和经验,着力于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在田野调查中收集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为完成此书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内容与观点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一书,首次提出少数民族妇女有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文化。她们的知识和文化就是传统手工艺及服饰的图案。该书主要阐释了少数民族女性知识的缘起和发展;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知识的内涵;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中的技艺知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样性;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关于本书选题的背景,作者开篇即言,并且在文中着力强调,由于深远的性别不平等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历史中缺少妇女的文化知识和经验的记载,少数民族女性更是在史书、教科书和其他文献资料中“缺席”与“失声”。而事实上,各民族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在场”。作者以妇女的知识证明:在中国这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人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中当然包含女性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而少数民族文化是由少数民族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女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知识的创造主体,她们的知识与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女性的文化知识,是其“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创造和积淀”[2]7,“它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过去的传统社会,而且在今天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存在,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2]7作者强调,“女性有文化知识,少数民族女性也有文化知识,这种文化和知识,具体表现在由女性创造和传承的女性民族民间手工艺和服饰上,这种文化,女性穿在身上,戴在头上,用在生产生活中。”[2]7本书正是要在抢救、再现、保护、传承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知识方面,发出女性的声音。
该书是在文化多样性与并存共生、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视角下,探究少数民族女性知识和文化的。作者认为,纵观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儒家文化又以父权制、宗法家族制为核心,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父权文化。儒家文化奉行封建宗法制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没有地位,是男子的附庸,女性文化被遮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更被隐没。与汉民族儒家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特性。在儒家文化传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之前,少数民族社会大都保留了母系文化的特点和遗迹。许多少数民族妇女生活在一个男女平等或者比较平等的平权社会,少数民族女性和男子一样是本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她们有权决定家庭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事情,有的甚至是家庭生产生活的掌控者。作者认为少数民族女性及其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建立在少数民族女性鲜明的主体性、个性、开放性基础之上的。少数民族妇女是本民族文化的开拓者和传承者。少数民族妇女文化的载体就是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和服饰。它凝聚着丰富的文化,是经典的文化符号,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瑰宝。它具有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宗教的内涵,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是各民族社会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再现,它记录并传承着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诸如,长期以来,将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古歌、史诗、创世神话等,以手工艺和服饰的形式在民间传承和传播,它是民族历史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形式。
四、特色与价值
该书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方法别致、图文并茂等特点。
首先,本书运用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所谓女性主义视角,不仅指该书彰显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与文化,填补历史文化中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知识与文化的空缺,而且突出体现为,发掘女性创造、记载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方式,从而揭示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差异性。具体说来,人们通常以为,历史学家主要运用文字工具,以史书、传记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形式记录历史,这才堪为历史科学与知识。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创造与记录历史的方式与男性具有相同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是因为女性具有与男性不同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与经验。该书发掘各民族女性织绣、轧染、印染在手工艺品和服饰上的无字的历史与文化,体现了女性主义看待历史的立场与方法。其女性主义视角主要体现为,一方面,确认“无字”的织绣与服饰可以看作是具有价值的知识与文化,是对历史的记录,这是对女性创造历史与文化的“承认”,承认既是对女性在历史与文化中的主体性的认同,也是对“文化生产领域”“社会等级”的挑战;[3]9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女性记录历史与文化独特方式的认可,即是说,民间传统手工艺与服饰是女性记录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方式。因此,该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该书的学理支撑具有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因素。
其次,该书的内容特色主要表现在:对民间传统手工艺与服饰的阐释方面,着力于技术与文化的交融。一方面,作者力图详尽地说明各民族传统手工艺与服饰的制作程序与技术,另一方面着力阐释文化含义。例如该书关于苗族妇女百褶裙、背牌技术与文化解读,可窥见一斑。首先,作者详细描述百褶裙的样态,包括面料、颜色、尺寸、工艺等。文中谈到:“通常裙边及腰均有2厘米宽的蜡染几何纹,二者之间为大面积白地,蜡染内边各加0.5厘米宽的布条,红黑各半。白地有上下两组四环绳辫纹和四组红黑二色布条的平行线段,第三组为两段,第二、四组为三段。每段长约18厘米。中部三段红黄相间,叠压并行的布条从上而下依次代表黄河(上朗)、平原(布点)、长江(下朗),白地象征洁净的天空。”[2]52这样细致入微的描述再配以清晰的图案,就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它的样态。同时,再加以解释它的图案(符号)象征意义,进一步阐释了它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作者如是说:“一条裙子,就是一幅表示苗族田园山川河流的地图。”对其历史意义的解释,作者引用了苗族的古歌:
我们的姑娘聪明又智慧,
我们织出漂亮的裙子,
像平坦的泽国水乡,
像望不到边的田埂。
道路宽敞四通八达,
我们裙子上的条条花纹,
就是我们原来的田园,
那阡陌纵横的田地,
那流水清清好插秧的地方。[4]77
该书关于少数民族妇女的民间手工艺和服饰的文化解释,常常采取“互文”的方式,即将民间艺术与服饰结合起来,将民间艺术与服饰文化的各个文化单位(文化质点)联系起来,这是本书在写作方法上的特色。比如,将苗族妇女的百褶裙与背牌的文化意义结合起来呈现。书中写道:苗族妇女的背牌,有的认为其象征城池,有的则认为象征苗王蚩尤的大印。[2]52关于符号象征意义的由来,作者谈道:“这是因为,苗族历史上迁徙途中战事频繁,队伍容易混乱,为了避免错杀自己人,苗王就在人们背上盖上苗王大印以作标记,便于识别。”[2]52背牌的制作,是用白、红、绿、黄、橙、蓝、紫多色丝线挑刺而成,黑布底,四方形几何图案。前后两块背牌,用布或绸缎连接,胸前一块略小。背上的背牌由三块不同图案拼成,中间一块为背牌心,四方形,中央是三角形,八角星。也有“井”字形的,还有两个四方形呈交叉角的,俨若一方印鉴。将苗族妇女百褶裙、背牌的技术与文化内涵联系起来考虑,可以看到更为丰富的意义,诸如,在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关于战争、地域、民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开启通过实物文化研究向文化系统拓进的渠道。
该书的主要价值有两方面,一是学术价值,二是实践价值。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其一,它探究了少数民族女性民间工艺与服饰的历史文化意义,彰显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与文化,纠正这一知识领域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知识的偏差;其二,探讨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知识在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现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与知识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成分,是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核心元素。主要依据是少数民族女性民间工艺与服饰是在生产生活中的创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活动,基于这“第一活动”的文化选择是文化体系中的基础成分。同时,少数民族女性民间工艺与服饰所承载的厚朴、绚丽、多样等文化个性,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等特征。该书的实践价值主要在于,其在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女性知识与文化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如前所言,本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民间工艺与服饰的技术、符号意义,历史传承,所涉及的其他文化形式,诸如神话故事、古诗、古歌、宗教信仰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和服饰,就是各民族社会不同时期生产生活的体现。它反映了人类意识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它是各民族某种自然灵物崇拜或宗教信仰的“遗留”,蕴藏着各少数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它以不同的符号表现不同民族在过去时代的生活影像,反映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各民族的等级差别和财产观念;它是民族性格、心理的折射。这些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对它的抢救和保留价值无量。
该书呈现了许多具有经典文化意义的图片,堪称图文并茂,首次系统地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和文化,是一本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著作。
然而,少数民族女性民间工艺与服饰所承载的文化可谓丰厚悠远,余韵无穷。许多文化符号的解释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是需要拓展新的方法论与方法,从而进一步形成文化系统意义上的解释。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异同,有些观点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书所承载的内容已够丰厚,不忍求全责备,唯待学者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丰富女性学学术园地!以此恭贺共勉!
[1]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杨国才.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潘光华.苗族古歌[J].民间文学论坛,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