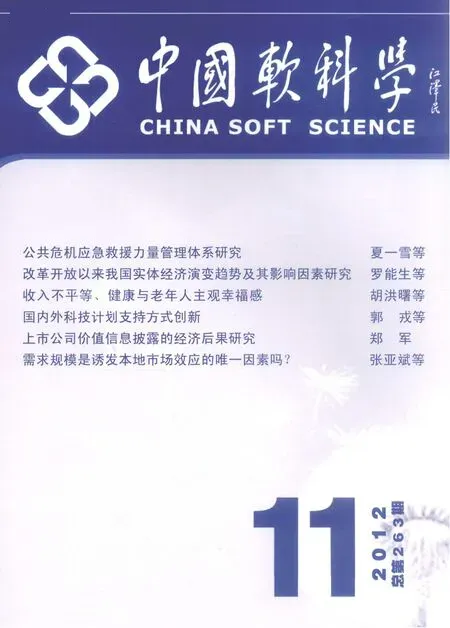政府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双门槛效应研究
刘渝琳,刘 明
(1.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044;2.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44)
一、引言
政府优惠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等的重要工具,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如欧盟为消除成员国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德国、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为消除本国内部差距,均采取了各种优惠政策去促进其区域经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各省、市也相继实施了许多优惠政策。至2008年,我国已在全国设立5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14 个边境经济合作区①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报告(2008)。,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相继成立,开放区域已经扩大到全国,并且我国政府仍在继续扩大开放区域。这些区域优惠政策的出台旨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然而其实际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政府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研究。Harrison(1996)[1]、Stéphane(2001)[2]等学者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视角出发,对优惠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适当的优惠政策能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先进技术,同时本地企业可以从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中获取新技术,在引进和吸收发达地区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另一方面,优惠政策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市场化,扩大区域内市场容量,提升区域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回报,促进该区域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此外,Krugman(1991a)[3]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通过强调经济集聚和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扩散,在一定条件下,优惠政策能打破地理位置决定论,降低欠发达地区生产成本,促使该地区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基于这类早期的研究模型,Martin(1999)[4]、Puga(2002)[5]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基础设施、技术与生产等方面的补贴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享有政府优惠政策的地区通常会加快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该地区的运输成本、工资水平及地租,引导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向该地区转移,扩大当地市场容量,最终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在对我国优惠政策的研究文献中,Fleisher & Chen(1997)[6]、Démurger(2002)[7]等国外学者研究表明优惠政策有弥补我国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扩大就业等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Kim & Knaap(2001)[8]、Fujita& Hu(2001)[9]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政府优惠政策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王小鲁、樊纲(2004)[10]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进行了分析,认为优惠政策等因素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11]利用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认为政府优惠政策是导致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阙善栋、刘海峰(2007)[12]分析认为优惠政策可以通过弥补私人边际成本的方式使经济活动满足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这一效率条件,从而矫正市场失灵,获取规模经济、科技进步、先进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素质提高以及环境条件的改善等诸多外部效应,带来长远动态经济利益。Yanqing Jiang(2011)[13]通过构建技术溢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优惠政策可以获取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促进本地区的生产效率,显著促进开放地区的经济增长。
然而,尽管政府优惠政策能带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技术水平、扩大劳动就业等正面效应,但优惠政策引起的负效应也日益受到关注。Boldrin& Canova (2001)[14]、Midelfart-Knarvik & Overman (2002)[15]从效率角度出发,认为尽管优惠政策能增加投资、扩大就业,但优惠政策所涉及的财政支出是无效率的资源再分配,并没有显著提升优惠区域的生产效率。Cristina & Guido(2011)[16]分析了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优惠政策,结论显示该地区的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被补贴企业的总产出和当地就业水平,但与未被补贴企业相比,其全要素生产率更低,这种优惠政策对长期生产率和增长的消极影响极大抵消了短期的正面影响。国内学者针对我国的优惠政策的负效应也进行了研究,沈桂龙、于蕾(2005)[17]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反思了我国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加剧国内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等问题。杨玉明、杨福明(2007)[18]研究认为部分优惠政策会给企业带来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对国内企业的成长产生压制作用,最终会降低我国国内的社会总福利水平。罗云辉(2009)[19]认为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竞相让利于投资方来吸引外来资金,为争取项目进驻本地,甚至不惜让渡掉部分或近乎全部正面效应。
目前,关于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在理论上仍没有一致的结论,且以往研究较少考虑到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不一致性。在实证方面,以往文献主要从线性关系来验证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较少考虑到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效应。为弥补这些不足,本文借鉴Clemens & Bernd(2006)[20]的理论分析思路,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地区政府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与以往研究仅从线性关系进行实证不同,本文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我国1985-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优惠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二、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模型
本文假定一国存在东、西部两个地区,东部为经济发达地区,西部为经济落后地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和地租成本均高于西部地区。该国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且各地区均存在一个地方政府。全社会的商品由垄断企业提供,企业所需生产要素为劳动力和土地,初始条件下,垄断企业集中在东部地区,由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均低于东部,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可能将生产设施迁移至西部地区,会因在西部地区新建工厂而产生一个固定开办费用。为分析方便,将该国总家庭数量标准化为1,假定东部地区家庭数为n,则西部地区家庭数为1-n,每个地区对商品的需求量与该地区的家庭数量严格成比例①现实情况中,对商品的需求不一定与该地区家庭数量严格成比例,例如城市家庭对商品的人均消费可能高于农村家庭,但该假设并不影响对理论机制的阐述。在现实分析时,只需对不同人均消费水平的家庭赋予相应的权重,便可以解决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人均消费不一致等问题。。
(一)家庭部门
借助 Horstmann & Markusen (1992)[21]、Markusen et al.(1995)[22]等学者频繁采用的效用函数,可得家庭的效用函数:

其中,i∈(e,w),分别表示东、西部地区,Ui表示i 地区的家庭效用, f 表示货币化商品,ci表示i 地区边际劳动负效用,li表示i 地区家庭的劳动供应数量,θ 表示分布在(0,1)区间内的差异化商品指数,qi(θ)是i 地区的一组差异化消费品的数量。
每个家庭外生拥有m 单位货币化商品,i 地区的家庭获得pi的利润收入。因东部地区视为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视为经济落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可假定企业主集中在东部地区,有pw=0,于是可以得到地区家庭的预算约束:

上式中,wi为地区的工资水平,p(θ)表示θ 种商品对应的价格,Ti表示i 地区家庭向政府交纳的税收额,在(2)式的预算约束下,对(1)式最大化,可得到价格需求函数:

加总各地区所有家庭的需求函数,由于该国总家庭数为1,得到:

(二)企业部门
一旦企业在某一地区投资设厂,会因开办新的厂房而产生一个固定开办费用F,企业开始生产后,进入成本F 成为沉没成本②本文分析思路是采用逆序分析的方法,先假设市场已经达到均衡,再分析均衡时的固定开办费用的临界值,在此基础上分析最优的政府优惠政策水平。故先将固定开办费用视为沉没成本,后面另行计算。,于是可得企业在i地区投资设厂后的利润:

其中,ri表示i 地区单位产出的地租水平,t 为单位产出税收额①此处的税收额指中央政府统一设定的税收额,各地区该税额相等,将中央对部分地区的税收减免优惠视为地方优惠政策补贴,不被包括在该税收额中。,将(4)式代入(5)式,可求出企业利润最大时的均衡需求:

均衡价格为:

将(6)和(7)式代入(5)式,可得企业在地区投资设厂后的最大利润:

从(6)-(8)式可以看出,不考虑企业的固定开办费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与补贴差异,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由各地区的工资和地租水平决定。
(三)政府部门
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实施针对企业投资设厂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完善市场环境等措施直接或间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吸引区域外企业投资设厂。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综合评估从政府优惠政策和工资差异中的获益,选择获利最大的地区投资设厂。如果企业选择迁移,则重新迁移会产生新的固定开办费用F(θ),不同企业所产生的固定开办费用不同,有F(θ)分布于区间(Fmin(θ),Fmax(θ))。企业在进行区位决策时,将权衡迁移后的获利与因迁移而产生的固定开办费用,会出现固定开办费用的临界值F*(θ),当固定开办费用小于F*(θ)的企业将选择工资水平更低的西部地区投资,大于F*(θ)的企业选择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继续生产或进行新的投资②在我国许多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外资可以选择在东部或西部投资设厂,无论在哪一地区投资都会产生固定开办费用,但两地区的优惠政策、土地成本等存在差异,会导致外资在两个地区投资所产生的固定开办费用不同,为将外资引入本模型,可视外资的重新迁移产生的固定开办费用为F=Fe-Fw。此时,可以将外资视为已在东部发达地区投资设厂,使用与分析东部地区资本同样的方法分析外资的区位选择。。当企业分别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生产所得利润相同时,可以得到临界值F*(θ),于是存在均衡公式:

上式中,Se(θ)、Sw(θ)分别表示东、西部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③将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的税收减免、完善市场环境等措施量化为地方政府优惠政策补贴。。将(8)式代入(9)式,可以得到④对生产各类商品的企业而言,在同一地区生产时,商品的均衡数量、价格和利润服从一致性分布,故为简化分析,可去掉商品差异化指数θ。:

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想通过实施恰当的优惠政策来实现本地区福利最大化,必然需要设定合理的政府补贴水平来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入。由(10)式可知,如果找出东、西部地区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固定开办费用F*,则可知道各地方政府的最优补贴。据此,先构建东部地区的福利函数如下:

在(11)式右边,前两项表示东部企业迁往西部地区生产时,东部地区的消费者获取的剩余和企业主获得利润,后两项表示东部企业仍留在当地生产时,东部地区的消费者获取的剩余和企业主获得的利润。当时,F*为东部地区福利最大化时向西部迁移的固定开办费用临界值,将F*值代入(10)式,可得东部地区福利最大化时的地方政府优惠补贴:

因东部地区为发达地区,西部为落后地区,有we<ww和re>rw,根据(12)式,等式右边括号内第一项反映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与土地市场扭曲程度,其值为负,第二项表示东部地区内部劳动力扭曲程度,其值为正。假定各地区均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则当东部地区仍处于发展中时,会存在大量非意愿失业,即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We远大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Ce,如果东、西部地区间的工资、地租水平差距不大时,有>0,此时,东部地方政府增大本地福利的最优选择是继续实施优惠政策,补贴本地区现存企业和吸引外资流入。当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市场会存在少量非意愿性失业,且东部地区工资、地租水平会远高于西部地区,有<0,此时,东部地方政府增大本地福利的最优选择不是继续实施优惠政策,而是通过各种措施鼓励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
类似于东部地方政府如何选择优惠政策的分析思路,构建西部地区的福利函数:

与东部地区的福利函数相似,(13)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在西部生产时西部地区消费者的剩余,第二项为西部地方政府对企业提供的优惠补贴,由于企业主集中在东部地区,该补贴以利润的形式被东部企业主获得,需从西部地区福利中扣除,第三项表示仍在东部生产时,西部消费者的剩余。最大化西部地区的福利,可得:= (1-
由于西部为落后地区,有ww<we和γw<re,知(14)式右边括号内第一项为正,表示通过西部地方政府的优惠补贴,可削减东、西部间的工资、地租水平扭曲,增加西部地区福利水平;又因西部地区存在大量非意愿性失业,有ww>cw,可得第二项也为正,反映了西部地方政府实施优惠补贴的第二个原因。由于两式均为正,可得>0,即西部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优惠政策,可以吸引区域外企业进入,从而最大化本地福利水平。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工资、地租水平低,非意愿性失业严重时,该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吸引区域外资金的优惠政策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当某区域经济处于发展中,工资、地租及非意愿性失业处于合理水平时,继续实施优惠政策仍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当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开始出现高人力成本、高地租等外部负效应时,再继续实施优惠政策会导致企业外部环境恶化、政府税收流失等不利后果,降低该地区的福利水平。目前,我国各地区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均争相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入,而这些优惠政策是否都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需进一步研究。
三、模型的构建与门槛值确定方法
(一)双门槛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根据(12)和(14)式的结论可知,要衡量政府优惠政策对某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时,需考虑该地区的工资、地租及企业固定开办费用等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一些因素,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随着这些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区间效应。为了避免利用线性回归分析此问题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Hansen(1999)[23]发展的门槛回归模型,进而更科学地研究各地区不同政府优惠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地区呈现出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间的工资、地租等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许多因素也因此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可采用双门槛①Hansen(1999)将仅有一个门槛值的模型定义为单门槛(Single Threshold)模型,有两个门槛值的模型定义为双门槛(Double Thresholds)模型。面板模型将经济水平划分为三个阶段,据此,本文将基础计量模型设定为:

在(15)式中,PGDP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i 地区t年的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GPi,t为解释变量,代表i 地区t年政府优惠政策水平;SIi,t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变量,本文为各地区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γ1、γ2为特定的门槛值,内生地将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划分;I(·)为指标函数;Xi,t为一组对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各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利用外商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出口状况和科教文卫投入水平等;a 为相应的系数向量;μi用于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体效应,如地理条件、思想观念等不易量化因素;εi,t代表i地区t年的随机误差项。
上述(15)式中涉及的关键变量包括两类,一类是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优惠政策水平;另一类是控制变量,即向量中所包含的其他影响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的变量,有关代理变量及数据来源的说明如下:
1.核心变量的选取与描述。(1)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消除通膨因素影响,采用各地区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2)政府优惠政策。采用刘渝琳、刘明(2011)[24]构建的政府优惠投资指数②刘渝琳、刘明(2011)计算了1985-2008年间的政府优惠政策指数,2009 和2010年的优惠政策指数根据同样方法计算而得。来衡量各地区的优惠政策水平。
2.控制变量选取与描述。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Martin(2001)[25]、Durlauf(2005)[26]分别以全球88 个和102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别得出12 个和43 个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变量。而Krugman(1991b)[27]、Fujita(2001)[9]等人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认为各地区需求、运输成本等因素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本文总结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国内部分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选取了如下影响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控制变量:(1)地区需求(C)。C 为各地区最终消费支出,反应各地区需求状况。(2)人力资本(EM)。EM 为各地区就业人员数,反应人力资本状况;(3)外商投资(FDI)。FDI 为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人力资本投资水平(GE)。GE 为各地区政府对科教文卫的财政支出水平,反应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5)交通成本(GCS)。为反应各地区区域内交通成本状况,本文用各地区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总产值进行衡量;(6)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FE)。(FE)为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水平;(7)对外开放度(EX)。EX 为各地区出口额。
3.数据来源及处理。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我国29 个省③西藏和重庆市的数据不完整,未将其包括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1985-2010年间面板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1985-2008年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0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部分年份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各省的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而得;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根据名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计算所得,2009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摘编自《中国统计摘要2011》,2010年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年鉴2011》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替代。
(二)门槛值的确定
门槛回归模型是非线性模型,其估计方法与线性模型有所区别。对于给定的门槛值,按门槛值的划分原理,可以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得到βi(i=0,1,…6)的估计值。为了得到参数估计量,首先,需要计算单门槛值,从每个观察值减去其组内平均值以消除个体效应,即

变换后的模型为:


对于给定的门槛值γ,可以采用OLS 估计(17)式得到β 的估计值:

相应的残差平方和表示如下:

通过最小化(20)式对应的S1(γ)值来获得的估计值:


得到参数估计后,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门槛效应是否显著,原假设为Ho∶β1=β2,备择假设为H1∶β1≠β2,检验统计量为:

其中,S0为不存在门槛值条件下残差项平方和,为具有门槛值条件下的残差平方和。门槛值γ 是无法识别的,因此,F1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Hansen(1999)建议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方法来获得其渐进分布,从而构造其P 值。

LR 为非标准正态分布,但Hansen 提供了一个公式来计算其置信区间,即当LR1(γ)≤c(α)时,不能拒绝原假设。其中c(∝)=- 2ln(1-,其中,α 表示显著性水平。
以上假设模型中仅存在单一门槛值,而双门槛模型的假设检验与单一门槛情况下类似,此文不再赘述。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为更准确描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优惠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估计和检验门槛回归模型来进行验证。本文采用STATA11.0 软件实现对上述模型的估计。
(一)检验结果
估计门槛值时,需要确定是否存在双门槛值。首先,运用格子搜索的方法寻找门槛值①门槛值中存在极大值与极小值,这些个体样本会显著影响实证结论,造成结论偏误。因此,需将这些异常值排除。借鉴Hansen(1999)的格子搜索方法,本文先将门槛变量按升序排列,然后取门槛变量的序列区间为(5%,95%)。假定样本总数为N,门槛搜索值为n,则去掉异常值后样本序列区间为(0.05N,0.95N),该序列区间对应的样本值区间为(Xmin,Xmax),则所取门槛值分别为Xj =Xmin +(j-1)(Xmax-Xmin/n),其中,j=1,2,…,n 。考虑到本文的样本数量,将门槛搜索值设为100。,即把样本按照门槛变量SIi,t按升序进行排列,然后选取不同的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作为门槛值逐一对模型进行估计并计算残差,残差平方和最小时所对应的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即为门槛估计值。依次对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和两个门槛的原假设下对模型(15)进行估计,得到F 统计值。再采用“自抽样法”方法模拟F 统计量的渐近分布及临界值(实证分析重复次数为1000 次),从而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1)显示,单门槛和双门槛效应都非常显著,相应的自抽样P 值分别为0.0810 和0.0000,存在双门槛值。

表1 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门槛模型的原理,门槛估计值是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 为零时γ 的取值,为更清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的构造过程,分别绘制了两个门槛估计值的似然比函数图(见图1、图2),图中的实线为门槛变量似然比,虚线为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7.35)。两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相应的95%置信区间见表2,结果表明两个门槛估计值在95%置信区间下分别是2095.3973 和7296.6870。

表2 门槛值估计结果
(二)实证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政府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按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划分成三个阶段,依次为经济欠发达地区(SIi,t≤2095.3973)、发展中地区(2095.3973 <SIi,t≤7296.6870)和发达地区(SIi,t≥7296.6870)。分别对三类地区进行门槛回归估计,可得到门槛回归结果(见表3)。

图1 第一门槛的估计值

图2 第二门槛的估计值

表3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政府优惠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当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小于2095.3973 亿元时,即相应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政府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会促进当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13.88%,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小;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提升,且提升幅度很大,政府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会促进当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48.85%;但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越过7296.6870 亿元这一门槛值后,即相应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优惠政策指数每增长1%,会促进当地人均生产总值增长153.72%,可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合理的政府优惠政策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会大幅降低。这也证实了相关研究结论:政府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作用效果先是增加,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极值后,如果不对优惠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其作用效果会显著下降。虽然对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区而言,这一极值有所不同,但都表明政府优惠政策并非越多越好,多于或少于这一极值的政府优惠政策都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三)对我国优惠政策的具体分析
1.对我国各地区优惠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
实证结论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优惠政策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会有所不同。为比较我国各地区优惠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取1985-2010年间各省份政府优惠政策指数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值进行比较①各地区某一年的优惠政策指数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取1985-2010年间的平均值,降低一些随机因素的干扰。,为直观比较两者的发展水平,先对两者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结果见表4。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辽宁、山东和福建9 个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标准化值均大于0.30,除北京、天津两直辖市外,其余7 个省份的优惠政策指数标准化值均大于0.30,平均值为0.55;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4 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标准化值在0.20-0.30 之间,优惠政策的标准化值在0.17-0.24 间,平均值为0.22;新疆、湖北、山西等18 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标准化值均低于0.20,除新疆、海南、广西和云南4 个边疆省份的优惠政策指数标准化值较高外,其余14 省份的平均值仅为0.04。
图3 为对两者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直观比较图,图中横轴为地区序号,与表4中的各省份相对应,纵轴为标准化值。该图显示各地区优惠政策指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较为相似,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应的优惠政策水平也越高,反之亦然。具体而言,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优惠政策水平也最高,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省份的政府优惠政策水平次之,而湖北、河南、陕西、贵州、宁夏、甘肃等广大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的优惠政策水平最低。清晰表明我国各地区优惠政策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呈梯状递减,而没根据各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表4 标准化结果
2.根据实证结论对政府优惠政策的双门槛效应分析。

图3 各地区优惠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关于双门槛效应的实证结论显示,我国各地区之间及各地区内不同年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图4 反映了我国各地区在三个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如图所示,1985-1995年间,我国所有省份的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在这段时间内的平均值均低于第一个门槛值2095.3973亿元,各地区经济处于欠发达区间,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低廉,此时,政府优惠政策可以加大开放度、完善投资环境,对各地区区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有较强吸引力,优惠政策开始显现其正向促进作用。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1996-2005年间,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份越过了第一个门槛值,进入第二区间,且随着我国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开始全面开放,到2006-2010年间,除甘肃、贵州、宁夏、青海、新疆等少数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仍为欠发达地区,其余东、中部省份均超出了第一个门槛值,即大部分省份处于经济发展中地区,此时,政府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会促进当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48.85%,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开放程度得到提高、投资环境不断被完善,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吸引了国内外大量资金、技术及人才,并较好利用了当地的土地资源与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仍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但2006-2010年间,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等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迈过第二个门槛值7296.6870亿元,经济处于初步发达阶段,优惠政策指数每增长1%,会促进当地人均生产总值增长153.72%,与处于第二区间的发展中地区相比,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作用降低了195.13%。此时,相应地区开始出现高人力成本、高地租成本与交通拥挤等外部负效应,对区域外资金的吸引力大大减弱,如果政府继续提供以往的优惠政策,就可能引起降低当地税收、对本地区资金产生“挤出效应”与造成更严重的交通拥挤等外部负效应,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开始出现政府优惠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下降,甚至产生负效应。

图4 各地区三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区域间存在工资、地租和就业水平等的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导致政府优惠政策对本地区福利的促进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当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通过实施减免税收、完善基础设施等优惠政策,可消减地区间的工资、地租水平的扭曲程度,吸收区域外企业进入,增加本地区的福利水平;当某区域经济较发达时,劳动力市场会存在少量非意愿性失业,且其工资、地租水平往往高于落后地区,继续实施优惠政策会加剧地区间的工资、地租水平扭曲,导致企业外部环境恶化、政府税收流失等不利后果,降低该地区的福利水平。为避免以往学者采用线性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了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当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在2095.3973-7296.6870 亿元时,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会促进人均生产总值增长348.85%,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当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高于7296.6870 亿元时,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大幅下降。该结论进一步证实,政府优惠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
上述结论也表明,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均存在不同的最优优惠政策水平。为实现本地区福利最大化,应综合考虑本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权衡优惠政策的成本与效益,实施合理的优惠政策,有效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福利。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开放时间较长,地理位置优越,给予了大量政府优惠政策,经济发展迅速。但伴随大量企业聚集,开始出现交通拥挤、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外部负效应,且区内资金充裕,继续实施普惠制的政府优惠政策,会带来降低税收、扭曲市场对资源配置等不利影响,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因此,这些地区应取消不合理优惠政策,有针对性地对高科技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环保产业等提供优惠政策,实现经济转型,降低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化发挥优惠政策对发达地区的经济促进作用;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政府优惠政策仍处于较低水平,优惠政策应更多向这些地区倾斜,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低工资、低地租等优势,将国外及东部发达地区剩余资金、技术及人才等生产要素吸引到中、西部地区,为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打下坚实基础。
[1]Harrison A.Opennes and Growth:A Time Series,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48(2):419-447.
[2]Stéphane D.The Opening Policy in China:Simulations of A Macroeconometric Model[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1,23(4):397-410.
[3]Krugman P.Geography and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1.
[4]Martin P.Public Policies,Regional Inequalities and Growth[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9,73(1):85-105.
[5]Puga D.European Regional Policies in Light of Recent Location Theo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2,2(4):372-406.
[6]Fleisher B M,Chen J.The Coast-Noncoast Income Gap,Productivity,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7,25(2):220-236.
[7]Démurger S,Sachs J D,Woo W T,BAO S,Chang G.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Loc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nd Having the Right Incentive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13(4):444-465.
[8]Kim T J,Knaap G.The Spatial Dispers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1952- 1985[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1,35(1):39-57.
[9]Fujita M,Dapeng H.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1.35(1):3-37.
[10]王小鲁,樊 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1):34-44.
[11]金 煜,陈 钊,陆 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6,(4):79-89.
[12]阙善栋,刘海峰.税收优惠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探讨[J].当代财经,2007,(6):36-39.
[13]Yanqing Jiang.Understanding Opennes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3):290-298.
[14]Boldrin M,Canova F.Inequality and Convergence:Reconsidering European Regional Policies[J].Economic Policy,2001,16(32):205-253.
[15]Midelfart-Knarvik K H,Overman H G.Deloc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Is Structural Spending Justified?[J].Economic Policy,2002,17(35):322-359.
[16]Cristina B,Guido P.How Are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in Private Firms Affected by Public Subsidy?Evidence from A Fegional Policy[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1,41(3):253-265.
[17]沈桂龙,于 蕾.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思考[J]. 世界经济研究,2005,(11):4-10.
[18]杨玉明,杨福明.对外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效应评价分析[J].经济问题,2007,(1):63-65.
[19]罗云辉. 地区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竞争与先发优势——基于声誉模型的解释[J]. 经济科学,2009,(11):96-106.
[20]Clemens F,Bernd H.Can Regional Policy in A Federation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6,90(3):499-511.
[21]Horstmann I J,Markusen J R.Endogenous Market Structur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Natura Facit Saltu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2,32(1- 2):109- 129.
[22]Markusen J R,Morey E R,Olewiler N.Competition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when Plan Locations are Endogenou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5,56(1):55- 77.
[23]Hansen 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345-368.
[24]刘渝琳,刘 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J]. 世界经济研究,2011,(6):3-9.
[25]Martin P,Ottaviano G.Growth and Agglomeration[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1,42(4):947-968.
[26]Durlauf S N,Johnson P A,Temple J R W.Growth Econometrics[C].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05,Vol.1A,Elsevier Press.
[27]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b,99(3):483-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