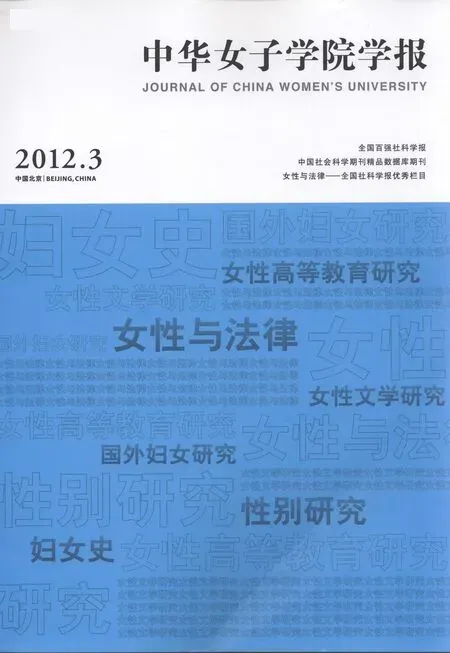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
李洁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
李洁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视角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的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大量普通女性和底层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历史建构过程之外,但是书写历史的神圣性常让人们遗忘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中挽救和建构妇女史。相比于文字材料,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在于对讲述者主体性的尊重和恢复,以及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起来的研究双方的平等关系。
口述历史;女性主义;妇女口述史;主体性;真实
口述凭证(Oral Testimony)古已有之,远古传说和歌谣就是其形式的一种。随着文字的出现和文献资料的兴起,口述凭证日益失去其在学术和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口述历史学方法才重新得以复兴。其标志一般被认为是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口述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更多的真实、一手经验以及目击证人,“通过对过去事件亲历者的访谈,达到历史重构的目的。”[1]前言然而逐渐地,这种追寻事物“原本面貌”的实体论倾向被削弱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口述历史并非要用其所发掘的‘事实’去替换先前的事实。而是要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尽管这种接受可能并不情愿——历史本身具有某种开放性。”[2]前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和使用口述历史学方法。口述历史学方法因其反思性、批判性和多元性获得了来自内地、台湾、香港等地女性主义研究者的青睐。近年来,在女性口述史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研究主要包括:李小江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妇女口述史研究”、台湾中研院近代中国女性口述史研究、美国加州大学贺萧(Gail Hershatter)教授与陕西省妇女研究所高小贤研究员合作进行的集体化时期妇女口述史研究,以及中国女性图书馆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国女性口述史研究,等等。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史料收集方式,为何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中国妇女史及女性主义研究较为广泛的采纳和使用?二者在关注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定位等方面是否存在某些天然的亲缘性?本文通过阐述口述史和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厘清二者在研究路径上的契合性,从而为推进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中口述史学的方法作出努力。
一、谁是历史的书写者
传统社会科学往往是知识精英在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建构的充斥着不平等和支配关系的知识体系。社会上层、主要族裔和成年男子掌握着文字、意识形态和传播媒介,并控制着知识和真理的话语权。似乎只有男性上层精英才能够书写历史,同时成为文献资料中的被书写者。而那些长期被主流历史所忽略的普通民众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却远离社会科学炫耀的殿堂。
图海纳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他说:“有谁在倾听那些被束缚者、被压迫者、被遗弃者、被剥削者、被征服者、被放逐者的声音?那些在石头上铭刻碑文,树立石碑,在纸草、羊皮和纸张上书写文字的人们却无法让他们的言行被记载。被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却包含着比泛黄的老旧地图更多的未知领域。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无尽的沉默并沉浸其中,正是这些沉默划定了所有知识的边界……”[3]217
与图海纳同期的福柯和德勒兹早就警醒过知识分子,他们并不能代表被权力压迫的、具有多样性反抗形式的民众——“那些行动和斗争的人”。[4]117因为归根结底,男性上层精英与社会底层、妇女和少数族裔是有着不同知识结构、文化意识和表达方式的群体。传统男性主流知识分子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无视社会中现存的支配关系,而成为权力压迫的帮凶。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认识到,“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5]1妇女史研究与口述史几乎同时崛起于20世纪下半叶。当历史学开始反思传统档案、书信、传记文学等文字史料局限性的时候,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妇女史研究也开始注意到女性史料在主流文献中的极度缺失。历史记载中,女性的身影往往被遮蔽于改朝换代、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的“男性历史”(His Story)之下,如同福柯笔下偶尔被权力之光照射到的阴暗角落一般。即便偶尔出现女性的身影,也大多都是由男性视角出发评价和记载的上流社会女性,而极少出现对少数族裔和底层普通女性的专门研究。[6]21由此,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出,妇女口述史的目的就在于“向男权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史学挑战、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来研究,通过重视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她们在历史上一贯的主观能动性,来揭示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7]86
二、历史承载的内容
传统历史学记载的内容多是有关改朝换代的政治精英史,或是推进人类经济、技术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少部分涉及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史。其中,关乎最普通的女性日常生活的琐碎事件往往极少成为“历史”关注的内容。
在这一方面,当我们以男性视角的主流历史框架去询问普通女性时,她们往往缺乏对宏大历史事件及变迁的明确认识和表述。方慧容在其研究中指出,许多农村的女性被访者并没有明确的历史时间感,她们更多的是与“大儿子出生那年”、“老二还没出生那会儿”一类的私人生活事件结合在一起。[8]48对大部分普通女性而言,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无序地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时间次序和边界,也看不出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关联。然而社会性别的研究视角提醒我们,这种叙述中的“无事件境”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性别过程的结果。正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普通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和正式场合之外,所以她们并没有形成被主流社会接受的表述方式、甚至是记忆框架(Frame)的资源和机会。
另一方面,尽管女性关于养育孩子、婆媳关系、料理家务和身体病痛的记忆是清晰、具体且鲜活的,但是这些描述却往往显得琐碎、狭促,无法成为主流历史记载的内容。台湾中研院历史所的游鑑明女士提出要打破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方式,从女性受访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访谈,并指出,“这类口述史却是家庭口述史的最佳素材。同时,藉由口述可以访问到生育文化、养生之道、家政技艺、理财或消费等观念,又能为经济史、文化史、或医疗史提供丰富素材。”[6]22
换言之,即便普通女性的记忆因其个体化和身体化,而与传统宏大历史叙事相去甚远、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妨碍女性“用身体、用生命去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9]287相反,任何一个历史变迁的经历者都应当有权利从他们/她们自身的角度描述和建构那段生活经历,以此呈现他们/她们个人和家庭生活与宏大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而不论这种描述是多么无足轻重、琐碎庸常。
三、如何看待“历史真实”
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学家认识到,相比于文字材料而言,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不在于它能够更好地保存过去。相反,就事实本身而言,口述材料必然是经过加工的。这原本是所有材料的共性,只不过书写的神圣性往往让人们遗忘这一点。与传统历史学研究漠视这样一种已存的权力关系不同,口述历史学不仅承认群体记忆在叙述历史过程中与事实本身的分离(Departure),而且将这种“分离”本身作为研究灵感的重要源泉。
在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波特利《路易吉之死》一文中,“历史”对一个工人的死亡事件出现了官方和群体记忆的几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形式。波特利指出,事件和回忆之间是一种同构异型的关系。之所以对相同的事件产生不同的叙述,是由于所有的叙述者都是在自己的立场上,以独特的语言策略对这一事件进行加工、阐释和呈现。[2]18-19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叙述与事实本身的背离而否认其价值。相反,从叙述者和事件的关系,叙述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以及叙述者用以普遍化先前事件的范畴等叙述形式,研究者可以透视出叙述者如何对过去赋予意义,如何将个体经历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以及人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换言之,研究者所关注的不仅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当时的人们想做什么、认为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现在看来当时做了什么。这时候,发生在叙述者之外的事件和叙述者内心的情感之间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事实”(Socail Fact)。
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对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生育史的研究中记录了一位被访者的历史记忆:“接生人家说,叫人坐地上,害怕把炕弄脏了,叫人坐地上,坐下人发晕,说是血迷心,眼看着鲜血流呀流几盆……”[10]314从“客观真实”的角度而言,一个成年人的血液在6000毫升左右,妇女在生产的过程中不可能流出“几盆”鲜血,因而这段口述材料是不可信的。但是从“社会事实”的角度而言,这段口述融合了女性对身体、生育和人类再生产过程的恐惧、担忧和害怕,是对其脆弱的社会处境、巨大的身心创伤以及经历人生重大转变的不确定性的直观且鲜明的表述!就此而言,这段历史表述具有情感真实和记载当时历史条件下妇女内心经历的不可磨灭的价值。
可见,与现代主流社会科学强调所谓的“客观真实”不同,女性主义和口述史方法的共性在于它们都给人的“主体性”留下了位置。所谓主体性,是个体用以表达其自身历史感的文化形式和过程,它同样拥有其自身的客观法则、结构和图示。[2]前言换言之,在女性主义者和口述史学家看来,叙述与事实的分离正是叙述者的主体所在。与其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客观性”遮蔽和否认主体性的存在,不如恢复人类讲述本身的立场和意义。因为已然发生的事件必然在群体的记忆中被不断地加工、阐释和改变,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自己的意义价值体系,最终作为一段传说、某种象征或特定的符号表达着群体的意愿和梦想。
郭于华在对集体化时期女性口述史的研究中,发现该时期的妇女对那样一段艰苦岁月的“集体记忆”却充满了愉悦、兴奋和集体欢腾的感受。[9]301此时,研究者提醒我们注意到,记述者的作用不在于从表面上否定这些口述历史所表达的情绪与当时客观环境之间的不一致,而在于认识到这些口述历史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真实,以及造成这种心理感受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何在?正是这些“误识”(Misunderstanding)和迷思表达了这段历史讲述者所有的梦想、愿望、欢乐和痛苦。在这些看似“谬误”的背后,是讲述者自身的情感,他们/她们对事件的参与,以及事件本身对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四、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对意境和主体性的承认与关注进而意味着研究双方关系的改变。传统的社会科学要求研究者以一种外在、客观和公正的姿态去评述社会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以一种“全能全知”(Omniscient)的第三人称身份出现在研究作品之中,将自身视为真理的代言。
在口述历史和女性主义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被放在了更加平等的位置上。口述历史学不再标榜历史的独一无二性,而是承认一种开放的可能。叙述者不但回忆过去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可以发表自己有关过去事件的解释。而研究者的任务则是投入到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情境之中,再现社会历史的“多重声部”,将他人(Other)作为主体加以表达。口述历史学家指出,尽管口述历史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体,但是不同讲述者之间片面性和局部性的碰撞,反而是口述历史最大的魅力所在。[2]57-58与此相似,女性主义研究也强调女性参与知识建构的过程,让群体成员本身承担着生产知识的目标,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打破传统知识体系的话语权威,而让女性真正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
此外,与主流社会科学家客观、外在、不干预的立场完全不同,女性主义和口述历史学方法都将自身视为行动主体,即研究者是一定知识资源的占有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研究对象发生影响。通过与被访者的沟通和交流,研究者希望介入到人们揭示自己生活和周围世界的过程中,以期影响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变迁。
当下,口述历史学家已就下述观点达成共识:有关过去的知识和解释对当今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非常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在对过去进行回忆和解释的过程中,他们对个体进行赋权(Empowerment),并协助边缘社会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口述史已经被应用于帮助老人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帮助疾病患者重新树立自信,帮助社区居民增强个人和集体认同,以及为工人、妇女和移民群体争取应有的社会福利和支持。[11]213类似地,女性主义学者也强调妇女口述史的意义不只在于将被访者看作资料收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妇女口述史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即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的自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7]85,并最终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参与。
没有女性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正如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一样。然而,书写方式记载的女性史料如此之少,这就使得女性主义学者需要借助于口述历史的方法去拓展史料的收集。在口述历史材料的收集和使用过程中,女性主义学者和口述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除了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之外,两者的亲缘性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两者都开拓了历史研究所承载的内容;强调对被访者主体性的恢复;要求改变研究双方的不平等关系。正是由于这些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亲缘性,催生了中国妇女口述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1]Perks Robert,Thomson Alistair.The Oral History Reader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rdge,1998.
[2]Portelli Alessandro.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
[3]Touraine Alain.The Voice and the Eye: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福柯,德勒兹.知识分子与权力[A].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李小江.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N].光明日报,2002-08-06.
[6]游鑑明.她们的声音: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M].台北:五南文库,2009.
[7]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J].浙江学刊,1999, (6).
[8]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D].北京大学,1997.
[9]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A].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0]贺萧.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A].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Bornat,J..Reminiscence Reviewed:Perspectives,Evaluations,Achievements[M].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责任编辑:张艳玲
O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Oral History and Feminism
LI Jie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oral history and feminism in terms of research subject,substance,view on truth,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er and subject.Both share the view that a large number of ordinary women and low-level people are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history due to various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However,this is often forgotten due to the sanctity of written history.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oral history can help us to reconstruct women’s history from the everyday life narration of women.It is in the equal relationship of the researcher and research subject that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oral history resources lies.
oral history;feminism;women history;subjective;truth
10.3969/j.issn.1007-3698.2012.03.017
2012-03-12
C913.68
A
1007-3698(2012)03-0094-04
李洁,女,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研究方法。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