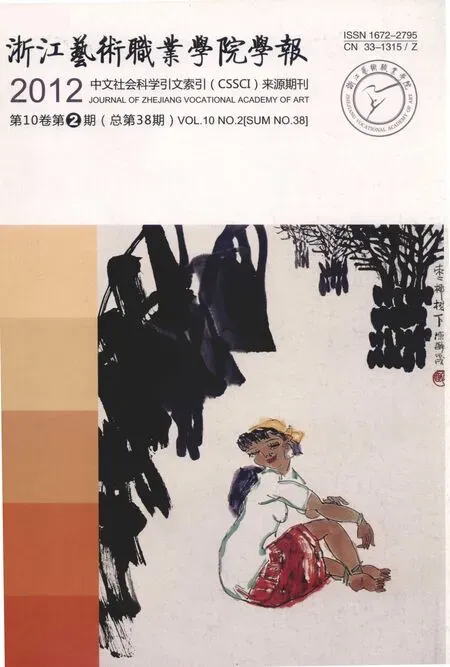清代戏曲思潮的演变*
周立波
明末清初,一批思想家将“人欲”与天理并提,发展成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受其影响,苏州派剧作家着眼于市井平民,传统的才子佳人戏受到挑战。而一批正统文人剧作家则以古寓今,以戏曲寄托自己对故国的追思。更有一些戏剧家以戏曲为业,更加注重戏曲舞台的实际演出效果。到清中叶,思想界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出现了追求抒发个人性情的性灵说,另一方面出现了继承实学思想的汉学。影响到戏曲界,戏曲作品出现了一方面夸大教化功能的剧本,另一方面较以前更加注重舞台的艺术实践。短小单元的呈现逐步取代长篇大戏的演出。单折杂剧创作开始兴盛,折子戏成为剧场的主导。乾隆之后,清朝的衰落与思想界的活跃形成巨大反差,“变革”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一批思想家向传统不变的祖宗之法发起了挑战。主张改革旧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洋务派则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维新思想家则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主张彻底变革旧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维新思想仍在继续。在戏曲领域,经过花雅之争后,花部取代了雅部的地位,尤其是京剧的兴盛直接导致了戏曲改良思潮的兴起。
一、民族主义影响下的追忆思潮
自晚明开始,文人集社现象就很普遍,至清初,文人集社更加兴盛,大批文人在经历了朝代更迭之后,其作品大多流露出对故国沦亡的忧思。据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然甬上僻处海滨,多其乡之遗老闲参一二寓公。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1]这种情绪最终导致统治者的反感,兴起了一起又一起针对文人的文字狱,最著名的当数康熙二年的“明史案”,庄氏一家十八人皆被处死,甚至将已故的庄廷钅龙的墓掘开,“焚其骨”,并将所有“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共计处决七十余人。[2]另外,还有“南山集之狱”、“汪景祺之狱”等。从这些文字狱的侧面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存在故国忧思情怀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种情怀表现在戏曲创作上,便掀起了一股故国追忆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吴伟业、尤侗、洪昇和孔尚任等。吴伟业所作传奇《秣陵春》通过徐适和黄展娘之事,借南唐亡国,抒发内心情怀。冒襄曾经评价这部传奇说:“去夏偶得刻本,读之喜,心倒极,字字皆鲛人之珠,先生寄托遥深,词场独擅。”[3]吴伟业在杂剧《临春阁》和《通天台》中通过对陈亡和梁亡的凭吊,同样流露出内心的悲苦。尤侗的传奇《钧天乐》,通过沈白、杨云的科场失意,揭露了科场的黑暗。他的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同样通过屈原、王昭君、陶渊明、聂隐娘、李白的故事,抒发了对个人遭际的悲愤。王士祯《池北偶谈》称之:“既而世庙升遐,尤一为永平推官,以细故罢去,归吴中,时时以乐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卫》二传奇,尤为人脍炙。”[4]洪昇的《长生殿》是借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寓含对国家的兴亡之感。洪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且古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玉环倾国,卒至殒身,死而有知,情悔何极?苟非怨艾之深,尚何证仙之与有?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殆若是欤?”通过歌颂李、杨之间的真情,将真情融入特殊的大环境下,其意义更为深远。而孔尚任《桃花扇》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很明确地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顾彩也在《桃花扇序》中说:“斯时也,适然而有却奁之义姬,适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适然而事在兴亡之际,皆所谓奇可以传者也。彼既奔赴于腕下,吾亦发抒其胸中,可以当长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吊零香断粉,可以悲华屋山邱。虽入其人而事其事,若一无所避忌者,然不必目为词史也。”顾彩对《桃花扇》的理解可谓切中要害。
二、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实用思潮
清初在延续了泰州学派倡导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学说,更将李贽的“童心说”进一步光大。王夫之曾经说过:“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无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5]王夫之辩证地看待人欲与天理的关系,认为只有二者的关系和谐,才能实现世界之大同。这一观点与黄宗羲的看法相同。黄宗羲认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6]二人都将“人欲”与“天理”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在充分肯定人欲的同时,认为“人欲”是实现“天理”的具体显现。这是对李贽自然性情的进一步阐释。
尽管如此,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对宋明理学基本上还是持批判态度的。黄宗羲曾经批评宋明理学:“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明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7]认为无论是王阳明的心学还是程朱理学大多是空谈,无助于明理实用。顾炎武更是强调:“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虚。”[8]提倡以“修己治人之实学”来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探求治世之道。
由于实学思想的影响,导致文学艺术观念的更新,从晚明的表现自我、个性解放、率真本色转向清初的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顾炎武在论诗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9]认为“诗本性情”,应如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黄宗羲也说:“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10]认为诗人的性情与天下的治乱是相通的,诗歌应为时、为事而作,这与顾炎武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些思潮的涌动必然带来戏曲思潮的变革。明末清初的一批苏州地区的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特点鲜明的市民形象,既有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商贩,也有地位低贱的家奴仆役,以及僧侣、道士、妓女等,如《一捧雪》中的家奴莫成、裱褙匠汤勤,《清忠谱》中的商人子弟颜佩韦,《万民安》中的纺织工人葛成,《翡翠园》中的县役王馒头、绣花女赵翠儿,《万寿冠》中的漆匠蒲奉竹,《双和合》中的裁缝唐竹山,《称人心》中的裁缝洛小溪,《人中龙》中的木匠王廷相,《胭脂雪》中的砌街匠韩若水,《五高风》中的家奴王安,《未央天》中的家奴马义、臧婆,《双熊梦》中的屠户尤葫芦,《渔家乐》中的渔夫邬飞霞,《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钟、妓女莘瑶琴,《快活三》中的柴贩居慕庵,《艳云亭》中的相士诸葛暗等。这些平民形象融入了剧作家自身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而苏州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创作的主流从儿女私情转向关心时事。有通过历史针砭时事的朱素臣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丘园的《党人碑》、李玉的《千忠戮》等,更有取材于时事的李玉的《清忠谱》、《万民安》等。这股表现下层市民生活的创作思潮,明显是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更加追求人的自然本性。
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在戏曲领域,同时出现了讲求实用主义的戏曲,即讲求戏曲的实际舞台效果。实际上,自沈璟开始,就已经将编剧的着眼点放在舞台演出上。据孟称舜记述:“沈宁庵耑尚谐律,而汤义仍专尚工辞,二者俱为偏见。然工于词者,不失才人之胜;而耑尚谐律者,则与伶人教师登场演唱者何异?”[11]孟称舜的评价尚属客观,但也不尽然,沈璟不是专尚谐律,汤显祖也不是只工文辞。而他说专尚谐律的沈璟与“伶人教师登场演唱”一般,可见沈璟的创作十分贴近演员演唱。到了苏州派,则进一步推动了戏曲从红氍毹回归勾栏瓦舍。他们的作品不但在题材上更加贴近下层平民,在艺术上也更加追求与实际演出效果的紧密结合。当时就流传着“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可见当时李玉作品的影响可以与《长生殿》相提并论。而在戏曲领域将实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是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的李渔。
李渔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对戏曲艺术的经世致用予以阐述。他创作的传奇剧本首先考虑的是观众的审美趣味。他曾经说过:“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12]李渔的戏曲实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戏曲创作,另一方面是蓄养戏班亲自教授新戏。在戏曲创作上,他秉承戏曲艺术的实用性,即既要具有娱乐性又要具有教化功能,这一点在苏州派作家的作品中已有体现。李渔曾经说道:“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及稗官野史,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13]自清顺治五年从兰溪移家杭州,李渔便开始隐逸市井的生涯,特别是寓居南京芥子园期间,组建家班,自任家班的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演员。他带领家班四出游历、演剧,据他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中所说:“予数年以来,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诸姬悉为从者,未尝一日去身,……”李渔的戏曲实践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存,这一最基本的目的致使李渔不得不首先考虑观众的需求,因此从编写剧本到舞台呈现,都以观众口味为第一。为此,杨恩寿批评说:“《笠翁十种曲》,鄙俚无文,直拙可笑。意在通俗,故命意遣辞力求浇显。流布梨园者在此,贻笑大雅者亦在此。”这恰恰可以说明李渔在创作风格上为了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和迎合普通观众的趣味而体现出来的通俗自然,因此,杨恩寿又转而称赞他的作品“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诨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与颉颃,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14]。
三、性灵诸说影响下的回归传统思潮
到了清代中叶,一股有别于实学思潮的追求个性解放、抒发内心性情的思潮开始抬头。袁枚以其性灵说向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出质疑。他曾经说道:“情之见于去时者,道之存于平日也。道何在?行乎已者是。情何在?存乎人者是。”[15]而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则提出了“由词以通道”的治学,以此开捍卫实学思潮的地位。他在《孟子字义疏证序》中认为,孟子所说的“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盖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16],对传统理学进行了批判。汪中同样以其博学,进一步验证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传统理学发起了更为尖锐的挑战,尤其对婚姻问题,更是与传统理学格格不入。针对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或守节的恶俗,他批评道:“事苟非礼,虽有父母之命、夫家之礼,犹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婿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婿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乡之士君子得而止之。”[17]他甚至认为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应该弱化。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传统理学思想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思潮也出现了传统理学思潮与汉学思潮,以及文学上的性灵说、格调说、肌理说相混杂的局面。
在这样思潮的影响下,在戏曲领域出现了以蒋士铨为代表的一批戏曲作家,他们一方面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逐渐摒弃戏曲的案头化而代之以戏曲创作的重视舞台演出效果。舞台表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大量传统剧目的折子戏,杂剧创作也兴起了一波高潮,而“乱弹”诸腔则得到迅猛发展。
据袁枚所言,蒋士铨“谐谑风发,听者倾靡。胸无单复,不解嗫喏耳语。遇不可于意,虽权贵,几微不能容”[18]。他为人耿直,性格倔强,是典型的正统文人。在他看来,“变化古人诗法而独抒其性真之所至。故其微言大义,感发乎忠孝,激昂乎古今,慷慨于事势物理之难齐,而周知乎天理人情之必至”[19]。他所说的性情有别于李贽的自然性情,是“微言大义,感发乎忠孝,激昂乎古今”的性情,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的性情。他在《香祖楼》第十出《录功》中曾经说道:“万物性含于中,情见于外。男女之事,乃情天中一件勾当,大凡五伦百行,皆起于情。有情者,为孝子忠臣、仁人义士;无情者,为乱臣贼子,鄙夫忍人。”很明显,他心目中的有情之人是指传统伦理所颂扬的忠臣孝子。蒋士铨曾经创作《西江祝嘏》四种杂剧,是专门献给皇帝的歌功颂德之作。明宁王朱宸濠的妃子娄氏因劝宁王未果而投江自尽,在蒋士铨看来,她是女子的楷模,应大力颂扬,他曾经创作了杂剧《一片石》、《第二碑》,传奇《采樵图》记述其事,他还曾经恳请当时的布政使彭青原为娄妃立碑。由此可见,蒋士铨是要通过自己的戏曲作品起到教化民众的效果。除了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外,夏纶的《惺斋六种曲》、董榕的《芝龛记》、吴恒宣的《义贞记》、永恩的《漪园四种曲》等,都是极力宣扬忠孝节义的作品。对于夏纶的《惺斋六种曲》,梁廷枏认为:“惺斋作曲,皆意主惩劝,常举忠、孝、节、义,各撰一种。以《无瑕璧》言君臣,教忠也;以《杏花村》育父子,教孝也;以《瑞筠图》言夫妇,教节也;以《广寒梯》言师友,教义也;以《花萼吟》言兄弟,教弟也。事切情真,可歌可泣。妇人孺子,触目惊心。洵有功世道之文哉!”[20]扮演封建卫道者角色成为这一时期戏曲创作的一股潮流。
从戏曲舞台表演角度来考查这一时期的戏曲,在舞台上出现了以短小单位的呈现取代长篇大戏演出的局面。这股潮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单折杂剧创作的兴盛;二是折子戏的广泛演出。
这一时期出现的单折短剧,每折叙述一个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分别是独立的单元。这种短剧虽不及整本大戏那样排场气势,但便于排练演出,则是其胜之一筹的地方。据记载,蒋士铨的《四弦秋》刚一脱稿,就被扬州江春的德音班排演,道光年间,北京四喜班的名旦扈连喜曾以“能《四弦秋》全曲”而闻名[21]。短剧的受欢迎,这与折子戏的流行是密切相关的。
自乾隆年间开始,花部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与昆曲的日渐衰落相关。昆曲本身的逐渐雅化使其越来越脱离更广大的普通观众群体,演出的场所也越来越局限于皇宫贵族、达官贵人之家。而与之相比,流传于民间的弋阳腔开始占据戏曲舞台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在乾隆皇帝于十六年、三十六年为太后过寿,五十五年为本人庆生期间,一些地方戏的演员得以进入宫廷。特别是秦腔戏班和徽班的进京,使花部获得了更多的赞誉。据昭槤记载:“(魏长生)甲午夏入都,年已逾三旬外,时京中盛行弋腔,诸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之变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兼之演诸淫亵之状,皆人所罕见者,故名动京师。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22]
四、维新思想影响下的改良思潮
乾隆之后,大清已趋衰微之势。一批思想家对传统不变的祖宗之法发起了挑战。其代表人物就是龚自珍、魏源、包世臣。他们首先提出变革旧制的主张。龚自珍认为:“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也非革前代之败耶?”(《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劲改革”的结果便是朝代的更替,只有“自改革”才能长治久安。魏源也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与其使利出三孔二孔病国病民,曷若尽收中饱蠹蚀之权使利出于一孔?”(《筹篇》)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车酋纪行》开始,中国人的眼界不再局限于泱泱大国的五千年文明,而能看到更多的纷繁世界,传统的“华尊夷卑”的观念受到质疑。包世臣曾说过:“兵法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势也。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皆非中华之所能。……又嘉应州贫士多有就英夷之馆者,一请三年,习其地势人情,似宜明示宥其既往,收为我用,或亦可得制炮之法。盖天下物之利者,无不有制也。”[23]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
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开议院,倡议民权,限制封建君主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文化上,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维新的思想仍在延续。以梁启超、杨度、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以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派,主张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腐朽的封建制度终于在辛亥年土崩瓦解。
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表现在戏曲领域,守旧的昆曲已近乎消亡,新型的剧种此起彼伏。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京剧。除了京剧之外,尚有梆子腔、高腔、弦索腔等,时有“南昆、北弋、东柳、西帮”的说法。花部已取代了昆曲雅调的地位,成为戏曲舞台的主力军。胡适就曾经将花部的兴起看成是戏剧史上的一场革命,一方面花部戏剧的崛起对中国戏剧的冲击力是多么巨大,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导致戏剧改良运动的兴起。[24]
鸦片战争之后,尽管传奇戏曲已走向没落,但仍有一部分人在从事传奇戏曲的创作,但这些作品大都着笔于现实政治,带有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如梁启超的《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惜秋、旅生的《维新梦》,孙雨林的《皖江血》,浴血生的《革命军》,湘灵子的《轩亭冤》,华伟生的《开国奇冤》,另外还有以历史题材宣扬民族思想的作品,如川南小波山人的《爱国魂》、吴梅的《风洞山》。也有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事件以宣传民族革命的作品,如雪的《唤国魂》、玉瑟斋主人的《雪海花》、南荃居士的《海峤春》等。郑振铎先生称这些作品“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25]。伴随着这批政治剧曲的诞生,一场戏曲改良运动也开始了。
戏曲改良运动首先始于京剧的开演新戏。而开京剧改良风气的第一人是汪笑侬。他一生自编自演的戏很多,包括自己创作、从传奇等移植改编、整理加工京剧旧本等。其作品大多托古喻今,影射时政,表达了激昂悲愤的民众心声。光绪二十七年,他改编演出了《党人碑》,以哀悼戊戌六君子。光绪三十年,他自编自演了《瓜种兰因》(一名《波兰亡国惨》),借波兰亡国,影射清政府的腐朽。后来又如《哭祖庙》、《博浪锥》等,都是“低回呜咽,慷慨淋漓,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笑侬殆以歌场为痛哭之地者也”(《耕尘舍剧话》)。光绪三十年,第一本京剧专刊《二十世纪大舞台》问世。柳亚子署名亚庐在《发刊词》中说:“南都乐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翠羽名珰,唤醒钧天之梦,轻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美洲三色之旗,其飘飘出现于梨园革命军乎!”将汪笑侬、陈去病、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等提倡戏曲改良的人比喻为梨园革命军。署名“美国留学生”的陈去病在《致汪笑侬书》中指出:“欲造新世界,除非鼓吹文明感动大众,使之咸思奋趋,则一国之兴矣。今笑侬以新戏改良,处处激刺国人之脑,吾知他日有修维新史者,以笑侬为社会之大改革家,而论功不在禹下也。”汪笑侬在给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曾少卿的信中说:“抵制风潮现正吃紧,孝农等爰排一戏名曰《苦旅行》,取波兰遗事,内容甚富,表明不爱国之恶果,与无主权国民之苦况,以证波兰亡国原因。”[26]以此表达自己坚持戏曲改良的主张。这一年在天津,严范孙、李琴湘以演出时装戏《潘公投海》响应北京的戏曲改良。光绪三十一年,四川以黄吉安为首的戏剧家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明确提出“改良戏曲,补助教育”的口号。黄吉安一生创作和改编川剧80 余种、扬琴剧20余种,其中《忠烈图》、《金牌诏》、《三尽忠》、《林则徐》都是以歌颂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为题材。光绪三十四年,潘月樵和夏月润、夏月珊兄弟在上海创建“新舞台”,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新式舞台与布景、上演新戏的重要场所,时装京剧大量涌现,京剧改良运动达到高潮。宣统元年,王钟声在天津倡导演出新剧,有新戏《爱国血》、《浸海石》、《血手印》等。宣统三年,李桐轩、孙仁玉在西安创办了易俗社,培养演员,编写剧本。易俗社将教学与演出结合起来,培养了大量的戏剧人才,对秦腔艺术的继承和发扬,起了积极作用。戏曲改良运动的展开标志着戏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封建时代已经终结,民主时代已经到来。
清代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从创业到兴盛,最后走向衰亡。社会思潮伴随着朝代起伏而变化,而戏曲艺术同样随着社会思潮的起伏而不断更替。
[1]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M]//杨凤苞.秋室集:卷一.清光绪十一年陆心源刻本.
[2]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M]//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刻本.
[3]冒襄.同人集:卷十[M].蜀北蕘公藏本:67.
[4]王士祯.尤悔庵乐府[M//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五:谈艺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357.
[5]王夫之.论语里仁篇一一[M]//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284.
[6]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M]//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2.
[7]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M]//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5.
[8]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M]//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381.
[9]顾炎武.作诗之旨[M]//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141.
[10]黄宗羲.诗历题辞[M]//黄宗羲.南雷诗历.清郑大节刻本.
[11]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M]//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2]李渔.词别繁简[M]//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清康熙刻本:6.
[13]李渔.与陈学山少宰[M]//李渔.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164.
[14]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65.
[15]袁枚.送许侯入都诗序[M]//袁枚.袁枚全集:第二册: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82.
[16]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序[M]//戴东原集:卷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25.
[17]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M]//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376.
[18]袁枚.翰林院编修候补御史蒋公墓志铭[M]//袁枚.袁枚全集:第二册: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443.
[19]蒋士铨.胡秀才简麓诗序[M]//蒋士铨.忠雅堂集校笺:忠雅堂文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014.
[20]梁廷枏.曲话:卷三[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67.
[21]杨懋建.长安看花记[M]//杨懋建.京尘杂录:卷一.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349.
[22]昭槤.啸亭杂录:卷八[M].中华书局,1980:237-238.
[23]包世臣.与果勇侯笔谈[M]//包世臣.安吴四种:卷第三五.清同治年刻本:10.
[24]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M]//胡适.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9:201.
[25]郑振铎.晚清戏曲录叙[M]//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768.
[26]心青.致曾少卿书[M]//阿英.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