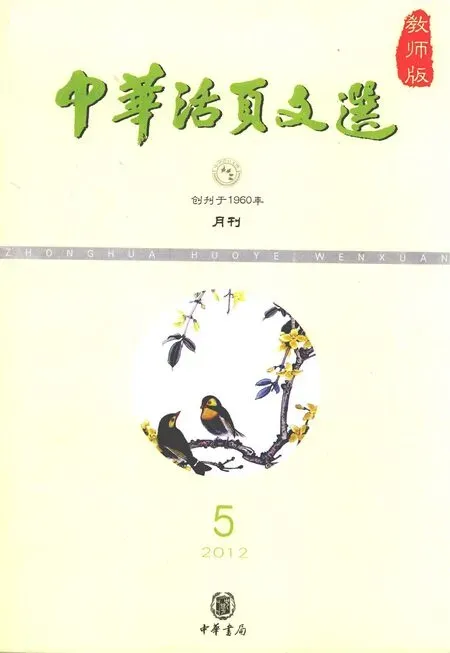从老王到《老王》 实现自我救赎——解读杨绛创作《老王》的心路历程
■ 马金岚(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读者阅读《老王》,对作者的“愧怍”可谓见仁见智。笔者想从作者为何写这篇散文入手,分三个阶段,通过三个问题,来走进作者的内心,做出阐释。
首先,在老王活着时,杨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对待这个普通车夫的?应该说,这是在特殊时期两个善良人之间的交往,他们都怀着善心去帮助对方,但双方的心理距离不相等,因而双方的情感也不对等。老王是一个“失群落伍”的单干户,这在当时人们都急着从属于某种集体组织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堪的事,在社会上没有归属感;他又是一个几乎没有亲人的孤病老头,在情感上也没有归属感,所以,杨绛一家善良的对待,让他分外感激,并逐渐有了亲人的感觉,以至他一心把杨绛一家看做亲人。他代送冰块,费用减半;送钱先生去医院不要钱,悄悄问杨绛“还有钱吗”,“悄悄”是何等亲近;病后,先“扶病”去杨绛家,不能走便托人“传话”,也许怕杨绛一家惦记吧;临死前一天,像僵尸一样地去杨绛家,把最珍贵的香油和新鲜大鸡蛋送给最亲近的人们。然而杨绛怎么做的呢?傍晚,夫妇散步,见老王蹬着三轮进了一个破破落落大院,不知道是不是老王的家,也没有跟进去看看,也许她觉得没必要知道他家住何处;老王送冰,她猜想“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主顾”一词是她的心理定位;“文革”中,钱先生生病要去医院,老王认为送自家人去医院是应该的,不要钱,她坚决给钱,因为是主顾关系,而且她同情更加贫寒的人,认为自己再困难也比老王强,不能叫老王吃亏;老王病了,她“不知什么病”“不知什么药”,反倒是老王“扶病”去她家,托人“传话”给她,可见,她从未去过老王家,因为从后文她的话“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看出,她都是“托人捎”,未亲自去;老王最后一次去她家,她应该看出老王的死相了(那段恐怖的描写便是明证),却没有和他说说话,也没请他坐坐喝口水,慌忙用钱打发他走了,而且自己也不觉得亏欠他什么。这时,虽然不是主顾关系,但老王仍然是个外人。此时的杨绛,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有不妥之处。
其次,老王死后,杨绛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首先是“惊”,作者先是慢悠悠地叙述,“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才问老王的情况,知道他在去她家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自然是惊,任何人都会这样,她也仅仅是“惊”而已,对老王死后的情况“我也不懂,没多问”。回到家里,睹物思人,似乎有些歉意,所以“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于是又得到自我安慰,内心暂时平衡,因为一个外人送来物品,自己给了钱,又表示了感谢,于情于理于物都不欠老王的了。但如果到此不再思考这件事,那就不是杨绛了,不是一个既受古代士大夫“立心”“立命”熏陶、又受西方平等博爱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了。接下来,她陷入了极度的良心不安之中,“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一个“每”与“总”,写尽了她的惶恐与不安。于是她开始反思,“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是自己收入高,却吃很贫穷的老王的东西而不安吗?不是。对一个外人来说,他送来东西,她给他钱,两讫了,何来不安呢?杨绛曾两次谈到自己工资高,一次在《干校六记·学圃记闲》中说工资极高,“使国家吃亏不小”“自觉受之有愧”,只好安分地学种菜;一次在《我们仨》中说工资高,不能好好为人民服务,还得国家赔钱“重新教育”,“分明是亏了国家了”:都有些反讽的味道。所以,作者将原稿中“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中的“多吃多占”改为“幸运”;是自己拿钱“侮辱”了老王吗?注意,此时杨绛已经使用了一个令她倍感痛心的词“侮辱”来定性自己的行为,看来已经对自己的作为不加宽恕了,但她马上又否定了,那就意味着有更严重、更深层的原因使自己不安,只是不明白这原因是什么而已,而这不明不白的不安却更强烈地折磨着杨绛。
第三,几年后,杨绛觉悟到什么?长时间咀嚼着良心的不安,她不断反思,换位思考。她在《隐身衣》中说:“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人家眼里没有你,当然视而不见;心上不理会你,就会瞠目无睹。你的‘自我’觉得受了轻忽或怠慢或侮辱,人家却未知有你;你虽然生存在人世间,却好像还未具人形,还未曾出生。这样活一辈子,不是虽生犹如未生吗?”这不就是老王的写照吗?自己不是和世人一样对待老王的吗?她“渐渐”明白了自己不安的深层原因:自己曾经受到老王亲人般的对待,享受着那个卑微之人无比的亲情,而自己从未以如此真挚的亲情回报;自己是“幸运”的,而老王至死也未能得到自己亲人般的情感,是个彻底的“不幸者”。她觉悟而痛悔着,一个具有平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无比善良的女性,觉悟到自己的愧怍而无法原谅自己,更无法释怀,几年来内心一直被咀啮,终于诉诸笔端,在文字的流淌中,释放自己的心情。写着写着,又仿佛回到了开头第一节的情景中——“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车。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也许会对自己说:“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把老王当做亲人!”
从老王到《老王》,杨绛不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她的创作,是为了释放自己的愧怍,怀念那卑微善良而不幸的老王,实现自己灵魂的救赎。这是极其可贵的品质,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里说:“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杨绛不属于这一类人,但她理解并践行着丈夫的建议,以自己的虔诚和良知来反思,敢于写出自己的愧怍,把个人情感变成经典作品,客观上产生了一次升华,让个人的愧怍成为普世价值,促使每一个阅读者拷问自己的良心:在这个崇拜金钱、物欲横流的功利社会里,我们怎样对待身边的不幸者或弱者呢?我们心有愧怍吗?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愧怍吗?
如此说来,《老王》作为初高中都选的教材,在其主题编排上就有进一步商榷之处了。人教版初中教材编在“爱普通人,尤其关爱弱者”的单元中,单元导语为“这个单元就以‘爱’为主题,几篇课文都在诉说对普通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关爱。让我们从课文中感悟到‘爱’这种博大的感情,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苏教版高中教材中与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品质》一起组成“底层的光芒”板块,文本研习设计:“格斯拉是鞋匠,老王是人力车夫,按世俗的观念,都属于‘底层’人物,结合作品内容,说说两篇作品是把人物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描写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怎样的性格特点。”显然,高中教材侧重于对“老王”的解读,重视散文的“所述”,而忽视了本该重视的对作者情感的把握(即散文的“自述”),不如初中教材的编排角度好;再者,高中教材对老王身上的“光芒”(善良)的解读,更表象化,缺乏深度,比初中教材的设计更浅显。如果一个学生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学《老王》,是否该颠倒一下其主题编排呢?或者在高中教材中将《老王》编入“心灵的追悔”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