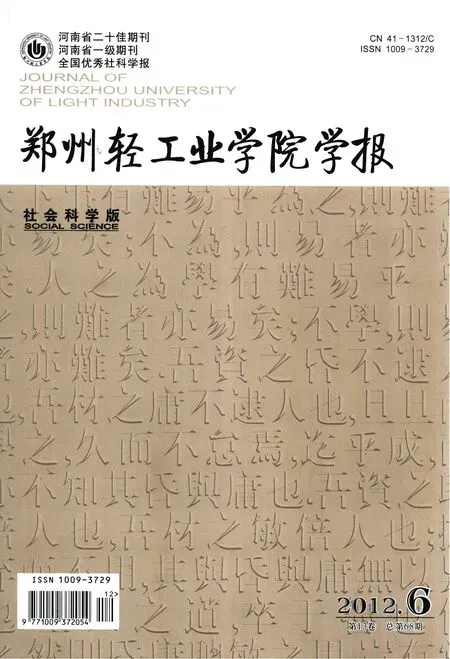自然事实、客观事实与科学事实——当代科学哲学关于三种事实的理性辨析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自然事实是指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指天然事实,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就是指日常事实。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自然事实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它们与实践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凡是与实践内在相关并保持敏感性的事实,就构成实践性的客观事实;凡是与实践外在相关、或根本无缘的,就是日常事实或者天然事实。而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也同样是有区别的,它们的重大差别在于:究竟其可靠性是取决于它与描述体系的一致性抑或是与实践的一致性。本文拟从概念解析入手,弄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尊重事实、研究事实,进而以事实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建构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我们以事实为基础,与从狭隘经验出发“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1]和从本本出发在主观观念中虚构事实的主观主义划清界限,提高认识能力、推进科学发展,也极具理论意义。
一、自然事实及其非实践性
自然事实(天然事实或日常事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和人的生存性状,即客观事物本身或者人的非本真存在,包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存在之物和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万象,它是与客观存在或客观实在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对于人及其活动而言,自然事实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当纯然外在的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尚未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时,它还只是自存自在的“物自身”,只有当它与主体发生认识—实践之关系,即发生反映与被反映或者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时,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这种自在之物才转化为“为我之物”,具有认识对象或者实践客体的意义,才成为我们认识—实践的客观事实。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是偶然的和无限多样的,它具有自主性、自在性、自因性。在人类认识—实践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上,纷然杂陈的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只有一部分能够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认识—实践的客体。随着人类认识—实践能力水平的进步和提高,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越来越多地向认识客体转化。促使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并向认识客体转化的根本力量,是人们客观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无疑是任何一个理论得以确立的经验基础,是判断该理论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真理性的生活基础。尊重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的实在性、真实性、唯一性,是从事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出发,进而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是保证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不从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客观事实本身及其真实的相互关系出发而从想当然出发的研究者,以及以主观臆造的联系替代真实的关系的研究者,都很难在科学上有所收获。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人们永远也腾飞不起来;没有事实,人们的一切“理论”都是在枉费苦心。中国古代人们为了长生而进行的炼丹术和巫术活动,西方历史上进行的视灵者的实验和以太实验等,最终都被证明是荒诞的、背离科学本性的,其关键就在于没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二、客观事实及其实践性
哲学上的事实是指特定的、真实的事件,它是已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事件、现象、关系、性质、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客观事实就是认识论上所说的客体,但并非指所有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指可诉诸实践的事物,是一种实践性的事实或者基于实践而确立起来的事实。客观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是由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本性所决定的。物质性或先在性只是客观事实的自然前提或本体论基础,而非本质性要素和决定性环节,构成其本质内涵与决定环节的只能是社会实践。因为,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属于人的事实、打上人活动印记的事实,哲学上所说的自然是第二自然、属人的自然。马克思讲,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2]。我们总是生活于人化自然中,没有留下人化印记的天然事实或者自在自然已很难寻觅。自然同社会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实践是整个感性世界的物质基础。单纯外在性的自然,对人说来是“无”——它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意义。换言之,客观事实之所以能成为客体,从根本上说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性和先在性,而是取决于它的对象性或指向性,取决于它能否及如何进入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并被人们的实践所捕捉而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因此,认识—实践客体的广度和深度,依赖于主体及其能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状况,认识—实践客体的界限也取决于主体的探索手段、能力与范围。在此意义上,客体是指在主体之对象性的认识—实践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活动的两极并发生了相互作用之功能关系的外部事物或客观事物,它是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实际指向的对象。马克思认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3]质言之,人不可能创造或消灭客观事实,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予以改造。而那些在实践活动中被改造并打上主体烙印的客观事实,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表现形态而已,其客观性并未因此而消解。客体首先属于客观世界,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着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客观世界都是当下意义上的现实客体,只有被主体纳入其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那部分,才能从潜在意义上的客体变成现实意义上的客体,从天然之物变成人化之物。
旧唯物主义者仅仅把客观事物当做直观意义上的客观事实,把直观对象等同于客观事实,没有从主体的能动的本质力量和实践活动方面和相对于主体及其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并把握客观事实的客观规定性,因而陷入了唯客体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泥潭。正如马克思所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哲学的对象是感性的人及其自然,自然和人都在直观意义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基础,一切非思维的存在都是人的现成的客观事实;进而,他们从“唯物”的角度出发,认为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于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是自在自因的,而思维只是这种存在的主观映像。旧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实就是与“思维”相对应的“存在”,即它是作为人的感性对象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非思维的存在。
旧唯物主义事实观的一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不是从与实践的关系上区别客观事物与客观事实的,而是从与思维的关系上来区分两者的,他把客观世界看做人的感觉、直观反映的对象,没有看到客观世界是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的对象,即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看起来很‘唯物’,实际上完全不了解自然界的真正本性。”[5]譬如,费尔巴哈,他虽然强调人属于自然,却没有看到人也能动地改变自然,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主体,他对客观世界只是从客体的角度或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和实践方面去理解。换言之,费尔巴哈只是对事实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而没有同时对之作实践的理解,在他对事实的理解中并没有实践的位置,他没有看到实践作为客观事实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的重要意义,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事实并非从来就有、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离开现存世界的物质性实践,就不能真正理解已经在实践的作用下改变了的自然事实,也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历史事实。
三、科学事实及其经验性
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既不是指那种普遍存在的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亦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指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并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描述体系对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进行判定所形成的单称命题或者经验事实。可见,科学事实是与个体存在相对应的主观陈述和经验事实,这一特点说明科学事实描述的是个体经验而不是个体所属的类的经验。科学事实强调的就是认识特殊事物的感性活动及其经验内涵,而不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理性活动及其抽象表达。凡是经验事实都应有可复核、可重现的特点,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对同一现象再次经验并且对认识结果的陈述是相同的。那种不可重复、不能复核的事件都不是科学事实,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它们的真实性。凡是经验事实都应该具有精确性和系统性,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对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不能进行系统描述和精准测量的事实构不成科学事实。
经验事实的客观性,不是取决于事实本身或者实践需要,而是取决于获取经验事实的手段本身是否科学,取决于通过观察和实验等科学实践活动获得的关于经验事实的信息是否可靠,还取决于以什么样的科学语言来对经验事实进行表达。在科学活动中,人们要描述自己观察到的事实,就必须使用特殊的话语,这些特殊的话语总是属于特定的理论体系,而人们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的过程,也就是该事实获得理论解释并使之转化为科学事实的过程。仅仅成为客观事实的,并不能被直接视为科学事实,它只有得到一定的理论解释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事实。当然,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人们解释它的方式方法不同,所获得的科学事实也不相同。
四、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别和联系
1.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本差别
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哲学上的客观事实本质上属于实践性事实,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是一个从属于实践意义上的范畴,无所谓对错之分。[6]客观事实一旦被人类所认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察判断,它就转变成科学哲学所说的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范畴,它的形成经过了人类大脑的加工,有对错之分。科学事实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它的内容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它的形式却是主观的,因而其认识—实践结果就具有可错性。因此,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存在误差的。引起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实验方法、思维方式和人文环境的制约。一个科学事实往往是先通过观察,然后通过推断,紧接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验证和应用才被人所承认。这期间当然要受到人文环境以及实验手段的制约,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能说它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而且,科学事实由于受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主体极有可能歪曲事实,它作为描述物质现象与过程的经验事实,其真理性有待于科学共同体的进一步审查。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系统鉴定的事实,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事实。但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也受各方面的限制,因而即使是公认的科学事实也是相对的、可错的。
科学事实描述的都是个别事件,形成的都是单称判断,极其复杂的综合事件及其全称命题不属于科学事实,而只能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科学事实是否具有可重复性,需要科学共同体来确定,“非科学人员的‘重复’,甚至是行政当局、新闻报界的大肆鼓吹,即使一时得逞,最终仍不能确认为科学事实”[7]。科学事实需要精准检验,在定性与定量上都需要高度准确,而这非常不易。当代混沌学认为,由于混沌系统初始条件的极度敏感性,初始条件的细小变化就会带来整个系统未来性状的极大差异,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科学上的真实要靠事实来验证,科学事实是任何理论获得确立的基础,离开足够多的科学事实的支撑,再优美的理论也不能成为科学真理。科学事实既可以出现在科学理论之前,亦可以出现在它之后。在当代,科学假说就常常走在科学事实之前,当它遭受质疑与反驳时,就需借助更多的科学事实来验证,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2.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统一
古典经验主义者如弗兰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纯粹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对它的观察不能携带任何主观因素,观察不能受任何理论的污染,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感官反映活动,要像镜子那样直观地映现事实,反对主体的先见(前理解)对事实的构建作用。正如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所说:“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坐在事实面前,准备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恭恭敬敬地照着大自然指的路走。否则,就将一无所得。”[8]现代经验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莫里茨·石里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中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与语言描述相联系,凡是通过语言规则系统与观察事实发生关联,就可从中获得经验蕴含[9]。只有保持科学观察的中性,才能保持科学事实的中性。要防止主体先见的无端介入,就必须使自己的观察要么直面事实本身、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因素;要么依据特定的、大家公认的逻辑规则进行客观性的描述,以确立公认的经验命题。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取决于观察的逻辑蕴含、逻辑规则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无自性观察”(又叫“零度观察”、“零支点观察”),认为观察纯粹是随意的、任性的、毫无目的的。观察就是观察,理论就是理论,二者互不相扰,一切都停留于当下。观察不为任何理论提供经验基础,也不接受任何逻辑规则的检验,更不顾及实践的需要,它仅仅与人的那种无限延异、无穷解构的情绪内在相关。后现代经验主义试图推翻任何带有整体性、主体性踪迹的客观性描述,认为回到事实本身就是仅仅切问碎片与泡沫,事实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都应被纳入解构环节之中。——连一切科学理论都被解构了,哪里还管什么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别和联系呢?
其实,在我们看来,观察与理论是辩证统一的,观察是理论的基础又不断推进并检验着理论,而理论则导引着观察并使之日益延拓和深化。二者之间良性的循环发展,就会使错误的观察得以矫正、使错误的理论得到淘汰,逐步实现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一致,促进科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当然,二者获得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不可能是主观虚构或者逻辑表征。
五、结语
总之,科学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和自然事实,科学理论及其使用都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因为科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至上”与“科学万能”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万能的东西不是科学”[10]。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反驳、被质疑、被充实和被修正的历史,也是错误的理论内容与方法不断被发现被纠正的历史。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一个理论的科学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可错性,该理论“不管曾获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11]。波普尔“唯有可错的才是科学的”的观点可能有点极端,但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不能把科学理论等同于真理,更不能把科学事实认定为客观事实,否则就会把科学绝对化、神圣化,造成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这非但不能推动科学前进反而会束缚它的发展。
[1]郁乐.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J].伦理学研究,2010(3):10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5]肖前,李淮春,杨耕.实践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4.
[6]李醒民.科学事实与实验检验[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43.
[7]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7.
[8][英]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陈捷,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53.
[9]张灏.意义与事实——对逻辑经验主义意义理论的质疑[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1):10.
[10]陶德麟,王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7.
[11][英]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M].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