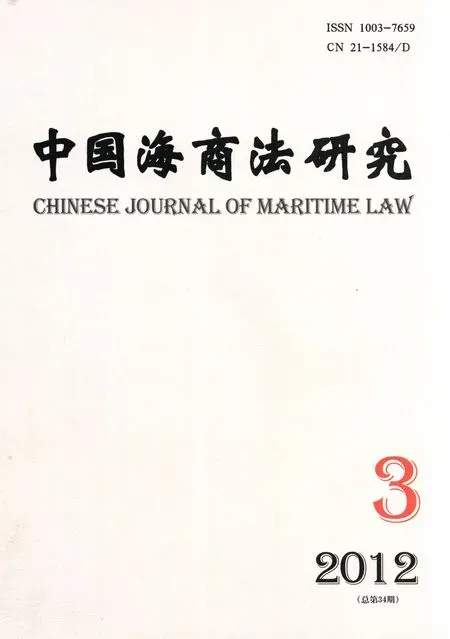论海商法之于民法的独立性①
王世涛,汤喆峰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26)
在中国,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1-4]其依据主要在于,与民法一样,海商法是由平等主体参与的,调整的是横向的社会关系。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所有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法律被统一纳入民法之中,这种宽泛的划分标准造成的结果是各法律部门之间界限和调整范围的不确定性。它不仅模糊了民法、商法之间的区别,而且相应地,其他法律部门如行政法、经济法都可以被简单地化约成为与民商法相对应的调整纵向法律关系的法律部门。它无法全面体现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差异性,而学科划分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体现差异性确定不同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围。其实,法律部门是在大陆法系的学术体系背景下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不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众所周知,普通法国家一般不进行严格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法律体系的建构是法学研究逻辑抽象的结果,并非完全反映法律的社会真实。因为,它过分纠结于各自的研究领域,而弱化了法律对某些边缘性问题的作用①。可以说,将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是法律体系逻辑思维的精神错乱。这一通识性的错误,极大压抑海商法的独立发展空间,妨碍了海商立法和司法的进步。
一、海商法与民法不同的历史渊源
海商法学者普遍认为,“海商法的许多制度,究其渊源是民法基本原则在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中的应用。”[5]这似乎暗喻着,海商法是在民法的基础上,通过适应海上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海商法是由民法派生的。但从产生发展的过程来看,海商法不是在民法已经建立和形成后产生的;相反,在民法产生发展以前,海商法已经产生。另一方面,海商法也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海上运用的结果,其实海商法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虽然,民法对海商法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海商法在许多方面也曾深刻地影响着民法。
海商法在商人群体的推动下,以大量海商习惯和惯例为历史渊源独立成长,它以海上商业行为形成的范围为界限。海商法的历史渊源与民法有所不同,它并不以罗马法为主,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罗得法(Lex Rhodia),甚至公元前18世纪的汉穆拉比法典。而且伊斯兰法也在推动海商法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6]在欧洲,公元前3世纪左右已有《罗得海法》,此后200年,从罗得岛,经阿玛斐、巴塞罗那、奥列隆,到威斯比和吕贝克,形成了海洋普通法——海商法体系。中世纪的海商法特点表现为:第一,以习惯法为法律渊源;第二,实行商人自治;第三,统一性和通用性。海上市民的习惯法和契约法克服了各地陆法的主观性和封闭性,是一种带有国际法性质的船舶集散港中心的海商法。由于中世纪海商法源于各沿海城市的海事习惯法,脱离罗马法(大陆法系成熟的民法典体系)而独立存在,海商法几乎没有受罗马法影响;相反随着商事交易的发展,海商法规则逐渐运用到陆上商事交易,陆上的大部分商法制度均源于中世纪海商习惯法。迄今民法已经与商法充分合流。法国商法学家帕尔德斯(Pardesus)在《18世纪的世界海法集成》中认为:海法(这里的“海法”主要包括海商法,但比海商法的范围更为宽泛)具有世界性(统一性)、不动性和习惯法起源性三个特征,由此海法与民法绝对对立。[7]4英美法系海商法起源于英国海商法,英国海商法是通过海事法院判决而形成普通法(不成文法),但美国在海法领域创设了许多成文法。英美海法也具有结构和功能上的独立性,不轻易受时代和其他因素的影响。[7]6至今两大法系逐渐趋同,但海商法仍保留其自身的特性:普适性、习惯性、通用性。
虽然海商法独立产生,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与民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换言之,在民法影响海商法的过程中,海商法同样影响着民法。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宏观的原则和理念方面,又表现在微观的制度设计方面:一是在基本价值方面,即商人的平等性对民法价值取向的影响;二是具体法律制度方面,海商法的一些制度被民法接受和吸收。[8][9]22-23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海商法是民法在海上商事活动中的运用,也不能认为,海商法是民法从大陆向海域的扩展。准确地描述海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各自发端、独立成长、相互影响、逐步融合。晚近以降,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影响与日俱增,但随着民法成为法学中的显学,海商法的独立性及重要地位被民法的光环所遮掩。
二、海商法与民法不同的法律属性
民法是通过对罗马法复兴得到发展的。罗马法复兴由11世纪的一批法学家发起,他们通过对《学说汇纂》等罗马法进行大量的研读和注释,希望将先进的罗马法与现实结合起来。这些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复兴时期的法学家普遍被吸收到各国国王政府中担任官职,积极参与立法与司法实践”,[10]这一优势使得这些学术成果成功地转化为立法成果。除罗马法以外,民法还吸收了一些本国的习惯与宗教中的部分。[11]由是观之,民法的发展,就其推动力而言,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认可;就其历史渊源而言,以罗马法为圭臬。这也造成民法发展以国家权力范围为界限。历史上民法的确立标志都是各个民族国家的主权意志,如法国的《拿破仑民法典》。可见,民法虽属于私法,但实际上却始终没有脱离国家权力的底色:“(罗马法中的)私法的绝大多数内容并非立法产物,但是只要愿意,罗马人是能够在其集会上对私法加以修改的……立法只在相对少的场合被适用,但是它的干预却是极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而,如果不时常参考执政官的敕令,私法的发展历史便很难被正确理解。”[12]所以民法的产生与发展往往和国家权力紧密相关,国家可以通过认可习惯使之具有强制性,反之也可以宣告其非法。
此外,与海商法强调效益相比,民法更为注重伦理。例如是否采取一夫一妻制?父权应当在什么范围内行使?罗马市民与外国人是否平等?物的所有权归属于谁?民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总是要考量伦理价值。当然这一伦理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会有所不同。所以“民法的规范偏重于社会伦理性,很强烈地反映着一国民族文化(甚至宗教)的特征,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9]19可以说,民法社会伦理性,是与其民族性、地域性相适应的,反映的是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的伦理性。
海商法的成长则独立于民法,它的推动力与历史渊源都与民法迥然不同。海商法首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国家权力的规制。如《罗马汇集》中就写道:“某人向安多耐诺斯国王提出一个关于船难事件的诉讼,寻求得到解决,但国王回答道:‘我确实是陆地上的最高君主,但海洋的君主是惯例,让这一诉讼由被我们的法律所接受的罗得海法来决定吧’。”[13]中世纪重要的海商法都是由私人编纂的惯例或判例汇编,而非国家制定的法典。直到17世纪,随着民族国家逐步壮大,国家权力试图对海上事务进行实质控制,才出现了国家制定的海商法典。即便如此,国家制定的海商法典也多是以既有惯例为蓝本的。而商人之所以建立行会和法庭,其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保护商人免受封建主、教会等其他人的损害,二是促使商人遵循共同的交易惯例和规则,以便利交易。[14]由此可见,海商法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商人群体自身。
由于海商法是独立发展形成的法律体系,因此它具有完全不同于民法的特征。海商法归根到底是商人自治的产物,其目的在于为海上商事活动服务。海商法与民法的区别,在于海商法的自治性、效益性和普适性。自治性反映在规则制定方面,为了避免受到外来干预,商人力求游离于国家权力的桎锢之外,摆脱封建主和教会的干涉,由自己制定商业活动的规则。因此海商法对商人的强制性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商人群体自身。效益性反映了规则本身带来的成本,即要求通过海商法可以尽量降低海商行为中的成本,凡是不利于降低成本的规则都会被改造或取消,这也是商人逐利性的基本要求。又因为海商法调整的是各个国家的商人共同参与的国际性商业行为,所以它必然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商人,只要参与到海商活动中,就必须遵守这个统一性的规则,否则会出现大量相互矛盾的规则,这将会导致海商活动因缺乏有效规则而难以进行。因此海商法又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
由此可见,海商法与民法各具特性:海商法具有自治性、效益性和普适性,而民法则具有国家性、伦理性和地域性。海商法的独立性取决于海商法的世界性与民法的民族性的根本差异。
语言可以形成对比,对比也可以突出语言的特色。在一些具有“对比”意蕴的语言里,语言彰显着自己的幽默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欧·亨利的作品独树一帜,在众多的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中,他作品的风格不是对痛苦的刻画,而是对痛苦的嘲弄。[3]本来痛苦应该引起读者的怜悯,可是欧·亨利的语言却使读者感受到了事实对“痛苦者”的嘲弄。
三、海商法与民法不同的规范体例
从法律形式方面,海商法与民法也迥然不同。海商法通常的法律形式是习惯法,而民法则表现为体系完备的成文法。由于民法具有国家性,其形成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因而其法律形式为成文法。古罗马时期的民法就以国王命名,形成了法典化形式,如《查士丁尼法典》。近代以降,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而海商法则不同,由于海商法自治性和通用性,其通常的规范形式当然是习惯法。如中世纪重要的海商法汇编奥列隆惯例集(Lex Oleron)、康索拉度法(Lex Consolato)、维斯比法(Laws of Visby)等,都是由私人编纂的惯例或判例汇编,而非国家制定的法典。当然,随着法律的不断发展,海商法也不完全是习惯法,正如民法不完全是成文法一样。但由于二者本质属性决定,海商法仍保留着习惯法的主导形式,如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而民法基本上仍以国内成文法典为主。
中国于198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而后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当然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不久的将来,中国可望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在不同时期,中国民事单行立法的成文法形式与中国继受了大陆法系的传统有关。而正是这一原因,在中国,不成文法因得不到国家的确认而不能取得法律效力,甚至,将世界上通行的习惯法以法典的形式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制定的。当然,中国的海商法融入了大量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有些条文甚至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翻版。在《海商法》出台后,中国作为IMO成员国,签署了较多的海商海事的国际公约。
从规范体系上看,较为成熟的德国民法典体系是潘德克顿学派在注释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潘德克顿学派及其深邃的、精确而抽象的理论的产物,它极其重视用语、技术和概念构成方面的准确性、清晰性和完整性。这个体系把民法典分为五编: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民法学者对拟定中的中国民法典的体系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会以近些年出台的单行立法为基础,《物权法》《合同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不可或缺。《海商法》的体系与民法完全不同,《海商法》的主体内容从第一章至第十四章分别是:总则、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航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上保险合同、时效、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在中国既有的立法例中不难发现,海商法与民法的法律框架和规范内容完全不同,完全看不出二者母法与子法的“亲子关系”。
从规范的内容上看,海商法与民法从原则到规范都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基本原则在各个部门法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法通则》第一章即规定了“基本原则”,然而在中国,《海商法》却没有规定基本原则。在学术界,学者们论及海商法的基本原则,往往只简略地指出海商法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5]3[15]然而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16]既然海商法从实质上有别于民法,海商法应当有不同于民法的基本原则。由于海商法是为海上商事活动服务的,故海商法的原则应当集中反映这一目的。因此海商法的基本原则应以保障海上商事交易为价值取向,这与民法以伦理性为核心不同。
海商法具有专业性、特殊性、涉外性,这使得海商法与民法或者其他部门法难以兼容,而自成体系则更为适宜。例如海商法的专业性包括航海技术和航运业务两方面,具体而言则包括船舶驾驶、航线制定、雷达观测、货物的配载、装卸、轮机管理技术、船舶结构等。而且这些技术性内容关系到承运人的责任等问题。从具体的法律条文的设计上看,海商法和民法也存在重大差异。在民法中,除非因自己的先前行为导致他人处于危险境地或者因法律之规定或合同之约定,并不负有救助义务。而《海商法》第174条规定:“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这是在海上特殊的场域,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海商法将道义责任法律化,这也符合SOLAS国际公约的规则。如果在海上对人命施救,按照民法规定属于无因管理。而无因管理无论后果如何,管理人都不得索取报酬(当然可以请求一定数量的因管理产生的费用)。而《海商法》则规定有效救助的救助方有权取得报酬。又如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发生货损时承运人的免责事由亦与民法大相径庭:《海商法》第51条第1款规定,“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一)船长、船员、引航员或者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驾驶船舶或管理船舶中的过失……”这即是航海过失免责制度,即《海商法》中特有的一种法律救济制度,实际上确立了不完全过错责任原则;而《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还附加了一个过错推定制度。《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污染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中国海商法理论界和海事司法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当因为两船碰撞而导致一船漏油时,应当首先由漏油船对受害人承担海洋污染责任,而后漏油船再通过协商或诉讼与另一碰撞船舶按照碰撞责任比例分担漏油船已经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总额。
四、海商法与民法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中世纪,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中形成了职业商人这一阶层。他们从封建领主处争得自治权力,建立了被称为商人“基尔特”的自治机构,处理商人之间的争端。而由于民法对国家的从属性,民事争议也通常诉诸国家审判机关来解决。在中国,海商法与民法的纠纷解决机制有所不同。
第一,适用的程序法不同。民事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诉法》),而海事诉讼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简称《海诉法》),《海诉法》没有规定的,才适用《民诉法》。《海诉法》中大部分规定与《民诉法》不同,如海事强制令。
第二,审理机构不同。英国高等法院下设王座法庭,王座法庭负责处理海事案件。在中国,海事法院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单独设立。全国有10个海事法院,大多设在沿海沿江中心城市,审级等同于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上诉审到当地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说,海事审判只有在初审阶段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因此,海事诉讼实际上是三级两审终审制,而不是民事诉讼的四级两审终审制。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指出,由于海事审判专业性强的特点,由普通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作为一审海事案件的上诉审法院,高级法院的海事审判量少质弱的弊端就突出了。为了解决二审困难,不少高级法院借调海事法院审判干部,清理再审案件,有的甚至将一审案件合议庭成员抽调到高院经济庭直接参加二审合议庭审理上诉案件,实际上将一、二审合并审理。因此,在中国有必要设立自成体系的海事审判体系,保证海事审判全程的独立性。
第三,与民事诉讼国内法的传统不同,海事诉讼具有国际统一化的倾向。由于海事诉讼案件大多具有涉外性,因此,在海事诉讼中,适用的法律有时会涉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第四,较之民事纠纷较多适用诉讼程序,海商纠纷较多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仲裁比诉讼更能体现商人的自治性,国家权力干涉较少,程序更简单,保密性与效率也都高于司法程序。
国外有学者认为“如同民法与普通法是完整的法律体系……海商法拥有实体与形式上的广阔范围,有自身的法院与管辖范围,其中还包括了私法部分与公法部分,因此确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18]
五、将海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危害
将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不仅是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在实践中,这一错误认识对于海商法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
首先,民法的伦理性抑制海商法的效益性。将海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也就意味着应当用民法的方法来研究海商法。而民法注重伦理性与海商法注重效益性是不易相容的。事实上,人类的伦理性似乎天然地抑制商业性①。与此同时,海商法的效益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社会伦理的全面颠覆。根据富勒的观点,由于商业行为具有互惠性和充分的流动性,“平等”才具有实质意义,“道德和法律义务”才可能发展。[19]也就是说商业行为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道德:完全背离道德的效益性是不可能存续的。商人为追求利益,具备依一定程度道德行事的动因②,而且其程度会随着商业的进步而提高。这一观点在海商法中有所体现,例如海商法中规定的海难救助义务。对于民法而言,救助义务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民法并未将其法律化。而海商法则将其确定为一项法定义务,这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为何二者在此处出现了道德要求的错位呢?原因就在于对航行而言,海难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任何人都难以通过自身努力避免这种危险,为了所有人的安全故将这一义务法律化。也就是说,这种救助存在着“互惠性和充分的流动性或可逆性”的《联合国运输法公约草案》基础③。又如1978年《汉堡规则》和2008年《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又称《鹿特丹规则》)取消了航海过失免责,火灾免责也实行完全的过失责任。其原因并不是商人道德水准的提升,而是“随着航海科学技术的发展,船舶技术状态的改善,以及船员素质的提高,海上风险相对于海事法律制度建立的初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界给航运带来的客观风险,已经大大减弱。”[5]15也就是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运风险减小,成本也就随之降低。成本降低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本愿意进入航运市场,也就是“流动性或可逆性”更加充分了。可以预见,如果航海的特殊风险完全消除,海商法对于船方的特殊保护也将被取消。但是如果基于民法伦理性的要求,取消对船方的特殊保护,则违反了科学规律,不利于海商法以及海上商业的发展。
其次,民法的地域性消解海商法的普适性。民法是国家权力的产物,海商法则更多体现了商人的自治性。权力都具有扩张的趋势,过去海商法之所以能够独立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权力尚不强大。可以认为,海商法的法典化是国家权力扩张的结果。但是民法具有地域性,各个国家的民法往往由于民族、宗教、文化和历史等原因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要将海商法纳入民法体系,就必须使得海商法适应这些与民法的差异。所以将海商法作为民法的代价之一是其统一性遭到国家的地域性限制。于是出现了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同时,“海事立法却越来越国内化,从而导致了各国海商法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不统一”的奇怪现象。[5]12但是海商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国际间的商业活动,各国海商法不统一不仅会降低海商法的效益性,严重时还会使商人在国际海上商事活动中无所适从。因此,“从19世纪末以来,各国航运界要求采取措施,消除各国海商法的差异。”[5]12可见虽然国家将地域性加之于海商法之上的原始意图在于保护本国利益、促进本国商业发展,但是却伤害了海商法的统一,最终遏制了海商法的生命力。
最后,民法的私法性限缩了海商法的范围。如果将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那么此处是指狭义的海商法,即“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特定法律规范的总称”,而广义的海商法则“是以与海上运输和船舶有关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民商事法律规范、海运行政法规范和海上特殊的刑事法律规范。”[20]在海商法被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之前,一直都是广义上的海商法。国家将海商法纳入其法律体系时,需要为其寻找合适的定位,具体做法是将其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但由于广义的海商法中包含了公法性规范,因此为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必须将这些公法性规范予以剔除。可以说,作为民法特别法的海商法是被整改过的。这也存在于中国制定《海商法》的过程中:“中国海商法起草时,在第十稿至第十七稿都是采用广义海商法的概念,直到1991年3月31日的修改稿才基本改为狭义海商法的表现形式。”[20]然而,海上的公法规范是与海商法共同发展形成的,因此具有与海商法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的公法学者面对海事公法时经常会因为缺乏海商法知识背景而难以涉猎,而海商法学者又把这些海事公法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最终使得中国的海事公法研究极为薄弱。
此外,如果一味地强调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那么海商法必然会“削足适履”,这极大地损害了海商法自身的充分发展。在中国,《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颁布,都会在海商法领域产生很大的认识上的困惑,每次民法的重大立法或法律的修改,都需要对海商法进行调适。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法律实践领域都会造成巨大的成本的付出。
六、结语
将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不但在学理上不能证成,在实践中也有害无益。因此,应当将海商法从民法的子法地位中独立出来,并与民法相并列。可以说,海商法对民法可以借鉴,但不能盲从。只有这样,才能理顺海商法与民法逻辑关系,为海商法学术研究提供更为广泛的空间,并促进海商的法律实践的健康发展。正如司玉琢教授所言:“海商法在国际上,特别是航运发达国家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少有近百年历史了,随着中国海运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海运立法的不断完善,中国海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从立法上把海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比简单地将其划归为某个法律部门的分支或属于某个法律部门的特别法更为适宜。”[1]这就意味着,应当以上述狭义的海商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海事行政法、海事刑法在内的海法体系。[21]
[1]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
SI Yu-zhuo.Maritime law[M].Beijing:Law Press:2003:6.(in Chinese)
[2]王千华,白越先.海商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3.
WANG Qian-hua,BAI Yue-xian.Maritime law[M].Guangzhou: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2003:3.(in Chinese)
[3]张丽英,邢海宝.海商法教程[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4.
ZHANG Li-ying,XING Hai-bao.A course of maritime law[M].Beijing: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Press,2002:4.(in Chinese)
[4]吴焕宁.海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5-16.
WU Huan-ning.Maritime law[M].Beijing:Law Press,1996:15-16.(in Chinese)
[5]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SI Yu-zhuo.Maritime law[M].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8.(in Chinese)
[6]KHALILIEH H S.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ca.800-1050)[M].Leiden:Brill Academic Pub,2006:1-10.
[7]何勤华,李求轶.海事法系的形成与生长[J].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5(5).
HE Qin-hua,LI Qiu-yi.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law’s system[J].Jounal of China Lawyer and Jurist,2005(5).(in Chinese)
[8]施天涛.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
SHI Tian-tao.Business law[M].Beijing:Law Press,2010:15.(in Chinese)
[9]张民安.商法总则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ZHANG Min-an.The general system of business law[M].Beijing:Law Press,2007.(in Chinese)
[10]夏锦文,付建平.罗马法复兴与西欧法制现代化[J].比较法研究,2003(2):21.
XIA Jin-wen,FU Jian-ping.Revival of Roman law and modern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J].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3(2):21.(in Chinese)
[11]劳森.罗马法对西方文明的贡献(下)[J].黄炎,译.比较法研究,1988(2):75-79.
LAWSON F H.Roman Law’s contribution to western civilization(II)[J].translated by HANG Yan.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88(2):75-79.(in Chinese)
[12]劳森.罗马法对西方文明的贡献(上)[J].黄炎,译.比较法研究,1988(1):57.
LAWSON F H.Roman Law’s contribution to western civilization(I)[J].translated by HANG Yan.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88(1):57.(in Chinese)
[13]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M].何勤华,李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750-751.
WIGMORE J H.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M].translated by HE Qin-hua,Li Xiu-qing.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750-751.(in Chinese)
[14]史际春,陈岳琴.论商法[J].中国法学,2001(4):94-95.
SHI Ji-chun,CHEN Yue-qin.On commerce law[J].China Legal Science,2001(4):94-95.(in Chinese)
[15]吴煦.论海商法基本原则及其成因分析[D].上海:上海海事大学,2002:3.
WU Xu.On foundation principle of maritime law[D].Shanghai: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2002:3.(in Chinese)
[16]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1.
ZHANG Wen-xian.Jurisprudence[M].Beijing:Law Press,2007:121.(in Chinese)
[17]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4.
BERMAN H J.Law and revolution[M].translated by HE Wei-fang,et al.Beijing: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1993:414.(in Chinese)
[18]TETLEY W.Maritime law as a mixed legal system[J].Tulane Maritime Law Journal,1999(spring):319-322.
[19]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30.
FULLER L L.The morality of law[M].translated by ZHENG Ge.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05:28-30.(in Chinese)
[20]司玉琢.海商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
SI Yu-zhuo.Maritime law monograph[M].Beijing:China People University Press,2007:6.(in Chinese)
[21]王世涛.论海法的统合[J].时代法学,2011(2):3-10.
WANG Shi-tao.On the integration of law of the sea[J].Presentday Law Science,2011(2):3-10.(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