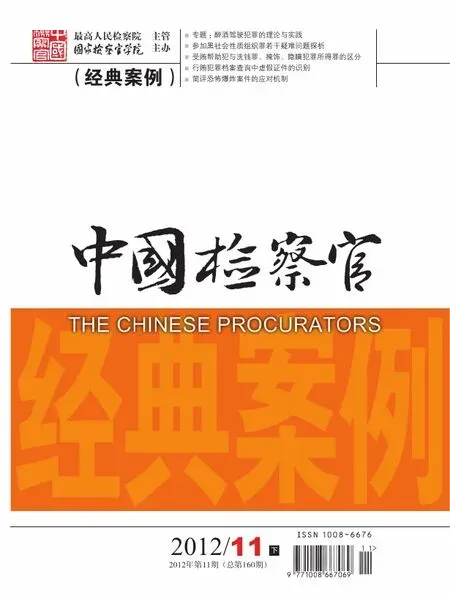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文◎赵 靖*
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文◎赵 靖*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犯罪嫌疑人肖某、陈某共谋将他人的机动车车牌盗走后藏匿,并将写有肖某手机号码的纸条贴在车的挡风玻璃上,在失主按其留下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二犯罪嫌疑人后,二犯罪嫌疑人让失主将一定数额的现金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二犯罪嫌疑人确认取得钱财后,告知车主被盗车牌的藏匿地点。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期间,犯罪嫌疑人肖某、陈某采取上述手段分别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江北区、渝北区、北碚区等地作案70余起,勒索60余名车主约8500元人民币。
二、分歧意见
对于此案的定性,存在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肖某、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要挟手段,强行索取被害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肖某、陈某为了敲诈车主的钱财而实施盗窃车牌的行为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盗窃罪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符合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肖某、陈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牵连犯,盗窃隐匿车牌行为触犯了盗窃罪,以车牌勒索钱财行为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应根据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从一重罪处罚即盗窃罪处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本案属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理
根据吸收犯的理论,吸收犯中的吸收是罪的吸收,其特点为:第一,事实上有数个不同的行为,每个都能独立构成犯罪,而且都分别符合刑法分则相关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第二,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罪的吸收关系,由于罪被吸收,当然刑也随之被吸收。吸收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1.法条内容上的吸收关系,即按照法律规定,一罪的犯罪构成为他罪所包括;2.一般经验上的吸收关系,这种吸收关系因为数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常常处于同一犯罪的过程: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的必然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自然结果。本案中行为人的行为较为符合吸收犯中第二种吸收关系的特征,但是二人构成的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之间不存在当然的关系,或者说,盗窃行为不是敲诈勒索行为的当然实行方法,而敲诈勒索行为同样也不是盗窃行为的必然发展结果。
在刑法理论上,吸收犯可以分为下述三种类型:(1)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例如运输毒品以非法持有毒品为前提,定罪的时候,运输毒品罪自然吸收非法持有毒品罪,对非法持有毒品罪不再另行定罪。(2)主行为吸收从行为。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先教唆杀人后又帮助杀人的,定罪的时候,杀人的教唆行为吸收帮助作为,对杀人的帮助行为不再另行定罪。(3)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例如行为人为杀人进行预备活动,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中断,后又再次预备后完成其杀人行为;或者行为人先教唆杀人,后又直接参与杀人之实行的,应分别以杀人的实行犯论处,对于杀人的预备与教唆不再另行定罪。由此可以看出,吸收犯要求犯罪行为属于同一罪质,即不管该犯罪行为是属于基本犯罪构成,还是修正犯罪构成,都属于同一犯罪行为,也即同一犯罪的不同形态;也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可吸收性。并且,按照吸收犯的理论,如果数个犯罪性质不同的话,则构成数罪,而不是一罪,否则只能实行数罪并罚,如果强行吸收的话,就根本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本案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其犯罪行为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牵连关系,犯罪的目的和手段触犯了两个罪名。行为人盗窃车牌敲诈勒索钱财,是在一个犯罪目的和故意支配下实施的两个犯罪行为,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是目的,两行为之间具有目的和手段间的牵连关系。即行为人通过盗窃车牌,要挟车主赎回车牌,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牵连犯实质上是数罪,而在裁判上一般是从一重罪处罚。本案中,行为人客观上构成两个犯罪,形式上触犯了三个罪名,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基于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以其牵连犯中的从一重罪处理。
(二)本案作为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行为人实施了敲诈行为是关键。就本案二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来看,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是利用补办车牌相对较高的费用及繁琐的手续和与之相比较为低廉的赎金之间的差异,来要挟被盗车主,以实现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行为人的犯罪意图中,具有要挟他人并非法勒索他人钱财的的主观故意,并且数额较大,依法构成犯罪。其之所以实施犯罪行为,就是利用车主不愿意去办理车牌的心理来要挟车主并勒索钱财。由此分析,犯罪嫌疑人客观上具备了实施了敲诈行为这一关键要件。但是,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结果犯,构成本罪还应以勒索财物数额较大为必要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就规定了以1000元至3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重庆市 “五长”联席会议纪要中,进一步明确将1500元作为重庆市追诉敲诈勒索罪的起点。
该起案件中,二人的犯罪行为基本不存在单次达到法定追究数额的情形,但犯罪嫌疑人大多短时间多次作案,其多次累加后的数额可以达到法定追究数额,那么是否能把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数额予以累加呢?笔者认为,不应当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是行为人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其敲诈勒索数额就可以累加起来。理由是:根据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任何行为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时才认为是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对该类案件每次作案的数额可以累计,或者在多长时间内累计,累计每次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试想,如果可以这样简单的相加,将行为人多次作案金额予以累加,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为何又对数额累计的问题特意作出规定呢?
因此,按照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类推。那么,要将本案作为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三)本案不宜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有人认为,被告人为了敲诈车主的钱财而实施盗窃车牌的行为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盗窃罪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符合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但是,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司法解释将“车牌”解释为“国家机关证件”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7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从以上规定看,四机关制定该解释是“为依法严厉打击盗窃、抢劫机动车犯罪活动,堵塞盗窃、抢劫机动车犯罪分子的销赃渠道”,因而该解释的范围是适用于“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中。所以,具体适用“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时,在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中,才将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的行为,以及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按照“国家机关证件”解释;换言之,该规定的效力范围是在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时,对于“伪造、变造、买卖车牌”的行为才将国家机关证件的外延涵盖机动车号牌,适用国家机关证件。该解释未将盗窃车牌行为纳入《规定》的范围,即该解释针对的是伪造、变造、买卖车牌行为适用伪造、变造、买卖“国家证件”,未扩大到盗窃车牌。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脱离《规定》的范围,直接将“车牌”理解为“国家机关证件”会造成解释的扩大化。
第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达三本以上的,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一解释中没有使用“牌证”一词,而使用叙明表述的方法,只规定了行驶证和登记证书这两种证件,这就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表明了,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第三,汽车牌照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作出明确解释之前,我们不能贸然将汽车牌照纳入国家机关证件的范围之内,擅自扩大打击范围。结合刑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关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并未规定将盗窃证件的价值作为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按通常理解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是行为犯,不以犯罪金额作为犯罪构成,如此理解,那么是否盗窃车牌一块,也应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呢?如果只要发生盗窃车牌的行为,就适用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这就会造成国家机关证件含义的扩大,入罪的门槛也就随之降低,这就意味着刑法严厉性的急剧增加。
因此,脱离《规定》适用的具体环境将造成解释的扩大化,并且如果按照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对该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会造成刑法中出现一个新的“盗窃车牌”罪名,按照立法的权限,这样的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
(四)本案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肖某和陈某的行为即属于典型的牵连犯:二人实施犯罪行为有一个犯罪目的,就是利用车牌勒索钱财。围绕这个犯罪目的,二人实施了准备工具、买手机卡、设立银行账户、盗窃隐匿车牌以及留纸条等数个行为。这些行为互相联系共同为了勒索钱财这个犯罪目的服务,是勒索钱财的方法和手段。其中盗窃隐匿车牌行为触犯了盗窃罪,以车牌勒索钱财行为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在确定本案是牵连犯之后,让我们再根据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从一重罪处断来对二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如前所述,二人触犯了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两个罪名。其中盗窃罪是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应当按照价格鉴定书认定的车牌价值认定二人的盗窃数额,二人作案70余起,盗窃车牌110余块,车牌鉴定价值应该高于本市盗窃罪1000元的最低追诉标准;二人敲诈勒索数额为8500余元,均属于“数额较大”。根据《刑法》第264条、274条规定,盗窃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比较而言,盗窃罪的法定刑除主刑之外,还包括附加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明显重于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
另外,从本案来看,二人的主观故意是盗窃车牌后实行其变现的价值,实际上,盗窃行为是直接行为,敲诈勒索是盗窃后为实现直接目的而实施的又一附属行为,或者说是手段行为,目的是将盗窃所得的赃物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盗窃罪名更能体现其主观恶性。
因此,按照牵连犯的理论,并结合本案的特点,对肖某、陈某按盗窃罪处罚比较适宜。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4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