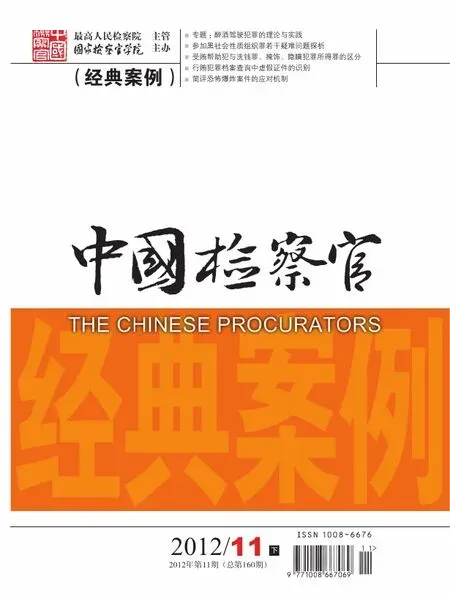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行为之理解与适用
文◎郭志平 许 航
《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行为之理解与适用
文◎郭志平*许 航**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的“户”需要具备两大特征,即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包括日常生活性、久居性和封闭性与排他性。“入户盗窃”未窃得财物以及窃得的财物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倘若“入户盗窃”针对的是有价值的财物,即使最终未得逞,也应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入户盗窃”是否入罪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客观手段、造成的后果及其他相关情节分别认定。
20 11年5月1日正式生效的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行为新增为《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基本罪状,从原来的“定性加定量”单一模式转变为“定性加定量”与“定性不定量”并举的双重模式。[1]此举对盗窃罪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年多时间里,各地司法机纷纷转变办案模式,将“入户盗窃”行为一律入刑,这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极大争议。为此,有必要重返法律规定本身,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入户盗窃”行为进行分析。
一、“户”的定义与特征
要正确理解和适用修正后《刑法》关于“入户盗窃”行为的规定,首先要明确“入户盗窃”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界定行为人非法侵入的场所是否属于“户”,这是准确把握“入户盗窃”行为认定标准的前提。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对“户”的概念及其范围存在争议,以下将具体展开。
(一)“户”的定义
对于“户”的定义,理论界存在较多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认为“户”仅仅指公民的私人民宅,不包括其他场所;[2](2)认为“户”是指以此为家,有居住功能的场所,如私人住宅,学生、员工宿舍等,但不包括宾馆房间及值班宿舍等临时居所;[3](3)认为“户”是指公民长期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只要特征符合私人住宅的,都可以将其视为“户”,包括酒店房间、固定值班人员的宿舍等场所;[4](4)认为“户”指一切供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场所,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办公场所;[5](5)认为“户”是允许特定人员出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的院落和办公室,还包括旅店房间等。[6]以上观点从不同层面体现了“户”的某些特性,但上述第四、五种观点似乎混淆了“户”与“室”的概念,有扩大“户”之外延之嫌。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1999年10月《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中称“入户盗窃”的“户”指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院落、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蓬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2000年11月22日《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进行抢劫的行为。2005年6月8日《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户”做出补充:“户”的范围指住所,特征是为他人提供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集体宿舍、临时工棚、旅店宾馆等不宜认定为“户”,但特殊情况下,具备了上述两个特征时,也可以认定为“户”。通过相关司法解释不难看出,“入户盗窃”中的“户”其核心特征应与“家庭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户”的含义解释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外界相对隔离、具有相对封闭性、私密性和排他性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单位、学校为员工提供的具有家庭生活性质的宿舍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一般情况,集体宿舍、临时工棚、旅店宾馆等也不宜认定为“户”,但特殊情况下,具备了上述两个特征时,可以认定为“户”。
(二)“户”的特征
从上文“户”的概念可以看出,其需要具备两大特征,即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具体而言包括:
1.日常生活性和久居性。这是户的功能特征,它是判断某场所是否属于“户”的核心因素。其与营业性的商用房、开放性的学习、单位等公共建筑、半封闭式的商住两用房不同,这里的“户”指的是专供他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繁衍后代、存放财物的特定私人空间。“入户盗窃”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财产权益的同时,还对他人的隐私权甚至是人身安全造成了潜在的隐患。
2.封闭性与排他性。这是户的场所特征,居住者对“户”享有排他性权利,外人非经允许或有法定事由不得随意入内,居住者有权要求非法侵入者离开自己的住所。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对某些场所的属性难以界定,如商住两用的房屋、城市商品房、农村毛草房、灾区临时搭建的帐篷、乞丐居住的桥洞、汽油罐、山中洞穴以及学生集体宿舍等,此时,判断的依据仍然是其是否具备“户”的两个特征。
(三)“户”与“室”的区别
实践办案中,还经常出现将“入户盗窃”和“入室盗窃”混同的现象。事实上,早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立法机关就将条文中的“入室”改为“入户”,这说明两者是有区别的。尽管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室的外延要大于户,户强调的是起居生活性,而室的功能不局限于居住,还可用于办公、经营等。因此,只有当“室”具备了“户”的“日常生活性”后,才能被认定为“户”。办公楼、厂房、校舍、值班室等场所,虽然也是相对固定、封闭的内部空间,但主要功能侧重于办公、学习以及临时休息,不具备“户”特有的日常生活性,故不能认定为“户”。
二、司法实务中准确把握“户”的范围
本节将选取四类在实务工作中较为常见的特殊场所,对其是否具备“户”的属性展开分析与探讨。
(一)集商业经营与生活起居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能否认定为“户”
这类房屋俗称商住两用房。最高人民法院曾在《纪要》中写明: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但该规定过于笼统,没有明确何时为“一般情况”,何时可作为特殊情况而被视为“户”。笔者认为,应结合犯罪区域、营业时间、场所功能等因素对场所属性加以综合判断。具体可分为典型性房屋和非典型性房屋。
1.典型性商住两用房。此类房屋经营和生活起居功能基本均衡,可以通过场所区域或者营业时间加以划分。
[案例一]贾某系废品回收站经营人,其夫妇二人居住的场所属于沿街的庭院房,屋外挂有某某废品回收站的店牌,大门内前院用于堆放回收的废品,后屋用于生活起居。李某与张某经事先商议后决定进入贾某的回收站内盗窃。某日下午,李某和张某以商谈销售废品业务为名进入贾某的废品回收站后,期间李某谎称借用洗手间,从而进入贾某居住的后屋并在房内窃得手机两部。
关于本案,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二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入户盗窃”?第二,如果贾某房屋的格局为外屋里院,进入贾某用于经营废品的后院需要路过贾某夫妇生活起居的房屋,则二人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从作案地点判断,该场所是商住两用房,房内分为院落和里屋,院落作为废品堆放及交易的场所,具有公开性和营业性,而里屋与院落之间被砖墙隔开,且中间有门,作为单独的生活起居场所,具有私密性,两处互不影响,互不干涉。此种情况下,里屋具有“户”的属性。李某非法进入贾某的里屋实施盗窃的行为,应视为入户盗窃。而如果贾某房屋的格局为外屋里院,进入贾某用于经营废品的后院需要路过贾某夫妇生活起居的房屋,此时贾某夫妇居住的房屋成为了不特定人员与贾某进行交易的必经之路,属于经营场所的一条通道,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公开性,因此不能再认定为生活区域,李某的盗窃行为也就不能视为入户盗窃。
2.非典型性商住两用房。此类房屋在经营和生活起居功能上有所侧重,通过空间和时间较难划分,应结合其功能特征加以判断。
[案例二]卖淫女李某将其提供性服务的场所设在自己为生活起居而租用的小区公寓内,嫖客王某光顾过几次,并看见李某将嫖资放在房间某抽屉内。某日,王某以实施盗窃为目的,谎称嫖娼而来到卖淫女李某的住处,趁李某洗澡之际,从房内窃得钱款1000元后逃离。
上述案例系行为人将自己生活起居的住所兼用于违法活动的情况,这与住户偶尔在家中召集相对熟识和固定的人员进行赌博活动的情形类似,由于居住者每日用于非法活动的时间和次数有限,顶多只能认为其住处兼具非法活动性质,其主要功能仍侧重于生活起居且具有相应的私密性和封闭性,故应属于“户”。
但如果是在居民楼内租房专门用于从事赌博等非法活动,部分人员居住其中的目的是为了“看场子”和随时营业而非为了饮食起居,则行为人无论何时进入盗窃,均不能被评价为“入户盗窃”。
(二)职工、学生的宿舍能否认定为“户”
判断此类场所的属性,应根据房屋坐落的区域、内部格局、居住者人员关系等多项因素方加以具体分析:
1.单位在小区住宅内为员工生活起居而租用的房屋应认定为“户”。从布局来看,社会观念中的“户”通常指民用住宅(如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等),其主要功能是供他人家庭生活所用,单位在小区住宅内租用的员工宿舍,其外观特征及内部结构与普通民宅毫无区别。从功能来看,员工下班后的日常起居均发生在该房屋内,加之居住者成员彼此认识,相互之间能够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生活联系,在此情况下,员工宿舍具备了“户”应有的“日常生活性”。有观点认为,多人居住的员工宿舍,其成员间没有独立的空间,也不具备排除其他成员的亲友进入房间的权利,因此缺乏私密性和排他性。事实上,除了夫妻之外,即便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其共住一房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自由,要求房内居住者的自由状态达到完全排他的程度,似乎过于苛求。同时,要求员工宿舍的封闭性达到“绝缘”的程度,也实属不可能和没必要。一来即便是正常的家庭,有亲友拜访也是常事,因此不能要求群居的宿舍完全杜绝访客。二来通常住房的钥匙只有居住者才有,无论是哪名居住者的亲友探访,都有迹可循。三来既然是用于生活起居的场所,就不会出现络绎不绝的陌生人进出住房的情况,这也是宿舍其本身的生活起居功能所决定。因此,基于坐落于小区住宅内的员工宿舍具备了日常生活功能以及必要的私密性和排他性,应认定为“户”。
2.单人居住的高级学生公寓应认定为“户”。目前在高校中有部分学生公寓是针对留学生或者是硕士、博士研究生而建造的,内部格局与设施配备基本可以满足学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且公寓系单人间,私密性较强,虽然房门钥匙居住者和公寓管理者均持有,但未经学生本人允许或法定事由,其他人无权入内,学生可在房间内自由地休息、生活以及放心地存放财物。因此,这类高级学生公寓也应认定为“户”。
3.坐落于校内的学生集体宿舍不应认定为“户”。此类住房通常被称之为“集体寝室”,作为学生学习上课之外居住的场所,其功能更体现在供学生休息。在房间内,通常为四至八人共同居住,每位同学所能支配的空间也不足几平方米,其基本上不具备“户”的“日常生活”功能。虽然学生集体宿舍与外界相对隔离,但这种封闭性、私密性和排他性却无法与“户”相提并论。
(三)合租房能否认定为“户”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中明确规定:“户”可以包括他人为生活租用的房屋。其并没有限定租用者之间必须具备血缘或者婚姻关系,也未要求居住者必须为两人或以上。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人口迁徙频繁,在外务工人员、蜗居一族同租一房,留守城市或农村的老人独居家中,这种情况实属普遍,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居住的房屋因没有血缘或婚姻纽带连接、没有较多的固定成员,就不是“户”。相反地,他们的隐私权、财产权同样应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更何况合租房其本身从功能特征、场所特征以及居住者的使用目的来看,均与“户”基本一致。首先,合租房坐落于民用小区内,配备了完备的生活起居设施,只要居住者愿意,其完全可以实现居家生活的需要;其次,大部分选择合租的人群是相互认识甚至是关系较好的,合租者以家庭生活的意思居住其间,成员相对固定,关系相对紧密,对房屋的控制、支配及排他力均较强。这种情况下,合租房显然已具备了生活起居的功能和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功能,因而可以被认定为“户”。
(四)酒店宾馆、临时简易建筑能否认定为“户”
1.酒店旅馆。此类场所通常是供客人临时落脚和休息,多用于商业经营而非家庭生活,其流动性与公共性很大,经常会有不特定的人可以合理进出,加之居住者也不具有久居的意愿,因此一般不认定为“户”。但如果是长期租用供生活起居的房间,则具备了一定的“户”的特征,如有些旅客将家属迁至本地,全家人长期在酒店包房作为家庭住所,并在房内添置了必要的生活物品,如电磁炉、电冰箱等,未经旅客同意,酒店工作人员及他人无权进入和打扰。在这种情况下,酒店的长包房就可以被认定为“户”。
2.临时简易建筑物。包括为进行看护而搭建的各类棚房,如瓜农的瓜棚、鱼塘的渔棚、临时搭建的值班室、建筑工地的工棚等。[7]判断其房屋属性时主要看其是否融入了生活的元素并具有相对私密性。比如工地上为看护建筑材料而搭建的工棚,如果看护工人仅将此视为值班室,其另有固定的住所,则不能认定为“户”,但如果值班工人单身或者是全家人没有其他住处,把工棚当住所使用,则该工棚应认定为“户”。又如现在新兴的“草莓园”,农民每年有几个月定期居住在简易瓜棚内看护和销售草莓,晚上收摊后瓜棚就成为了其用于家庭生活的封闭场所,这时瓜棚可以被认定为“户”。但对于那些在建筑工地搭建的集体宿舍式的工棚,由于居住人员多而混杂,成员间彼此关系不固定,流动性大,因此缺乏必要的生活性和私密性,不能认定为“户”。
三、“入户盗窃”犯罪形态的把握
在理论界对盗窃罪(未遂)的争论多体现在其与既遂的分界标准,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却在于情节轻微的盗窃未遂能否定罪。本节要探讨的是“入户盗窃”未窃得财物以及窃得的财物不具有经济价值的情况,倘若“入户盗窃”且针对的是有价值的财物,即便是最终未得逞,也应认定为盗窃罪(未遂)。
(一)“入户盗窃”未窃得财物(包括未实行终了)不能认定为犯罪
盗窃罪作为典型侵犯财产权犯罪,其社会危害性集中反映在盗窃数额上。我国刑法历来以盗窃的财物价值大小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界限。“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罪中特殊的犯罪形态,其侵害的法益包括他人的财产权益,故在既未遂认定标准上应服从于盗窃罪的基本罪质,以实际取得财物为既遂标准,系结果犯而非行为犯,如果行为人在实行终了后未实际窃得财物,或者是未能实行终了且盗窃对象不明或无价值,应当认定为盗窃未遂不构成犯罪。
(二)“入户盗窃”取得不具有经济价值的财物不能认定为犯罪
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应具有经济价值,这是盗窃罪作为侵财类犯罪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不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无法称之为“财”物,不可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也无法为刑法所保护。要判断物品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要看其是否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两者均低廉时,盗窃行为因不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能纳入刑法评价的范畴。
四、适用“但书”条款让情节轻微的“入户盗窃”行为出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要具有法益侵害性且达到一定的程度,即“质”与“量”的统一。尽管“入户盗窃”没有明确规定数额和次数要求,但刑法对犯罪有着隐形的“量”的要求。就如盗窃罪明确规定了普通盗窃行为只要达到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但同时又通过司法解释将情节相对轻微的盗窃行为排除在刑罚之外。因此,司法实践中对“入户盗窃”行为不能一概“入罪没商量”,而是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行为人“入户盗窃”时的主观动机、客观手段、造成的后果以及其他相关情节做出不同的处罚。对社会影响恶劣如惯偷、累犯、团伙犯罪、持械犯罪等加大打击力度,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未遂犯等,根据其悔罪态度和再犯可能性,适时地运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将其降格为行政法规调整的范畴,实现公正与效率并举。
注释:
[1]金昌俊:《浅析刑法修正案(八)中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载《延边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2]陈兴良:《刑法疏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435页。
[3]熊洪文:《再谈对抢劫罪之加重情形的认定》,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7期。
[4]周振想、林维:《抢劫罪特别类型研究》,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期。
[5]肖中华:《论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5期。
[6]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编:《最新刑法释义与适用指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427页。
[7]郭立新、杨迎泽主编:《刑法分则适用疑难问题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310014]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3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