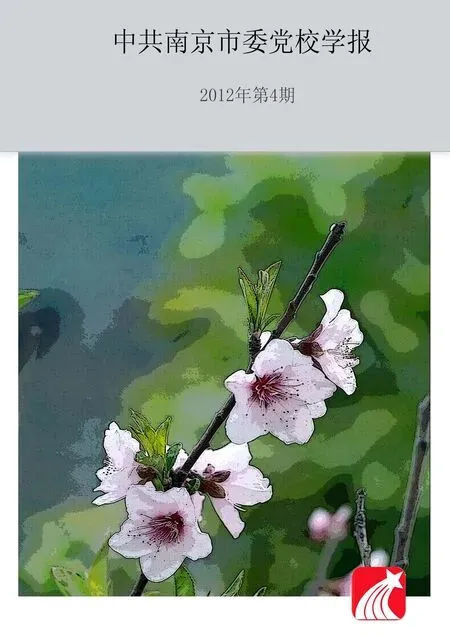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基层组织*
刘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限于人口与资源矛盾及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大部分农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移到城市,他们还要依托村庄完成人口再生产和家庭再生产;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要兼顾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农村稳定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经济体系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以上诸项条件的约束造就出农村在国家战略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空心化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大众传媒的渗透,人际关联变得理性化、工具化;随着村庄社会边界的开放,村庄共同体解体,农民沦为“无公德的个人”;[1]随着收入结构的变化,农民经济分化严重,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原有的伦理道德和地方规范瓦解,村庄舆论不再发挥作用,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不禁思考:变迁中的乡村秩序如何维系,如何定位嵌入于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
一、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与功能
学术界一般认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的推行,中央在农村社会实行“乡政村治”模式,即将行政权力上收到乡镇一级,在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也有学者不将乡村两级组织加以区分,笼统的称为“基层政权”,如张静称村级组织为“村政府”。[2]更多学者认为,由于乡镇政府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不完整,且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与自利性,使得“乡政”的实际运作状态远较制度设置复杂得多,吴思红索性用“半官僚制”[3]来说明乡政的尴尬。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对村庄事务行使自治权,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一部分,对本镇事务行使管理权,乡村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际的乡村组织互动却用私人关系替代公共规则,乡镇政府根据上级任务的轻重缓急对村级组织或干预或放任或庇护,使得“赢利型经纪”或“保护型经纪”的定性分析不能完全概括村级组织的角色。总的说来,乡村组织的角色性质模糊且尴尬,它们都具有“准政权”的性质。
我们将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分为基础功能和具体功能。[4]所谓基础功能,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回应自上而下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目标和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变迁要求的功能。所谓具体功能,是指乡村组织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完成的阶段性具体性任务的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性质的乡村社会中,基层组织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但具体目标要顺应总体目标,具体功能要与基础功能相配套。基层组织在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不可替代。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和社会主义目标决定了基层组织的基础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基层组织的具体功能会有变化,但它应该与基础功能方向一致。旨在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层组织改革必须统筹好基础功能与具体功能,不能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功利性短视性的过激过快政策调整。
晚清以来,为了回应西方挑战,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开始国家政权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以深入农村社会的组织体系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民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它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较为柔弱,从农村汲取上来的资源被中间层大量消耗,造成杜赞奇所说的政权内卷化[5]后果,国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大受影响,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乃至暴力抗争。新中国利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不仅将分散的农民整合起来以促成有效率的农业生产,而且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真正克服了国家政权内卷化难题。另一方面,正是人民公社的制度设置,使国家加强对农村资源提取力度的同时保持住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从而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从村庄撤出,但压力型体制却让县乡村三级组织牢牢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并没有消减,只是以另一种社会面貌出现。权力结构的虚弱和政绩工作的重要形塑出乡村两级组织的利益共同体特征,它们在完成上级任务的过程中将基础功能和具体功能分别对待,导致治理社会的缺位、错位及越位,引发1990年代中期后的三农危机。
我们将基层组织的基础功能概括为:应对乡村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秩序问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战略支点和腾挪空间,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公民素质;将基层组织的具体功能概括为:执行上级交付的任务工作,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组织农民集体应对生产生活。考察基层组织何去何从应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出发,将具体功能的完成情况,及与基础功能的匹配程度作为重要衡量指标,而不是仅仅考虑短期的经济社会利益。
二、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组织与农村社会
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负担逐渐加重,基层治理出现严重危机,政府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李昌平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口号为解决三农问题奔走呐喊,引发社会各界的共鸣。为缓和干群矛盾,加强对基层组织的监管,修复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央政府于2000年在安徽省实行税费改革实验,并终于在2006年底在全国正式免除农业税费。为切实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性因素,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支持,中央政府陆续推出相应的配套改革政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乡镇机构改革、乡村债务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改革等政策措施陆续进入农村社会。乡村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有的地方甚至取消村民小组长)、取消两工制度、取消农业共同生产费,实施种粮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等。乡村体制改革重构了乡村治理格局,对乡村组织的权力运作和功能发挥影响巨大。
税费改革及其相应的配套改革试图通过取消农业税费和加强转移支付实现乡镇政府从“管治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而县乡体制设计和财政制度调整造成乡镇财政的空壳化,乡镇政府不得不四处借贷,向上级跑钱要项目,对应有的服务职能却不予重视,逐渐成为“悬浮”型政权。[6]另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引起的干群矛盾不再是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并不是说乡村社会至此平安无事,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对乡村治理提出严峻考验。乡村体制改革使一些重要职能部门权力上收,乡镇政府已没有多少实质性权力,但在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评压力下,基层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性治理策略,通过变通、跑关系来完成上级任务,从而滋生出丧失政治性、原则性的策略主义行为,如给无理上访者以好处,“花钱买平安”,利用灰黑势力摆平矛盾,把社会势力吸纳进体制。权力和和责任的不对称使基层政府在失去做坏事能力的同时也丧失做好事的能力,他们失去创新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动力,只好以“不出事逻辑”维护乡村的底线秩序。
村级组织是村庄事务的直接管理者,与乡镇干部不同,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具有非正式色彩,是所谓的“不脱产”干部,村庄事务的突击性、不规则性、综合性、临时性特点使村干部必须灵活处理各种关系,因地制宜管理村级事务,软硬兼施摆平不合作者。在农业税时代,村级组织要组织农业生产,每年都要进行公益事业建设,最典型的是义务工和积累工制度,正是集体活动的存在使村级组织成功嵌入村庄社会。如果村干部不调解村民矛盾或组织渠道维护,村民就可能因此拒缴税费,不配合村干部工作,村干部和村民通过利益连带被捆绑进村集体。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和村庄社会的“制度性关联”[7]机制被打破,村干部介入村庄事务的积极性下降,对村庄的制度性控制能力降低。但村级组织既没有变成服务型组织,也不是无所事事,一些地方的村干部向上跑项目捞资源以自肥,导致村级组织的脱嵌化;一些地方的村干部则将原来的“软指标当硬指标搞”,如建立民事档案、实行制度上墙,推行坐班制度,村级组织的规范化和形式化倾向明显。[8]这个时期的村干部也会在意农田水利建设、村民纠纷调解,但关注重心却发生变化,只要农民不上访,不影响社会稳定,怎么作为都可以,民情民意和村庄秩序很少被村干部上心。在治权弱化的背景下,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相互不得罪,村级组织日益“悬浮”于村庄社会。
在后税费时代,村庄原生型权威解体,迫切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以维护村庄秩序,但此时的乡村治理却遭遇重重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社会灰色化严重。混混、无赖户、钉子户等边缘群体崛起,他们不仅威胁农民的身体和心理,而且利用暴力手段攫取国家资源,甚至将势力触角延伸进乡村社会内部,造成基层治理内卷化和国家合法性流失。二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公益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下降。税费改革后,国家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制供给农村公共品,但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够大,且组织实施机制缺乏针对性有效性,造成资源浪费和供给不足并存。三是乡村内部的矛盾纠纷得不到有效化解,村民之间的积怨长期积压,很小的一点生活摩擦即可能大打出手,村民之间因出“气”而频频上访的情况出现,给基层信访治理带来很大压力。四是村庄经济分化强烈,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农民公共偏好的表达不畅,不同阶层的利益整合不足,贫富差距拉大,为富不仁现象出现,极易引发社会泄愤事件,危害乡村的团结稳定。
通过上述我们发现,当前乡村组织的权力结构与基层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乡村组织没有发挥好它的应有功能与乡村体制改革政策有关。当前的乡村治理危机既与决策者对政策后果估计不足有关,也与他们对乡村组织的功能认识错位有关。要想彻底消除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治理性危机,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序,保证国家战略发展的总体目标,必须重建农村基层组织。
三、为什么需要农村基层组织
关于乡村体制改革政策的主流意见认为,乡村组织的“黑恶化”和“营利化”是农民负担加重的根源,为了堵住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口子,斩断乡村组织作恶的黑手,必须强化对基层财政的预算管理,规范基层权力的运作,加强对基层组织的监管力度。按照这种改革逻辑,乡村组织作为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其功能只是从农村汲取资源以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当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农业税费对中国现代化意义不大时,乡村组织就已完成历史使命。且国家很难解决农业税费征收过程中的贪污腐败、工作作风粗暴等技术问题,从理论上讲,乡村组织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乡村体制改革正当其时。国家正好利用税费改革的契机减少对基层组织的财政支持,通过内在的资源“倒逼”迫使乡村组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撤乡并镇,合村并组,最终达到转变行政职能,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9]
这种政策思维有两个漏洞:一是乡村组织有具体功能和基础功能的区别,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乡村组织要执行不同的功能(即具体功能),但它一定要和基础功能相合拍。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要完成“规划的社会变迁”,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就必须保持一个强大的基层组织以接应自上而下的政策任务,从农村汲取资源的任务伴随乡村组织很多年,但乡村组织的功能不仅于此。杜赞奇曾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二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公民权利和义务逐渐扩大。[10]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乡村组织的基础功能之一是将传统的中国农民改造成具有民主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这一功能的发挥才刚刚开始,任重道远。
第二个漏洞是:限于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国农村在未来的50年内不可能消失,大部分农民还要依托村庄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好农村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功能意义重大。既有的政策研究对维持农村秩序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农民有合作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农民善分也善合,当农民主体认识到合作能达到更大收益,能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便会自觉建立起基于利益连带的合作组织。乡村秩序是一种公共利益,当农民认识到村庄稳定对个体利益的重要性,且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达成均衡时,就会自觉合作以担负起维护村庄秩序的任务。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通过发展NGO组织来维护村庄秩序。成立NGO组织好处多多,如它体现公民社会的特性,能够实现社会的自主发育,甚至能自觉代表社会与国家争夺话语空间,表达公共声音和公共需求,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NGO组织与传统民间组织的不同在于它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公益性特征,从而可以代替乡村组织,实现提高农民公民素质的任务。在国家权力撤出农村后,NGO组织正好可以跟进,只要获得国家制度的授权,NGO组织顺利进入基层社会,它就能创新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以实现组织目标,进而实现与基层政府的互惠关系,保持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
上述两种意见都在应然层面回应秩序问题,有诸多可商榷之处。第一种意见没有考虑到在当前的村庄社会里,农民经济分化剧烈,不同群体农民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一些村民的主要收入依靠土地获得,对农田水利维护很是重视,对缴纳水费也很积极,但那些主要利益在村庄外部,将种田当作附加收益的村民,则一般会对农田实行粗放耕作,不管不问农田保水情况,造成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另一方面,农民的理性只是个体理性,他们在生产合作中无法克服“搭便车”行为,无法达成集体合作的理性。且农民的理性与现代公民的理性差别巨大,他们不会孤立计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而是在村庄场域中通过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是否行动,个人得失多少不必在意,但是别人不能从我的行动中白白得到好处。[11]我们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时听说的“怕饿死的就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即是农民这种特殊理性观的体现。①第二种意见没有考虑到乡村组织不仅承担收取农业税费的任务,还要承担保持农村社会安定,执行自上而下政策命令的任务。乡村组织的退出并不意味着NGO组织的顺利进入,村庄边缘群体的崛起给农村稳定带来巨大影响,一些黑灰势力会趁机介入村庄事务,利用国家权力真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且NGO组织缺少强制性与命令性,农民可以自愿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农民合作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农民利益的多元会加剧合作的难度。且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所承担的行政任务是大大减轻,但并不是说它们就无所作为,可有可无了,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投入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来接应;国家实行对农民的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下达各项政策文件和战略规划需要基层通知转达。总之,乡村组织在国家现代建设事业过程中发挥诸多不可替代的功能,我们必须重视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基层组织
基层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纽带,要协调好自上而下的国家目标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的任务,就要将“基础功能”和“具体功能”统筹兼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规划社会变迁”的要求,国家必须配置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引导农民向着既定目标步步推进,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无论是税改前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以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还是税改后国家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其总体目标都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吉登斯说,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史是将传社区内部的人不断解放出来,突破地方性规范的束缚,直面行政监视、工业管理、国家规范、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12]中国农民挣脱土地束缚,从村庄中走出来,并不会直接变成现代公民,他们需要国家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组织要发挥出相应的整合动员功能,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就必须拥有相对完善的组织结构和相对强大的权力资源。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庞大工程,在不同的国家任务和不同的乡村社会中,基层组织的权力配置不同,需要承担“具体功能”也不同。现实情况常常是一项旧任务刚刚结束,另一项新任务又接踵而来,一些突发性紧急性任务也会突然降临,不同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分,对基层组织的功能要求也不尽相同,但只要我们认识清楚基层组织的基础功能和具体功能的关系,就能兼顾好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大众传媒的强力渗透下,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必须思考乡村社会的稳定及农村工作的开展。当前乡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接应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投入,为农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同时创新社会管理,整合不同层次农民的利益,实现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要想高效开展农村工作,需要对乡村事务的特点有基本了解。1980年以来,国家一直推动政府体制改革,试图建立一套分工明确,结构合理的科层制组织,不仅在乡镇设立职能对接的党政办公室,而且设立对应农村公共需求的专业化服务组织——七站八所,村干部也成为拿钱的办事员。上层建筑的变革目的是为实现政府现代化,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但条条式的管理模式到乡村后就必须统合成块块,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事务的琐碎性及综合性特点使乡村干部必须“下去一拢统,上来再分工”,他们必须走家串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农村事务的非规则性造成正式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无力应对,乡村干部必须借用地方性习俗、人情面子、暴力威胁等手段软硬兼施,因地制宜地解决;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在夏季农田用水高峰期,乡村干部要做好组织统筹,在冬季农闲时要组织冬修,年前一些地方容易出现偷盗事件,乡村干部也要组织人联防;农村事务具有突发性,如应对非典、禽流感,搞新农村建设,组织农网改造,传达各项惠农政策……农村事务的乡土性、不规则性、突发性等特点要求乡村组织结构与之相配套,开展农村工作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如果不实事求是地考察农村基层工作的特点,盲目建设一套结构复杂、分工明确、缺少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基层组织,其后果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且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农村需要。
在笔者看来,要想将乡村组织的基础功能和具体功能结合起来,将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与维护农村安定和谐统筹起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重建农村基层组织:一是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能力,加强对上访户、钉子户、无赖户、混混等边缘群体的分类治理能力。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分化剧烈,农民的利益需求越来越多元,如何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以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共秩序是乡村治理的题中之义。同时,随着村庄共同体的解体,内生权威在村庄事务中的作用下降,村庄舆论不再发挥作用,边缘群体崛起且不再受到村庄约束,他们利用制度软肋进行“要挟型上访”,捞取不正当好处,严重影响农民的公平观念和社会稳定,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二是提高组织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效表达农民的公共品偏好。受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等因素影响,县乡村无力形成公共品筹资和供给的有效机制,且当前的农村社会空心化严重,村庄内部缺乏整合能力,一事一议等筹资手段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项目制和专项资金的注入没有针对性,瞄准率低,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及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就要“还权于村,还利于民”,通过扶持村级组织,完善村民自治,使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得到基层社会的接应,实现上下联动,供需结合。三是设置沟通渠道使农民能顺利表达利益诉求,吸纳和整合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并非单向度的管理与服务,而是通过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资源输入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利益偏好相沟通相连接,实现双方的积极互动,从而达到农村社会的善治目标。现在的农民思想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明显提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不仅要组织好农民,还要设置农民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有效渠道,只有适应农民高涨的民主参与诉求,加大民事纠纷的调解力度,才能排泄掉社会愤懑,保证基层和谐和政治稳定。
总之,只有在理解农村基层组织所面对的国家战略任务和乡村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将基层组织的基础功能和具体功能协调起来,实行踏实稳健有序的乡村体制改革,才能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品,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序。
注释:
①在旱情出现的时候,只有那些公益心高的怕饿死的农户才会主动承担抽水费用,而那些不缴水费的农户却得到免费水。抽水每年都有,那些公益心高的人就会成为一些村民期待的对象,他们在每次农田灌溉中得到与其他村民较少的好处,最终,这些怕饿死而出钱抽水的村民成为利益损失最多的人,而那些不怕饿死的村民却总能搭车受益。在与其他村民的比较中,公益心高且自愿多出水费的村民也会无所作为,农田水利从此走向瓦解。详见郭亮,《对当前农田水利现状的社会学解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1][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0.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
[3]吴思红.结构功能分析中的乡镇体制改革[J].江苏社会科学,2005,(4).
[4]贺雪峰.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6.
[5][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3.
[6]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
[7]吕德文.制度性关联的消解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09,(4).
[8]申端锋.软指标的硬指标化[J].甘肃社会科学,2007,(2).
[9]李芝兰,吴理财.“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J].社会学研究,2005,(4).
[10][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3.
[11]吴理财.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
[12][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