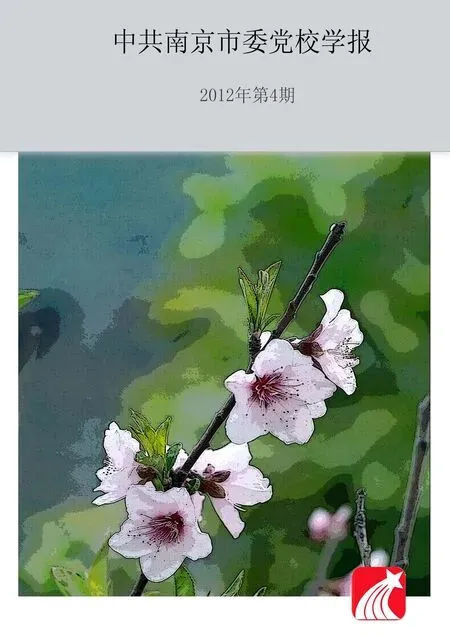政治娱乐在选举政治中的工具性效用*
——以台湾选举政治为例
陈 琦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物质的相对过剩导致了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生理的需要,充实精神世界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以视觉刺激、情感刺激为主的娱乐文化唤醒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娱乐需求,整个世界渐渐进入了娱乐经济时代。“越来越显得清楚的是,所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商务都不得不带上几分娱乐色彩,以便自己在日益拥挤的市场中能引起人们的注意。”[1]政治领域同样如此,为了使生产出来的政治产品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并“购买”某种特定的政治产品,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们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越来越多的政治事件经过简单化后被包装成娱乐,几乎一切都被涂抹上娱乐的色彩,卷进娱乐的漩涡。
一、娱乐与政治娱乐
在定义政治娱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到底什么是娱乐?与其他几乎所有的定义一样,关于娱乐的解释纷繁复杂到可以让人迷惑的地步。从最简单的字面意思来讲,所谓娱乐就是“欢娱快乐;使快乐”,就是获得感性愉悦或使人获得感性愉悦之意。[2]如若再深入探究这个词语,我们可以发现,比如,娱乐可看作是一种通过喜怒哀乐,或自己和他人的技巧而与受者喜悦,并带有一定启发性的活动(Bryant&Miron,2002)。但无论如何定义娱乐这个词,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这样一个特征——吸引受者的注意。
当然,政治娱乐也不例外,但政治娱乐区别于其他娱乐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政治性。关于政治性,有学者曾这样解释,它是“一定阶级或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对于现实环境的本来发展所做出的主动的刺激、反应、开拓,它总是和阶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政治活动紧密相联的。”[3]而政治娱乐的政治性决定了它的存在只能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为政府、政党、压力团体、大众团体等组织利用的工具,来“指导、诱导大众的意识行动朝自己所设想的政治目标发展”。[4]基于这点认识,我们可以给政治娱乐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政治娱乐就是以政治需要为最终目标,在吸引公众眼球的前提下,将政治目的隐藏在娱乐活动的表象中的一种政治现象。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选举造势、政治八卦、政治秀场、新闻报道、竞选广告宣传等等都可以被称作是政治娱乐。
二、政治娱乐在选举政治中的价值诉求
随着民主化的发展,选举政治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eter)把民主定义为对执政者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安排,通过定期举行选举,人们选择那些能够表达他们意志的人,“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的幸福”。[5]作为衡量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以及政治娱乐渗透最彻底的一个领域,选举政治将作为本文考察的立足点,以观察政治娱乐如何发挥其工具性作用。在选举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广大的选民,一切候选人以选民的好恶为出发点;反过来讲,选民的好恶也成了各候选人关注的焦点,通过投其所好引导选民来达到竞选胜利的最终目标。具体而言,政治娱乐在选举政治中的价值诉求体现为以下五种。
(一)功能性价值
所谓功能性价值是指,选民期望某位候选人在当选之后将会给它们带来的实际利益,选民基于各个候选人所倡导的不同议题及政策在他们当中做出选择。这可谓是最理性的选择,因此各候选人也在该方面做足了功夫。
在台湾选举政治中常见到的政见宣示、广告宣传及大型造势活动等所谓的“文宣攻势”即属于此类。文宣既要有明确的竞选主轴,也要有适当的选举口号,还要讲究策略和把握时机,使宣传攻势具有“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的重大影响力和杀伤力”。[6]以2001年台湾县市长、立法委员选举为例。国民党为2001年县市长、立法委员选举提出的口号是“抢救经济为人民,融合族群为台湾”,文宣策略是既大打“经济牌”,猛烈抨击民进党的无能和腐败导致台湾经济衰败;又大打“政治牌”,揭示民进党的种种“乱政”及其在处理两岸关系中的失误,并为此设计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台湾民众可能不知道国民党、民进党的党纲党章是什么,也不重视意识形态理论,但他们能深刻体会到的是这些新政到底可以为自己带来些什么;他们可能并不在乎自己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但他们在乎的是经济能否好转,工作能不能保得住。因此,各候选人抓住民众的这点小心思,大打“政策牌”,将当选后的社会前景描述得天花乱坠,能否实现那则是后话。到现在,大家还在讨论马英九08年的竞选宣言到底实现了多少,但这已经不影响他成为“总统”的事实了。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不要对选举语言太在意,也不要对选举承诺太当真。
(二)社会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是指,候选人被刻意与某些社会群体联系起来以在选民心中产生某种固定的印象,从而加深与所瞄准的那些选民群体之间的联系。候选人可以通过几种方法创造自己的社会性价值,包括通过广告提倡特定议题或者表现出某种政治理念,以此争取选民个人或群体的支持。关于这一点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政治广告。
政治广告在选举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创造对候选人的兴趣,提高候选人的知名度,刺激民众参与,提供对候选人支持的动力,宣传政策与建立公众辩论的话题,展现候选人的才华,提供娱乐”[7]等。正如谈到2008年“总统”大选中的国民党,大家一定会想到马英九讨喜的长相和他在中南部的农田里做秀般地插秧施肥以及那句“台湾向前行,台湾一定赢”。
这就是所有成功政治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8]
(三)情感价值
情感价值同样是有关候选人如何塑造自身形象的问题,候选人所具有的情感价值来自强调自身个性而强化自己在选民心目中的印象,并借此与选民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候选人的个人魅力成为吸引选民的有力武器。
2008年大选中,马英九一反国民党之前身份优越的形象,学讲着蹩脚的闽南话,低下头来在中南部“拜码头”。最初蓝绿阵营都普遍不看好,深蓝质疑这样到底有多少效果,而深绿则冷嘲热讽国民党和马英九直到今天才知道农民的苦,可最后大家还是跌破眼镜地看着马英九效应的持续发酵。这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人类族群、特别是弱势族群的普遍心理,一个学着蹩脚中国话的外国人在中国受到的欢迎往往远胜过另一位普通话说得特棒的中国同胞。因此,当大家明明知道马英九是在做秀的时候,中南部民众的回应还是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期。
(四)情境性价值
情境性价值是指,候选人利用自己与竞争对手个人生活中的一些故事,以及国内或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偶然事件影响选民的选择。这是台湾选举政治中最常用的策略——“抹黑”、“抹黄”。
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的“黑金政治”泛滥,政治人物与黑道、财团勾结,以金钱、黑道势力控制选举,成为国民党腐败的重要特征之一。国民党虽曾尝试“扫除黑金”,但是收效甚微,并使“黑金”成了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软肋,经常成为民进党等的攻击靶子。民进党利用民众厌恶“黑金”的心理,将“抹黑”竞争对手视为制胜法宝,不但竭尽全力收罗对手的“涉黑”证据,甚至挖空心思编造证据,将对手与“黑金”绑在一起。宏观的“抹黑”策略是通过清理国民党“党产”和清算旧案,将国民党与腐败、“黑金”联系在一起;微观策略则是针对具体候选人“下猛药”。[9]如2004年的“总统”选举,对国民党、亲民党联合参选的连战和宋楚瑜,一方面大张旗鼓侦办与宋楚瑜有关的“兴票案”,另一方面发行小册子,质疑连战上百亿家产来源的合法性。如“抹黑”不成功,还可以“抹红”或“抹黄”对手,或动辄给竞争对手戴上“联共卖台”的“红帽子”,或深挖竞争对手的私密,揭示其生活中的不检点,甚至无中生有地编制婚外恋等传闻,将对手“抹黄”。
(五)认知价值
认知价值是指,候选人通过某种方法激起选民的好奇心和对新事物的追求。说得更直白点就是推销选举人,其目的是要吸引媒体的注意,扩大选民的参与,使选举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使被推销的候选人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常采用的形式有:政见会、募款餐会、歌舞秀、买书及专用纪念品等等。
以2000年选举为例,陈水扁阵营最早推出文宣商品,“扁帽工厂”推出“abian”系列产品。连战阵营则以其竞选标志——蝴蝶缤为核心设计理念,推出一系列相关的蝴蝶产品。宋楚瑜的纪念商品则以“打拼为台湾”为主轴,包括五花八门的商品,还有宋楚瑜的签名。一些政治倾向比较明显的节目如中天电视台的“李敖大哥大”、“文茜小妹大”等,也几乎从不间断地设计选举话题。
三、政治娱乐在选举政治中的工具性效用
竞选宣传、电视辩论、政见会、政治广告甚至各种与选民的见面会都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娱乐,这些政治娱乐现象在吸引了选民注意的同时,也为竞选者赢得了大量的选票。正如政治娱乐的定义所言,吸引眼球仅仅是表象,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才是目的,政治娱乐同样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因此,在选举政治中,政治娱乐更多体现着的是自身的工具性效用。
(一)传播政治信息
娱乐早已渗透进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透过娱乐这个平台,最近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得以通过低姿态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先进的传播媒介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顺畅,它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广大的公众报道当前事态的基本信息。这是政治娱乐最基础层面上的作用。正如每天晚上七点档的《新闻联播》曾经达到过全民皆看的收视率,即使是这样,都没有完美地完成教育任务。相反,各类政治娱乐节目、政治脱口秀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们的民主精神,影响着我们对政治的态度。
(二)影响公众舆论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地方事务等较简单的问题能够形成自己的意见,但对于许多瞬息万变、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人们没有足够的信息、知识和经验形成自己的看法,于是,人们求助于大众传播媒介,不仅为获得信息,更为寻求说明。但大众传媒“不仅报道政治事件,而且常常就政治事件进行评论,这种评论既有新闻性,又有引导性。它可以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下来。”[10]
英国学者戴维·巴特勒发出这样的感叹,“媒介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自由的卫士,这种主张怎么能站得住脚呢?……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能允许大众媒介免受某种形式的规定或限制而自由发展。大众媒介对公民的影响太大了,不能给它们无限制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各种势力把控制媒介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11]对此,当代西方信息传播学者马克·斯劳卡说得更直白,他认为,“以高新传播技术为特征的‘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12]美国学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中也认为:“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联合性媒体越富有、影响力越大,参与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13]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曾经以为是“第四种权力”的新闻界可能正在悄悄改变着它的实质。他们或许在维护基本人权、伸张政治正义、批判专制统治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也可能被政客或者政治利益集团所利用,而成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谋取私利的工具:“政治语言是设计来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空气像是固体。”[14]政治家、政治组织也包括中央政府都像商品一样,他们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公关、广告语言和技巧把自己包装起来,以推销自己和他们的政策,而真实面貌往往被掩盖了起来。
(三)缓解阶级矛盾
政治的市场化在扩大了政治的影响力之余,也给政治本身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各种政治产品充盈于市,导致生产过剩和激烈的竞争。在政治市场化时代,生产一种政治产品容易,但让这种政治产品得到人们的认同则十分困难。现代政治的问题日益转变为如何让人们认识到并“购买”某种有价值的政治产品。
在大众传媒产生以前,政治家、政治统治者主要依靠政党这个中介机构去宣传政治主张,组织队伍,吸引选民,团结民众,支持其政策。公民的政治参与也主要通过参与政党这一形式,政党成了政治工具和中介。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出现之后,逐渐改变着这种政治过程,政治家可以依靠大众传媒直接诉诸大众。政治精英常常有选择地解释政治性场景,他们把自己的行为与美好的动机、目标和发展结合起来,以显示行为的正义性。[15]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娱乐意识,无疑为社会关系的创造和维持提供了润滑剂,正因为娱乐话题的存在,使得大众模糊了政治的严肃性,政治娱乐得以通过降低政治权威性的方式来减轻来自体制内外的压力。
就像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所说的那样,“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16]
(四)实现政治控制
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有这样一段名言:“在可以见之于所有政治组织的恒常事实和倾向中,有一样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大多数不经意的观察也可以注意到。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承认这种统治阶级的存在。”[17]
而统治阶级的支配性明显地表现在对受众的说服渴望和对媒体的支配要求上。中国学者刘明华用“木铎意识”阐释了这种说服受众的特性。[18]“木铎”是含木舌的铃,中国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的,用以比喻宣扬教化的人。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政治传播者包括个人、组织和媒介机构都具有极强的“木铎意识”,意图通过媒介宣传教化、支配受众。希特勒本人在纳粹党的初期也曾办过报,他毫不含糊地宣称:“报纸、电台就是要努力把一个观念强制给予人民。”[19]而且“按照政治学的解释,信息即权力。严格控制信息,有助于延续权力。”[20]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政府追求政治传播、政治娱乐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
政治统治系统正是通过影响或控制大众传媒,以政治娱乐的方式,影响儿童和成年公民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改变,以使广大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现行的社会和政治规范,认同、支持政治体系;或者通过大众传媒有目的地传播某种政治信息,造成某种强大的政治舆论,去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五)引导大众心理
在04年台湾“总统”竞选前期,为了拉抬选票,连战上过一个名为“康熙来了”的台湾娱乐节目。在节目中,敬爱的连主席被主持人小S逼问:“敢问您平常在家都穿什么型的内裤?”,“是四角的吗?”,“会比较高腰一点吗?”有别于政治操作的隐秘和一脸严肃,这些搞笑把政治的脸孔衬得滑稽。小S这些八卦问题的意义在于向民众宣布,政治家也是要穿内裤的,他们是普通的人,而不是被权力光环笼罩的神祇。因此,政治娱乐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洪水猛兽,它给政治戴上了一个亲民的面具,它将人们讳莫如深的贵族式理论问题,变成了街头巷尾人们拉家常式的“四角内裤”八卦,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政治完成了它的世俗化过程。
在权力交替不那么顺畅的转型期社会,或许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戴上了面具的政治。正是这种异化了的政治,掩盖了它原本的高高在上,把政治变成了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大家需要的只是遵守游戏规则。在游戏过程中,扯头发、扔椅子都是可以接受的“意外”,各种游行示威也属正常的意愿表达。但一旦结果确定,大家都应该坦然接受,因为这只是一场游戏,没有谁会去那么计较游戏中的输赢。这场关于政治的游戏,尽管弱化了原本沉重的使命感和道德要求,以部分牺牲政治的权威性作为代价,但它可以换得一个更加稳定、民主、开放的政治环境,使得民众对各种政治事件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容忍度大大增强。
四、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启示
本文认为政治娱乐具有工具性效用,本身并不含褒贬之意,而且工具理性本身就是一个中性词汇,但是政治娱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却是有利有弊。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政治娱乐的作用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而言,表现出来的矛盾特质尤为突出。第一,政治娱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信息的传播,但也在引导着舆论的导向。不可否认,政治娱乐在推广政治目标、传播政治信息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在为政府决策制造舆论方面也功不可没。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不仅时常利用政治娱乐塑造民意,而且还常常通过政治娱乐宣布决策或透露政府想公布而不便正式出面宣布的某些决定。第二,政治娱乐在促进民主的同时,实现着政治控制。政治娱乐的产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但也正是通过这种“胡萝卜”再加上法律“大棒”的形式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控制。“政府通过法律‘大棒’和透露内部消息——向那些不曾惹起政府不愉快的记者采取‘胡萝卜’手段”[21]实行非常有效的控制。
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尽管政治娱乐存在矛盾性,但仍具有借鉴意义。首先,政府的宣传控制与公众要求知情权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我们需要政治娱乐在这样一组矛盾中充当润滑剂,减少社会摩擦。其次,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底层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对社会的不满日益增多,整个社会就像一只压力锅,一旦达到公众的忍受极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将随之产生,我们需要政治娱乐充当减压阀门,给公众一个发泄的途径,使社会压力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最后,在转型期社会,尽管神圣的君权已经逐渐消解,但整个社会的塔式结构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治娱乐的存在则是使得不同经济阶层的人们享受同等的娱乐,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拉近,这种距离的缩短使得人们对经济差异的容忍度更高。
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政治娱乐本身就是为实现目的而存在的,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当行为指控它时,行为的结果却应宽恕之”。在社会转型期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法律制度亟待健全的时期,尽管我们需要这样非制度化的手段来更好地达成社会稳定的目的,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政治娱乐可能带来的负效应。由于娱乐文化追求感官刺激和趋于媚俗的特性,一味的政治娱乐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垮塌,而且政治娱乐在削弱政治权威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政治权威合法化危机。因此,我们在承认政治娱乐合理性的同时不能放弃清醒的价值评判。
[1][美]米切尔·沃尔夫.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28.
[2]高小康.狂欢世纪——娱乐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
[3]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25.
[4][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176.
[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社,1999.395-396.
[6]黄嘉树、程瑞.台湾选举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70-81.
[7]彭芸.政治广告与选举[M].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92.27.
[8][16][美]尼尔·波茨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6、121.
[9]史卫民.解读台湾选举[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02.
[10]唐晓.当代西方国家制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273.
[11][21][英]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67-68、78.
[12][20]杜骏飞.弥漫的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4、213.
[13][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8、9.
[14]肖滨.知识分子与政治符号产品的质量[J].学术研究,2003,(5).
[15]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79.
[17][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判者[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372-373.
[18]刘明华.西方新闻写作与采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
[19][德]希特勒.我的奋斗[M].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4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