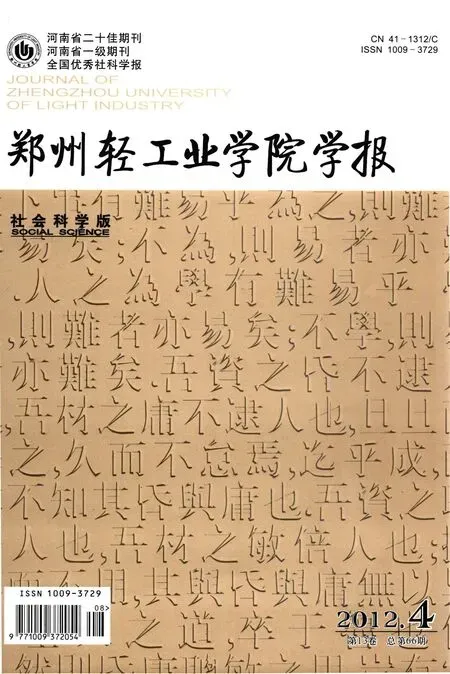“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
高建军,苗沛霖
(1.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政府法制办,河南郑州450004;2.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20世纪末,“终结论”者面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欢呼雀跃,并认为终极社会已近在咫尺,“胜利的曙光”马上就会照亮大地。然而近20年来,“终结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危机日益深重。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取得了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模式”成为西方之外的典型范式。在中国,近年来社会主义宪政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宪政理论研究还是宪政实践,都说明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不仅不是历史的终结,反而被社会主义宪政所超越。学界探讨社会主义宪政者较多,却鲜有人把“终结论”与社会主义宪政相联系进行研究。本文拟在分析“终结论”所遭遇的挑战之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宪政对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超越及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一、“终结论”的提出
1989年,正值苏东发生剧变之时,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P1)。自由民主的理念无法再改善。[2](P24)4年后,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重述了这一观点,并针对其他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福山[1](P1)声称,之前人类社会的种种社会制度因为具有严重的缺陷而走向衰落,当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不存在内在的根本性矛盾而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福山的这一论断并非毫无根据,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发生了令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为之兴奋的事情,带有西方色彩的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胜利,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从而使西方世界认为历史的终结已为期不远。[1](P4)不仅福山持这样的观点,其他不少学者面对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提出“民主现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认为世界许多地区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靠拢是20世纪最重大的变迁,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它包围着东亚、俄罗斯、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从右的方面席卷了权威主义政权,从左的方面冲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3]
当然,福山们的某些观点是有道理的,如他认为“民主在各个地方和各种人中的成功意味着自由平等的原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种族偏见的结果,而是作为人的人性的发现”[1](P58-59)。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专制政权对这些价值仍然嗤之以鼻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包括自诩为自由民主国度的各西方国家在内的多数政权,至少在形式上都把民主和自由的实现当做自己的核心价值目标。这就是说,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及其存在的制度架构——宪政、法治等,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向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但同时还应看到,即便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民主和宪政在形式上却有着千姿百态的表现,关于自由的内涵也有着不同解释,因此实现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也就会有所差别。而福山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之论实质上是延续了冷战思维模式,以资本主义民主否定其他民主制度与发展形式,“人权”这一最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概念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战的前哨。
二、“终结论”遭遇的挑战
福山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看法。由于一些欧美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于是一些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论采取多么有特色的发展模式,最终都将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不幸的是,关于“历史终结”的论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证明,西方的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模式在同非西方文明的交锋中也未能取得胜利。就“历史终结论”本身而言,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终结”的一种隐喻。当福山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彻底“战胜”共产主义的时候,法国学者德里达却给这个“好消息”划上了句号,他说这场所谓的“胜利”可能预示着一场灾难。盼望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获胜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类似“9·11”的灾难在等着他们,“获胜”所带来的灾祸并不比它带来的利益要少;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人,他的“幽灵”不是一个,还有其他“幽灵”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的终结”,其实只是某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终结,仅仅代表了特定的历史概念。他虽然在一个舞台上终结,却在另一个舞台上发挥影响。[2](P11)相反,如果我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如果美国模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模式,整个世界成为美国文化的附庸,英语最终替代了其他语言,而各民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这不仅不能看做是民主自由的胜利,而恰恰是它的悲哀。[2](P15)
正如我国学者周峰所说,“历史的终结”可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周峰认为,福山所推崇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即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面对新近发生的使全球为之震荡的经济危机,不免失语。随着这种带有所谓“普遍主义”特点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其结果不仅不是世界大同,反而将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价值世界的失序和颠倒,而对于“现代马克思”的呼声则越来越高。同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国可谓独树一帜,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已引起众多西方学者的兴趣,并称其为“中国模式”。[4]“中国模式”的提出否定了西方模式的所谓普遍性,并且具有比“东亚模式”更强的说服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是一个拒绝“华盛顿共识”而又能成功融入全球市场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范式已被判定为“中国模式”。[4]这里的“华盛顿共识”代表了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西方模式的价值内核。“中国模式”的提出至少说明了现在做出“历史终结”的判断显然为时过早,西方模式未必就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西方模式所追求的价值也未必是人类的终极价值。
更进一步来说,民主宪政的价值不容置疑地取得了普遍的承认,但它仅仅是民主宪政本身获得了认可,而非西方模式所取得的“胜利”。民主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可以生长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也可以生长于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一种通行于全球、适合于每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将西方的制度模式塑造为“标杆”的做法只是一相情愿。
三、社会主义宪政对“终结论”的超越
“终结论”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遭遇了来自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的颠覆性挑战。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西方之外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宪政民主制度。事实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制度形式,即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并没有否定宪政的普世价值,也没有完全抛弃资本主义宪政的某些形式或外壳,但是其实质与内涵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法律学说中,对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阐释占据了重要地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批判之时,所提出的关于人权、法治、民主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思想源泉。
在对资本主义民主宪政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观。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最多的还是民主问题。在分析民主的阶级性之时,马克思总结了民主的一般特征,他指出,民主的一般意义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是:国家制度在这里毕竟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5](P39-40)。在阶级社会中,民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实现阶级利益的政治形式。所以,“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6](P84)。工人阶级也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尽可能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构建自己的民主制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6](P293)在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有效地利用普选权等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形式,是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新的斗争方式。[7](P602)由此开创了科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在论及人权问题时,马克思认为,无论作为法定权利还是一种政治主张,人权的产生、实现和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P12)。社会主义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在本质上为人权的保障和发展提供了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和人权思想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就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比较年轻,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宪政尚没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即便如此,社会主义宪政还是表现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之处,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数民主制、对社会公平和实质正义的追求等。这本身正是对资本主义宪政的一种纠错与超越,并再次验证了“终结论”的荒谬。
四、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在资本主义宪政理论遭遇重大挑战以及西方民主政治暴露出固有缺陷之时,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扬弃和超越,社会主义宪政得以建立,并在资本主义内部架起了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
1.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于巴黎公社之后。出于对巴黎公社失败的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随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于民主国家内部,通过议会民主等途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与此同时,恩格斯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并特别声明无产阶级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存在区别,前者主张和平过渡,后者主张暴力革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宣言》中暴力革命的方法同样是有局限性的,一种和平的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手段是可以存在的。[7](P595-603)民主社会主义借助资本主义制度内成熟的宪政机制,以和平的方式将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加以表达,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实现,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破坏。
当社会开始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发展时,就应当以合乎理性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宪政建设,而不能总是诉诸过激的手段。无论是超越资本主义,还是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暴力革命都只能是最后的选择。而且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自身来看,它也在不断地吸收社会主义理念,并通过制度内的变革与调整来实现自我的更新与发展,这些制度内的调整为资本主义宪政向社会主义宪政的迈进提供了契机。民主社会主义正是生长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力量,它架起了由资本主义宪政通往社会主义宪政的桥梁。当然,民主社会主义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通过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超越,科学社会主义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同样,通过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超越,科学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才能够在资本主义宪政基础上发育成熟。在我国,虽然历史的发展已经否定了“补课”的可能性,但并不否认从西方宪政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并建立一种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
2.市场社会主义
经济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并非经济和民主的简单结合。有学者将经济民主解释为“不过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享有的某种自主的权利,是人处于主人的地位分享经济利益”[8],并进而强调人在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即便单单从人民主权原则出发,经济民主也必然要求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同时,经济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并存现象的纠正,主张将政治民主与平等的原则贯彻于经济过程。而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经济民主的发展并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载体。
马克思也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批评,但他所批评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而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摒弃了存在于上述两个领域的弊端,并保留了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领域。在经济民主模式下,劳动力市场被消灭,资本市场也被投资的社会化所取代。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原则发展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不过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赞成政府对企业的微观运行进行直接干预,而是由作为企业主人的劳动者按照自我管理的方式进行自主决策,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9]
虽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受到批评,市场经济却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不断完善,它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这一机制的弊端不断暴露,从而提出了纠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而建立起来的,并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经济基础。
3.民生福利原则
虽然存在很多争议,但是民生福利原则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并为多数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所接受。然而民生福利原则与资本主义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与福利原本是分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垄断资本的出现、贫富分化的悬殊、市场机制的失灵、社会矛盾的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大规模介入和干预不可避免,西方的宪政理论也随之发生转向,民生福利原则开始成为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很显然,这种加入了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纯正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混合模式,在经济上被称为“混合经济”[10],在政治思想领域也渐渐演化出一种积极宪政理念,政府负有促进公共福祉的义务则成为宪政理念从消极向积极转变的主要特征。面对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西方各民主国家的政府纷纷扮演起慈善家的角色。
福利国家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它旨在调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修复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并通过调节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福利原则毕竟与资本主义的本质背道而驰,从其运作结果来看,福利原则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政策消解了劳动者参与劳动市场的心理,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11]但是这种瓦解并非一种倒退,而是在资本主义母体内发生的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成长。
五、结语
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宪政,在其普世价值之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特征,不同的本土资源之上生长出的宪政亦会千姿百态。当然,并非所有的宪政模式都是理想的、可以学习或预期的,在标榜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贫穷国家仍然是大多数,即便是被当做楷模存在的宪政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社会主义宪政虽然是新生事物,但已经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与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些都昭示着资本主义宪政必然被逐渐发展成熟的社会主义宪政所替代的历史前景。
[1]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英]斯图亚特·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M].王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M].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4] 周峰.“历史终结论”下的中国道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5-12(03).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王慎之.经济民主论[J].学习与探索,1987(5):23.
[9] 张嘉昕.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评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1(2):143.
[10] Case,Karl E,Fair,Ray C.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Globalization[M].Prentice Hall,2004.
[11] 郭忠华.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77.